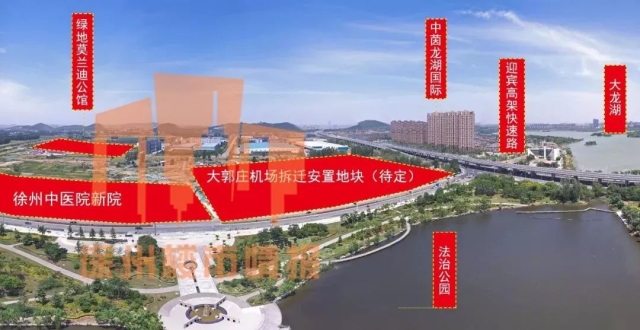他在新聞裡看過其他“釘子戶”的遭遇。重慶“最牛釘子戶”,開發商為迫使住戶遷離,把四圍挖成深坑,留下房子高於地面十餘米,像孤島一樣聳立著。他從未擔心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大城市不會這樣做。” 他肯定地說。
文 |程靜之
編輯 |王珊
紅的,黃的,藍的,白的,圍成一圈一圈的洪德高架橋上,車像彩色橡皮糖一樣,穿梭在巨大的環形滑梯裡,伴著“簌簌”的氣流聲飛馳而過。每天只要一抬頭,11歲的郭浩就能透過窗戶看到這樣的景象。
他的家就在這座高架橋中央,一棟刷成黃色的八層小樓,被360度圈了起來。
2008年年底,廣州市海珠區洲頭咀隧道的中段項目啟動。白色的拆遷通告貼在了小樓的各個出口,這裡被規劃為配套綠地,但樓內幾戶人家不滿足補償條件,拒絕搬遷,最終,小樓被整體保留下來。
郭浩一家七口住在一層,如今是小樓裡唯一的常住戶。十年來,這裡水電照常供應,橋上還增設了隔音屏。除了旁邊的洲頭咀隧道控制中心,高架橋就是他們唯一的鄰居。
夜晚的洪德高架橋,路燈和車燈編織出兩條鮮亮的A片子,流淌向更遠處的高樓,融入深藍色的霓虹燈裡,“圈中樓”就像鑲嵌在中間的一顆黑石子,成為廣州的一道特色風景,郭浩一家被網友評為廣州“最牛釘子戶”,甚至是“最幸福釘子戶”。
但“從外面看好看,裡面是另一個樣子。”郭浩的爸爸郭利說,高架橋一點點聳起,樓裡的燈一盞盞滅下去,小樓最後變成一具空殼,成為附近流浪貓的落腳處。
高架橋破土動工那年,郭浩從媽媽的肚子裡跑出來,和高架橋一起長大。
他看著挖掘機像張開嘴巴的大鯨魚,一口一口咬著房子,最後變成平地上的一堆破碎瓦礫。高架橋建成通車後,他跑上小閣樓,透過鐵護欄的窗子向外面張望,擔心汽車飛進自己家,把房子戳一個大窟窿。
他最先發現橋上出現了兩層的公車,和奶奶嘗試了附近月台每一條線路的公車,到了總站又坐回來。在沒有玩伴的童年,這成為郭浩覺得最有意思的遊戲。
這裡沒有強拆,沒有斷水斷電,沒有鄰居,也沒有人注意。這些年,廣州塔、天河城等建築相繼落成,昔日的農田、林地、池塘變成今天的住宅、商場、路線。他們還要繼續與橋為鄰。在這個喧囂的城市,以文明的名義,成為大橋下面一顆特殊的“釘子”。
最牛“釘子戶”
永興街28號,要找到這個地址並不容易。
快遞員過了“永興街26號”,就再也找不到編碼了,“這裡還能住人啊?”他很驚訝。郭浩的老師來家訪,不小心走到高架橋對面的房子,怎麽也繞不進來。同學寒假時想找他玩,沒有找到,開學時告訴他,“你家太亂,太難找了”。
“就像繞著一條龍,我們的房子就是中間那個蛋”。郭浩的媽媽這樣說。
但在11歲的郭浩眼中,這個蛋殼一樣的房子,就是自己的豪宅。
這間藏在樓房背面的屋子只有三十平方米,被黑褐色的木板分成了兩層。一層有廁所和廚房,兩個人在裡面打轉都有些困難;二層小閣樓再被木板和發黃的布塊隔出三個小單間,三張褪色的木頭床幾乎佔據了所有的空間。冬天,陽光很難照進來。
三年前,大伯一家受不了高架橋的噪音,搬了出去。這之前,七口人“蝸居”在這裡。
“挺豪華的,是吧!”郭浩神氣地說,“我住的可是豪宅,因為有兩層。”
推開木門,“吱呀”一聲,屋裡的時間像是停滯了。老式日歷掛在左邊的牆壁上,橘色的低矮茶几上,一台有線電話用來和外界聯繫。這裡沒有WiFi,也沒有電視。
六七年前拆遷的時候,施工隊把有線電視的電纜剪斷了。父親郭利打了四五次投訴電話,對方說,只剩一戶人家,重新拉線會很麻煩,建議報停。最近,他們乾脆把閑置多年的“大屁股”電視機賣了,換了25元錢。
對於纏繞著家的這座高架橋,郭浩很不喜歡。“很醜,老土,都是白色”。要是把它改裝成過山車就好了,“在房子中間打個洞,繞著‘釘子戶’轉,比十環過山車還刺激,那才是‘最牛釘子戶’!”如果在兩邊掛滿亮著彩色螢幕的手機做裝飾,那就更好了。
很少有人知道這戶人家至今還住在這兒。小樓幾十米之外的住戶肯定地說:“沒有人住,從來沒看到亮燈啊”;計程車司機從高架橋上經過,“不可能吧,一棟房子只有一戶人,那多恐怖,和鬼屋一樣”;每天駛在橋上的公車司機甚至都沒有注意到這棟樓。
2015年高架橋剛通車的時候,媒體來了一波又一波,他拉著記者給自己拍了很多照片。
在學校裡,同學跑到他面前說:“你上電視啦!”
“嗯,知道了。”他沒告訴同學,家裡沒有電視。
放寒假了,白天,只剩郭浩和奶奶在家。他經常坐在短木沙發上發呆,偶爾在家門口的空地上跳一跳,或者自己下飛行棋,左手PK右手,再看一看“翻了幾百遍”的《中華成語故事》。
老師說,他在學校裡和別的小朋友性格合不來,打電話給家長,建議他們最好換個地方住。

高架橋下,小樓裡唯一的留守戶。程靜之 攝

小樓已是一具空殼,成為流浪貓的落腳處。程靜之 攝
橋與樓
郭利開一輛租來的藍色豐田汽車,行駛在廣州各個角落,他到過繁華的天河城,也到過老城區的小巷和髒亂的城中村,又窄又小的巷子裡,散落著各種瓶瓶罐罐和快餐便當。
夜裡兩三點,做滴滴司機的他收車回家,高架橋上的車稀疏了很多,周圍看不到一個人,也看不到什麽燈光,像被卷進一個大黑窟窿裡。回到家,他打開自家那盞瓦數很低的燈。
十幾年前,郭利家附近還是熱鬧的商業街。街道兩邊是兩排長形平房,中間用鐵網或木板隔著,年輕的老闆娘用粵語吆喝,“又便宜又漂亮,手慢就沒了,快點過來買啊”。
郭利的父親在附近的木器公司工作,“以前的老住戶大多和我爸爸是一個工廠的。”出門買菜,滿街都是互相打招呼的人。
他們所住的小樓一層是公司放木材的倉庫,每年交給公司1107元租住。
2004年,廣州市決定建設洲頭咀隧道,位於廣州西部老城區,跨過珠江,是廣州市最大的過江隧道。隧道區域環境複雜,芳村端北面有一家大型化學有限公司,又與有百年歷史的德國教堂及掛牌古樹“狹路相逢”,最後教堂為隧道“讓步”,進行平移。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隧道方案借鑒了上海南浦大橋的經驗,在海珠一側隧道和內環路連接處,設定繞圈式引橋。內環路一方是高架橋,一方是地上通道,繞圈讓車輛能夠緩慢上升或下降,確保行車安全。
市政工程設計研究院為此設計了三種立交布置方案,最終選擇了耗資較大,對環境影響相對較少的一種,拆遷量也較合理。
看到貼在大樓旁邊的拆遷公告時,郭利沒什麽擔心,“跟著一起搬就是了”。拆遷辦提出了兩種補償方式:一種是給住戶提供相同面積的安置房,另一種是按市價提供等面積的補償款。
這對郭利來說遠遠不夠。
“我哥也有一個孩子,加上我老媽7個人,要麽多給我一套一廳一房,或者給一廳三房。”郭利說。他最初提出過三套房的要求。
拆遷辦解釋,按照政策,只能補償一廳二房(兩室一廳)。
雙方沒有談攏,挖掘機已經開了進來。每搬走一戶人家,施工隊就把電線和水管拆掉。
對郭利家,拆遷辦沒有過激的行為。為了保證這家人正常的生活,居委會的一個負責人說,“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以前的電是一個網絡出來的,哪根線能剪,哪根不能剪,就像照顧一個特殊的孩子。
一天,郭利家突然間斷電斷水,他找到拆遷辦負責人。
“我去看看。”身材微胖,有些禿頂的負責人說。他讓工人重新接回去,一兩個小時後,水電恢復了。
住戶一家家搬走,周邊的房子都被推倒了,他們像被包圍在一片廢墟中,黃色的泥漿從地面打的樁孔裡冒出來。“家就在面前,可就是過不去。”郭浩的奶奶說,有時候背著孫子去買菜,新挖的一條大溝橫在房子前,“出去了就回不來了”。
後來,拆遷辦的人留了一條小路,方便這家人出入。
一個大雨天,雨水滲進了家裡的四壁,泡了水的牆上,塗料都爆出來了,起了一個個小疙瘩。郭利又去找拆遷辦。負責人打電話叫來工人,找到被拆的排水管,用鐵皮把雨水引到另一個管子裡。
2015年初,隧道正式建成通車,拆遷辦從這裡離開,兩年後,負責人也換了新的一批。
郭利和新負責人反應情況,路線擴建辦特意為此開了一次會議,據他回憶,對方最終決定補償兩套房子,但手續又卡在了項目辦,認為這樣安置不合適。他們建議郭利找木器公司。
郭利夾在中間兩邊跑,最終沒有結果。
新修的路線把房子周圍的地勢抬高了,去年台風“山竹”來襲,晚上八九點,積水像海浪一樣一片片湧進家裡。郭利讓兒子趕緊上小閣樓,他和妻子把鞋子、衣服匆匆裝進布袋子往高處搬。不到半個小時,水就沒過了膝蓋,冰箱漂了起來。凌晨三點多鍾,水才退去,留下遍地泥漿。
房子邊角的木料老舊了,吸水太重也會掉下來。2010年,廣州開亞運會時,為房子“穿衣戴帽 ”,小樓外牆塗了一層鮮亮的黃色,邊框加了一些材料,增加了立體感和層次感,看上去大氣了。幾年過去了,好幾次,郭利看到脫落的材料砸在水泥空地上,碎成好幾片,他擔心,有一天會砸到家人。

郭浩和奶奶兩個人的午餐。程靜之 攝
喧囂與孤獨
郭利沒想過妥協,他認為房子既然納入紅線,遲早會拆,只是不知道會拖到什麽時候。
他在新聞裡看過其他“釘子戶”的遭遇。重慶“最牛釘子戶”,開發商為迫使住戶遷離,把四圍挖成深坑,留下房子高於地面十餘米,像孤島一樣聳立著。他從未擔心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大城市不會這樣做。” 他肯定地說。
最有希望搬離的一次,拆遷辦找到郭利,說申請批下來了,兩套房子,讓他們去辦公室簽合約。
一家人去看過要搬進去的那棟大廈,距離這裡只有4.4公里。嶄新的奶白色外牆、明亮通透的陽台,站在大廈高層遠眺,可以看到廣州塔和珠江。
那天中午,這家人下館子慶祝,只等最後一道蓋章手續通過。但三年過去,拆遷辦換了新的負責人,換房的消息還是沒有著落。
他覺得搬離這裡基本上不可能了。

白天的洪德立交與郭浩的家。圖片來源網絡
廣州大學公法研究員王達曾參與過許多徵收拆遷項目,遇到過形形色色的“釘子戶”。他認為為了公共利益修建高架橋,是沒有爭議的。
“最高法院確定的基本規則是合法房屋等面積安置,但在法定標準之外,同時還要考慮住房保障。”他說,政府在公平合理補償的大原則之下,還要突出社會保障,不應當形成今天這種局面,“不管是路線用地,還是綠化用地,都應該拆。兩側來來往往的車輛,很容易出現交通事故,對駕駛員來講是潛在的危險,對住戶更是一種威脅。”
他記得深圳一個村莊,上千戶都拆掉了,最後只剩一棟房子,拖延了九年時間。在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長期拆不掉,加劇了供地不足問題。
浙江大學一個博士在《土地房屋徵收釘子戶問題及其治理》論文中,曾對2003至2014年間有過完整報導的50個標誌性釘子戶案例進行梳理,發現征地拆遷過程都是一場漫長的“拉鋸戰”,基本經歷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因交通樞紐建設拆遷的不在少數。有人以極端形式抵抗,地方政府時常處於“四處救火”的窘境之中,大多數情況下以依法強徵收場,而對項目進行重新規劃,繞過拆遷戶房屋的,只有百分之四。
類似郭利這種橋與房並存的情況並不多見。廣州市建委的工程人員接受媒體採訪時解釋,由於留守戶所在的住宅樓並沒有擋住工程,隧道才能在留守戶堅持不搬遷的前提下也能開通。
郭利的母親今年84歲了,背已經佝僂,步履蹣跚。 一個人在家時,她總會把生鏽的鐵柵門鎖起來。“很多貨車停在旁邊”,居委會的人也提醒她,“要小心一點”。
她最怕刮風下大雨的時候,天色一下子沉下來,屋子外面的枝條甩動,玻璃乒乒乓乓地響。
她感覺自己一家就好像生活在荒島上。門前的橋一高一低、一層一層、一圈一圈地環繞著,車輛揚起的塵土總會落在家裡的茶几上,沙發上,廚房裡,她拿抹布一遍一遍地擦也擦不乾淨。
半夜,大貨車“嘭”地一聲急刹車經常讓她驚醒。
“奶奶,外面好吵。”睡在一旁的郭浩也醒了。
“那你就用被子把頭捂住吧。”
郭浩迷迷糊糊縮進被子,阿婆哄著他,一會兒又睡著了,她卻再也睡不著。
即將到來的除夕夜,阿婆的女兒和大兒子將回到這裡,十幾口人,擠在房子裡吃團圓飯。沒有電視,沒有春晚,這就是房子最熱鬧的時刻了,歡笑蓋過窗外車輛駛過的聲音。高架橋終於安靜下來。
程靜之
一頂鴨舌帽,一雙採訪鞋。
為嚴肅閱讀提供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