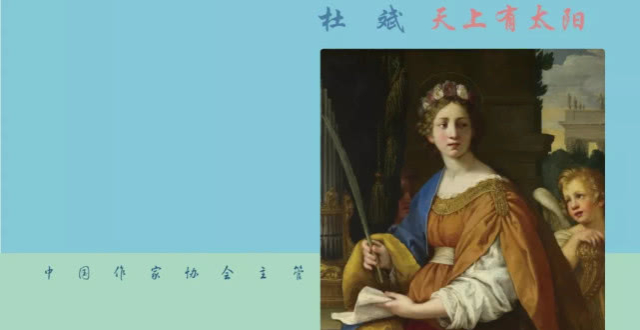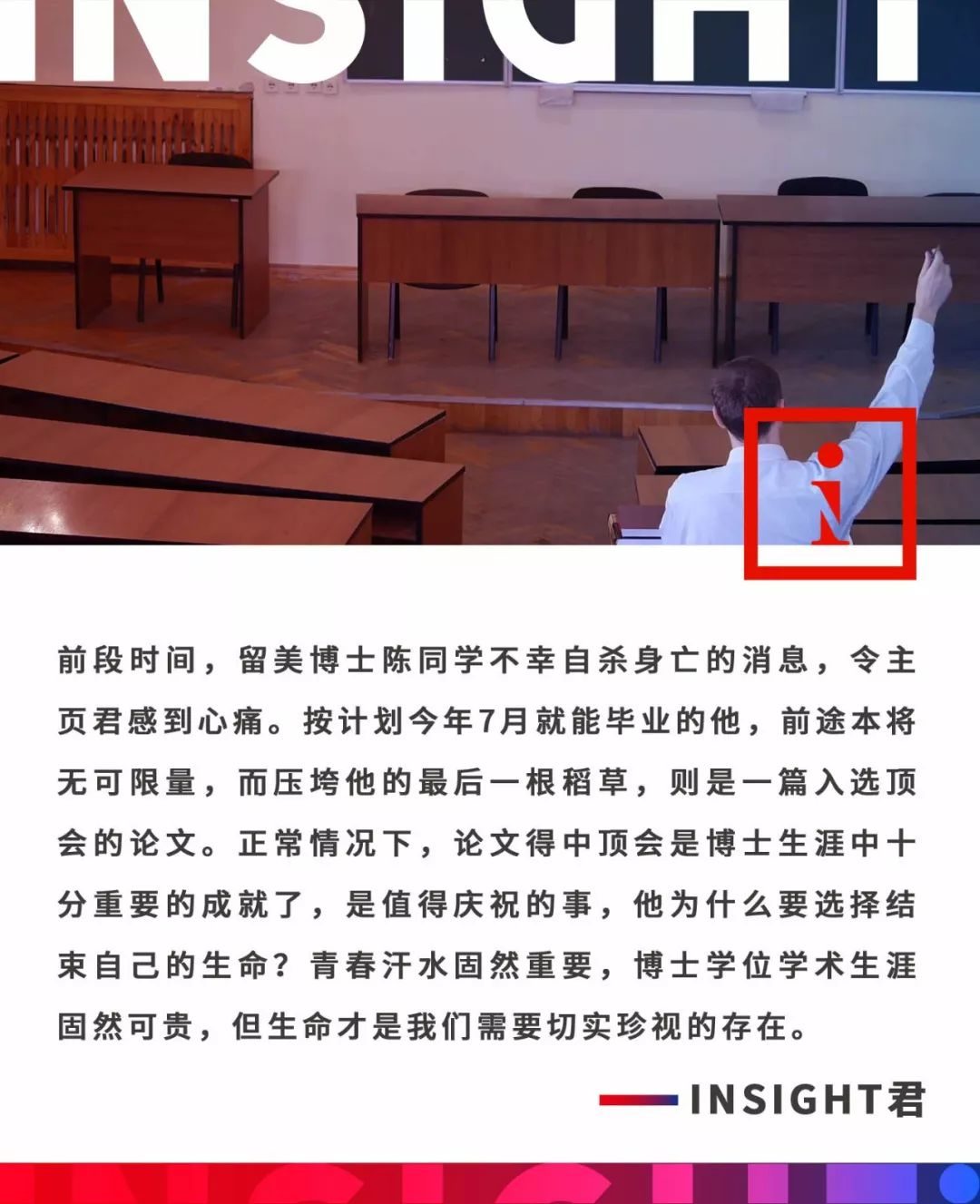訪談:張千帆
張千帆教授,曾於1984年7月獲得南京大學固體物理學士,1989年12月獲得卡內基-梅隆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1990年-1992年在UniversityofCalifornia從事生物物理學的博士後研究;1992年-1995年在UniversityofMaryland研習法律;1995年-1999年獲得UniversityofTexasatAustin政府學博士,1999年8月獲得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學博士。張老師是棄物理而從法律,頗有當代魯迅之精神。
記者:是什麽原因促使您由物理轉向法律、政府學方向?
張:首先,應該說,我從中學開始的理科歷程還是相當“一帆風順”的,在學校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到國外以後,課程與科研工作也都受到導師們的高度評價。從大學到博士畢業,我從事自然科學近十年,從原來的固體物理進入到後來的生物物理,我深切感受到自然科學的“美”。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雖然未必能直接轉化為有形的社會效益,對我來說真是一種美的享受。記得在美國完成了碩士課程以後遇到選擇博士研究方向的問題,有一次我偶然發現我們學校有人從事視杆細胞的非線形光譜研究,從中進一步讀到視覺的生物物理學機制,體驗到光和生物世界相互作用的奧秘,竟激動得一夜不能入眠。就個人愛好來說,我至今對它都很感興趣。
但我畢業於中國風雲變幻的年代,國內的ZZ風波對我產生了很大的震動,並使我陷入了深切的憂慮。今天看來,這種儒家式的憂患意識也許是“杞人憂天”,但它畢竟改變了我的人生旅途。在做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我突然對我以前工作的價值從根本上改變了看法。記得我在和兒時的朋友閑談時,我曾和很多人一樣盲目地認為科學——這裡主要是指自然科學——可以造福於人類;現在,這種希望竟突然變得很渺茫了。我發現以前的工作與成功只是一種自我陶醉,它和中國的現實離得太遠了。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或許不是這些傳統的科學知識(儘管我從來沒有否定過它們的重要性),而是一種新思想、新知識,至少對於像我這樣身在國外的留學生是如此。因為中國從來鼓勵自然科學研究,中國人也很聰明,不會缺乏這類人才;社會科學卻很不一樣,國內當時對某些領域的限制還相當嚴格。我認識到法律與政府學對中國社會很重要,很想在這方面做點事情,但由於自己從前的愚昧和偏見,對此幾乎一無所知,以至於空有一腔熱情,而沒有一點“底蘊”。我迫切感到,要使國家富強,自己首先要經歷一次“自強運動”。我是在這個背景下毅然決定轉向的。
我得說明,這是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我並沒有像釋迦牟尼那樣坐在菩提樹下一夜“頓悟”,我是一個覺悟很慢的人,是一個只有在走了許多彎路之後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歸屬的人。其實早在大學階段,我對人文科學就很感興趣,但由於我把時間幾乎全部撲在功課上,一直沒有空去關注自己的這一塊興趣。到了大學四年級,才旁聽了一些哲學課,但還是沒有能建立自己感到迫切需要的“世界觀”。在美國的研究生階段也是如此。其實現在看來,有些自己花了很多時間、覺得非做不可的事情,卻不是很重要的。結果,在決定轉向的時候,我的社會科學知識基本上是從零開始。只是在做博士後的兩年多時間中,我才抽出時間有系統地聽了X方政治思想的課程。當時也曾經想過是否就做一名“業餘愛好者”,在從事自然科學的同時關注一點社會科學,但我很快打消了這一念頭,因為美國大學對論文發表的壓力很大,自然科學本身是一項很艱苦的工作,要求全力投入,因此“腳踏兩隻船”是不現實的。除了徹底“改行”之外,別無選擇。
這個選擇無疑是艱難的,因為它表示我將和自己喜愛的專業告別,並且以後也確實遇到了困難。原來“順”得令人羨慕,現在一下子幾乎變成了一個“落魄文人”,似乎難以令人理解。然而,我內心一直很堅決,雖然偶爾感到有點“不平衡”,但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懷疑或動搖。因為我相信,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是一項值得自己付出的事業。雖然別人不一定馬上知道這項工作的價值,但我相信它最終會得到中國人的承認。做一點對中國社會有價值的事情——這是我在以前一直沒有找到的感覺,而現在卻找到了。“求仁而得仁”,我還能再奢望什麽呢?我一直想報答養育過自己的“黃土地”,我認為這是最好的報答。中國曾經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史,現在應該以一種新的文明的姿態驕傲地站在世界的面前。但只有當中國人成為偉大的人,中國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而不是反過來);要完成中國的轉變,只有靠每一個中國人的努力。我真的希望能通過我個人的轉變,來促成中國的轉變。
記者:那您轉型期遇到的主要困難是什麽?
張:首先當然是學習上的壓力。萬事開頭難。我當時對社會科學的知識可以說是“一窮二白”,完全重新開始,因此要吸收的知識量很大。同時,文科對於閱讀與寫作的要求比理科高得多。這也是一個很不適應的地方。記得在寫一篇政治經濟學期末論文的時候,我坐在電腦前,儘管知道要寫什麽,但卻一個詞也打不出來。自己對寫作也不夠自信,好象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把自己罩住了。後來這篇論文居然還相當成功,得到了老師很高的評價,並構成了我第一本書的思路。在此之後,我專門在英語寫作上下了工夫,到法學院以後,就慢慢習慣了,再經過在德克薩斯大學的練習,可以說已經得心應手。世上凡是困難的事情,一開始總是令人望而卻步,但只要堅持下去,總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做得越來越好。
其次是經濟上的壓力。在轉向之前,理科有有獎學金的資助,後來做博士後又有一定的工資,因此少有一點積蓄。但來到Maryland大學的法學院,就失去了穩定的收入,而且法學院的學費很昂貴。整個第一學年,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銀行儲蓄迅速地接近零點。這是我一輩子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心裡產生了恐慌。我在馬裡蘭沒有能解決“溫飽”問題,但我沒有馬上放棄。第二年和第三年,我仍然在那裡旁聽,但是已經沒有經濟能力注冊,因而也就沒有學分。我是一個不願意依賴別人的人,不願借錢,也不願像別人那樣出去“打工”掙錢,因為那將浪費很多時間。幸運的是,我在大學電腦中心找了一個低薪但還算清閑的谘詢工作,勉強“糊口”,同時利用空余時間收集了大量的資料,並繼續寫作。第三年結束,我的同學們終於一個個熬出了頭,興高采烈地參加畢業典禮。我則默默地帶上書的草稿,開始了新的起點。
馬裡蘭的這三年大概是我人生中的低潮吧,總有一種危機感。第一年在學業上面臨很大壓力,以後又面臨著經濟上的壓力,甚至還面臨過死亡的恐懼。但這也是非常充實、相當多產的三年。我目前已經發表的成果,絕大多數是在那個時期完成的。來到德克薩斯的時候,危機算是過去了,因為經濟問題獲得了解決(對很多人來說可能還沒有,但我的要求從來不高),而我的思想也獲得了一個很大的飛躍。在此後相對寧靜的三年,我能坐下來對困惑自己的一些基本問題作一個比較深入的思考,可以說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尋求的“世界觀”,一種自己感到能夠“安生立命”的東西。
從我的經歷,我想奉勸大家不要害怕逆境。人生都有不那麽順利的時候,千萬不要知難而退。只要你所追求的事業是正當的,那就用你的努力、勇氣和智慧去實現它。孟子曾經說過,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不是沒有道理的。“順境”可能反而會耽誤你,逆境卻可能會逼迫你思考,發現真實的自我。
記者:您在對未來的選擇一定有獨到的看法。目前,很多同學選擇專業著眼於就業情況,出現了重工輕理的情況。您對此有什麽看法?
張:對未來的選擇要看自己的能力與興趣所在。同是學物理,對理論感興趣的,適合做理論工作;對實驗感興趣的,適合做實驗工作;對兩者的興趣相差不大的,出於就業考慮進行選擇也無可非議。對於基礎研究,也只需要少數人奉獻其中。但如果只是一味隨大流,違背自己的意願,選擇一個大眾認為的“熱門專業”,那樣是很難快樂的。我很高興沒有放棄自己的興趣,我從事的始終是我的興趣所在。儘管中間困難重重,但我一直很快樂、很充實。
-版權聲明-
文章來源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為傳播而發,如有侵權,請聯繫後台,會第一時間刪除,文中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