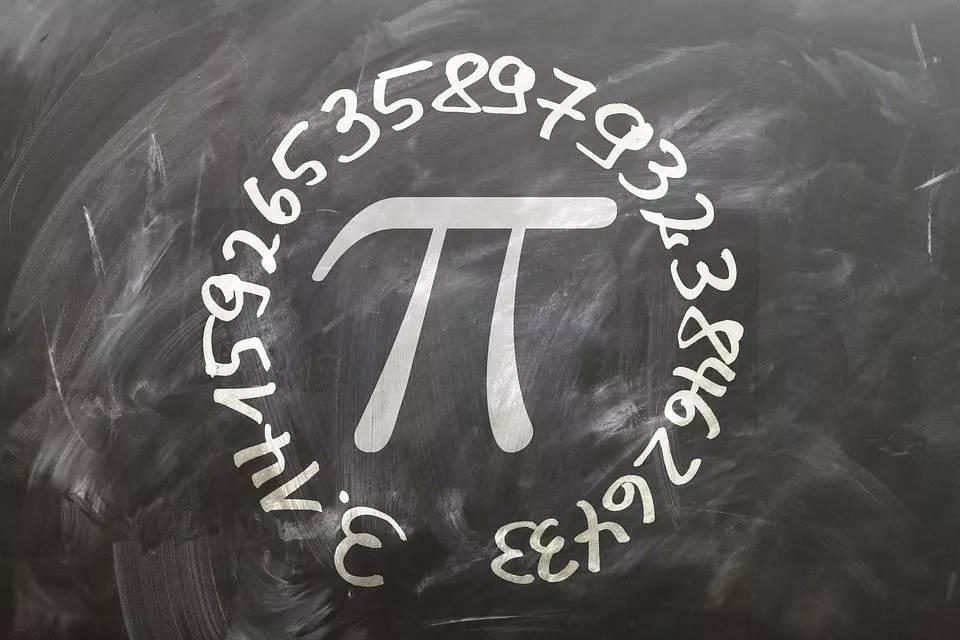撰文/宋金波
在我看來,“大一女生要4500元/月生活費遭媽媽拒絕!”這類“新聞”,通常來自於一個“製造”出來的話題。

網上流傳的“大一女生每月要4500元生活費”的截圖
通過不明來路的“熱帖”,設置反差巨大的場景,撩撥起閱讀者內心隱秘而易共鳴的某種情緒,在傳統媒體時代這就是常見的套路,自媒體繁盛之後更滿目皆是且效果奇佳。像年度性反覆流傳的《月薪三萬還是撐不起孩子的一個暑假》這種帖子,就是如此。假如傳統媒體的理想之一是“在這裡讀懂中國”,這些新聞最終做到的經常是“在這裡讓你讀不懂中國”。
自然,“策劃”出來的新聞,背後也可以有真問題。
有闊太太炫富,就可能有大學生炫富;有社會人哭窮,就可能有大學生哭窮。“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大學生也是人,是社會局部,必然不會與這個社會的整體氣質相去太遠,有什麽大驚小怪?
但或許,大學生和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人”又不一樣。中國有“貴族幼兒園”“貴族小學”“貴族中學”,但“貴族大學”還不多。大學生生源無論在地域上還是在階層上,都會更廣泛。這樣的大學階段,大概是很多人一生中惟一一次和那些經濟條件、社會階層相去較遠的人,“在一個鍋裡吃飯”了。過了這個階段,各回各家,各找各媽,在大都市的格子間裡低頭不見抬頭見,或是在某個生產車間蜂飛蟻走,不管怎麽著,身邊都是和自己差不太多的人。當然,有人會飛升,有人會沉淪,但是,除了做領導秘書,離你最近的,總是和你條件差不離的。
相比之下,年輕敏感的大學生,肯定更容易感受到“差別心”吧?
差別心來自於人根深蒂固的秉性。你說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大學生與今天的大學生在這一點上有什麽不同嗎?他們更高尚或更低俗嗎?我可不敢說。當年的大學生面對的經濟社會條件和現在倒是大不同。絕對數上,當時的收入水準,當時的基尼系數,與今天相比,無疑都差別巨大。“同學少年都不貴”,就算有差別,也不會拉開到讓人眼暈的地步。

電影《中國合夥人》裡刻畫的八十年代大學生
我1992年上大學,入學時還需要帶糧票。此前兩年大體宏觀經濟通縮,與八十年代末的情況沒差太多。對多數人來說,舒膚佳的香皂與兩面針的香皂,或者吃飯的時候有人多一副雞架一瓶啤酒,這種區別,可能會生發一些豔羨一些差別心,但斷不至於形成碾壓,形成兩個世界的斷層與隔膜,更不會激發出冤罪殺機感。如果當時一個寢室裡有人饅頭鹹菜,有人瑪莎拉蒂,可能會不大一樣。
短缺與匱乏,限制了想象力——攀比與衝動消費,大約也要靠想象力才能繁茂。
我們是農林學校,學費本身就不高,生活費,多數同學每個月百元以下也夠了,但一些來自西南或中南山區的同學,家境確實不好,有些甚至達不到每月四五十元。一位江西同學,喜歡書法,為了買一套《三希堂法帖》,足足一個學期,都是鹹菜饅頭白水。而這已經不算是最差的條件。農林院校有獎學金,平均五十元每人。成績好些的女生靠自己的獎學金已經可以完全夠吃,還能給男朋友分點。

1990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的這套《三希堂法帖》,定價85元
1992年,高考錄取率25%,當年只有75萬人踏入大學校門——這一數字在2018年是近800萬人。那時的社會,對大學生多少還是另眼相看,加意照顧。我相信,包括相當多城市家庭子弟在內,多數大學生在學校食堂不會比他們的家人吃得差,甚至會吃得更好。
1992年,“南方講話”掀起的新一輪開放還沒拉開帷幕,我所感受的,應該是一種普遍並且穩定的世相。當然,其時“改開”已屆14年,更早的大學生,有更多的苦故事可講,那是無疑。不止在大學,當時的中國,憶苦思甜,一代一代間,已是定式。要到新世紀,大學擴招,教育產業化,經濟突飛猛進,人心才開始更容易失衡。失衡的人心,正是很多撩撥人心的網帖死命盯住的社會G點。
我並不想為貧窮粉飾。貧窮本身不會帶來任何美好。對有些家境更差也更敏感的同學,我能感受到他們有時難以避免的不適和尷尬。那幾年,《平凡的世界》在大學風行,無非是與這種仍然普遍的校園生活發生了共鳴。在那時,以及那之前很遠,無論是文藝作品,還是學生作文中,類似因為貧窮而做了某種錯事,甚至造成不可挽回後果的故事,懊悔甚至懺悔的人心,比比皆是。至於表面所常張揚的某種“安貧樂道”,倒更可能是匱乏下的“禁欲”美化,不然,80年代、90年代讀書的大學生,何嘗看見他們在進入社會後對物質主義絕緣了?

1990年出版的《平凡的世界》
這也是我對“大一女生要4500元/月生活費遭媽媽拒絕!”這類新聞有些反感的原因之一。一路操作下來,無非老生常談,不如不說,甚至能感受到這種百無聊賴的關注背後,有某種強製與強迫的普遍心理。
我對經濟發展帶來的人的健全有過很大期望。朋友交流,我一直堅持,1990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人,是中國第一代整體遠離了饑餓記憶的人。饑餓是可怕的尊嚴碾壓機,它能在極大尺度和範圍內破壞一切美德、傳統。它會在人類最底層的認知面板上,留下本能的恐懼——對匱乏的恐懼,對失去飯碗的恐懼,對能剝奪掉一碗飯的任何強力的恐懼。它讓人們的行為變形,從扯光公共衛生間的衛生紙,哄搶降價商品,到安於歲月靜好,不肯為公眾利益多付出一點力量。
我一直相信,“90後”及更後的年輕人,會因為缺少這些可怕的記憶本底,顯得更超脫、更自由,遠勝於在匱乏、饑餓、恐懼中成長的先輩群體。

但今天看,也許能影響一代人發展的因素太多,物質條件、經濟發展,只是其中一面。今天我們的“90後”“00後”,與歐美,與日本,與中東、非洲,乃至與同在華人世界的那些同齡人,他們所說的,所做的,所關心的,所願付出的,毋庸諱言,差別巨大。與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前與他們同齡的學長們,同樣很容易區分。
我在校時,見過最晚的1980年代入學的大學生,我始終覺得他們身上有某種後來的大學生身上缺少的東西,外向的、激烈的,充滿理想的,家國與共、身土一體的,你可以說那是某種熱情,也可以說是某種幻覺——甚至這種區分本來就是我自己的某種錯覺。這種感覺,與是否存在一個金光閃閃、人心向上的1980年代一樣充滿爭議。

《中國合夥人》的劇照
我想,也許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對彼時的大學生,大學是一種人生創業,是孤注一擲的投資,是改變自己與家庭命運的創業,是自覺與國運相關的浮沉。而對現在的大學生,大學的屬性,則更像一種消費,甚至不是自己的消費,而是父母的,自己充其量是在為父母打工。創業者與打工者、消費者的心態,終歸不一樣。
我不覺得這不同的心態必須要有高下之分。身土一體的理想主義,並不一定帶來理想的世界。求田問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既可以消解虛偽的宏大,也可以淡漠真實的記憶,既可以無視精心編織的謊言,也懶得去追求另一種世界的真與美。
無論基於哪一種立場,為了哪一種目的,對這一代年輕人的表現,態度都會是矛盾的、猶疑的、曖昧的。不是一個簡單的結論就可以為他們定性,為他們圈定一個明確的未來。
《三體》中,劉慈欣說:“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格言像玩具風箏,就這樣飄來飄去。
對大學生活費的記憶,或許已經是幾十年來幾代大學生僅有的共同興趣點了:“還記得你爸媽花了多少錢供你上大學嗎?”
版權聲明
本文系騰訊《大家》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
關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閱讀精選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