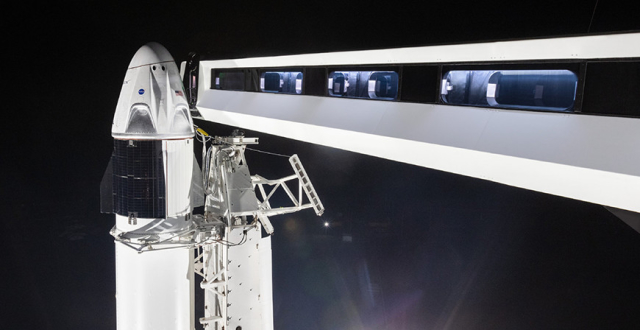青海冷湖晝夜溫差大、乾旱蒸發量大、土地含有高氯酸鹽、地處無人區、風蝕地貌,為國家在探月工程、火星著陸計劃、模擬火星環境的生物圈研究提供了極好的模擬環境。(張克/圖)
“2040年,當你登陸火星,一定會想起二十年前在地球的這個下午。那時的你,作為火星實習宇航員,徒步在中國青海無人區,尋找‘火星水源’(N38°20′8″,E92°55′11″)。烈日灼燒著海拔2700米的沙漠,方圓百裡毫無遮擋,你不時仰望紫外線爆表的藍天,視線穿過滾滾熱浪,仿佛看到了5500萬公里外的那顆紅色行星。”
2020年7月22日,一名火星實習宇航員寫下這段文字。當時,他席地坐在無人區沙漠的流星余跡湖邊,中國軍工專家曾在此研發流星通訊技術——理論上,人們寫給未來的信,可以通過流星掠過時的電離雲反射無線電波,將信息發送到另一個時空。
與他同行的,有九名青少年,最小的七歲,最大的十三歲。二十年後,他們很可能成為中國火星宇航員的適齡候選人。
這些少年的火星登陸實習,是從2020年7月20日開始的。1969年的同一天,人類乘坐“阿波羅”號飛船首次登上月球,這一天從此成為“人類月球日”。2020年7月23日,少年們結束實習。台灣時間當天中午12:41,中國第一顆自主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在海南文昌成功發射。
2040年登陸火星,正成為人類的共同目標,全球眾多科學家、企業家和天文愛好者已經開始為此努力探索。中國“火星少年”們的登陸實習,就屬於其中一場籌備兩年的探索。
突如其來的疫情,迫使2020年這場探索的規模臨時縮減,也使得這場探索更有現實意義。“疫情讓人感到未來的不確定性。”這是科幻作家韓松加入探索的理由之一。多年來,韓松只要出門,包裡都帶著齊全的急救物資,以增加自己在突發災難中幸存的概率。而火星,是當全人類面臨滅頂之災時,首選的移民星球。
火星少年們大多也有備而來。來自山西太原的11歲小學生張瀚升,受到在航天系統工作的母親影響,兩歲半就開始讀霍金的《時間簡史》。
當領隊老師問起探索火星的意義,此前沉默寡言的張瀚升兩眼放光,一口氣說了很多:在太陽系行星中,火星與地球最像,直徑約為地球的一半,陸地面積和自轉周期與地球很接近,最重要的是火星有水,可以孕育生命……
7歲的小女孩王芊憶是跟著爸爸一起來的,她想去“火星”挑戰自己。芊憶的爸爸從事旅遊行業,曾在西北做玄奘之旅的徒步項目,因疫情停業思考期間,他瞄準了時空更加闊大的“星際旅行”。這是他第一次單獨帶女兒出門,臨行前做足了生存功課,唯一的困難是“不太會給女兒梳頭”,去“火星”的路上,他指著女兒蓬亂的頭髮,向其他家長求助。
11歲的楊欽涵是唯一獨自上“火星”的孩子,他來自山東濟南,2019年初因為電影《流浪地球》開始對太空產生興趣。一年多的時間裡,他翻看各種圖書和紀錄片,“研究範圍”從太陽系裡的柯伊伯帶一直擴展到系外行星和其他星系。楊欽涵看過“好奇號”等火星探測器傳回地球的所有火星圖像,他像談論家鄉的山東半島一樣,親切地說起火星上的水手號峽谷,幾億年前河流和海洋遺跡。
與火星少年們同行的還有科幻編輯和作者。科幻編輯李晨旭畢業於歷史碩士專業,如今的工作內容卻聚焦人類未來。他對火星的憧憬源於科普讀物《趕往火星》,書裡寫道:“去火星能發財”——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戰爭都是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一旦人類開發太空,資源就是無限的,人類不再需要為此開戰,那時候人們研究的重點將變成“把火星資源販運到地球的商業模式”。來而不往非禮也,來自湖北黃岡的科幻作者小述,希望去火星時帶上他家鄉的特產——黃岡密卷。
他們一起上“火星”,在84個小時內,應對著人類登陸火星時可能遭遇的所有生存問題。
登陸廢墟:這裡曾生活著十萬人
2020年7月20日 8:00
火星實習宇航員們系好安全帶,集體倒數十個數,高呼“發射”——他們乘坐的大巴從敦煌市區開出。敦煌人吳明激動地說,1600多年歷史的敦煌莫高窟壁畫,描繪著古人心目中的彼岸世界;如今的火星計劃,則是今人對當下遙遠世界的全新探險。
大巴穿越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和“胡煥庸線”,開往二百四十多公里外的青海冷湖鎮,那裡的年均降水量只有17.8毫米,全鎮人口不到一千,實習宇航員戲稱,這輛大巴開過去,當地常住人口激增10%。冷湖鎮60公里外的俄博梁雅丹地貌無人區,從地貌、土壤到氣候,都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之一。曾寫過行星論文的小學生張瀚升2019年去過那裡,他形容,只要加上紅色濾鏡,然後把太陽染成藍色,冷湖就跟火星一模一樣。
一路上,草木逐漸稀少。途經亞洲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熱電站,這座在沙漠中熠熠發光的高塔,由一萬多面鏡子組成,反射太陽光加熱熔岩,24小時持續發電。光熱電站充分利用著西北最豐富的能源之一——太陽能。
大巴在甘肅阿克塞縣短暫休整後重新出發,實習宇航員們稱之為“二級火箭分離”。翻過海拔3600米的當金山,大巴進入青海,手機信號和沿途的綠色植物一起消失,人們與“地球”失聯了。此時,領隊向所有人發放火星任務書,第一頁隻印了一句話:火星沒有救援,拯救全靠自己。
2020年7月20日15:00
飛船穿越火星大氣層時,會產生劇烈的摩擦,飛船通訊聯絡中斷,伴隨著噪音和顛簸,這個現象被稱為“黑障”。
為了模擬“黑障”,大巴上所有乘客戴上眼罩,車行駛在冷湖鎮“火星1號”公路上。這條88公里長的路是當地2018年在戈壁灘上生鑿出來的土路,崎嶇不平,行駛中的顛簸感恰似登陸火星。
“黑障”的干擾,會使得登陸火星的飛船偏離預定坐標。作為“實習登陸”,大巴也沒有開到火星營地,而是“誤入”一片廢墟。
郵局、銀行、學校、宿舍依稀可辨,但它們都沒了房頂、窗框,成片的斷壁殘垣,正被黃沙吞沒。難以想象,曾有十萬人在這裡長期生活。1954年,冷湖勘探出石油,有的井一天能噴80噸油,成為當時中國四大油田之一。這座廢墟,當時就是冷湖油田的三大生活區之一。
冷湖是一座人造的城市,一切生活物資都是從幾百公里外的敦煌、德令哈等地運來的。張亞平是土生土長的冷湖人,她生於1967年,印象中自己童年從來沒缺過牛羊肉,每個月還有大卡車從遠方運來新鮮蔬菜和水果。1980年代去外省上大學時,張亞平驚訝地發現,自己從小穿的裙子,玩的洋娃娃,與北京上海的同齡人相差無幾。
她沒想到,冷湖的輝煌會在幾年後戛然而止。1989年,冷湖地表淺層石油開採殆盡,國家做出決策,在短期內遷走了冷湖的石油生產區和生活區。當時市場經濟初興,當地人發現廢舊建材的商機,紛紛加入拆遷行列,把磚混結構房屋的廢鋼、木梁、窗框、屋頂統統扒光,運往附近的城市賣錢。張亞平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隻用了兩年時間,十萬人生活過的社區就淪為廢墟,暴露在整年的狂風烈日下,三十年後成了現在的樣子。
因油而生,又因油而衰。冷湖如同地球的縮影,自然資源能孕育人類,也會驅逐人類。
尋找水源:有生以來走過最長的路
2020年7月20日18:00
實習宇航員們的登陸地點,在遠離火星大本營的荒漠中。
他們在廢墟裡找到一些物資,並完成了隊內分工。分工角色包括指揮全隊的“指令長”、辨位導航的“領航員”、開路搭橋的“火星工兵”、培育作物的“生物工程師”等13種。9歲的龐雅馨來自北京,她認領的角色是“環境工程師”,理由是這個角色“只需要撿垃圾,其他的(角色)太難了,我不會”。8歲的劉文澤自薦“指令長”,分工第二天他指揮全隊徒步二十公里,感歎隊伍不好帶:“之前我走過二十公里,這次就是大人走得有點慢,老照相。所以我每隔一會兒就點一次名。”
天色已晚,實習宇航員們無法趕到火星大本營,只好就近扎起連排的帳篷。夜裡刮起十級大風,強風卷著沙粒,劈劈啪啪打在帳篷上,南方人鄧楓濤躺在帳篷裡,以為外面在下雨,第二天早上一些北方隊友被他逗樂,另一些隊友卻說,昨晚還真下過一陣雨。
“火星的氣象就是變化多端的。”火星實習登陸的課程總監蒲佳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想要走到大本營,就得先預測火星的氣象。這天露營前,“機械工程師”帶頭組裝了一個地面天氣衛星信號接收站。
地面站是蒲佳意和同事們自己設計的,所用的鋁型材,是國際空間站和南極科考站裡用的同款材料。接收天氣衛星信號,是火星宇航員的必備生存技能。而搭建地面站,考驗的是實習宇航員們使用說明書的能力。“這個世界就是一本大的說明書,它是用數學和物理的語言書寫而成的,讓孩子們學會閱讀說明書,是很重要的一種能力。”蒲佳意說。
地面站搭建成功後,蒲佳意為實習宇航員補習了衛星和天線的相關知識。露營點上空,每天約有四顆天氣衛星經過,下一個接收信號的時間窗口,是第二天早上七點半——現學的知識,將在那時經受實踐檢驗。
2020年7月21日 7:30
“衛星要來了。”實習宇航員們調整天線仰角,在白噪聲中聽見嘀嘀的聲音,所有人安靜下來,圍著顯示器螢幕。嘀嘀聲愈發清晰,螢幕上逐段顯示衛星雲圖,儘管不太清晰,但是可以確定,今天的氣象適合徒步。遇到好氣象需要運氣,2018年9月,劉慈欣等科幻作家來青海冷湖,原計劃徒步七公里,結果遇上沙塵暴,中途被迫折返。
徒步前,蒲佳意給實習宇航員們補習了地理課,她列出了起點和目的地的坐標,讓孩子們通過赤道周長計算出坐標點之間的距離。導航用的是指南針、GPS和手持天線,前兩者用於確定位置和方向,手持天線用於接收散落在火星的物資包發出的信號——這片沙漠沒有手機信號,天然屏蔽了智能手機地圖,人們只能用更原始的工具尋找出路。
上午九點,全隊向火星大本營出發,由於路途遙遠,而實習宇航員隨身攜帶的生存物資有限,當天的目標是“保證自己活下去”——找到水源地。
昨夜下過雨,地未乾透,隊員們踩在戈壁的沙質脆殼上,深一腳淺一腳,這對體力和關節的消耗很大。11歲的張瀚升不愛運動,走得比較吃力,他自我安慰:“在火星徒步會比這裡輕鬆得多,火星的重力是地球的三分之一,跳一下就上一截。”
這是9歲的龐雅馨有生以來走路最長的一天。她的母親、科幻作家凌晨一路鼓勵女兒。凌晨想到了科幻電影《終結者2》,預知未來災難的女主角莎拉,從小培養兒子各種生存技能。“這時候大變局,以後的形勢我們也不知道會怎樣,”凌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們只有培養孩子吃苦,關鍵是要有很好的體質。遇到大災難,體質好的人可以活下來。”
歷時六個小時,實習宇航員們走到水源地。“好奇號火星車每秒走1厘米,每走10秒休息20秒,幾年來以這樣的速度,一點一點走了18公里。”薑峰在水源地為孩子們樹立榜樣,“這是一種毅力。”
“成為宇航員光了解太空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體能、數學能力和大智慧。”11歲的學霸張瀚升事後總結。來“火星”的九個孩子有八個都體重超標,白白胖胖的張瀚升就是其中之一,他用米飯打比方,“太空知識就是個桶,體能和智慧都是裡頭的飯粒。你知道會遇到什麽問題但沒法解決,那是不行的。”
來到水源地,“機械工程師”和“化學工程師”合作,搭建淨水機。他們使用壓力泵抽水,再用RO反滲透技術過濾水中的雜質。“這是一個航天技術的民用,”蒲佳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今天的淨化效果還可以,原來水裡的固體總容量值(TDS)有九百多,淨化後降到六十多,是相對澄清的。”
火星大本營已經遙遙在望,實習宇航員們今晚露營時輕鬆了許多。深夜,沒有光汙染的漆黑夜空出現燦爛銀河,蒲佳意為大家補習觀星課。這堂課同樣實用——能幫助火星宇航員找到回地球的方向。

參加2020年火星登陸“實習”的九個孩子,年齡在7歲到13歲之間。到2040年,他們將是中國火星宇航員的適齡候選人。(張克/圖)
“火星”遇險:意料之外的世界
2020年7月22日 8:00
下雨了,十年一遇的暴雨。
這片荒漠的年均降水量只有17.8毫米,這場不合常理的暴雨卻下了九個小時。夜裡聽到雨聲,南方人鄧楓濤入鄉隨俗,認為又是風沙,早上醒來,卻看到帳篷外成了一片澤國。
放在帳篷外的鞋子變成泥團,許多實習宇航員狼狽地躲進露營點的充氣式大帳篷,圍著煤氣灶取暖。這時科幻編輯大步穿著沙灘褲和人字拖走進大帳,眾人驚呼:你怎麽會帶這些?大步疑惑地說:這不是沙漠必備的嗎?過了一會兒,張瀚升和母親高治潔穿著雨衣走進來,看著眾人驚訝的眼神,高治潔反問:這不是必備的嗎?科幻編輯李晨旭打趣道:“一會兒再進來個扛皮劃艇的,對我們說,這不是沙漠必備嗎,你們不會都沒帶吧?”
“雨傘也是野外必備的,即使去沙漠,”參加過多年汽車拉力賽的高治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尤其是我們女同志,方便時用傘遮擋,遇到野獸和壞人還可以當武器。”
連火星實習登陸的主辦方都沒料到這場暴雨,他們的活動預案裡,完全沒有應對下雨的B計劃。強風裹著大雨,從四面八方撞擊著大帳,所有人躲在這裡,能做的只有等待。9歲的龐雅馨翻出媽媽的平板電腦,點開《瘟疫公司》的遊戲,她玩得很好,在遊戲中成功將病毒傳播到全世界。她看著地圖上滿屏的紅色病毒標誌,再看看帳篷外的風雨,皺起了眉頭。
來到“火星”的科幻作者和編輯們,此時也在玩遊戲。所有人圍成一圈,依次講一個離奇的故事,然後讓其他人辨別真假,能騙到的人越多就越成功。他們講的大多是真事,但總是被其他人懷疑是虛構的——就像他們正在經歷的沙漠暴雨。
暴雨下到中午,也沒有停歇的跡象,人們開始討論,如果被困在這片高地,會有什麽後果。攝影師張克回憶,2018年他曾在這裡露營九天。起初什麽生物都沒有,第四天,蒼蠅不知從哪飛來了。第七天,鳥來了,一群小型猛禽直奔營地廚房找吃的。
劉慈欣、王晉康、韓松和眾多年輕科幻作家都來過“火星”,這裡總在刷新他們的認知。來自山東的科幻作者黎木第一次來青海冷湖,路過青隴交界的當金山終年積雪,他見了很意外:“如此乾旱的地方有雪山,我由此想到,人類登陸火星也許會發現,火星不像好奇號探測器傳回的圖像那樣枯燥,可能也有壯麗的峽谷和山巒。”連續三年把科幻編輯和科幻作家帶到“火星”的,是科幻世界雜誌社前副主編、八光分文化創始人楊楓,她回憶,2018年科幻作家在這裡遭遇沙塵暴,眾人躲在車裡,車外飛砂走石,一米以外什麽都看不見,風、沙、石頭全往車上砸,感覺車窗都快被拍裂了,“沙塵暴過去後,很多在小說裡寫沙塵暴的作者都趕緊去改稿了”。
從2018年起,冷湖火星小鎮聯合北京行知探索集團和成都八光分文化創辦冷湖科幻文學獎,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地名命名的科幻文學獎。這個想法源自從事旅遊業的科幻迷袁振民,2017年9月袁振民來冷湖考察,跟同行的曲向東說,這麽蠻荒的地兒,特別適合拍《三體》,很像小說裡的羅輯,一直想象自己身邊有個女朋友,其實沒有這個人,太孤獨了。
劉慈欣聽了很感興趣,把他在《三體》裡虛構的“紅岸基地”等名詞授權給冷湖使用。2018年1月,楊楓、科幻世界雜誌社副主編姚海軍等人來到冷湖,大家討論認為不應該跟《三體》掛鉤。因為這部作品太有名了,每個讀者對《三體》的想象都不一樣,來到這裡大部分人會失望,不如創造屬於冷湖的科幻小說。眾人在飯桌上決定,創辦冷湖文學獎,評選中短篇科幻小說。
冷湖文學獎要求,每一屆投稿作品必須寫到“異常光波異塵餘生”,來自火星營地母公司董事長、前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曲向東的創意。2018年的一天早上,曲向東忽然想,冷湖這麽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為什麽突然聚集了十幾萬石油工人。他想出的科幻情節是:一個外星人在途經太陽系時飛船失靈,一頭扎進冷湖的俄博梁雅丹地貌無人區。打開艙門那一刹那,它看到火星地貌,以為自己在火星。為了修飛船,它開始探測周圍的資源,發現地底下湧動著黑黑的黏黏的東西,它就靠磁場影響地質學家過來勘探,再召集十幾萬石油工人過來開採。采出石油,它發現不能用來修飛船,就通過異常光波異塵餘生,給母星發信號。“他想表達的意思就是,我墜毀在火星了,能源已經枯竭,求母星來救援。”袁振民說。火星、墜毀、能源、救援,也成為火星實習登陸的四大關鍵詞。
“科幻一定走在科學前面,登陸火星只是第一步,我們以後要朝著更遙遠的外太空前進,要用到星際飛船、光速飛行,面對黑洞,實現這些都要靠腦洞。”袁振民說,“我們需要聚集國內腦洞最大的一批人,把科幻變成科普再變成科學。葉永烈老師1978年出版《小靈通漫遊未來》,寫的就是科幻,幾十年時間,大多都實現了。”
照進現實:第二次火星探索熱潮開始了
2020年7月22日 13:00
雨停了,火星實習宇航員們在泥濘中徒步,三個多小時後抵達火星大本營。
他們用前一天晚上接收並破解的摩斯電碼,打開了火星大本營的密碼箱,這裡有製作火箭的材料。蒲佳意對自製火箭的要求有兩個,能飛,能降落。“因為我們不管是去火星,還是從火星回來,火箭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蒲佳意為孩子們補習物理課,從火箭發明之初到現在,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穩定性,只有讓質量重心在火箭前端、壓力重心在火箭後端,這樣的火箭才不會在飛行時像陀螺一樣旋轉。前者取決於燃料的多少,後者取決於尾翼的形狀和大小。
晚上七點,實習宇航員自製的火箭在大本營發射。火箭箭身是礦泉水瓶,固定在自製的發射架上,通過控制操作台加注燃料(水和空氣),按下發射鈕。最遠的火箭飛了一百多米,所有火箭都平穩降落。90後“火箭少年”胡振宇曾經也做過類似的火箭,如今他已成立了自己的民用火箭公司,在冷湖建立了發射基地,能把火箭發射到十萬米高空。
2020年7月3日,由中學生參與研製的“西柏坡號”科普衛星成功發射上天,參與的學生主要來自石家莊鹿泉一中。這是中國航天科技國際交流中心2016年發起的青少年科普教育衛星工程,首顆衛星是北京市八一學校的學生參與研製的,他們在造衛星的過程中參觀了中國航天空間技術研究院和宇航員訓練中心,學習了航天專家關於衛星結構、測控的專業課程。中國航天科技國際交流中心的劉曉嵐在調研中發現,有個女生此前物理不及格,如今幾乎能考到滿分。“在這個過程中,她覺得學那些東西不是學學就完了,她可以去應用,所以她覺得物理知識對她有幫助。”劉曉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20年7月22日 17:00
第三屆冷湖文學獎在火星大本營頒獎。中篇科幻小說《閉環》寫到這場頒獎儀式,小說中,火星大本營被人燒毀。讓作者付強意外的是,他的這部小說從六百多篇投稿中脫穎而出,獲得二等獎。被問起這篇小說,冷湖鎮黨委書記馬文武笑著說:“我們沒那麽大腦洞。所以是你們(科幻作家)發展,我們力所能及創造環境。”
馬文武1997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冷湖工作,在這裡娶妻生子,也親歷了冷湖油田的衰落。衰落的資源型城鎮,普遍的思路是發展旅遊,冷湖也不例外。但是早期冷湖旅遊開發的方式簡單粗暴,“就在公路邊豎幾塊牌子,寫上‘青海冷湖’四個字”。直到2017年,時任冷湖行委副主任的田才讓去北京見曲向東、袁振民,碰撞出“火星小鎮”的創意,科普、科幻項目紛紛落地,冷湖有了復甦的跡象。
田才讓又背著包去找中科院國家天文台,為冷湖爭取科學項目。經過考察,國家決定在這裡建成亞洲最大的國家級天文觀測站。觀測站建在海拔4200米的賽什騰山上,與冷湖鎮的落差達到1500米,兩地之間沒有路,觀測塔的每一塊磚、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鐵絲和木條,都是用海西州的警航大隊直升機運上去的。“管直升機的領導心疼地說:警航直升機,你當成拖拉機使。”馬文武回憶。
觀測塔修成了,科學家每個月從北京來到這裡采集數據、維護設備。上山沒有路,他們就爬五個小時上去,晚上睡在山上簡易木屋的地上,白天再走五個小時下山。馬文武感歎:“這是青海的高原地區,你手腳並用走一個小時看看。”如今,觀測站已經建成三架天文望遠鏡,常駐冷湖的科學家有五六位。觀測站計劃在2021年底建成30架天文望遠鏡,袁振民預計,到那時,常駐冷湖的科學家、博士和博士後會超過一百人。
2020年7月23日 9:00
回“地球”之前,17名實習宇航員們參加了一場《火星生存哲學討論會》。每人隨機領取一張職業身份卡,競選首批移民火星的四個名額。每個人要根據自己領到的職業發表競選演說,陳述自己“為什麽很重要”。最終入選的是心理醫生、農夫、動物學家和科幻作家。
主持人讓“首批移民”討論建設火星的計劃,以及第二批移民的人選。“他們討論完說,我們四個不行,我們要把飛船開回來。”蒲佳意笑著複述四個孩子的推理過程,他們覺得團隊裡少了一些工程師,沒辦法解決飲用水的問題,也沒有帶動物上去,動物學家只能研究另外三個人。“所以他們最終給出的方案是,心理醫生把另外兩個人催眠了,有機作物農夫把飛船開回地球。”
2020年7月23日15:30
火星實習宇航員們在返回“地球”的途中,收到了天問一號順利發射的消息,整個大巴瞬間沸騰了。在此三天前,阿聯酋發射了火星探測器,一周後,美國也將發射火星探測器。
“全世界第二次火星探索熱潮開始了。”劉維佳說,他2000年進入科幻世界雜誌社做編輯,2019年主編了《中國火星紀事》,“上一次熱潮是冷戰時代,人類科技進步最快的時代。第二次的勁頭不如第一次,歐洲就因為疫情推遲了火星探測器的發射。中國起步很晚,好在終於要開始了。”
2020年7月23日20:00
大巴回到敦煌,實習宇航員們結束了84小時的火星之旅。接下來的180天內,孩子們每人要寫一篇論文。
這是11歲的張瀚升第二次來“火星”,上一次,他學會了搭建生物圈、製作火星車,還了解了Arduino程序和杜邦線。這一次,他學到了新的火星生存技能。“我們,是火星上的追風少年!”張瀚升在回憶文章的最後引用了李白的詩句: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裡。
南方周末記者 劉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