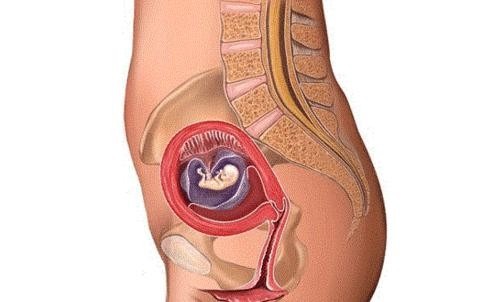你寫下的,是別人不知道的悲歡喜憂
文 | 雨習習
本文系“澎湃·鏡相”非虛構寫作大賽參賽作品
投稿原標題:
《矽谷生產經歷:美國婦產科裡的殘酷和冷漠》
1
我沒想到5-1-1需要整整兩天。
五分鐘陣痛一次,每次疼滿一分鐘,此種情況持續至少一小時的產婦,才會被醫院收治,否則的話,就算喊破喉嚨哭成瀑布,也沒人理。對這種看似荒謬的規矩,美國醫院有自己的道理:如果沒有疼到5-1-1,很可能宮口還沒開,入院越早,在醫院呆得越久,越有可能求醫生給自己用止痛藥,而用藥太多對健康無益。
星期一一早見紅,我疼了一整天,星期二又疼了一整天,基本停留在七八分鐘一次,按照產前課上教的,我倒著跨坐在一把墊了靠墊的椅子上,疼痛厲害時就把頭埋在椅背上,繃住身體使勁忍耐,除了呼吸像是滯重、滾燙而潮濕的歎氣以外,不發一聲,兩天之後我媽都感慨,書讀多了,人果然不一樣……
其實我只是很能忍痛罷了,在異國他鄉獨自生活的時間太長,生病也習慣了安靜地生。其實陣痛比生病好,間隙時還可以若無其事地聊天看小說。但到了兩天以後,疼痛就像一塊尖銳石頭來回摩擦在宣紙上一樣,漸漸地將耐性刮出破洞、拉扯出一絲絲纖維,幾十小時的疼痛已經讓我覺得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於是我在深夜說,去醫院吧。
婦產科門口的保安一看我步履維艱眉頭緊鎖,就直接告訴我們往哪裡走,值班護士問我老公:“她這樣子多久了?”答:“兩天。”“不是,我是問她疼到現在這個程度多久了。”答:“就是兩天啊。”
一檢查,果然已經開了三指,護士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想到楊絳在《我們仨》裡寫自己在英國牛津生孩子,洋護士眼看她疼得要死卻一聲不吭,奇怪地問:“中國女人都通達哲理嗎?中國女人都不讓叫喊嗎?”
作為舊金山灣區最好的婦科醫院,這裡只有12間產房,每年出生5千個嬰兒,已經居灣區首位。當初在這家醫院和同樣著名的史丹佛醫院間做抉擇時,這裡的一大優勢是因為所有產房都是單人間。還有就是老公說如果史丹佛有橄欖球賽時,附近會大堵車,怕趕上我要生了卻開不進醫院。那時我們都沒經驗,以為娃是坐滑梯出來的呢。
因為我和老公都是史丹佛畢業的,所以我一直傾向去史丹佛醫院生,直到我媽說這是“史丹佛情結”,我才下決心選了這家醫院。我本能地排斥“情結”這個詞,想證明史丹佛給我的是理性判斷和審慎決定的能力,而不是沽名釣譽盲目崇拜。
凌晨三四點時護士送來了點菜單,因為覺得自己早飯之前肯定能生,我拒絕了老公幫忙,忍痛自己拿鉛筆圈了自己想吃什麽。
別說早飯,午飯的時間都過了,我也沒生出來。
我上了無痛分娩,羊水已經被人工破掉了,手臂上插著粗粗的管子,掛著生理鹽水和催產素,百無聊賴地躺著,但不知為何開到八指就不再開了。下午兩點多我的醫生Dr. H過來說,因為催產素的劑量已經很大不能再加,現在要把我推去剖腹產。
老公眼睛濕濕的,說會一直陪著我,讓我堅強,其實我並不害怕剖腹產,只是覺得之前的一切徒勞都是為了順產的寶寶更健康,那一瞬間真的覺得對不起肚子裡的寶寶和幾天來忍受的痛苦。
2
因為剖腹產手術需要的醫護人員比順產多,只有一個家屬能陪產,護士出去忙,老公也送我媽出去了,我隻感覺到眼淚不停地從眼角滑入頭髮裡,似乎這些天的疼痛都變成了苦水。漂亮的小護士進來了,我求她再給我檢查一次宮口開的程度。她充滿同情心地答應去問問醫生,回來很遺憾地告訴我,因為剛檢查過,所以現在再看也沒有什麽意義,隨後把我從昏暗的產房被推進了燈光刺眼的手術室。
因為緊張害怕,我覺得自己在控制不住地劇烈抖動,真到了無影燈下,反倒心裡坦然了——漫長的煎熬快要結束,就能和寶寶見面了,另外推進手術室,真的和電視裡演得一樣啊。
唯一難受的是脖子因為長時間躺著不動,醫護人員把我抬到手術床上,脖子簡直痛到要炸裂了。我說脖子好疼啊,雖然手術室裡人很多,但他們都像電影裡一樣,緊張有序地做著自己的事情,沒有人理我,我等了一會,覺得就算是腦袋掉了也不過如此吧,用盡全身力氣喊(其實也就是呻吟)到:我的脖子疼到不能忍受了!
還是沒人理我,只有麻醉師一邊給我上麻藥一邊安慰了幾句,麻醉上來了,脖子也就不疼了。
麻醉師用針頭扎了扎我的肚子,問我還疼麽,我說疼,過會兒他又扎了扎,問我還疼麽,我說還是疼,又過了一會兒,他說開始吧,我心想:可我還有知覺啊!
好在隻感到醫生在肚子上橫著劃了一刀的力度,然後就是孩子清脆的哭聲。
開刀之前,我看了我的醫生Dr. H一眼,我一直覺得穿白大褂的醫生換上藍綠色的手術服以後很帥,少了點白色的純潔明亮,多了一些專業和緊張的感覺,我看到他的藍眼睛非常清澈鎮靜地盯著一個地方,長長的吐了一口氣,就像武功高手運氣,想到這樣的手術他做了很多次,感到非常安心。
我出國後的四五年一直在念書,所接觸最多就是教授們,他們大都是慈愛可親的白人老爺爺。作為美國名校的教授,他們慈祥、敏銳、充滿智慧、風度翩翩,令人敬重信任。而我在無意識中,竟把這種感覺擴展到一切“白人老爺爺”身上。
我選中的Dr. H,和我的老師們一樣的禿頂白發,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在挑選醫生時,潛意識告訴我他是最好的,我甚至忽略了Yelp——美國版大眾點評網上——對他很低的評價,認為這種不能經過證實的微詞采信度不高,完全沒有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謹慎,事後想想,與其在選定最重要的產科醫生時僅憑一點直覺,還不如跟著“情結”去自己本能上倍感親切的史丹佛醫院。
3
寶寶從藍色遮擋布的那一側被醫生舉起來時,我看了他一眼,覺得他上唇很鼓有點像齙牙——其實嬰兒哪裡有牙——想當然地說:“可真是醜啊!”
漂亮的小護士把新生兒放在我胸口,我才發現他非常乾淨,就像是洗過澡一樣,身上沒有白白黃黃的胎脂或是血痂,眼線長長的,很俊美的樣子,沒有哭,非常安詳。小護士開心地說:“他真好看啊,笑一笑!”用手指點點他的臉蛋逗他笑,他居然真的笑了,露出一個深深的好看的酒窩,和老公一模一樣。小護士驚呼:“啊!他有酒窩!來,再笑一個!”他居然真的又笑了。
我的孩子秋秋,一生下來就笑,似乎挺不尋常。雖然父母都暗暗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天賦異稟,但我卻覺得新生兒最可愛的地方,就是他們都是一樣的稚嫩、乾淨。秋的那種笑,並不是《大宅門》裡白景琦那種亂世裡天降異象的笑,而是一種溫暖的相認,一種單純的快樂。
我突然感到一種渴,一種喉嚨冒煙的撕心裂肺的渴,因為打了無痛分娩,已經有很久很久沒喝水了,於是我說,我要喝水,雖然我知道手術後不能馬上喝水。
醫護人員還在忙著收拾孩子,很久後才說這裡沒有水,我感到老公在我耳邊沒話找話,想要幫我轉移注意力,可是眼睛在一種抵抗不住的力量之下正慢慢地閉上,我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說:再不喝水我就要暈倒了。因為喉嚨太乾燥,這幾個字像是吐出來的。
麻醉師一直坐在我頭邊的右側,大概此時動了一點惻隱之心,他說:“有漱口水,就是淡鹽水,你喝嗎?”
“喝。”
於是他拿出一小支淡鹽水,擠了一點在我的嘴唇上,我費力地吸了一點點。
推到觀察室,我漸漸地感到傷口的疼痛,因為坐不起來也不能動,那裡的護士在紙杯裡插了根吸管喂我喝,喝到最後杯子裡沒水了,我吸了一口空氣,隨即想要劇烈地大咳,可是剛一要咳,腹部的傷口卻像是要炸裂開,那是我一生中咳得最左右為難膽戰心驚疼痛難忍的幾下。
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我自己是在北京婦產醫院生的,這一點似乎全家人都倍感自豪。姥姥有相熟的醫生,我媽就獲得了當時人們很難爭取到的剖腹產的機會——在八十年代末,剖腹產不是想剖就剖的,除非是危險的難產。一切所有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東西,都會令人珍惜,甚至包括這個比順產痛苦得多的剖腹產。
秋秋全程既不掙扎,也不哭泣,護士把他放在我旁邊的床上為他檢查,我平躺著不能動,但眼睛的餘光可以看到他的小腳就在空中悠閑地來回擺動,打一針,他就響亮地啼一下,針頭拔出,戛然而止,護士說從沒見過這麽輕鬆的孩子。
他戴著一頂新生兒的紗布帽,小護士說他們還有樣式特殊的小帽子,要去找一頂,她真的找來一頂,頭上有一個淺黃色布系著的粗粗的結作為裝飾,後來我和老公戲稱那是懶羊羊式的帽子。這個懶羊羊的帽子不太適合他,因為那個黃色的結比較重,總是墜著帽子往後掉。第二天來給他洗澡的老奶奶——醫院有專人負責給新生兒洗人生中第一個澡,說她太喜歡這個寶寶了,要送個帽子給他。在美國有很多好心的退休婦女湊在一起織帽子捐給醫院,醫護人員可以送給新生兒。洗澡的老奶奶說她快退休了,有一頂特別可愛的帽子她非常喜歡,要送給我的寶寶,後來很珍重地拿來交給我。那是一定很可愛的藍紫色毛線帽,上面還織出兩個尖尖的小耳朵。只可惜三月天裡戴有點太熱了。我的兒子出生兩天,就賺了兩頂帽子回來,可是都戴不了,於是又戴回了那個白色紗布帽。
在他長大一點以後,我也給他買過寬簷的漁夫帽,抵擋加州太過熱情的陽光,但他絲毫不領情,一秒鐘也不肯戴。天冷時我一位畫油畫的美國朋友還用鉤針給他鉤了一頂土豆皮色的小帽,但他的頭繼承了我和我老公,又大又圓,戴上以後整個腦袋都像土豆一樣,不過好看不好看不重要,因為他同樣是一秒鐘不肯戴。
雖然看到孩子很是喜悅,但那天我心中總有一種奇異的悲涼感,大概是因為我的孩子如此完整而輕鬆,而我如此破碎而僵硬。孩子是如此的柔軟粉嫩和清新,但我的疼痛和疲勞卻銳利而沉重。即使是這樣,我個時候——我和我的孩子——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4
生完隔天,護士讓我自己去洗手間,看看能不能“響應大自然的召喚”(上廁所的委婉說法),自然的召喚我沒感到,但感到了一件極其恐怖的事情——一個東西從我的身體裡被擠了出來,掛在那裡。
那是一種非常難以形容但令人無比恐懼的體驗,我能感到掛在腿間的東西像是身體的一部分——但是很光滑完整,不是血塊或其他任何我在人生經歷中感知過的東西,它碰到腿的感覺像是我的腸子之類。它就懸在那裡,沒有再繼續往下掉。我完全沒有膽量低頭看,驚愕和恐懼令我失聲,只能蹣跚地走出洗手間向我媽求救,而她迅速找來了護士。那個看起來很有經驗的中年女護士說,這可能是子宮——有的女性生完孩子之後子宮會掉出體外,需要找醫生推回去。
震驚像是全身束縛咒語一樣把我固定在那裡,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人的器官掉出來了,空氣中這麽多浮塵和細菌,它還碰到了我的腿,這麽髒,直接推回去就行嗎?當護士讓我自己先坐到床上時,我斷然拒絕,因為怕坐在自己的“子宮”上。緊張害怕加上產後虛弱,我感到強烈的頭暈目眩,護士看到我的臉色後馬上按了病房中的緊急召喚電鈴,並且立即把探測心跳的儀器夾在我的手指上。
我並不知道自己後來是怎麽躺在床上的,隻記得值班的一位女婦科醫生雙手交替在拉那個脫垂在我身體外的東西——拉的時候並不疼,只能感到它被順滑地拉出去,拉了好一陣才拉完,她說那是“一些膜”(some membrane),我並沒有看,只知道她把那東西扔在垃圾桶裡就走了。
很久以後,嚇呆了我和家人才從瞠目結舌中緩過來,我們滿腦子都是問題:那是什麽膜?為什麽會在我肚子裡?我做的不是剖腹產嗎,為什麽醫生沒把它從我的肚子裡的拿出來?肚子裡還有沒有更多了?
我們找到護士,迫切地要求和剛才的醫生說幾句話,可是醫生一直不來。這是一件很出乎意料的事情,因為在美國,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可以找醫生谘詢,無論是手上破了一個看不見的小口、臉上長了個痘痘,亦或是想減幾磅體重,而所有的這些,都會被鄭重其事地對待。然而現在,在發生了這樣不同尋常的意外之後,病人如此虛弱而恐懼,而醫生——用通俗地話說——躲起來了。
那個和善的中年女護士安慰了我幾句,她帶著一個梳著粗粗長辮子、很年輕的實習生。那個姑娘似乎驚訝、好奇又有點興奮——估計第一天實習就能看到這樣百年不遇的場面,真是賺到了。
不過令人震驚的怪事才隻開了個頭。
當天夜裡,身體裡往外掉未知物這件事又在洗手間發生了第二次。但這次感覺只有一個拳頭那麽大,並且直接掉進了馬桶裡,讓我不知道自己肚子裡還有多少亂七八糟的東西。還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在連番驚嚇刺激下,我已經開始分泌的母乳徹底消失了,孩子因為餓而大哭,我媽一整夜都抱著孩子,她一直說這真是一個令人憐愛的孩子,即使餓得難受至極,只要你抱著他,他就會盡量忍耐著,隻發出一些可憐的抽泣,但你一試圖把他放下來,他就會哭得異常苦澀。我們有想過喂配方奶,但護士口袋裡都有一張名片似的卡,上面寫著配方奶會增加以後嬰兒拒絕母乳和肥胖的幾率,你一說想加配方奶,她們就把這張卡塞到你的鼻子底下。我那時也真的覺得,堅持母乳就是愛的一種,似乎眼前的一切困境,都是因為奶,而解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我的堅持。
孩子一直在哀哀地哭泣,大量出血且嚴重睡眠不足的我覺得自己的睫毛從來沒有這麽沉重過,但又完全睡不著。
那一夜,孩子的體重掉了12%,粉撲撲的小臉變成了全身嚴重的黃疸。
第二天老公來換班,看到兩個精疲力竭的大人和一個黃褐色的孩子,當機立斷給孩子加配方奶,寶寶終於吃飽了!如釋重負的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當天還有更荒誕的事情在等著我們。
5
因為我很異常地排出一塊巨大的“膜”,並且這件事發生了兩次,在我們的反覆追問下,當天值班的醫生讓我去做超音波。孩子必須要有監護人陪伴,老公不能跟我同去。於是我在極度的虛弱中被架上了輪椅。當時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冷,因為身上長長的還沒愈合的刀傷,我不能穿任何正常衣服,只有一件薄薄的病號袍,而輪椅是四面透風的,好心的護士在我身上蓋滿了毯子,讓我此刻像一個奇怪的木乃伊——我倒是有點羨慕木乃伊,至少他們身上的“繃帶”是緊緊纏著的,而我鬆鬆圍著毯子卻還是可以讓冷空氣肆意的透進來。
從產科到放射科的路很遠,護工只是在用正常的速度推,而我卻覺得涼風像刀割一樣襲人,更可怕的是,沿路的地面上有很多鼓起來的減速帶,每次推過去的時候,傷口都有一陣撕裂痛。
放射科在地下,我被推進昏暗的超音波室,護工離開前讓我躺到床上,那張床很高,也沒有病床的扶手,對於一個肚子上剛縫合傷口的人來說,就像是面對喜馬拉雅山一樣,我忍著撕心裂肺的疼痛,一點一點地挪,終於爬到了那張床上。
超音波技師是一個金發碧眼的優雅中年女士,她一邊準備給我做超音波一邊和我閑聊:“你剛生完孩子?為什麽要檢查五髒六腑?”
“我是來檢查子宮的,我剖腹產以後子宮中有殘留。”
“這就奇怪了,”她仔細讀著電腦螢幕上我的病歷,“這上面顯示你是來檢查五髒的……”
“那麽,技術上來說,子宮可以檢查嗎?”
“當然可以。”
“那能請您給我檢查一下嗎?”
“不可以,我只能做醫生授權的檢查,不能私自檢查別的。”
於是她給我檢查了五髒六腑,而我像經歷滿清十大酷刑一下爬下了那張床,顛簸著回到了病房。
回到自己的病房,我和老公迫切要求見當天的值班醫生,想問問她為何安排我做一個毫無用處的測試。但是這一位也拒絕露面,只是傳話說下午會讓我再去做一次子宮測試。於是我又多受了一次罪,回到了那件陰暗的地下房間,還好這次媽媽來接班看娃了,有老公陪著我。
到了超音波室,還是那位優雅的白人女士,她這次打開毯子,一看到我下腹部的傷口,就倒抽了一口冷氣。“你才生完第二天,傷口還全是青腫和血咒之城,我怎麽可能用超音波探測器使勁壓你傷口?”
於是她找來了一位同事做證人,詳細解釋了為什麽不能做這個超音波,然後就要給當值的婦科醫生打電話,我知道在電話裡有一些就能不能給我做超音波爭執,但我只是躺在那個閃著紫色光的黑屋子裡,疲憊、無助、迷惘。
晚些時候,再我又一次被推回病房的時候,第四位醫生出現了,她是一位自己也懷著孕的女性華人醫生,她是意外發生之後第一位願意跟我坐下來說話的醫生,也是第一位試圖安慰我的醫生,不過她是帶著任務來的,一直要給我做超音波。當我問她為什麽超音波師說現在不能做的時候,她說:“你要相信醫生,超音波師不是做手術的醫生啊。”
我從這句話裡除了優越感並沒有聽到其他。
產後第四天的凌晨,測黃疸的人來到了房間裡。自從生完孩子,每天到房間裡的人就像是走馬燈——來查產婦體征的、來查嬰兒體征的、到吃藥時間來送藥的、到送飯時間來送飯的、兒科醫生來看嬰兒的、哺乳治療師來哺乳的……再加上喂奶、練習自己站起來去洗手間、跟護士學習怎麽照顧嬰兒,以至於前幾天我每24小時的睡眠不到2小時。
秋秋之前餓出的黃疸在邊界線上——沒有嚴重到要去“照光”治療,也沒有輕微到可以自愈,也就是說需要有人到在他的小腳丫上取血檢查,監測情況。那天我雖然虛弱迷糊,但是對孩子的事情並不糊塗——測血的人已經來過了。於是我明確告訴這個女人,我的孩子今天已經取過血了,你不能再扎他的腳了。
“是醫生讓我來的!”那個推著小車進來的女人說話並不客氣。
“那你讓醫生給我打電話,跟我說說為什麽一天要扎兩次。”
她推著她的車走了,沒再出現,醫生也沒來電話。
隻憑觀感,美國的醫院給人以強烈的秩序感,這裡沒有人頭攢動的病人和焦頭爛額的醫生,環境優雅溫馨,所有人的病人都是提前預約好的,並且可以享受固定醫生和護士在一段時間內的二對一服務。我曾經因為這裡就醫的便捷從容而感到慶幸,但發生在我身上的一系列事件,讓我開始質疑這種表面的秩序背後,是真正的規範嚴謹嗎?
因為第二天我和寶寶都要正式出院了,護士送了我們很多尿布、濕巾、配方奶。我問我媽:為什麽護士都對我們特別好?
我媽說:“因為她們看你們有涵養。經歷了那麽多,沒吵鬧過一聲,醫生躲著不見面,你們也對護士很有禮貌,從頭到尾沒遷怒過任何人。”
在我出院之前的一再要求下,給我做手術的Dr. H終於出現了,他淡淡地說,剖腹產的時候,他把孩子和胎盤拿了出來,又用布把子宮裡面擦了一下,但胎盤的有些部分就是沒有跟著出來。我問他怎麽定義這件事,意外?失誤?過失?他說“一個可以接受的事件”。在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媽舉著手機錄了下來,他凶狠地說:“你知不知道,在這個國家這樣做是違法的!我對此感到很憤怒!”他把“在這個國家”幾個字咬得分外重。我媽說:“對不起,我們不是本國人,對醫療術語和相關知識並不熟悉,所以需要留證,我們剛才並沒有偷拍,如果您介意,我現在可以在您面前把已經拍的內容刪除,並且我現在詢問您,‘我可以拍嗎?’”他換了一副笑臉說:“謝謝刪除,但我希望你不要繼續拍。”
事後我跟我媽說,沒經過同意,舉著手機錄像確實需要醫生同意,他生氣也是有理由的。我媽說,不錄像可以,只不過如果一切順利,醫生一進來,你就給他一大束花,熱情地說“醫生,謝謝您!”,我也在旁邊錄著像,醫生會疾言厲色地製止嗎?
我承認大多數美國人玩“雙標”都玩得爐火純青,但我還是覺得,自己能用美國人所尊敬的行事方式在美國解決問題。
6
我從出院三個月以後,還在不斷的流血,有產後抑鬱的症狀,需要經常回醫院接受檢查。但從三月到六月,我還是用自己的休息時間詳細地寫了一份材料,記錄了我在醫院子宮遺留異物後所有不愉快的經歷,每一件事,都有精確的時間點和經手人,事情的來龍去脈,都附上了相關的醫療記錄和檢查結果。我用博士的專業素養和研究水準製作了這份材料,將它發給了醫院和醫生所在的醫療機構,期待他們能夠給我一個公道。
美國的醫療系統複雜得令人迷惑——醫生並不屬於醫院,醫生只是租借醫院的場地、器材和醫護人員進行手術,因此他們之間是合作關係。醫生一般屬於不同的醫療機構,比如這次給我做剖腹產的醫生,和後來出現問題後的幾位值班醫生,都來自矽谷最大的醫療機構。
舉一個例子,如果在剖腹產的時候,紗布落在了我的肚子裡,那就是醫院的責任,因為護士有責任把拿出來的紗布數量核對清楚,而護士是屬於醫院的。但如果胎盤落在了我的肚子裡,就是醫療機構的責任,因為把胎盤完整地取出來是醫生的職責,而醫生是屬於醫療機構的。
沒多久就收到醫院的回復——這是醫生的事情。一個多月後收到醫療機構的回復——他們在調查,可能需要一個月。
一個月後,他們說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就這樣一直到了十月,我收到了一張A4紙的信,上面寫著,很遺憾我們的服務沒有達到你的預期,值班醫生從你肚子裡把那個東西拉出來的時候告訴你那個是什麽了啊,謝謝你的報告,我們以後提高服務。
避重就輕,沒提東西為什麽會留在我肚子裡,沒提醫生的粗魯冷酷和不耐煩,沒提值班醫生連續給剛剛大出血過後的產婦安排錯誤的超音波檢查……什麽也沒提,不認錯、不道歉、不提供任何解決方案,作為一個文學博士,我對他們語焉不詳文過飾非的本事甘拜下風。
一個中國朋友跟我開玩笑:你應該在他們門口舉個牌子——“庸醫害人”,拿大喇叭宣傳一下他們的劣跡。我記得自己參加過一個學術會議,裡面有個報告很有趣:明清的時候,拉“庸醫害人”這樣的橫幅,甚至拆了醫院,揪醫生鬍子這樣事情了,不僅古書裡有這樣的故事,還有生動的插圖呢。
其實在美國什麽樣的抱怨,大喊大叫出來都是正常的。我曾經上課的教學樓,每天出來都看到有美國學生支著時任總統奧巴馬的畫像,上面加了兩撇希特勒的鬍子,在那裡激情澎湃地大呼小叫著什麽。
我為什麽絕不會做這樣的事?因為我“有涵養”?也許只是因為我對這個國家的某些部分太有信心了。在美國,商店裡面買的衣服拿去退換,裡面的人都是滿面春風,絕不問為什麽,大型連鎖超市裡也一樣,甚至一箱吃了一大半的蘋果和用了大半年的電器都能退。當年麥當勞因為客人喝咖啡時被燙到,不得不賠償幾十萬美金並在所有熱飲杯子上作出明確標示,美聯航將乘客強行拖下飛機,因此受到千夫所指,幾乎成了當年最大的醜聞。我總覺得一個產婦和新生兒在醫院這樣噩夢般的經歷,嚴重程度不亞於燙傷或是掉牙齒,我一定能夠得到一個說法,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標榜關注弱勢群體的國家。
我經常問自己,到底想管醫生要一個什麽樣的結果。結論是,我要他們的道歉。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我對醫生和醫院的心裡印象是中西結合的——對西方先進教育和科技的尊重、對“醫者有仁人之心”這一中國傳統觀念的堅信。
美國社會中,醫生受到很大的尊重——醫學院的激烈競爭,醫生執照的高要求,和成為醫生以後驚人的高收入,都讓人們對醫生職業產生豔羨。美國的醫生是標準的中產:很高的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收入、很高的社會地位。生了一個孩子,我和我的保險公司總計支付了超過八萬美元,而年薪二百萬美元以上、享有最優越資源和人們尊敬的醫生,應該這樣手滑又冷漠嗎?
7
在我們的一再申訴和要求下,醫療機構派出了一位女士和我們見面,見面的時間由對方單方面規定為30分鐘,一見面就宣布臨時改為15分鐘,她帶了一位號稱首席醫師的女醫生。她們問我想要幹嘛。
英語裡有個說法,叫做”房間裡的大象”,指一個問題顯而易見到難以忽視,考慮到人的子宮也沒有多大,一塊比胎兒腦袋還大的胎盤組織,是怎麽留在那裡面的,一直是我心裡的未解之謎。我問這個女醫生:
“醫生做手術的時候把胎盤如此大的一部分留在病人肚子裡,這在醫學上正常嗎?”
她用極快的語速和大量的醫學詞匯迅速把剖腹產手術的過程說了一遍,沒有回答我問題。
我看著她一臉的自信和漠不關心,堅持問道:“我隻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醫生做手術的時候把胎盤如此大的一部分留在病人肚子裡,這在醫學上正常嗎?我就需要一個明確的答案,Yes還是No。”
她風一樣地站起來,灰色的眼睛裡有一種高傲的凶狠:“我不喜歡你的態度。”然後摔門而去。
另一位女士給我們指了一部只能到地下掃帚間的電梯,揚長而去。
從那以後醫療機構徹底忽視了我們,如今距離我生產已經整整一年,事情完全沒有會解決的跡象。
許多朋友問我,你可以起訴他們並索賠。我說,我只想讓他們說sorry。
我到美國來的原因是讀碩士,後來留下來,是因為我又申請上了博士,遇到了同在史丹佛讀書的老公……我們其實一直生活在一個巨大的保護傘下,那就是德高望重的教授、高素質的同學和同事、一個互相尊重的平等社會。
我們在有生之年不打算改變自己的國籍,但我們確實曾經相信我們自己和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雖然是外國人,但也是這個國家的納稅人,我們能講流利的、和美國人全然無障礙交流的英語,我們在引領世界科技潮流、追求平等自由的矽谷,我們在這座城市生活的時間比許多美國人都長,熟悉這裡的方方面面,擁有大量值得信任的朋友……即便是這樣,我們仍有如此遭遇。那些離鄉背井只為赴美生子的人,又是怎樣度過這段人生中最脆弱的時光的?
我將投訴材料內容精簡後,發布在Google Map和Yelp上,希望能夠幫助到其他正在選擇醫生的孕婦。很快就收到了醫療機構在下面的回復:“您正在和我們解決問題中,有問題請找正在和您協商的團隊。”而事實上,沒有任何團隊在與我進行任何形式的聯繫,他們的回復,只是希望其他瀏覽這一評價的讀者相信,他們正在解決問題。
從前,美國醫院裡的人給我的感覺就和迪士尼樂園的人一樣,總帶著熱情而友善的笑容,我甚至覺得他們比迪士尼的人更加可敬和勇敢,因為他們有時需要面對剝離了尊嚴和一切粉飾的、病痛所造成的肉體醜陋和死亡陰影下的焦慮和憂傷。至今我仍然非常感謝那些善良的護士對我耐心的照顧,但我如今看到的,是這個醫療機構中的大財閥,是他們強大的公關和律師團隊,是他們刻意的忽視背後赤裸裸的有恃無恐。
在如今的美國,到處充斥著政治正確的言論,不知道某個人確切性別的時候一定要說“他或她”,簡單地說“他”就是性別歧視,提到白人的時候可以說white(白)但提到黑人的時候不能說black(黑),否則就是種族歧視,說到年長的人不能說老,否則就是年齡歧視,看到豐滿的人不能說胖,否則就是歧視別人的體型,我曾經說過希望自己的兒子以後男人一點,馬上就有人一本正經地提醒我——你不能這樣說,有的男人天生就是喜歡娘,這是他的權利,你不能搞歧視。
在這種政治正確的壓力下,隨便一句話就可能犯眾怒,對他人言論總能挑出毛病的美國人,看似是世界上最有正義感的一群人。就像是跟我見面的首席女醫師,可以用不喜歡我的態度這樣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從一個醫療機構和病人就重大醫療失誤所進行討論的會面中揚長而去。
一個看似如此注重自由和尊重人權的國家,種族和性別在這個國家真的達到了平等麽?
在這件事發生之後,在這裡生活的朋友——無論美國的還是中國的——都諄諄告訴我,如果要請律師,一定要請一個白人、男的,記住了嗎?白人男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請律師,但我只知道,采納他們的意見,意味著我為了在美國社會的遊戲規則下生存,要首先對自己的華裔女性身份認輸。
我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能量,能夠用蚍蜉撼樹的精神討要一個所謂的“公道”,但我知道在這裡生活,必須時刻勇敢。
在這所謂的勇士的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