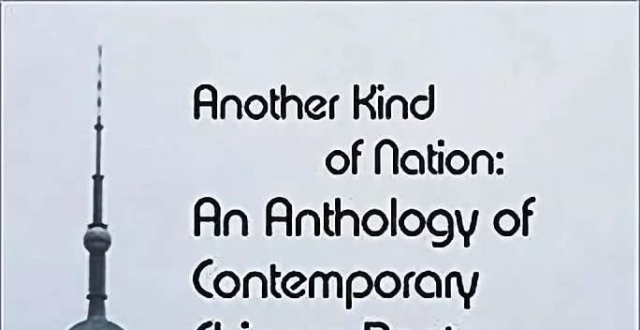作為和傅雷、錢鍾書同時代的資深翻譯家,許淵衝已經出版了120多本譯作和翻譯理論,涵蓋中英、英中、中法、法中4種類型。“精通這3種語言,能夠互譯,而且有作品出版。能做到這點的,全世界絕無第二個。”(圖/本刊記者 梁辰)
本刊記者 鄧鬱 發自北京 / 編輯 鄭廷鑫
“楊振寧是1957年獲諾貝爾獎,王希季是70年代(長征一號)火箭首射成功。我是2014年才得獎,比振寧晚了五十(多)年啊!”
93歲的許淵衝鶴發白眉,聲如洪鍾,中氣十足。
8月22日,外文局禮堂,中國翻譯協會為獲得國際翻譯家聯盟“北極光獎”的他舉行了盛大的授獎儀式。和他年齡相仿的昔日西南聯大同窗楊振寧和王希季皆到場祝賀。
因為前兩年動過手術,許淵衝上台時步伐較慢,耳力也不算好。但只要一開腔,就有震撼性的“音效”。
“他不是因為耳朵不好才大嗓門,他大學一年級嗓門就這麽大了!”楊振寧說,“我們3個人分別在文學院、理學院和工學院,並不太熟。那時候我們就有很大分別,我和王希季活動範圍小,許淵衝就不一樣,他很活躍。西南聯大當時的漂亮女孩兒,他都追過!”
坐在舞台正中的許淵衝沒有聽清,待身邊人湊近耳朵解釋方才明白。他擺擺手,臉上露出坦蕩的笑容。
這一天,他或許等待了一輩子。
作為和傅雷、錢鍾書同時代的資深翻譯家,許淵衝已經出版了120多本譯作和翻譯理論,涵蓋中英、英中、中法、法中4種類型。“精通這3種語言,能夠互譯,而且有作品出版。能做到這點的,全世界絕無第二個。”這是他平生最為得意、屢屢自誇的一點。他翻譯《楚辭》、《詩經》、《西廂記》、《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等經典,被譽為“20世紀下半葉中國典籍翻譯歷史上的豐碑”。
這些讚賞許淵衝笑納了,但他更樂意抓緊時間,做點實事。授獎儀式上,簡單致謝後,他便把演講變成了個人翻譯理論和心得的分享。從《詩經》到毛澤東詩詞,一首一首地講解許譯的妙處。講到暢快處,會把短袖的袖口還往上擼,或者手掌啪啪地碰到麥克風。
“你們看看,這像是一個和共產黨同齡的人嗎?”授獎儀式上,最後發言的嘉賓、中國翻譯協會會長李肇星問。
——任何時候,只要談起翻譯,耄耋之年的許淵衝便成了李肇星口裡說的ageless。
授獎一周之後,記者前往他在北大的家中拜訪。他興奮地拿起手中的《李爾王》英譯中手稿:“朱生豪和卞之琳的譯本有他們的優勢,但他們翻的沒有玩笑味兒,而且卞之琳太強調對等。比如這句‘那籬雀養大了杜鵑鳥,自己的頭也給它吃掉’。我翻成‘麻雀喂大了小鳥,小鳥要咬它的頭’。‘籬雀’和‘杜鵑鳥’雖然字面是精準,但誰知道這句話是表達什麽意思呢?實際上它說的是,李爾王養大了女兒,現在女兒卻要來對付他。只有翻出‘小鳥’才能表達這個意思啊!”
“翻譯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到這個年紀還在翻譯莎士比亞,一定有著強大的思想支撐。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羅米修斯,永遠進行著自己的事業。”和許淵衝相交甚篤的翻譯家許鈞說。
與他相伴了半個世紀的夫人照君則對我說:“許先生,是一個奇人啊。”
多年來,他是翻譯界的“少數派”。他的“過度”意譯風格長期不被人接受,甚至被斥為“亂譯”;倡導譯詩要押韻,也和國內多年流行的分行散文詩譯背道而馳。
率性、張揚的個性,也讓他在崇尚低調的翻譯圈子裡“獨樹一幟”。他在自傳《追憶逝水年華》中大方羅列出了國內外對他的各種讚譽;在散文自選集裡稱“三美”、“三化”理論達到了西方對等論無法達到的高度。即便是翻譯界的泰鬥傅雷,他也認為並非不可逾越:“可以拿我的《約翰·克里斯托夫》和他的比,整本水準絕對高過他。你隨便摘10段出來,我不怕。”
授獎那天,《北京周報》記者劉雲雲和同事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這位聞名已久的老前輩。在他們眼中,許淵衝就是一個特別活躍的老頭。“他能把古詩詞的意境翻譯得那樣美好、純粹,絕對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人。只有聰明的人才能有如此強大的聯想功能,才能博聞強識,並且自如地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切換。看得出來,他已經被壓抑好久了,自己的理念終於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有種‘終於翻身了’的感覺。”
一章一句都是真性情
多年來,翻譯界強調譯文要盡量在形式和內容上忠實於原文。許淵衝的翻譯卻不拘泥於原作,講求再創造。“西方語言裡,英、法、德、俄、西語90%可以對等,但中國語言和西方語言的對等只有50%。怎麽辦呢?”他認為譯文可以和原文不對等,“要發揮譯語優勢”。還認為翻譯是兩種語言和文化的競賽,譯文甚至可以超過原文,“文化交流的目的是雙方得到提高。”
這種“優勢論”和“競賽論”,成了他在翻譯界最受質疑和詬病的一點。陸谷孫、王佐良、馮亦代、許鈞等翻譯家都曾公開和他唱反調。
他與王佐良發生過一次論爭。法國詩人瓦雷裡的詩《風靈》描述了靈感的稍縱即逝,西南聯大學長王佐良的翻譯是:“無影也無蹤,換內衣露胸,兩件一刹那。”許淵衝詰問:“前面兩句沒問題,兩件一刹那是啥意思?”他譯成“無影也無蹤,更衣一刹那,隱約見酥胸”。
“王佐良說我這個‘酥胸’的譯法是鴛鴦蝴蝶派,他們就強調對等。“他們講究對等,不光內容,形式也要對等。問題是他們光是把劍亮出來,刺下去,我是把劍根也拿出來了。我是內科派。我這次得獎,就是‘內科派’對‘外科派’的勝利!”許淵衝用手比劃出刺劍和拔劍的動作。
他們之間的爭議是否影響到二人交情?許淵衝對此沉默了片刻。“不好說。我申請北大的博士生導師,王佐良說和我‘意見不同’,就壓下來了。他認為我是錯的……從1992年一直到1995年王佐良去世前半年,《中國翻譯》都不登我的文章。”
此後,許淵衝與江楓有關翻譯中形似與神似的論戰被稱為最“火爆”的一場爭鳴。江楓主張翻譯應先形似而後神似,而許卻認為在形似與神似統一時,譯文可以形似,在二者有矛盾的時候,譯文應該神似。
南京大學教授許鈞和許淵衝已有二三十年的交往,曾就許的“優勢論”等觀點和他有過專門爭論。但許鈞認為,這種爭論很有意義。“許老先生敢說敢想,非常好。到現在他給我寄書,都會寫‘許鈞小兄雅正’。我可比他小33歲呵!這些爭論從沒有影響到彼此的交往。”
不少人讀《逝水年華》,既覺得痛快,又感歎此人毫不自謙,語氣狂放。有人描述,這本回憶錄給人感覺“在人情上,他似乎不是中國人。倒有點像是從新大陸來的……他非常重視感情,又難說諳熟‘人情’。狂作文章信手書,一章一句倒都是真性情”。
在“北極光獎”授獎儀式上,許淵衝則謙遜地說,“這不是我個人的榮譽,是屬於全體中國翻譯者的。”
“這次國際上承認了,如果國內還有反對的,還可以駁一駁。我不怕辯論。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在家中受訪時,許淵衝告訴我。話語體系裡,還隱約帶著過去年代的痕跡:“我現在能‘打倒’他們,說明我是有道理的。”
“詩譯英法惟一人”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boat.
——柳宗元《江雪》,許淵衝翻譯
幾年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他的全民醫保改革議案時,許明將這首《江雪》寄給了他和一個共和黨議員。那個共和黨議員本來準備隨大流,和其他“同黨”一起對醫保議案投反對票。但在讀到《江雪》後,非常欣賞其中“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獨立精神,隨之做出了獨立於黨派之外的選擇,改投了讚成票,最後醫保議案以微弱優勢獲得通過。奧巴馬知道後很高興,還給許明寄了信件和照片,說許明是他的“廚房內閣成員”。
“你說文化的力量有多大?它看不見、摸不著,沒法像數學那樣精確計算,但是中國文化的魅力,經過我的意譯,就能讓西方人感動。”《江雪》的英譯者、許明的父親許淵衝說。
相對於“優勢論”的學術爭議,許淵衝在中國詩詞的翻譯成就上,早已得到了國內外的公認。但這條路的探索,卻是從挨批鬥開始。
1950年代初,他被說成是“名利思想”、“白專路線”,每年都要受到批判。由於曾在陳納德麾下當過翻譯,差點被打成國民黨特務。幸好審查了一年之後,得出“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膨脹”,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才幸免於難。接著是“反右”,“翻譯的路子一下子全堵住了,只剩翻譯毛澤東詩詞這一條路。”
有一次在烈日下陪鬥,又熱又累,度日如年。許淵衝忽然想起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就默默地背誦,並在心裡試著將其譯成英文。
“說來也許叫人難以相信,我一譯詩,就把熱、累、批、鬥全都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眼裡看到的仿佛只是‘山舞銀蛇,原馳蠟象’,心裡想到的只是‘略輸文采,稍遜風騷’。等到我把全詞譯完,批鬥會也結束了。”
毛澤東的《為女兵題照》中有句“不愛紅裝愛武裝”,他把“紅裝”譯為“powderthe face”(塗脂抹粉),把“武裝”譯為“face the powder”(面對硝煙),恰好表現了“紅”與“武”的對應和“裝”的重複。談到此處時,他說靈感很重要,但靈感也來自於生活。“這個‘facethe powder’就是我大二時看英文報紙記下來的。”
1980年代,許淵衝開始致力於把唐詩、宋詞、元曲翻譯為英法韻文。已故賓州大學教授顧毓琇讚譽許譯:“歷代詩、詞、曲譯成英文,且能押韻自然,功力過人,實為有史以來第一。”
例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他翻成“Youcan enjoy the grand sight,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這個有對仗美,而‘千里’,你要翻成li或者miles,都不好。把‘樓’翻成floor或者storey,都不是那個感覺。詩意全沒了。”
在不違反求真的條件下盡量求美,這是許淵衝一貫的堅持。“貝多芬甚至說過:為了更美,沒有什麽規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最熟悉的例子莫過於“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蘇聯人聽了沒覺得好。“因為他們不像中國人,不理解月亮是代表團圓的。他們沒這觀念。如果照字面翻,那確實是看不出美來。”許淵衝認為自己翻成“床曾經在如水的月光中,於是我也沉浸在鄉愁中”,是一種再創造。“譯成外文,必須為外國讀者著想!”
語言學家呂叔湘曾專文提出,詩歌翻譯成詩歌不好,不如譯成散文。許淵衝認為,如果把詩歌翻譯成散文,就會破壞唐詩原有的風格。後來呂叔湘接受了他的觀點,並邀請他重新合編《中詩英譯比錄》,“原先這本書隻收錄外國人翻譯的中國詩歌,後來把我的譯作也收進去。呂先生的學者風范,真是令人敬佩。”
許淵衝近乎固執地堅信,原詩押韻,譯者便有責任譯成韻文。但在後現代詩風盛行的當代,押韻被視為腐朽,批評家和不少現代詩人指責“因韻害義”。因為不同意押韻,王佐良沒有加入唐詩300首的翻譯隊伍。
有年輕學子讀過許淵衝翻譯的唐詩,直言“譯者風格盡顯,而詩人風格全無”,且韻腳過於重複。許淵衝回應:“艾略特說過,個人的才能有限,文化的力量無窮。個人的風格是個小問題。比如李白,我覺得只有我才傳達了他的風格,你也可以說那是我的風格。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宣揚了中國的文化。”
儘管爭議很難有定論,但他的學生余石屹覺得有一點是能說明問題的:“目前看來,西方採用中國人翻譯的書很少。許先生在這一點上是不錯的,他的譯詩在國外出版了不少,有的被選進了大學教材。”
許淵衝的自我點評更加狂傲:“不是院士勝院士,遺歐贈美千首詩。”他說在一生的重要關頭,他沒有考上公費留學。“假如我也去了美國,那20世紀就不一定有人能將中國古典詩詞譯成英法韻文了。”
《山西文學》主編、作家韓石山曾在某報發表文章批評《許淵衝的自負》。許淵衝也以《是自負還是自信》,進行有理有節的回答。結果投到同一報紙,對方卻未予發表。老先生坦蕩蕩地找到韓石山,說“要不發在你們《山西文學》上吧?”韓慨然說“好啊好啊”。於是兩人成了朋友。韓還書寫“春江萬裡水雲曠,秋草一溪文字香”的條幅,送給這位忘年交。
我在許家客廳裡看到了這幅字,許淵衝笑道:“呵呵,他這話看不出是褒是貶,意思頗有些曖昧!”
不過韓對許的心悅誠服並不止這一樁。
1998年暮春,德國藝術家組成的交響樂團來京演出,演奏了著名作曲家馬勒的《大地之歌》。樂曲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別名為《寒秋孤影》和《青春》,並特意注明是法國詩人戈謝根據翻譯的中國唐詩創作。
現場聽眾中不乏專家,卻無人能辨別出這兩章究竟取自何首詩作。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指示:“一定要盡快把德國藝術家演奏的兩首唐詩搞清楚。”
許淵衝回憶,中國詩詞學者研究了一年,毫無結果。他注意到《寒秋孤影》作者的德文歌詞署名是TschangTsi:“這是張繼。”他隨即找出戈謝的《玉書》進行中法文比照,再按照這位印象派女詩人慣用的“拆字法”逐一分析詩中句子:由第一句的“霜”字猜出是“月落烏啼霜滿天”,第二句的“心上秋”合成“愁”是“江楓漁火對愁眠”,他由此斷定第二樂章是張繼的《楓橋夜泊》;又根據“玉虎”合成“琥”而猜出“玉碗盛來琥珀光”,並斷定第三樂章是李白的《客中作》。
一樁文化懸案終於被破解。韓石山提及此事時說道,“這是要真功夫的。”
“你說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麽?”
“回顧我這一生,小學是全市最好的小學,中學是全省最好的中學,大學是全國最好的大學。不過我在這些最好的學校裡,只是一個不上不下、時高時低的中等人物,也就是‘人中人’。”
“我不是一個好學生。那時我們都崇拜那些不怎麽學習、但成績也很好的學生。覺得那才叫厲害。”許淵衝回憶,大一英文期末考試,兩個小時,楊振寧隻用了一小時就交了頭卷,成績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積分課的考試,不是100就是99分,“無怪乎他小時候就說將來要得諾貝爾獎了。這不是天才嗎?”
他在回憶錄中不吝筆墨地描述母校西南聯大。在那個戰火紛飛卻群星璀璨的年代,這所學校幾乎聚集了全中國的精英。
外文老師葉公超講《生活的目的》時,先要學生朗讀課文。學生才念一句,他能說出學生是哪省人;學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熱諷,叫人哭笑不得。許淵衝在別人念時沒聽,只顧準備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滿以為不會挨罵了。不料葉公超卻問:“你讀得這麽快幹什麽?你說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麽?”
“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沒有聽,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評我隻重形式,不重內容,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教訓。”許淵衝誠懇地自省。
聞一多講《詩經》,劉文典講《史通》,羅庸講唐詩,浦江清講宋詞,馮友蘭講哲學,柳無忌講西洋文學,蕭乾談“創作與譯詩”,卞之琳談“寫詩與譯詩”……這些都奠定了許淵衝的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根基。而他畢生追求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譯準則,則來自於朱光潛和錢鍾書的言傳身教。
受朱光潛的熏陶,他奠定了詩譯的理論基礎:不但要寫景,還要傳情。不僅存義,而且存音。把原文譯成英法文時要盡可能押韻,使詩歌保持其情義音形,來勝過現代散體的譯文。
1978 年初的詩歌譯壇仍然是分行散文一統天下。許淵衝把毛澤東詩詞的譯文和譯論一同寄給朱光潛請教,後者在信中說:“意美、音美和形美確實是作詩和譯詩所應遵循的。”這給了他很大的鼓舞。
“1983 年我到北大任教,朱先生那時87歲了,還親自來看我,贈我一本《藝文雜談》。書中說道:詩要盡量地利用音樂性來補文字意義的不足。又說:詩不僅是情趣的意象化,尤其要緊的是情趣的形式化。我從書中找到了譯詩‘三美論’的根據。”
錢鍾書留給學生許淵衝的印象不僅在於其才智過人、妙語迭出,還有“成為一代宗師之後,諄諄嘉勉後人”。1980年代以來,為了詩詞翻譯中的問題,他屢次寫信向錢鍾書請教。後者都不吝回復點撥。“文革”後,有同仁見許淵衝翻譯蘇詩,還曾以“翻譯老古董”作評。錢鍾書回信第一句,就把漢詩西譯稱為“壯舉盛事”,給了許淵衝無窮的動力。
“我最佩服錢鍾書的就是他能‘化平凡為神奇’,了不起。他說中文是duo(二重奏),西方文化是duel(決鬥),中國強調和諧,西方強調對抗。這個說得太對了!在記憶力上,我可不如錢鍾書。他太強了,過目不忘!”
收到許淵衝寄去的英譯《李白詩選一百首》,錢鍾書回信,笑稱“可惜李白不懂英文,假如活到今天,一定會和你(許淵衝)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但錢把傳真看得重於求美,認為翻譯不是創作,這和許淵衝的意見不同。“錢先生說:這個問題我說服不了你,你也說服不了我,還是各自保留意見吧。可見他的學者風度。”
“他是個特純的人”
授獎歸來,那座透明的“北極光”獎杯即被擱在許家臥室書架的最上層,不踮著腳、不經人介紹,幾乎意識不到它的存在。
比起獎杯,許淵衝更親近的是書桌上的綠格白底稿紙、放大鏡,和一台看不出年代的長城台式電腦。
如今他的作息如鍾表一樣規律:早上9點左右起,到陽台上做操——做的還是“馬約翰操”,那是西南聯大最好的體育老師留給學生的“遺產”;吃完早飯,開始翻《莎士比亞全集》;午睡起來後,看看報紙,便騎著自行車去宮門了。
年過九旬的老人,因為騎車已經摔過兩次。“勸過他別騎,不聽。這麽大的年紀,愛喝冰綠茶,愛吃甜食。像個孩子。”夫人照君的埋怨裡,有著一股疼惜。
她說,老伴兒晚上7點看完新聞聯播,晚飯後一定出去散步。回來以後就“來勁”了,繼續翻譯,直到深夜。“有時他會半夜裡坐起,打開電燈,把夢裡想到的東西寫下,生怕第二天忘記了。”
“我現在也不用功啊,一天才1000字。要是用功,早就不幹了。只是覺得有趣才乾。這也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許淵衝輕描淡寫地說。
提起楊振寧在授獎大會上的“爆料”,他毫不躲閃地回敬了這位老同學:“楊振寧調侃我,不過他比我強啊,他都找了兩個(夫人)了,我還是一個,哈哈。”
出版自傳《逝水年華》時,許淵衝已是八旬老人。他在書中大方地寫自己與同學小林的“陽宗海之戀”,對一位叫如萍的女子的刻骨思念,以及在巴黎與外國女郎的甜美邂逅、溫柔繾綣。
夫人照君對此毫不介意,“那時候他風華正茂,那些也都是在我們之前的故事,很正常啊。”她向記者展示他們相戀時的黑白照片,“許先生年輕時又高又帥,五官又好,很瀟灑!”
她說自己從家庭背景和生活習性上,和許淵衝其實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我是抗日英雄家庭出身,留蘇以後考上人大。當時完全是被他的才華傾倒……他個性特純,不是表面一套、心裡一套那種。”
北大暢春園的許家,一套70平米的簡陋居室。其中最惹眼的陳設,莫過於滿滿當當的書架。就連層層疊放的老式行李箱裡,擺著的也是書籍資料。客廳的沙發對面,有一張搭著蚊帳的小床。許淵衝每每看書、翻譯過後,便在此歇息。
“最開始譯羅曼·羅蘭的《哥拉·布勒尼翁》,(千字)才9塊錢,那時候月工資是150塊錢。解放前是需要我倒貼錢去翻譯出書的,解放後翻譯第一本,得了500塊,很滿意了。後來千字變成20塊,到90年代初還是。這得怪西方,因為英文和法文德文太像了,互譯很容易,所以翻譯不值錢。重印就更不值錢了,大概千字幾分錢,奇低無比。要不是我有教書的工作,光靠翻譯肯定餓死。”
如若不問,老人對這些也不會多提。照君說,“中譯英和中譯法的稿酬用的是版稅計算,許先生拿10%。但這些書印數少啊,說起來錢也不多。”
那像企鵝出版社那樣的國外大社,稿費應該不少吧?
“對,他們給的高多了。90年代給過16000英鎊,可也讓國內出版社拿了,我們一分錢沒拿著。這回清華出的《從詩經到毛澤東詩詞》(暫名),許先生這一輩子的精華都在裡頭。精裝書定價要一百多塊吧,他一分錢稿費也不要,權當做貢獻了。”
如今的許淵衝愛讀《參考消息》,常看《海峽兩岸》。早年在西南聯大受到的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現在被包裹在一顆濃烈的愛國心裡。他在授獎儀式上提起美國插手南海事件,在書中也寫道,“現代西方文化的缺點正是見利忘義、以強凌弱,所以天下不得太平。”
在他看來,美國在羅斯福當政時還是重義的。“到了杜魯門,日本便成朋友了,日本可不是可靠的。珍珠港事件時,‘利義合一’的時候,他們取義。到後來不合一,便取利了。安倍現在居然說,轟炸廣島是不對的,慰安婦也是自願的。這個太壞了。經過這麽多年,我覺得,我們(政府)還是對的。”
他心裡時刻懷揣著“趕英超美”、希望中華文化成為世界文明主流的焦慮。他引用楊振寧的話:“‘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幫助克服了中國人覺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國人的最強項,中國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這也可以長自己的志氣,滅他人的威風了。”
由於“反右”和“文革”,一耽誤便是二十餘年,他在心裡琢磨:“小平同志號召,到20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要翻兩番。我打算出20本書。這樣才能挽回中斷20年的損失。”結果在20世紀末前,他已經提前完成了翻兩番的目標。“走我這條路的人多了,中國文化就是世界一流了。”
他一直銘記老師馮友蘭提出的“四重境界”:“我現在,應該是在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之間吧。什麽時候,道德境界變成自然,那就是天地境界了。可是,世間有幾人能做到?”
(參考資料:許淵衝著《逝水年華》《往事新編》,《許淵衝:詩譯英法惟一人》《許淵衝:翻譯家的自信與自負》。感謝外研社付帥先生對本文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