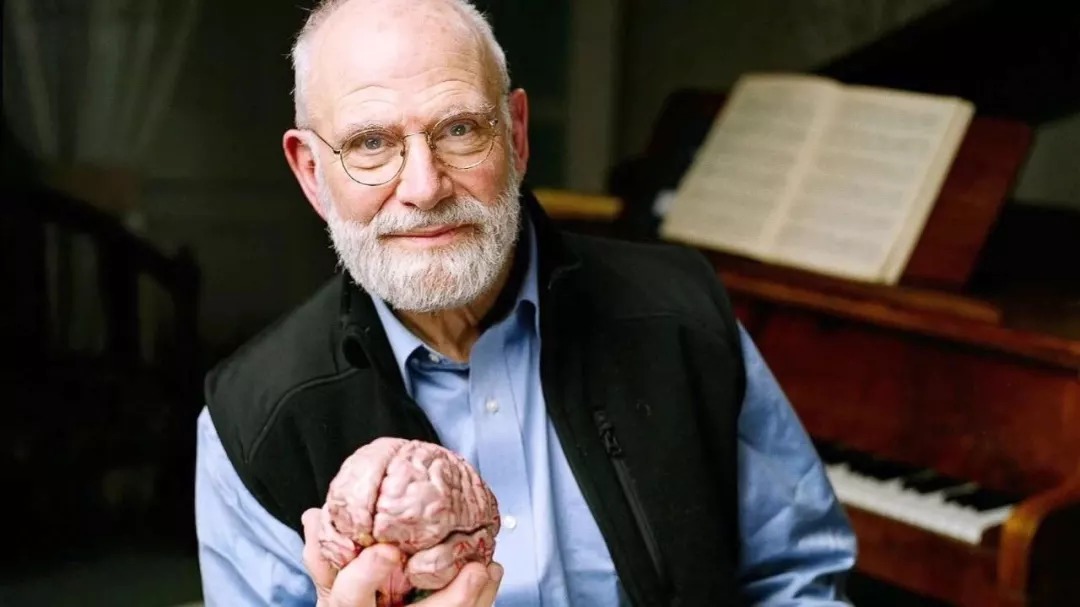文:余華
來源:愛思想網
二〇一〇年五月,我參加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節期間,去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紀念館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築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殺害了六百多萬猶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萬,還有一百多萬死難者沒有被確認。在一個巨大的圓錐狀建築的牆上貼滿了死難者的遺像,令人震撼。死難兒童紀念館也是圓形建築,裡面的牆是由死難兒童的照片交替出現組成的,裡面的光也是由這些交替出現的照片帶來的,一個沉痛的母親的聲音周而複始地呼喚一百多萬個死難兒童的名字。紀念館的希伯來文原名來自《聖經》裡的“有記念、有名號”,原文是:“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
紀念館還有一處國際義人區,這是為了紀念那些在大屠殺期間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展示的國際義人有兩萬多名,他們中間一些人的話被刻在柱子上和牆上,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話:“起初他們追殺GC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GC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話也被刻在那裡,一個波蘭人說出了一句讓我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麽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麽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麽,我只知道人是什麽。”
“我只知道人是什麽”這句話說明了一切,我們可以在生活裡、在文學和藝術裡尋找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無論這些例子是優美的還是粗俗的;是友善和親切的,還是罵人的髒話和嘲諷的笑話;是頌揚人的美德,還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時,人性的光芒總會脫穎而出,雖然有時看上去是微弱的,實質卻無比強大。
我在耶路撒冷期間,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給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營裡的幸存者,他被關進集中營的時候還是個孩子,父親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他從未說起在集中營裡的經歷,這是很多集中營幸存者的共同選擇,他們不願意說,是因為他們無法用記憶去面對那段痛苦的往事。當他老了,身患絕症時,他兒子(一個紀錄片導演)鼓勵他把那段經歷說出來,他同意了,面對鏡頭老淚縱橫地說了起來,現場攝製的人哭成一片。他說有一天,幾個納粹軍官讓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排成長隊,然後納粹軍官們玩起了遊戲,一個拿著手槍的納粹軍官讓另一個隨便說出一個數字,那個人說了一個七。拿手槍的納粹軍官就從第一個數,數到七時舉起手槍對準這第七個人的額頭扣動扳機。拿手槍的納粹軍官逐漸接近他的時候,他感到父親悄悄把他拉向旁邊,與他換了一下位置,然後他才意識到自己剛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個納粹軍官數著數字走過來,對準他父親的額頭開槍,父親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時候他還不到十歲。
說點輕鬆的,也是二〇一〇年,我去南非現場看世界杯,學會了好幾種罵人的髒話,因為每場比賽兩邊的球迷都用簡單的詞匯互罵,我記住了。可能是我個人的原因,什麽樣的髒話都是一學就會,現在這些髒話已經全忘了,後來沒機會用。差不多十年前,我家裡的餐桌是在宜家買的,桌面是一塊玻璃,上面印有幾十種文字的“愛”,開始的時候我看著它心想這世界上有多少數量的愛?有意思的是,為什麽全世界的球迷在為己方球隊助威時都用髒話罵對方球隊?為什麽世界上所有的語言裡都有“愛”?這讓我想起兩個中國成語:異曲同工和殊途同歸,接下去我就說說這個。
中國的明清笑話集《笑林廣記》裡有一個故事:一個人拿著一根很長的竹竿過城門,橫著拿過不去,豎起來拿也過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後對他說,我雖然不是聖賢,也是見多識廣,你把竹竿折斷成兩截就能拿過去了。法國有個笑話,這是現代社會裡的笑話:一個司機開一輛卡車過不了橋洞,卡車高出橋洞一些,司機不知所措之時,有行人站住腳,研究了一會兒,對司機說,我有一個好主意,你把四個車輪卸下來,卡車就可以開過去了。
這兩個笑話的時間地點相隔如此遙遠,一個是明清時期,一個是二十世紀;一個在中國,一個在法國。可是這兩個笑話如出一轍,這說明了什麽?應該說明了很多,我說不清楚,別人也說不清楚,也許有一點說明了,就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頭禪——人都是一樣的。
我再說說兩個與我有關的故事,第一個是《許三觀賣血記》,小說裡的許玉蘭感到委屈時就會坐到門檻上哭訴,把家裡的私事往外抖摟——這是基於我童年時期的生活經驗,當時我家的一個鄰居就是這樣。一九九九年,這部小說的意大利文版出版後,一位意大利讀者對我說,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許玉蘭這樣的女人,隔些天就會坐到門口哭訴爆料。第二個是《兄弟》,十二年前在中國出版時受到很多批評,二〇〇八年出版法文版時,一位法國女記者採訪我時對此很好奇,問我為什麽《兄弟》在中國遭受到那麽多的批評,哪些章節冒犯了他們。我告訴她有幾個章節,首先是李光頭在廁所裡偷窺,我還沒有來得及說其他的,這位女記者就給我說起法國男人如何在廁所裡偷窺的故事。這下輪到我好奇了,我說,李光頭在廁所裡偷窺的故事發生在中國的“WG”時期,那是一個性壓抑的年代,你們法國的男人和女人上床並不那麽困難,為什麽還要去廁所偷窺?她說,這是你們男人的本性。
類似的故事我可以繼續往下說,與我無關的應該比與我有關的還要多,讓我說一千零一夜是不可能的,說一百零一夜還是有可能的。從上述角度看,知道人是什麽似乎很簡單。可是換一個角度,從那位樸實善良的波蘭農民的角度來看,知道人是什麽就不那麽簡單了。“猶太人”在他的知識結構之外,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人是什麽,因此冒著生命危險去救猶太人。這個勇敢的行為意味著什麽?我們可以稱之為人性的力量,同時也意味著他確實知道人是什麽。這樣的人可能沒有我們認為的那麽多。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麽。他在《雕刻時光》裡談到“影像思考”時,講述了曾經聽來的兩個真實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群叛軍在執刑的隊伍之前等待槍決,他們在醫院牆外的窪坑之間等待,時序正好是秋天。他們被命令脫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著滿是破洞的襪子,在泥坑之間走了好長一段時間,只為尋找一片淨土來放置他幾分鐘之後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這個令人心酸的故事意味深長,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個告別生命的儀式,也可以理解為這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是存在的延續。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理解這個最後時刻的行為,如果是在平常,外套和靴子對於這個士兵來說就是外套和靴子,但是行將被槍決之時,外套和靴子的意義不言而喻。這個士兵在尋找一片淨土放置它們時已經沒有對死亡的恐懼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頓好,這是他無聲無字的遺囑。
塔可夫斯基講述的第二個故事是:“一個人被電車碾過,軋斷了一條腿,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面靠牆而坐,在眾人的注視下,他坐在那兒等待救護車到來。突然間,他再也忍不住了,從口袋裡取出一條手帕,把它蓋在被截斷的腿上。”
塔可夫斯基講述這兩個故事是為了強調藝術影像應該“忠實於角色和情境,而非一味追求影像的表面詮釋”。這第二個故事讓我腦海裡出現了西班牙作家哈維爾?馬裡亞斯的《如此蒼白的心》的開頭部分,這是近年來我讀到的小說裡最讓我吃驚的開頭,馬裡亞斯也是一個知道人是什麽的作家。《如此蒼白的心》是一部傑作,它是這樣開始的:“我雖然無意探究事實,卻還是知道了,兩個女孩中的一人——其實她已經不再是所謂的女孩了——蜜月旅行回家之後沒多久,便走進浴室,面對鏡子,敞開襯衫,脫下胸罩,拿她父親的手槍指著自己的心髒。事發當時,女孩的父親正和部分家人及三位客人在餐廳裡用餐。女孩離開飯桌約五分鐘後,隨即傳來了巨響。”馬裡亞斯小說的第一部分用了不分段落的滿滿五頁紙,精準描寫了在場的所有人對女孩突然自殺的反應,尤其是女孩的父親,他和同行的人跑到浴室時嘴裡還含著一塊沒有吞咽下去的肉,手裡還拿著餐巾,看到躺在血泊裡的女兒時他呆滯不動,“直到察覺有胸罩丟在浴缸裡才松手把這塊還攥在手裡或是已經落到手邊的餐巾覆蓋在胸罩上面。他的嘴唇也沾上了血跡,仿佛目睹私密內衣遠比看到那具躺臥著的半裸軀體更讓他羞愧”。
同樣都是遮蓋,呈現出來的都是敞開,我的意思是說,這兩個遮蓋的舉動向我們敞開了一條通往最遠最深的人性之路,而且是那麽的直接有力。不同的是,塔可夫斯基講述了影像中羞愧的力量,馬裡亞斯描寫了敘述裡驚恐的力量。設想一下,如果那個等待救護車的人沒有用手帕蓋在被截斷的腿上,而是用手指著斷腿處以此博取路人同情,那麽這個故事的講述者不會是塔可夫斯基;如果那個父親不是把餐巾覆蓋在胸罩上面,而是試圖蓋住女兒半裸的軀體,那麽這個細節的描寫者不會是馬裡亞斯。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一九八六年去世的俄羅斯導演,他留給我們的電影經久不衰;哈維爾·馬裡亞斯是一九五一年出生的西班牙作家,至今仍在生機勃勃地寫作。作為導演,塔可夫斯基講述這個故事的目的是為了闡明什麽是真正的藝術影像,就是構思和形式的有機結合。作為作家,馬裡亞斯描寫出來的這個細節呈現的是文學裡無與倫比的魅力,就是文學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現真實的魅力。
接下去我再說些輕鬆的。我先說了一個沉重的大屠殺紀念館和一個悲慘的集中營的故事,此後是兩個輕鬆的笑話和兩個與我有關的故事,接著是這三個令人不安的故事。為了最後的輕鬆,我拜訪了魯迅和莎士比亞,這兩位都是有時候沉重有時候輕鬆,毫無疑問,這兩位都是知道人是什麽的作家。
魯迅的《狂人日記》裡的例子我在中國舉過多次,莎士比亞的例子我也舉過,現在再次舉例是為了講述一個我自己的經歷。
《狂人日記》裡的那個精神失常者上來就說:“不然,那Z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我怕得有理。”我以前說過,魯迅寫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有些作家為了讓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寫了幾千字上萬字,應該說是盡心盡力了,結果人物還是正常。再來舉個莎士比亞的例子,他的《維洛那二紳士》裡面有一出幕外戲,一個鼻青眼烏的人牽著一條狗走到舞台中央停下,開始埋怨狗:“唉,一條狗當著眾人面前,一點不懂規矩,那可真糟糕!按道理說,要是以狗自命,做起什麽事來都應當有幾分狗聰明才對。可是它呢?倘不是我比它聰明幾分,把它的過失認在自己身上,它早給人家吊死了。你們替我評評理看,它是不是自己找死?它在公爵食桌底下和三四條紳士模樣的狗在一起,一下子就撒起尿來,滿房間都是臊氣。一位客人說:‘這是哪兒來的癩皮狗?’另外一個人說:‘趕掉它!趕掉它!’第三個人說:‘用鞭子把它抽出去!’公爵說:‘把它吊死了吧。’我聞慣了這種尿臊氣,知道是克來勃乾的事,連忙跑到打狗的人面前,說:‘朋友,您要打這狗嗎?’他說:‘是的。’我說:‘那您可冤枉了它了,這尿是我撒的。’他就乾脆把我打一頓趕了出來。天下有幾個主人肯為他的仆人受這樣的委屈?”
魯迅和莎士比亞描寫精神失常的人物時,說話都是條理清楚,他們是通過話裡表達出來的意思顯示出這個人物已經失常的精神狀態。不少作家描寫精神失常的方式都是讓人物說話語無倫次,而且中間還沒有標點符號,這已經成套路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語言黑壓壓地擺在那裡,這些作者以為用幾頁甚至十幾頁人物自己不知所雲的說話就可以讓讀者感受到這個人物精神失常了,這只是作者的一廂情願,如果讀者感覺到有人精神失常的話,也不會認為是作品裡的人物,而是懷疑這個作者精神失常了。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我去意大利的時候,邀請方給我安排了一個特別的活動,讓我去維羅納地區的一家精神病醫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進行一場文學對話,就是莎士比亞的《維洛那二紳士》裡的那個地方。*邀請方給我安排的翻譯很緊張,不過她看上去還是比較鎮靜。她開車來旅館接上我,在去精神病醫院的路上她說了幾遍“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活動”,她說院方保證參加活動的都是沒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者,她這話是在安慰我,不過聽上去更像是在安慰她自己。我開玩笑說,院方保證的只是過去沒有出現過暴力傾向的,並不能保證今天不出現。她聽後“啊”的叫了一聲,然後又說“這個活動太奇怪了”。我們來到精神病醫院的門口,應該是監控攝影頭看到了事先登記過的車牌號,大鐵門徐徐打開,我聽到機械的響聲。車開進去後我看到了一個很大的花園,裡面有幾幢不同顏色的建築,我們在最大的那幢前面停下,我心想這應該是主樓。
我們先去了院長辦公室,院長是一位女士,她握著我的手說,你能來我們太高興了。然後她請我們坐下,問我們要咖啡還是茶,我們兩個都要了咖啡。喝咖啡的時候,院長說每年都會有一位作家或者藝術家來這裡,她說病人們需要文學和藝術。院長問我,你在中國去過精神病醫院做演講嗎?我說沒有。
喝完咖啡,我們去了一個會議室,裡面坐了三十來個病人。我們走到裡面的一張桌子後面坐下,面對這些病人,院長站在我的左側,就像其他地方的文學活動一樣,院長介紹了我,我不記得當時這些病人鼓掌了沒有,我的注意力被他們直勾勾看著我的眼睛吸引了過去,院長說話的時候我拿出手機拍下了他們,我感覺他們的目光鐵釘似的瞄準了我的眼睛,好在後面沒有榔頭。院長介紹完就出去了,會議室的門關上以後,我注意到一個強壯的男人站在門那邊,用嚴肅的眼神審視屋子裡的病人,他沒有穿白大褂,我心想他不是醫生,可能是管理員。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我第一次置身這樣的場合,不知道怎麽開始,我的翻譯小聲問是不是可以開始了,我點點頭對他們說,請你們問我一些問題吧。翻譯過去以後仍然是沉默,我繼續說,文學的問題和非文學的問題都可以問。等了一會兒,第一個問題來了。一位女士問,你是意大利人嗎?我搖搖頭說,我是中國人。接著一位男士問我,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我簡單地介紹了自己,一個來自中國的作家,過去在中國的南方生活,現在住在北京。此後就順利了,他們問的都是簡單的文學問題,我的回答也很簡單。沒有人問到我的作品,我知道他們沒有讀過我的書。我注意到他們提問時幾乎都是將身體前傾,像是為了接近我,我回答後他們的身體沒有回到原位,前傾的姿態一直保持了下去。這個活動進行了大約四十分鐘,最後提問的是那位站在門邊的強壯男人,此前他給我的感覺是一直在監視這些病人,所以我認為他是醫院的管理員。他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問我在中國做一名作家怎麽樣?我說很好,可以晚上睡覺,也可以白天睡覺,作家的生活裡不需要鬧鐘,自由自在。他聽完後嚴肅地點了點頭,然後又問了第二個問題,你生活在意大利哪個城市?我心裡咯噔一下,這個我一直以為是管理員的人竟然也是病人,這個屋子裡除了我和翻譯,全是病人,而且門關著,最強壯的那個還是守門員。我回答了最後一個問題,我生活在中國的北京。
外面有人推門進來,是院長女士,活動結束了。往外走的時候我問翻譯,你能聽懂他們說的話嗎?翻譯有些驚訝,她說當然能聽懂,他們說的是意大利語。她理解錯了我的意思。我繼續問她,他們說話有沒有顛三倒四?她說,他們說話很清楚。我的翻譯不知道,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前面舉過的魯迅和莎士比亞的兩個例子。
院長送我們到門外,她再次向我表達了感謝,感謝之後是詢問我接下來在意大利的行程,她對我此後要去的每一個地方都是讚美一番,所以我們在那裡站了一些時間。那時候應該是午飯時刻,剛才和我坐在一個屋子裡的這些病人一個個從我面前走過,有的對我視而不見,有的對我點一下頭。我注意到一個男人拉住了一個女人的手,還有一個男人摟住了一個女人的肩膀,他們看上去都是五十來歲的年紀,親密無間地走向他們的食堂。好奇心驅使我問了院長一個問題,住在你們醫院的病人裡有沒有是夫妻的?院長說沒有。
我們上了車,這次開到大鐵門那裡,門遲遲沒有打開,我的翻譯有些焦慮,我再次開玩笑說,我們可能要留在這裡了。翻譯放在方向盤上的雙手立刻舉了起來,她叫道:“不要。”然後我們聽到機械的響聲,大鐵門正在慢慢打開。我們離開精神病醫院後,翻譯一邊開車一邊對我說:“我很緊張。”她一直很緊張,此前沒有說是為了不影響我,我們離開精神病醫院後她吐露真言。
後來的行程裡,我不時會想起維羅納那家精神病醫院的文學活動。我此前覺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個黑暗的無底洞裡,但是那兩對男女親密走去的身影改變了我的想法,因為那裡有愛情。那兩個男的和那兩個女的,他們可能各有妻子和丈夫,如果是這樣,他們的妻子和丈夫應該會定期來看望他們,可能中間的某一個某兩個甚至某三個和某四個已經離婚了,或者從來沒有過婚姻,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裡有愛情。
-版權聲明-
文章來源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為傳播而發,如有侵權,請聯繫後台,會第一時間刪除,文中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蒼山洱海邊,還有一間野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