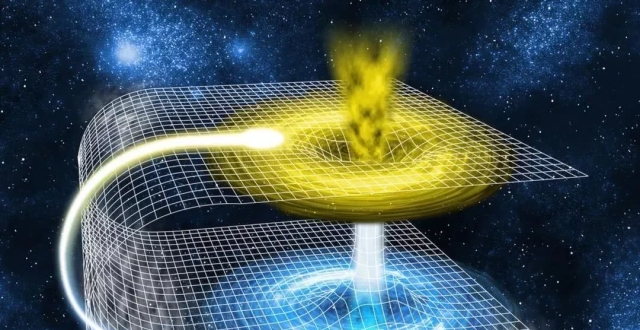布萊克有詩句:“在一粒沙子裡看見宇宙,/在一朵野花裡看見天堂,/把永恆放進一個鍾點,/把無限握在手掌。”“一粒沙子”是輕的,但“宇宙”是重的;“一朵野花”是輕的,但“天堂”是重的。散文的輕重關係,似乎也是這樣:在它所記述的事情和人物裡面,也許僅僅是一些常識,但作家要提供一個管道,使讀者能從常識裡看見“永恆”和“無限”。也就是說,散文的話語方式可以是輕的,但他的精神母題則必須是重的,她的裡面,應該隱藏著一些可供回味的心靈秘密。by-謝有順
我一直無法忘記下面這段文字:
這時,坐在我身邊的小喇嘛突然開口說:“我知道你的話比師父說的有道理。”
我也說:“其實,我並不用跟他爭論什麽。”但問題是我已經跟別人爭論了。
年輕喇嘛說:“可是我們還是會相信下去的。”
我當然不必問他明知如此,還要這般的理由。很多事情我們都說不出理由。
……
“其實,我相信師父講的,還沒有從眼前山水中自己看見的多。”
我的眼裡顯出了疑問。
他臉上浮現出一絲猶疑的笑容:“我看那些山,一層一層的,就像一個一個的階梯,我覺得有一天,我的靈魂踩著這些梯子會去到天上。”這個年輕喇嘛如果接受與我一樣的教育,肯定會成為一個詩人。
我知道,這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對方也只是說出自己的感受,並不是要與我討論什麽。這些山間冷清小寺裡的喇嘛,早已深刻領受了落寞的意義,並不特別傾向於向你灌輸什麽。
但他卻把這樣一句話長久地留在了我的心上。
這是作家阿來在一篇題為《離開就是一種歸來》的散文中的一段文字。這篇散文,你在初讀的時候,會覺得一切是這麽平常,並無多少意外的驚喜。但是,如果你多讀幾遍,慢慢的,你就會發現,小喇嘛的那段話居然使一個對多數人來說懸而未決的信仰問題瞬間就釋然了。——這難道不是一種文字的境界嗎?把一層層的山比作“階梯”,並說“我的靈魂踩著這些梯子會去到天上”,如此令人難忘的表達,使“我”以上的爭論變得毫無意義——信仰更多的是指向世界的奧秘狀態,是生命的一種內在需求,它並不能被理性所證明或證偽,因此,辯論對於信仰者來說是沒有意義的;當小喇嘛說出“我的靈魂踩著這些梯子會去到天上”時,他已經悄悄地從辯論的理性漩渦裡出走,來到了生命直覺的現場,或者說,大自然的奧秘輕易就製服了他心中還殘存的疑問。

《離開就是一種歸來》出自《語自在》
阿來記下了這個難以言說的精神奇跡。它也許只是一句話,但作家的心靈捕獲到這句話的分量時,他的文字就與這句話中廣闊的精神太空緊密相聯,散文,也就在這個時候離開了輕淺的外表,成了內在心靈的盟友。這使我想起詩人布萊克的著名詩句:“在一粒沙子裡看見宇宙,/在一朵野花裡看見天堂,/把永恆放進一個鍾點,/把無限握在手掌。”“一粒沙子”是輕的,但“宇宙”是重的;“一朵野花”是輕的,但“天堂”是重的。散文的輕重關係,似乎也是這樣:在它所記述的事情和人物裡面,也許僅僅是一些常識,但作家要提供一個管道,使讀者能從常識裡看見“永恆”和“無限”。也就是說,散文的話語方式可以是輕的,但他的精神母題則必須是重的,她的裡面,應該隱藏著一些可供回味的心靈秘密。
阿來散文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將散文的輕與重的關係處理得非常恰當。本來,像他這樣的藏族作家,寫起宗教和西藏,是很容易走向神秘主義的,話語方式上也很容易變得作態,正如其他一些作家那樣。但阿來沒有這樣,因為他對自己所寫的東西已經了然於胸,它們已經內化到了他的生活之中。我記得他專門寫過一篇散文,叫《西藏是形容詞》,目的是為了還原真實的西藏。他說,“西藏在許許多多的人那裡,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應該有著實實在在的內容的名詞。”“一個形容詞可以附會了許多主觀的東西,而名詞卻不能。名詞就是它自己本身。”“當我以雙腳與內心丈量著故鄉大地的時候,在我面前呈現出來的是一個真實的西藏,而非概念化的西藏,那麽,我要記述的也該是一個明白的西藏,而非一個形容詞化的神秘的西藏。”
——阿來對西藏的態度,其實也可看作是它的散文立場:他反對概念化和附會,追求“以雙腳與內心丈量”故鄉大地。比如西藏,這本是一個“重”的命題,但太多的膜拜者已經把它變成了一個過於沉重和神秘的地方,真實的西藏實際上已經遠去。這個時候,寫西藏就不該使它變得更“重”,而是要從西藏的神秘裡超越出來,走進西藏的日常生活,走進西藏的人群,重新找回西藏的真實。——可以說,此時,本真的西藏、不神秘的西藏反而成了西藏真正的“重”之所在,因為這樣的“重”不是附會上去的,而是從裡面生長出來的。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