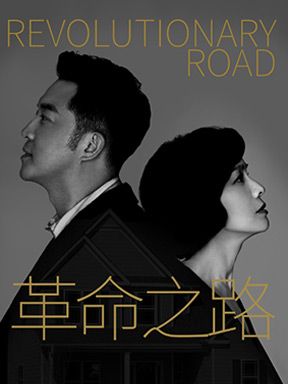讓文藝成為一種生活
王朝柱:為中國革命寫一部“大書”
文 | 路斐斐

2019年,北京香山,78歲的王朝柱正在為他最新編劇的一部電視劇劇本忙碌著。去年,由他編劇的講述1949至1954年新中國誕生前後歷史風雲的電視劇《換了人間》在央視播出,今年,他又開始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劇本進行各種後期相關工作了。考慮到身體,這兩年他的工作節奏放緩了些,但在重大革命題材領域的影視創作中,王朝柱依然令人敬佩地保持著旁人難以企及的創作速度和創作質量。幾十年來他獨居於香山腳下保持著有規律的寫作,一是怕家人時時看著自己忙碌而心疼,二是怕自己的創作受外界干擾而放鬆。從1964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算起,涵蓋小說、話劇、電影及至電視劇,王朝柱將自己至今以來的主要創作歷程分為兩個階段:前20年,以《李大釗》等作品為發軔,完成了近20部長篇史傳文學的創作;後20年,從《長征》等影視劇的創作開始,將史詩品格融匯到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劇本的創作中,將自己的名字與《辛亥革命》《尋路》《長征》《延安頌》《解放》《換了人間》《永遠的戰友》等一系列影視劇作品及其所反映的中國近現代革命史的藝術化呈現與表達緊緊聯繫了起來。從農村到城市,從音樂學院作曲系的普通工農兵學員,到後來中年轉行,以一已之創作成就了業內熱議的“王朝柱創作現象”,其人生軌跡與中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走向不謀而合。
以手中筆寫時代與歷史的真實
記 者: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您幾乎同時期創作出版了《李大釗》《龍雲與蔣介石》等幾部很有影響力的史傳文學。然而在此之前,您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後最早培養的大學大學生,就讀的卻是當時頗為“洋氣”的中央音樂學院,學習專業作曲,期間不僅發表過原創歌曲,後來還曾作為惟一一名青年人被選入了1984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35周年而特別創作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中國革命之歌》的九人創作小組(其中包括石祥、喬羽、魏風、時樂濛等音樂大家)。您是在什麽情況下決定轉向文學及影視劇創作的?

《永遠的戰友》劇照
王朝柱:上世紀50年代,15歲的我憑一支笛子和粗通的樂理,考入了當時的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後又順利升入音樂學院本科,跟隨當時的趙渢院長等學習西方交響樂。作為一名酷愛民族音樂的農村學生,我是當時音樂學院裡惟一討過飯的窮學生,身上有不少土氣,在音樂學院顯得頗為“另類”,但卻並未因此受到另眼相待,反而因為特殊的工農兵學員的身份受到了師友們的很多關照。雖然後來因為歷史的種種因緣我最終在畢業之後放棄了我所喜愛的音樂創作事業,但在音樂學院的學習和生活對我一生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除了收獲了珍貴的友誼,積累、開拓了很多方面的閱讀、學習外,我對音樂的理解和熱愛,以及音樂作為一種最為重視內在結構的藝術形式,對我後來畢生從事的文學及影視劇的“史詩性”“音樂性”創作而言,都有很多獨特的啟發。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使我們在音樂學院的學習、生活也受到了影響,學院的很多師生員工因此被下放到保定、張家口、天津等地的農村參加“勞動改造”,我也未能例外。但那時年輕,又興趣廣泛,一方面也參與著社會運動,一方面也暗自相信,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批判的人們一定會被平反,也始終莫名相信一切終會過去。於是,白天我們同大家一起參加勞動改造,中午我卻不想休息,就坐在湖邊柳樹下讀書也寫些東西,做了大量的積累。等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到上世紀80年代,我已開始在很多地方嘗試發表作品了。直到改革開放的到來,隨著西方各種文化思潮的湧入,面對我們民族曾經遭遇的一些磨難,社會上開始出現了一些尖銳的聲音,突然而至的紛繁現狀,使我也陷入了極大的茫然和憤慨,不光是在我後來被調入的《中國革命之歌》創作小組,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聽到一些激烈的爭論,我更加感到,我所鍾愛的音樂已難以表達內心的複雜了,於是便暗自決定“棄樂從文”,想以我手中的筆把我自己眼中所看到心中所感受到的時代與歷史的真實以及我自己的看法統統都寫出來。
記 者:1989年您出版了72萬字的小說《李大釗》。自此,以大部頭寫史論道幾乎成了後來您的許多史傳文學的“標配”。您曾說過,即使同樣的史料在不同人的眼中也會得出不同的看法,那麽您研究歷史、書寫歷史人物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又是什麽?
王朝柱:1989年李大釗同志誕辰100周年前夕,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歷時8年寫就的長篇傳記文學《李大釗》,並由出版社和《光明日報》聯合舉辦,在人民大會堂為這部書的出版特意舉行了座談會,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胡喬木同志出席了這次座談會並高度評價了這本書。那天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大釗之子李葆華、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以及潘峰、張明遠、劉白羽、李瑛等老同志。關於這本書的出版前後,我的責編也是我後來一生的好朋友李碩儒同志後來還專門寫文進行了回顧,並特別記敘了他第一次見到我這個名不見經傳、頭頂半舊的鴨舌帽、身上裹著綠色舊軍大衣的作者之情形。當時他收到的書稿還有我同時投遞的《諜海奸雄——土肥原賢二秘錄》,那本書的文獻價值和社會價值同時也得到了他的肯定,這是後話。在當時僅以手稿質量而論便下定決心出版也足可見編輯對這本書的認可與重視,也證明了我的選擇是正確的。在當時社會上風行著各種解構傳統、解構思想的風潮下,我寫李大釗更重要的是想用這個名字去寫一個時代。李大釗是河北人,而我也是河北人,是晉察冀的孩子。是歷史讓我寫李大釗,我是在寫李大釗,我也是在寫那不能被歷史淹沒的20萬晉察冀英雄人民。
可以說,在我一生最痛苦、最難過的這段時間,我的創作卻出現了第一個豐收期:我參加創作的話劇《決戰淮海》上演了,我寫的電影《龍雲和蔣介石》公映了,與朋友合作的電視劇《巨人的握手》等播出了,除了《李大釗》,我的長篇小說《愛的旋律》《女囚徒》等也相繼出版了。我還記得大評論家馮牧同志對此這樣評價過:“王朝柱一腳就把作家的大門踢開了!”
寫一部中國革命的“大書”
記 者:1996年,您任編劇之一的電影《長征》上映,5年後同名電視劇作為您在同時期影視劇創作的代表作之一,一經播出便因藝術特色鮮明、主題深刻宏大引起了社會很大反響,被評論界譽為當時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高峰之作”。作為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和藝術創作的重大題材,從1951年李伯釗的歌劇《長征》算起,幾十年來長征在舞台、銀幕、熒屏上已有過各種不同形式、不同視角的展現,您的創作在當時是如何打開視野的?
王朝柱: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聽著長征中的一個個傳奇故事長大的,對長征精神我從小就懷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崇敬之情。關於長征,1998年我曾出版過近70萬字的長篇小說《毛澤東周恩來與長征》,還寫過一個留有很多遺憾的電影文學劇本《毛澤東在長征中》,後來被拍成電影《長征》(1996年),電視劇《長征》當時的創作背景是為了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在中央文獻研究室、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等部門有關專家多次論證和推動下,決定由我出任編劇,由中央電視台投拍這部電視劇。

電影《長征》劇照
《長征》這部劇的創作中融入了我對影視劇史詩品格的很多思考。首先在劇作結構上,我心中的《長征》是獨特的。後來在《長征》文學劇本的前言中我曾寫過這樣一句話:“我希望大型電視連續劇《長征》能向著大氣磅礴、蕩氣回腸的美學品格前進。”近半個世紀以來,國產影視劇雖然對長征的每個局部事件幾乎都做過取材,但卻還沒有一部全方位反映長征的史詩問世。接到任務後,我重新審視了中央紅軍的這367天,將我對音樂的理解融入了整部劇的創作中,將整個長征過程看作是紅軍用生命寫成的4個樂章的交響曲:從1934年4月廣昌保衛戰打響到之後的湘江血戰,從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重回指揮崗位領導紅軍取得一系列勝利,再到兩大紅軍主力會師後又陷入的危機,直到臘子口戰役的勝利結束。在這部交響曲裡,我既寫了紅軍的慘敗與犧牲的慘烈,也寫了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的悲壯,同時以極大的勇氣寫了黨內錯綜複雜的矛盾以及李德、博古、周恩來等同志應負的歷史責任;不僅寫了毛澤東四渡赤水的用兵如神,也寫了他指揮土城戰役的失誤等。所以後來《長征》能獲得很大成功,使觀眾產生強烈共鳴,我認為與當時的創作環境下,整個劇作呈現出來的史詩氣質以及對重大歷史事件、領袖形象的真實展現和具有突破性的塑造是有很大關係的。
特別是在人物塑造上,電視劇《長征》中出場的敵我雙方有名有姓的政治家、軍事家多達百人,我以長征作為中國近代政治家表演的舞台,再現了各種各具特點的人物形象,其中最重要也最不易有所突破的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劇中我通過兩次激烈的黨內鬥爭,重塑了一個由楚文化孕育而成的、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毛澤東形象,既寫出了毛澤東敢於向強權做鬥爭的一面,也寫出了他面對恃強自傲的張國燾大義凜然的另一面,使一個新的毛澤東形象出現在了螢幕上;在對周恩來藝術形象塑造上,我也抓住了人物特有的心理——在清醒中的痛苦——來推演劇情,深化人物性格,因此這一個新的領袖形象在當時得到了很多觀眾的接納和認同。
記 者: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10年間,您以花甲之齡在影視劇創作領域特別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創作方面表現出了令人吃驚的速度和密度,以電視劇《長征》為節點,往前有《周恩來在上海》(1998)、《開國領袖毛澤東》(1999),往後從《延安頌》(2003)、《船政風雲》(2007)、《解放大西南》(2010)等,您的劇作在歷史的經度和緯度上,為觀眾帶來了一個豐滿而多元的時空呈現,因此也有評論家稱您為學者型作家編劇。您是如何保持如此繁盛的創作的?
王朝柱: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至少10年多的時間裡,我在影視劇創作方面確實保持了一個相對均勻高產的速度。2005年播出的電視劇《八路軍》就寫於近年來我創作狀態幾乎最好的時期,以當時的身體條件可以達到兩天寫一集的創作速度。我寫作的方式可能跟很多人不同,“讀”和“想”的時間往往要超過動筆的時間,一旦想好,大多提筆一氣呵成。所以,可以說當我開始進入從鴉片戰爭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段歷史題材的創作時,我對中國的這段歷史已做好了充分的史料閱讀與研究積累了。包括這其中涉及的中國共產黨、國民黨黨史,共產國際史,國共關係、中日關係等相關歷史,我都做了相對比較系統的研究準備了。這也因為我從很久以前就已下定決心,要以電視劇的形式為中國革命寫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500集的“大書”,並選定孫中山、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領袖人物作為這部大書的主人公。作為這部大書的一部分,2007年播出的由我編劇,以洋務運動、船政興衰為主要內容的重大題材電視劇《船政風雲》,從題材所涉時間來看,實際上才應是這部大書的開篇,而目前我手上這部尚未及投拍的,將反映中國共產黨建黨歷程的電視劇則更接近於大書的結尾。在這部大書裡,我已寫下了很多人,不管是張學良、冼星海,還是李大釗、孫中山,我認為他們的命運,都是中華民族命運的縮影,他們的奮鬥之路,都在從不同的層面、角度折射著中國人民自強不息、走向光明的不懈追求、不懼犧牲的偉大歷程與永遠值得被銘記、禮讚的民族精神與英雄魂魄。
電視劇《長征》之後,我有幸又開始了對表現我們黨在陝北窯洞指揮抗戰過程,並逐步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電視劇《延安頌》的創作。在這部劇以及之後若乾劇目的創作中,我在進一步以藝術創作的形式理清錯綜複雜的歷史過程中,在進一步挖掘並重現包括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在內的延安精神等中國革命歷程中留下的無數寶貴精神財富時,我也繼續遵循著並堅定地實踐著用唯物史觀解讀中國革命歷史、以史詩品格藝術再現歷史的創作理念。
尊重歷史、禮讚英雄,是我的使命與責任
記 者: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以您的文學劇本《辛亥革命》攝製的電視劇《辛亥革命》,被評論家認為是對20世紀以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的全過程、全方位、全景式深刻而又生動形象的藝術展示。兩年後的2013年,由您編劇的另一部電視劇《尋路》也在央視播出。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兩部作品的主題都在於尋路,今天來看,您是如何思考這兩部作品的創作的?

《尋路》劇照
王朝柱:對於一切有歷史責任感的嚴肅作家、劇作家來說,“為什麽而寫、如何才能寫好這部作品”是每次在構思創作一部新的文學、戲劇或影視作品時一定會發出的自問,我時常要經歷這樣長期而又痛苦的深思熟慮,方會動筆。特別是對於這樣兩個題材的創作而言。《尋路》顧名思義就是探尋中國革命之路。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探尋中國革命之路前仆後繼,用生命和鮮血鋪成了一條紅色之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繼承了中華民族這一光榮的革命傳統。
《尋路》選擇截取的歷史長度只有5年,但這5年中,幼年時期中國共產黨懷著一腔救國救民的熱情,在盲目地期望蘇聯模式救中國的錯誤革命道路上,先後經歷了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殺,直到1932年寧都會議毛澤東被剝奪軍權;但同樣也是在短短5年間,儘管依然阻力重重,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還是歷經千難萬險、九死一生,探尋到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歷史給後人留下了太多啟示與一筆了不起的精神財富。所以《尋路》這段歷史是極其複雜的, 在創作上的挑戰也是很大的。在這一點上2011年播出的《辛亥革命》也相類似,在這部劇的創作中,我堅持了兩個基本原則:一要旗幟鮮明地反對社會上曾流傳的否定革命的“告別革命論”,同時禮讚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行者的崇高品格。二也要寫出參加辛亥革命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兩面性,還歷史以真實,還人物以公道。
《辛亥革命》也好《尋路》也好,它們都深刻揭示了一個道理,就是道路決定命運。道路的正確與否,決定著中國革命的勝敗。而正確的道路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通過實事求是的思維方法和思想路線找到的,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是多麽不容易,所以我們更該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同時,我在《尋路》裡也濃墨重彩地張揚了一種革命正氣,我希望今天的人們能以史為鑒,警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在每一位中國人的心中牢牢地豎立起理想和信仰的大旗。
記 者:去年,您創作了講述1949至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後的這段歷史風雲的電視劇《換了人間》。以近80歲的高齡還能以旺盛的精力和腦力深耕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創作,這在中國的編劇界、作家群裡已不多見,多年來您收獲了很多國家級、國際級的最佳編劇獎,還有若乾終身成就獎,未來您還有哪些心願想去實現?

《換了人間》劇照
王朝柱:42集電視文學劇本《換了人間》完稿後,我曾像往常一樣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這部劇原來的名字叫《轉折》,創作早先是受了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振武同志所托,後來得了一場大病,這部劇的寫作就中斷了,再次重啟項目時,做了多方論證,認為原先的創作面有些窄,難以寫出當時我國內政外交等方面的全面轉折,所以後來就重新調整創作,劇名也隨之改為了《換了人間》。《換了人間》講的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之後發生的事情,這部戲的戲魂就是要藝術且形象地反映這一偉大的時代變革,讓今天的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明白新中國是怎樣誕生的, 中國人民為什麽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就是想以宏大的歷史視野, 還有詩人的激情來描述這一偉大的歷史。我目前正在等待手頭這部講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電視劇本的順利投拍,等到2021年這部劇播出,我心中的這500集大書、2000多萬字就算是寫完了。但我並不會停下來,我還會繼續創作沒有寫完的長篇小說。我常講我的創作觀說來簡單就兩點,一是尊重歷史,二是禮讚英雄。這兩點是永遠不會變的,是我身在這個時代,身為一個劇作家、一名作家的使命與責任。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7月26日5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