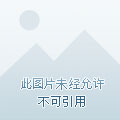第四屆伯鴻書香獎之閱讀獎:《史記》閱讀主題征文活動進行中。今天與讀者朋友們分享的是四川作家林趕秋撰寫《司馬遷能看到怎樣的蜀地風物 》一文——兩千多年的蜀地有著怎樣的風土人情,讓我們通過閱讀《史記》來發現。
在成為偉大的史學家之前,年輕的司馬遷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旅行家了。
“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對多數人來講,都是終其一生的追求,但司馬遷在二十六歲時接受父親遺命開始籌備寫作《史記》之前就已基本完成。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有這樣一段文字凝練而內涵豐腴的自傳:
“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關於這場弱冠之年啟程的、足跡遍布“東南和中原的大旅行”,李長之先生《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的第四章第二節已有詳述,茲不贅。圍繞本文主題,我們隻來說說司馬遷擔任郎中一職之後,他的那次西南之行,尤其是奉使西征巴蜀的一些細節。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二十五歲的司馬遷(我讚成李長之的看法:司馬遷生於公元前135年)奉漢武帝之命出使巴、蜀、滇,這是漢朝經營西南夷大政的重要一環。此前,郎中將唐蒙為了修通“西南夷道”,勞師動眾,引起了“巴蜀民大驚恐”,眼看就要嘩變,蜀郡成都人司馬相如受命前往,好一番書面曉諭、口頭安撫,才算穩定下來。同時,邛、笮(今四川西昌、漢源一帶)等地的首領也歸順了漢朝。
十九年後,司馬遷比他的前輩們走得更遠了,不但到了巴蜀以南,而且還抵達了滇中腹地——昆明(比現在的昆明範圍大)。這一年,漢朝設立了牂柯、越巂、沈黎、文山、武都五郡。至此,“西南的經營才算是更具體化,真正告了一個段落。司馬遷這一次的收獲,除在國家方面不言外,在文學上乃是《西南夷列傳》那篇很有韻致的地理文之產生。後來柳宗元的《遊黃溪記》和《袁家渴記》就都是模擬這篇《西南夷列傳》的。”

在蜀中,司馬遷應該還望見了綿綿“汶山”(即岷山),及“汶山之下”的千里“沃野”,即今之成都平原。後來,他追憶道:
“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禦滇、僰,(容易得到)僰僮。西近邛、笮,(容易得到)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貨殖列傳》)
看樣子,司馬遷與很多古人一樣,也是從褒斜道進入蜀地的。蜀中雖為四塞之地,蜀道雖有上天之難,但棧道千里相連,物資與文化想通往外界,也是勢不可擋的。以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為文明代表的古蜀時期已跟外域有了多樣的交流,何況是繁榮開放的西漢“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時期呢?

當時已遠銷南越國(國都在今廣州)的“蜀枸醬”,出口大夏國(一個中亞古國,位於阿富汗北部)的“蜀布、邛竹杖”(《西南夷列傳》),名揚趙國(戰國七雄之一)的“蹲鴟”(《貨殖列傳》。一種芋頭,其大無朋,像蹲著的貓頭鷹),司馬遷大概也是有所目睹的。
蜀布既然可以出口遠銷,證明在成都市面上已經接近飽和。當時人們常拿“蜀郡之布”與“齊陶之縑”相提並論,要知道,齊國絲織品可是“號為冠帶衣履天下”、流行一時的。

在我國西北居延等地區發現的漢簡上記有:“廣漢八緵布”。漢代織品以織作規格有七緵、八緵、九緵、十緵的分類,近似現代織品多少支紗的說法,體現成本和質量的差異。據漢初法律《二年律令·金布律》,政府為“徒隸”等勞作者提供的服裝,“布皆八緵、七緵”;漢景帝時制度,“令徒隸衣七緵布”;漢代邊防士卒的軍裝也以“七緵布”“八緵布”製作,價格比較低廉。所謂緵,或謂一升,等於麻縷80根,以布寬二尺二寸計算,如果是十緵布,就等於在二尺二寸的幅面上密布著800根麻經。工藝水準之細致高級,可見一斑。
“廣漢”漢初置郡,下轄“廣漢”縣。三星堆就在廣漢,這裡一度是朝廷倚重的手工業生產基地。正史所謂“蜀廣漢主金銀器”、“主作漆器物”,反映漢代廣漢郡“工官”(管理官府手工業的官署)的產業目標似乎主要在於滿足上層社會生活用器的需求。而河西簡文“廣漢八緵布”告訴我們,蜀中的紡織業產品已經形成優勢地方品牌,且可惠及大眾。
最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還是史上第一個遊歷、考察、記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名人。他在《河渠書》裡曾高屋建瓴地寫道:自從大禹治水之後,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兆計,然莫足數也。”

蜀守冰,乃是戰國秦人李冰的官稱。離碓,指的便是當時的都江堰,它可以避免水災、通航行舟、灌溉田地。在《河渠書》的結尾部分,司馬遷回憶說:
“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 ”
這回,他則將都江堰進行了更準確的定位:中國之西蜀岷山之下離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