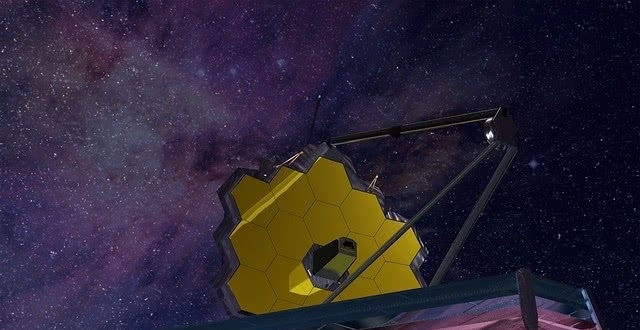作者丨[英]威廉·法爾布雷斯
近日,據上海發布報導,上海天文館
(上海科技館分館)
項目工地已正式復工。該工地位於浦東新區臨港大道與環湖北三路口,距離軌道交通16號線滴水湖站約700米。它包括1幢主體建築,以及青少年觀測基地、大眾天文台和魔力太陽塔等附屬建築,建成後將成為全球建築面積最大的天文館,預計於明年開放。

上海天文館項目工地。
作為上海天文館的設計方,Ennead建築設計事務所設計合夥人托馬斯·黃表示:“在國際獎項中屢獲殊榮的上海天文館設計象徵了時空一體的思維和創造力:現代化、前瞻性的建築設計和歷史文脈相接,在中國從古至今天文研究的豐厚積澱中,映射出中國對未來宇宙探索的雄心壯志。蘊涵歷史文脈的‘軌道’式設計和天文館本身的科研目的傳遞出超越科學本身的內容:在浩瀚、未知的宇宙中,作為人類所存在的意義。”
建築師威廉·法爾布雷斯為天文館寫下了一本“傳記”。天文館作為大部分人童年記憶的一部分,它究竟從何而來?它是怎樣模擬太陽系和宇宙,怎樣隨著天文學的發展而變化?它的內部和外部結構之間有著何種聯繫?對於現代天文館來說,天文學和宇宙學上的進展如何影響天文館?這些問題,都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答案。以下內容節選自威廉·法爾布雷斯所著的《天文館簡史:從星空劇院到現代天文館》,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天文館簡史:從星空劇院到現代天文館》,[英]威廉·法爾布雷斯著,朱桔譯,中信出版社·鸚鵡螺2019年11月版。
星空劇院的演示沒有闡明當時天文學的複雜性
讓我們回到簡單得多的埃及太陽女神努特的時代。她裝飾著星辰的軀體覆蓋了地球的表面。她在傍晚吞下太陽,又在清晨再次生下它——這是對人類靈魂無盡轉世輪回的表現。諸如此類的概念,哪怕本質上不可捉摸,也能以壁畫這種法老墓中與女神的神話相匹配的形式被闡釋。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對夜空的景象,哪怕這一理念背後隱含的複雜性在當時只被祭司們所參透。
鮑爾斯費爾德位於耶拿的天文館有其自身的簡單之處。它能表現行星系統圍繞太陽的運動,雖不及努特的神話有魅力,但每個人都能理解。星空劇院的演示模擬了觀察者在晴朗夜空中所能看到的景象,但沒有闡明當時天文學的複雜性。這些問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觀察者,比真實的夜空這一簡單景象要深遠得多。天文館圓頂的結構適用於具有明確邊界的太陽系的概念,複製了從地球看到的真實夜空景象。在一段短暫的時期中,天文館建築的外部和內部可以屬於同一個系統。
但時至今日,我們需要考慮不計其數的宇宙現象,它們難以與任何有限的建築空間相對應。這些事物通常自身就缺乏清楚的形態,或根本不存在於我們的視野範圍之內。這份名單以特定的天文學韻律延續著——黑洞、褐矮星、類星體、脈衝星、宇宙線、不同“味”的中微子 、大質量弱相互作用粒子
(WIMP)
、不確定性原理、微擾理論、蟲洞、白洞、軸子、暗流體、狄拉克海、外星人通信、多重宇宙以及其他許多在這一科學猜想恣意發散的領域中目前仍僅存在於概念上的事物。

上海天文館。圖片來自Ennead建築設計事務所官網。
天文學及相關的宇宙學和天體物理學成為各類潛在有趣現象出現的絕佳場所,好比那些中世紀天文學家提出來填充天空中空餘位置的精彩的動物和人類形象,或者文藝複興時期宇宙學家假想的各個等級的天使以及其他天上的存在。這些現象中有許多源自當代科學的理論主張,但沒幾個能用裸眼在地球表面觀測到,絕大多數都需要運用極其精密的儀器探測、研究並解讀。我們幾乎什麽都看不到,因為這些事物過於遙遠,並且當中許多本來就不可見。可見的和純粹物質性的存在漸漸被貶為了次要角色,因為宇宙如今在本質上被認為是不可見且無形的。
現在的天文學家推測
(但無法真的確定,因為理論和反理論皆發展迅速)
暗物質和暗能量在宇宙構成中的佔比遠超 90%。因此,我們人類甚至不是由與宇宙的絕大部分相同的物質組成的,我們或許只是一個大得多的故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這一推斷的影子能追溯到詩論和貌似早已被拋棄的遠古神話。
天體物理學家弗蘭克·克洛斯
(Frank Close)
在《虛無》
(Nothing, 2009)
一書中,對比了現今為分辨什麽存在而什麽不存在或可能不存在所進行的探索與《梨俱吠陀》中的古老經文:“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存在的/黑暗被黑暗所掩蓋/它變成的被虛空所包圍。”天文學的精確性正逼近神秘詩論的模糊性。一座闡釋虛無原理的天文館會是個有趣的提案。

蔡司投影儀投影出的火星和木星軌道,1996年。
天文學和宇宙學上的進展如何影響天文館?
從地球表面看到的夜空景象一直以來都是天文館傳統意義上的出發點,但夜空在漸漸被遮蔽。2016 年6月,意大利光汙染科學技術研究所和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一項聯合研究指出,由於光汙染,60%的歐洲人及80%的北美洲人無法再分辨我們星系的光帶,而世界上超過30%的人無法再分辨銀河。來自路燈和其他人造光源及照明設施的光線直達夜空,被大氣層中的水滴反射從而產生一種“天光”。如果能關掉城市裡和高速公路旁的所有電燈,這種光汙染便會減輕,這樣的問題從奧斯卡·馮·米勒的時代就開始逐漸顯現。
雖然我們在夜空的視野不斷縮小,但太空探測器正以驚人的精度觀測到越發遙遠的事物。1990年,哈勃太空望遠鏡在推遲多年後發射了,它是第一個能夠從地球大氣層之外進行觀測的望遠鏡;1992年,宇宙背景探測者衛星開始研究來自大爆炸的異塵餘生; 1997年,卡西尼號探測器被發射向土星,它的著陸器惠更斯號於 2005年降落在土衛六上;2012年,觀測天文學家使用夏威夷的凱克望遠鏡提供了黑洞存在的第一份證據;2015年,13億年前兩個黑洞合並產生的引力波被位於路易斯安那州和華盛頓州的雷射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
探測到;2017年,旅行者2號探測器正在接近星際空間,而朱諾號探測器已經穿過了木星極不穩定的磁場並開始了它37圈繞軌計劃的第一圈。
這些探測器能向地球發回高分辨率的圖像,並對其視場進行可視掃描。但它們也受到限制。不斷膨脹的宇宙中有一些現象距離我們太過遙遠,來自那裡的光線還來不及到達我們這裡。這意味著,假設光速是絕對的,我們無法從地球上看到這些現象。可見的宇宙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限制。
這些天文學和宇宙學上的進展是如何影響天文館的呢?天文館面對的不再是相對簡單的太陽系,它現在必須考慮到不斷膨脹的宇宙,其絕大部分超出了我們的可見範圍。天文館可以沿各種道路前進,每一條都指向不同的方向。它可以僅僅是一種展示陳舊的天文學理念並重複著常見的節目的博物館,有魅力但越來越不切題,就像數十年來一再上演觀眾耳熟能詳的劇目的劇院一樣。它可以成為一種模仿流行太空電影中的特效的天文影院,例如《地心引力》
(Gravity,2013)
、《星際穿越》
(Interstellar,2014)
,乃至《生命之樹》
(The Tree of Life,2011)
中以蠟和油製作出的令人著迷的宇宙模擬動畫。它可以與宗教和精神性這些在傳統上專注於可見之物以外的存在的概念相聯繫。它也可以更加技術化,隨著數字投影儀的出現,天文館能夠適應技術的不斷進步,而計算機強大的存儲能力,也使得現代天文學所需的越來越複雜的圖像能夠被投射到半球形銀幕之上。隨著現今智能手機功能越發強大的潮流,人們或許會好奇,天文館是否也將在不久的將來變得個性化,創造出個人版本的數字天空。
事實上,這當中的每條路徑都有天文館選擇,不同的路線也常常交織在一起,就像不同類型的戲劇
(神聖、粗俗、直覺戲劇等)
也會相互交錯混雜。不過,幾乎所有在天文館中上演的節目都具有社會性,都是一大群人聚在一起欣賞點點星光浮現的景象。隨著燈光漸暗、恆星戰役出現,他們不可避免地發出驚呼和感歎,就連當下認為自己早已熟知這一切的這一代人也不免如此。
投影技術的迅速發展改變了天文館演出的本質
隨著計算機科技的迅速發展以及存儲和投影極大量信息的能力的實現,天文館展望宇宙的方式發生了巨變。在我們這個時代,數字投影儀提供著相當於20世紀20年代鮑爾斯費爾德為當時局限得多的模擬世界帶去的效果。
無所不能的計算機一向是科幻作品的最愛,它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出現在天文館中,並往往與多年來最受歡迎的宇宙大災難的故事聯繫在一起。艾薩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的短篇故事《最後的問題》
(The Last Question,1956)
中兩者皆有登場。故事中,兩位穿著傳統的白色實驗服的科學家討論著宇宙的終結:
“我明白,”阿德利說,“用不著大喊。太陽完蛋了的時候,其他恆星也將不複存在。”
“它們當然不在了,”盧波夫嘟囔著,“一切都開始於最初的宇宙爆炸,不管它是什麽,一切也都將在所有恆星熄滅的時候結束。”
兩位科學家詢問一台功能強大的計算機,是否有降低宇宙中熵的方法——不斷增加的熵最終會令一切生命走向終點。計算機回答道:“現有信息不足以得出有意義的答案。”同樣的問題在超過百萬年的時間中被一再重複,而答案一直不變。終於,在宇宙滅亡的一刻,這台最終得到了宇宙裡所有能量的計算機突然閃現出早已消失的人類無法聽到的回復:“‘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整個傳奇性的故事再次開始。《最後的問題》是美國天文館中最受歡迎的節目主題之一。倫納德·尼莫伊作為敘述者的版本在密歇根的亞柏拉罕天文館、紐約的海登天文館,以及埃德蒙頓、波士頓、費城和其他許多地方的天文館中上映,甚至持續至今。不難相信這個故事對運營天文館的人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真正的宇宙終結了,星空表演也結束了,但一台作為機械“宗動天” 的計算機或投影儀,以對光的重生的神聖宣告重新開始了這場宇宙表演。
投影技術的真正進步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它的迅速發展改變了天文館演出的本質。美國馬裡蘭科學中心首次使用了包含6台幻燈片投影儀的全天空系統,其中每一台都帶有特製的廣角鏡頭,分別向從圓頂處劃分的頂角為60度的三角形分區投影,這些區域巧妙地合成一張覆蓋整個圓頂的360度圖像。投射在圓頂上的圖像並不全都與天文學相關,也可以是藝術作品或是氣象狀況,這個圓頂因而可以被用來製造身在他處的幻覺。全天空系統也可以投影建築的圖像,營造出譬如身處聖伯多祿大教堂的圓頂之下或阿爾罕布拉宮的星空大廳之中的感覺。

天文館的雷射表演,德國沃爾夫斯堡,20世紀80年代。
第一台數字式天文館投影儀數位星由數字圖形公司益世發明,並於1983年首先被安裝在弗吉尼亞州裡士滿市的天文館。它能夠將計算機軟體製作出的圖像序列透過一個魚眼鏡頭投影到圓頂上,從而擺脫了之前投影儀機械上的限制。由戲劇中的舞台特技借鑒而來的,所有那些以不同速度移動的精彩燈光和為當時的特效製作的各種幻燈片,如今都被一個簡單的盒子取代了。
這種早期的數字投影儀也有缺點,它們通過一個線框工作,因此只能生成黑白的點和線條。早期的圖像質量也很差,分辨率遠低於其對手模擬投影儀。它們也缺少巨大的蔡司啞鈴形投影儀在圓頂下的氣勢。但數字投影儀發展迅速,各種各樣的製造商不斷生產出細節越發精巧並帶有更高圖像分辨率的投影儀。
1993年,自20世紀20年代以各種形態出現的巨大的蔡司啞鈴形模擬投影儀,已經發展到被稱為“恆星球”的比例更適中的馬克七號。這台機器是一項了不起的技術成就,其內部所有複雜的機械設備都被組合在一個大致呈球形的外殼中。同樣是在1993年,慕尼黑的新德意志博物館天文館將恆星球投影儀投入使用,並配有80台單幅投影儀、6台視頻投影儀以及安裝在機械臂上的雷射發射器。觀眾可以使用座位上的按鈕控制內容。
20世紀90年代,諸如紐約、柏林和慕尼黑的那些高端天文館內的節目結合了幻燈片投影儀、雷射、影片和聲音系統,全部由計算機連接並控制
(因為此時各種投影設備已過於複雜,無法由講解員人工操控)
,生成令人眼花繚亂的特效——飛往銀河系深處的旅程、爆炸的恆星、浩渺的宇宙景象等。
個別時候,伴著重金屬音樂上演的精彩的雷射表演,使這些節目變得像是某種“天文迪斯科”。有那麽幾年,舞台搖滾和天文學的道路並行,形成了中世紀時由行星演奏的球體的音樂的升級版。平克·弗洛伊德樂隊的《月之暗面》
(1973)
在倫敦天文館發表,而發電站樂隊在體育館舉行音樂會時,在發光的行星背景前演奏了他們的純音樂曲目《彗星旋律》。

蔡司宇宙館投影儀。
原始天文館大膽和勇於試驗的精神依然存在
在21世紀初期,一些天文館演變成了令人驚歎的太空娛樂中心,它們既是科學機構又是巨幕影院。當時投影設備十分昂貴,只有紐約市羅斯地球與太空中心和芝加哥阿德勒天文館等資金充裕的天文館才能夠負擔這類節目。如今投影設備要便宜得多,並且能生成高清圖像,這使得數字投影儀幾乎成了天文館中的標準配置。
現在的數字投影儀能夠穿梭時間和空間,從任何視角展現太陽系和星系的景象,並能在微觀和宇觀尺度間縮放。天文館投影儀可以生成任何想要的效果,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可以投影出天文學中任何可視的進展,並提供類星體及黑洞等天體的假想景象。現在的一些天文館投影儀與網絡相連,能夠展示在軌望遠鏡和空間探測器發回的實時圖像,在實質上成為面向大量觀眾的數字天文台。相較於進行模擬表演的傳統使命,在現代天文館中,真實與想象越發交錯。

名古屋天文館,2011年。
然而,天空無法容忍地面上的平庸。原始天文館大膽和勇於試驗的精神依然存在。帶有球幕的現代天文館內部本身並無新奇之處,就像一個相當普通的電影院。但如果不再保留傳統的圓頂,對天文館內部的空間進行改變,又將如何呢?畢竟將圓頂作為人造天空的大致理念可以追溯到霍斯勞王的時代。艾蒂安–路易·部雷在設計他那宏偉的18世紀的圓球時,構想過完全球形的內部空間,但圓球從未被建造。曾經也出現過各種360度天文館的提案,配有能夠將高分辨率的圖像信息投影到球體內部的計算機。
1985年,倫敦的伊恩·裡奇建築事務所提出了一個名為“球體視野”
(Spheriscope)
的方案,計劃建於格林尼治本初子午線不遠處的河岸。建築被設計成一個直徑30米的玻璃球體,其內部是另一個沿橫截面嵌著無反射玻璃地板的鋼製球體。外部的球體由邊緣的外柱支撐。300名觀眾可以躺或坐在玻璃地板上,兩台投影儀
(一台負責上半球,一台負責下半球)
將影像360度投影到球體內部,以產生整體空間的錯覺。
現代天文館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其內部的節目效果,而非它的外部形態。光的投影創造出一個巨大的、沒有確定尺度的空間。這種對空間的去實體化是20世紀早期建築的野心之一,比如當時出現的各種帶有最低限度的內部空間劃分的玻璃建築的設計。天文館的節目更進一步,暗示實體邊界也可能一並消失。觀眾席上的觀眾同時身處於他們的日常生活的空間之內,和看似無邊無際的宇宙之中。
鮮有天文館的外部建築配得上這樣的雄心壯志,它們往往只是適應著某種建築風格的圍牆。在某種程度上,無論半球形內部圓頂裡的空間是什麽樣子,它都能被納入大多數建築形式——球形的、神殿式、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新現代主義或任何當前流行的風格。至於非視覺、非物質的天文學能夠啟發何種天文館建築,則是一個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
雖然沒有天文館有足夠的勇氣追隨球體視野的步伐,創造球形的內部投影空間,許多天文館還是採用了球體作為外部建築形態,令人自然地聯想到行星和其他天體。
以上內容節選自《天文館簡史:從星空劇院到現代天文館》,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英]威廉·法爾布雷斯
摘編丨何安安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