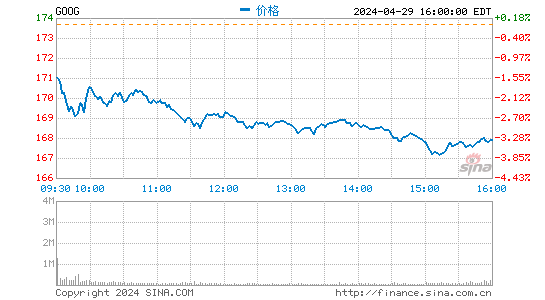2008年,著名的美國科技雜誌《連線》主編克里斯·安德森,在當年6月23日的《連線》上宣稱,“理論終結了:數據的洪流使得科學方法變得過時”。
其時谷歌剛剛十歲,風頭雖健,但那時我們尚相信理論。無論是從描述宇宙,還是到分析人類行為,理論就算不完美,也大致能夠解釋我們所處的世界。但安德森那時預言,在海量數據中成長起來的谷歌,將會使我們終將不再需要理論。

數據的計量部門,從字節到千字節,再到兆字節,那之後的GB、TB,普通中國人就不再熱衷於用對應的中文名字來稱呼它們了,不光因為太大,大到難以想象,中文名字失去了任何意義,還因為這些部門很快就被更大的部門取代,剛剛習慣就已經過時了。如今是PB年代,PB全稱是Petabyte,拍字節。
至此,仿佛完成了量變的積累:千字節時代我們用軟盤存儲,兆字節時代用硬碟,GB、TB有存儲矩陣,到了PB,一切便上到了雲端……就好像從文件夾到文件櫃再到檔案館的類比,終於,我們用完了可資類比的實體。
信息不再是簡單的三維或者四維空間裡的歸類和序列,它變成了不可知維度的統計學概念。谷歌不懂廣告業,甚至從不宣稱自己懂,也不打算去懂,但它征服了廣告業,靠的僅僅是數據,以及,對數據的分析。其基本哲學便是,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麽這個頁面比另一個好,如果接入鏈接的統計數據說它好,那就夠了,任何人類行為理論都是多餘的。誰知道人為什麽要做某件事呢,重點是他做了,而我們又能夠以前所未聞的精確度跟蹤測量。
世界已經由海量數據和應用數學取代了其他一切工具,只要數據足夠大,一切不言而喻。
征服廣告當然只是谷歌以及它所代表的數據年代主宰們的牛刀小試,儘管這已經顛覆了零售業、傳統媒體以及眾多行業,但這不是真正的目標,目標是要取代科學,重建自啟蒙時期樹立起來的知識和思考體系。
科學方法建立在可驗證之假設的基礎上。這些假設模型,大都是在科學家的頭腦中視覺化的系統,然後經過測試、實驗以確定其在現實世界中如何工作。幾百年來科學研究就是這樣在進行。
然而在PB年代的巨量數據面前,這種假設、建模、測試的方式似乎正在逐漸失去意義。拿物理來說:牛頓模型對事實進行模仿,雖然粗略但仍然有用;到了一百年前,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上的量子力學,提供了一個更為優秀的視圖——然而量子力學終究也只是另一個模型,不可避免地也有瑕疵。物理學因而很大程度流於理論猜想,只是現有實驗手段無法對其證偽。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生物學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PB給出了它的答案:只需要相關性。我們不用再去關心模型、假設,需要做的就是直接去分析數據。把數字扔進最大的計算機集群裡,讓統計算法來把科學不能找到的規律找出。
這,成為理解這個世界的全新方法,相關從此取代因果。所以安德森在那篇宣言似的文章結尾處,他說,是科學向谷歌學習的時候了。
又一個十年過去了。如今看來,他好像沒有說錯。算法和大數據在過去這十年間大顯神通,在某些領域比行業專家們貢獻了更多有意義的見解,以及更精確的結果。仿佛忽然之間,我們終於有能力去揭開潛藏在人、機器、商品甚至自然所留下的數據影子和信息軌跡裡的秘密。
但是,我們自己,潛藏在每一個人不知不覺生活軌跡裡的秘密同樣在被谷歌、臉書以及其他互聯網公司大數據揭開。幾乎所有的大零售商都在對銷售數據庫中的海量數據進行分析,這些數據庫通過信用卡、積分卡等與你關聯,目的是對你將來的行為做出一些看似不可思議的預測。前些年就有一個著名的例子,美國明尼阿波利斯一位憤怒的父親,一天衝進零售商塔吉特(Target)商店裡,投訴他們不斷向他十幾歲的女兒寄送嬰兒用品折扣券。事實是,這位父親確實不知道女兒懷孕了,但塔吉特知道。他們通過監測她的購物模式,並將她的數據與幾十億美金銷售的信息作比,推測出了這一看似匪夷所思的結果。
面對矽谷的成就,我們一向認為那是一些改變了現代生活的革新。向前回顧幾十年,有英特爾的集成電路,或者蘋果對個人電腦的重新定義。近十年更有臉書的連接一切,無所不能的谷歌搜索,浩瀚無邊的亞馬遜集市。這些令人歎服的技術帶給我們如此多的便利,同時也帶給我們沒完沒了的電子郵件,讓我們很難專注,也令我們更容易受到傷害——入侵、網絡攻擊、跟蹤甚至更糟。
如果我們需要付出的代價還遠不止這些,並且遠比這些意義更加重大呢?

對於巨頭為我們提供的廉價甚至免費的服務,我們從習慣已經逐漸過渡到不可或缺。但我們很少反過來想,這些廉價和免費的背後,是通過影響我們的思考和行為,使我們不知不覺地接受擺布,那些複雜的算法,針對每一個人進行的精準個性化建議,買什麽商品,看什麽視頻,已經並不真正是我們的決定,而我們得到這些建議的方法——推送到我們眼前的新聞、消費品、電影、音樂——卻一直對我們而言,神秘莫測。
《大西洋月刊》作者富蘭克林 富爾(Franklin Foer)在他2017年出版的《沒有思想的世界》(World Without Mind)一書中指出:“當我們將思考外包給機器時,我們事實上是把思考外包給了運營這些機器的組織。”
啟蒙時代所建立起來的,知識與力量之間的製衡關係,在這樣一個噸位的信息量面前被擊得粉碎。其結果,不僅僅是知識不再有力,它甚至已經不再是知識。一度被當成人類文明史上偉大構建的互聯網,我們期待著通過它,我們人人都可獲得技術層面的啟蒙。但眼前的進展並非如我們最初所料:
今天的我們,發現自己與一個浩瀚無邊的知識庫相連,但我們沒有學會思考。算法成為巫師手裡的魔杖,在知識庫翻雲覆雨,而手握魔杖的數據巨頭,正在成為新時代的總仲裁,比我們自己更知道我們的需求,和我們下一步的決定。原本用來照亮世界的知識,似乎將世界變得一片漆黑。我們舉目四顧,滿是唾手可得的過量信息,但我們越來越不知道該怎樣去理解這個世界。
就像亞馬遜倉柯瑞的取件員,他在貨架間遵循手執設備給他的指令,流利地穿梭來往,但離開這個設備,他即刻茫然失措。因為貨架的設置並不以其是否便於人眼查看為標準:書可能堆在鍋的旁邊,電視可能與兒童玩具擺在一起,僅僅因為這種堆放可能便於機器定位。這是一個沒有計算機輔助便不可能理解的系統,在這裡,人與機器之間傳統的相互關係被徹底顛覆。
亞馬遜的倉庫,正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個縮影。人類肉身變成算法的一部分,其用途僅僅在於,接受指令的同時,能夠移動,這使得他們更容易受雇,也更容易被炒,甚至更容易接受不公正的待遇。但我們所有人都在向這樣一個只能從機器角度來理解的世界妥協。
我們創造了一個徹底藐視我們,不屑於讓我們去懂得它的世界。
與此同時,因為人人都能訪問到無限量的信息和知識庫,人們對知識權威、專家的信任開始崩塌。美國總統川普在挑選顧問時,偏好沒有或者很少從政經驗的;他本人在大選中的勝利,當然更說明了選民對專業知識和經驗的嗤之以鼻。這是近年來上升的反理性主義大浪的一部分,它最大限度地顯現在公共辯論中,情緒對抗推理時,越來越強的優勢,以及真相與觀點和謊言之間界線的越來越模糊。“抵抗知識權威”與將“普通人的智慧浪漫化”聯繫在一起,互聯網在允許更多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獲得更大量信息的同時,也賦予了他們擁有“知識”的幻覺。
所有這一切,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反理性的大漩渦,不僅僅殺死了對專業知識的尊敬,也破壞了常識,阻撓了理性討論,將錯誤信息像流行病一樣傳播。谷歌的無處不在,將信息、知識和經驗三者混為一談。
在此之前,對現代歷史產生最大影響的技術進步應該是15世紀的印刷技術。它使得對經驗性的知識檢索成為可能,取代了儀式形式宣講的必要性。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逐漸取代了宗教時代(Age of Religion),個體的見解和科學知識,取代了信仰作為人類認知的基本標準。信息被系統化地存放在越來越大的圖書館內。

現代世界秩序的一切思想和行為都萌發於理性時代。
但眼下我們面臨的這種全新的,更加橫掃一切的技術革命中,這個秩序正在遭遇劇烈的震蕩,對其後果我們尚無清晰的認知。其結果,可能會像前文我描述的那樣一個依賴於機器的、荒涼冰冷的世界,我們所依賴的機器,又完全由數據、算法來驅動,不受任何倫理或哲學常理的支配。
我們已經生活在其中的互聯網時代,某種程度上已經提出了一些問題和麻煩;而正在降臨的AI,則只會將這些問題和麻煩變得更加尖銳。
啟蒙運動力求讓那之前的傳統真理向更加解放的、注重理性分析的人類理性讓位。而互聯網的目標則是,通過無限增長的數據積累和操作,來對知識賦予某種認可,人類認知的個體性不再具有意義,個體被簡化成數據,而數據統治一切。
互聯網用戶強調檢索及操作信息,而忽略信息的上下文,並對其含義進行概念化。信息因此對知識和智慧形成威脅。淹沒在社交媒體上大量的觀點和意見的海洋中,人們離自省和思考越來越遠。
互聯網和越來越強大的計算能力聚集並分析了海量的數據,前所未有的人類認知開始出現,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各種人工智能工程——看似能夠模擬人類大腦來解決複雜、抽象問題的技術。
對大多數人而言,人工智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是科幻小說中的虛構,直到谷歌的阿爾法圍棋擊敗了世界頂級圍棋手李世石那一天,我們如夢初醒。阿爾法圍棋的驚人之處在於,它沒有經過預編程這個環節。打個比方,它是在不斷的實踐當中“自學成才”,只需簡單將圍棋的規則告訴它,它在與自己的對弈中,從錯誤中學習,實時改良算法。在這個過程中,它飛快地超越了它的人類教練。

這遠遠超過了我們已經熟知的自動化。自動化所處理的僅僅是手段,它通過邏輯或機制來實現一些預定的目標。相反,人工智能所處理的,則是目的。它為自己建立目標。它的成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由它自己塑造的。它在獲取和分析新數據的過程中始終在調整和變動,從而在分析的基礎上尋求自身的提高。通過這樣一個過程,人工智能發育出了過去被認為由人類保留的能力。它所做出的對於未來的關鍵判斷,一部分基於編碼(例如圍棋規則),而另一部分則基於它自己采集的數據(例如下一百萬次棋)。
如果說AI此前尚一直局限於特定領域,如今已經開始著眼於能夠在多領域執行任務的“通用智能”AI。比例正在不斷增長的人類行為,在可見的時間範圍內,將能夠由AI算法執行。但這樣一些通過對觀測到的數據從數學角度進行闡釋而產生的算法,並不能解釋隱藏其下的現實世界。這也正是其諷刺所在,世界在越來越透明的同時,也越來越神秘。
是什麽將這個新世界從我們熟知的那一個區分開?我們該怎樣在其中生活?縱觀整個人類歷史,不同時代的文明有其不同的方式,來對其所處的世界做出解釋——中世紀的宗教,啟蒙時代的推理,19世紀的歷史,20世紀的意識形態。而對於這個我們正在進入的世界,最困難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人類對世界的解釋力被AI超越,社會將不再能夠對其所處的世界做出有意義的解釋,什麽將成為人類的意識?在將人類行為簡化為數學數據的機器世界裡,思想將怎樣被定義?
AI真正的獨到之處,卻並非迄今為止我們所認識和定義的思考,而是前所未有的記憶和計算。但決定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恰恰在於思考。
人文領域的知識分子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這個世界的概念秩序,這次終於顯得力不從心,他們要麽欠缺AI如何運轉的基本知識,要麽被它所能達到的成就驚得目瞪口呆,只剩下崇敬。另一方面,科學領域正一門心思地在探索它在技術方面的潛力;而技術領域則迷醉於它無比燦爛的商業前景。科學與技術這兩個領域的動力都在於進一步將發明和發現向極限推進,而非對它有更深的理解。至於監管,從目前來看,更多地著眼在處理AI應用本身的安全和性能方面,而非探索其已經開始的,對人類生存狀況的大改變。
啟蒙運動從根本上也始於新技術的普及,但我們的時代似乎在向相反的方向推進,它創造了具有潛在的統治一切的能力的技術。因此我們需要從倫理上、哲學上找到某種引領,而這些不是技術極客能夠回答的問題。從前技術總能成功,因為我們都相信“失敗是成功之母”,可以從錯誤中學習。火開始惹禍了,我們發明了滅火器;汽車開始傷人命了,我們開始使用安全帶……但是面對更加強大的技術,例如核武器,生物合成技術,以至超級人工智能,我們不能再從錯誤中學習。因為這學習代價太大,人類付不起。
2013年5月,谷歌在英國赫特福德郡邀請了大約200位特定的客人出席其“時代精神”年會。這一兩天的會議極度保密,僅有少量演講視頻在網上進行了公開發布。那些年間,這個年會的演講者一直以包括美國前總統、皇族、明星等高規格人物著稱,2013年出席的有數位政府首腦,歐洲諸多大企業總裁,英國軍方頭腦,以及最具影響力和煽動性的演講者。一個月後,這次年會的參與者的一部分,包括谷歌CEO埃裡克 施密特在內,再次回到那家酒店參加更為神秘的世界級年度非正式政要聚會,彼爾德伯格會議。施密特為會議以一篇技術帶來解放的頌歌開幕。他說:“我認為我們現在缺了某種東西……發明創造的本質,在谷歌以及在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足以讓我們整個人類更加樂觀。”

在隨後的討論中,他用手機,尤其是帶攝影功能的手機的流行,如何降低了“系統性作惡”的可能來說明,技術怎樣使世界變得更好:如果盧旺達1994年有手機。施密特的,或者說谷歌的世界觀,是相信讓一切變得可見便能改變世界。事實真是這樣嗎?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沒有被製止,真的是因為外界不知情嗎?2012年的審判中,控方出具了1994年5、6、7整整三個月的高清衛星圖片,那裡發生的一切,美國知道、歐盟知道、聯合國知道,災難並沒有因為可見而被消滅。在盧旺達缺位的不是信息,而是采取行動的意願和決心,是良知,這不是技術或者數據能夠帶給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