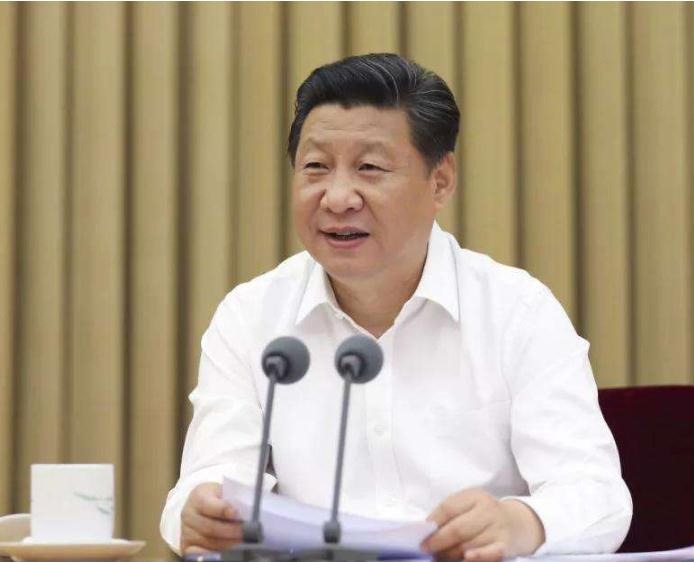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通用解釋,“高峰”一詞一般用來“比喻事物發展的最高點”,文藝高峰意味著文藝發展的“最高點”。在中國文藝發展史上不同的歷史階段曾經形成和存在著不同的文藝高峰。不同的歷史時代因為文藝高峰的存在而彰顯著自身的鮮明文化個性和藝術精神。借用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著名說法,我們也可以認為一代有一代之文藝,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之文藝,或者說文藝總是表現為具體時代、階段的文藝。文藝和時代之間的如此關係說明,文藝的確是在它成為全民族生活世界中的大事的時代達到、發展至它的高峰。從文藝高峰上可以看到那些以往沒有理解和感受到的美的事物,可以領會那些從來沒有得到領會的喜悅和崇高精神的東西。文藝高峰是文藝發展史的產物,也是文藝發展史的主要成果。但文藝發展史的實際也表明,文藝高峰並非短時段的文藝“突起”,文藝總是在經由長時段的醞釀、準備之後達到其高峰的。觀察文藝高峰的築就,需要考慮到文藝長時段的積累和文藝高峰的形成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文藝高峰與中國文藝的累積
中國文藝發展史上的文藝高峰是指文藝成為華夏民族生活世界中的大事的文藝高峰。源遠流長的文藝進程及文藝高峰一方面凝聚了華夏民族精神文化的卓越成果,一方面又將這一成果積澱為華夏民族精神文化在美學方面的共同特徵和原則。這使得文藝發展過程必然地和民族歷史經驗發生聯繫,文藝高峰必然地成為全民族生活中的大事,尤其是精神生活中的大事。“無論在任何社會中,藝術從來都不是純粹從美學內在的觀點來定義的。”假使我們過分看重“美學內在的觀點”對藝術的決定作用,那麽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可能會被忽視。事實上,很難以想象存在沒有社會和時代的藝術。即便單純地探究美的藝術,也需要將其美的力量置於“各種社會行動之模式中”、“含括到一種特定的社會生活模式的情景裡面”。不同的歷史時期存在不同的“社會生活模式”,因而文藝之美要被“含括到一種特定的社會生活模式的情景裡面”得到理解便不得不回溯到歷史長河、回溯到歷史長河的不同階段。領悟文藝高峰亦然。從文藝發展的歷史來看,不同時代既可作為劃分文藝史的界標又可作為辨識文藝高峰的界標——文藝高峰是文藝發展的結果,沒有文藝的發展便沒有文藝的高峰。考慮到中國文藝發展史的實際和長時段性,有必要從縱向的視野探析文藝高峰在文藝發展史上古期(先秦兩漢)、中古期(魏晉至明代中葉)、近古期(明代中葉至晚清)、現當代(五四新文化運動至當代)四個階段文藝高峰的形成原因、狀況、特徵。借用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一文提出的“三個中國”說法,上古期為“中國之中國”期、中古和近古期為“亞洲之中國”期,現當代則為“世界之中國”期。上古期的文藝高峰是華夏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奠基期。中古和近古期的文藝高峰是中國多民族統一體歷史時期的產物,也是其走出國門、影響鄰邦、雄踞亞洲的輝煌期。現當代的文藝高峰則是文藝走向世界、擁抱世界,在世界文藝大舞台上展現自我姿態的開放期。需要略做說明的是,中國古代文藝並非存在當下明確的獨立文藝門類,詩樂同構、舞樂同構、書畫同構在文藝史上為常態,這也使得文藝高峰經常體現為綜合各種藝術門類的文藝高峰。
第一期的文藝高峰以《詩經》、楚辭、諸子散文、漢賦、秦篆漢隸漢草、兵馬俑雕塑、鍾罄雅樂、樂府和《盤鼓舞》等為代表,它們在文藝各領域既開創了中國文藝尚情的審美傳統,也確定了獨具特色的民族理性精神。
第二期是文藝的自覺和深化期。魏晉為其開端,這個階段文藝逐漸走向自覺,陶淵明等文人的詩歌,鍾繇、王羲之的書法,敦煌宗教壁畫、造像和顧愷之的人物畫、山水畫等為後世樹立了創作的典範和基本美學原則,影響深遠。中古期的第二階段為唐至明中葉。這個階段,文藝高峰蔚為壯觀,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等偉大詩人、詞人代表了詩詞創作的最高成就,吳道子的人物畫,王維、郭熙的山水畫、花鳥畫,張擇端的風俗畫可謂各自領域的傑構,而書法和音樂、舞蹈入唐後,也出現了李邕、張旭、顏真卿、柳公權、懷素等大家和以《霓裳羽衣舞》為代表的宮廷樂舞。中古期的第三階段從元代開始到明中葉,在這個階段,文學領域出現了曲和雜劇等新的藝術形式,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等為其中最卓越者,而小說則以《三國志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為范例,它們的出現意味著中國迎來一個長篇小說的時代。這個階段書法長於帖學,帖學當首推趙孟頫,繪畫則有黃公望、倪瓚等人對水墨山水畫的推動。至明代,浙派、吳派(最有名者如董其昌)等文人畫的集中出現又將南宗、北宗的山水畫推向新的高度,明末,在人物畫領域耕耘最精深者當推陳洪綬。
第三期為中國封建王朝的後期。這個階段,小說創作呈現熱潮,白話小說最著名的是曹雪芹的《紅樓夢》,文言小說最著名的是《聊齋志異》,戲曲繼續發展,湯顯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達到傳奇的頂峰,音樂則隨戲曲的發展充分融合於戲劇表演之中。清代書法出現中興的局面,如何紹基、吳昌碩等人,繪畫則以遺民畫家石濤、朱耷的創新最為有名。
第四期的文藝處於中西歷史匯流之中。中國文藝真正做到中西合璧,文藝大師輩出,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如聶耳、冼星海、梅蘭芳、黃賓虹、齊白石、徐悲鴻、傅抱石,他們或弘揚民族文藝的優良傳統,或汲取外邦異域文藝的精華,從而將文藝推向新的高峰。
文藝只有通過高峰,其特徵與魅力才能得到真正體現。文藝高峰是對文藝特徵與魅力的典型反映。四個時期出現不同的文藝高峰,不同的文藝高峰說明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文藝形式、文藝類型,同時還給予以下啟示:第一,文藝高峰多峰聳立,但前峰影響後峰,可謂峰峰相連;第二,峰峰相連,且推陳出新、各美其美;第三,文藝高峰之間通過文藝“平原”、“高原”才得以相連。文藝高峰經常體現為文藝傑作的大量產生和文藝大家的天才式貢獻。但在高峰形成的準備、醞釀期,文藝不必然地造就傑作和天才。文藝高峰的形成和存在(這個過程自然包括其對與文藝“平原”、“高原”關係的吸納)既反映了具體的文藝高峰的不同形態特徵,又體現了文藝發展所遵循的共同規律。袁行霈就文學自身發展論列九個方面的表現、條件:(一)創作主體的發展變化;(二)作品思想內容的發展變化;(三)文學體裁的發展變化;(四)文學語言的發展變化;(五)藝術表。現的發展變化;(六)文學流派的發展變化;(七)文學思潮的發展變化;(八)文學傳媒的發展變化;(九)接受對象的發展變化。文藝發展的關聯領域總是促進文藝將自身發展和社會進程不斷協調起來,中國文藝發展史的四個時期在各自的階段充分地展示文藝高峰的形成被“含括到一種特定的社會生活模式的情景裡面”。無論就文藝創作主體還是就文藝活動的社會環境而言,每個時期的文藝高峰都在整體上反映特定時代的“社會行動模式”對文藝實踐的影響,並充分地利用特定時代的藝術概括能力將這一關係揭示出來,因而文藝高峰不僅受製於文藝自身的內在規律,也受製於文藝發展的外在社會條件。
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藝術家們創作的大量藝術珍品決不僅僅關注“美學內在的觀點”,他們首先是他們所生活時代的藝術家,接受著當代的思想、情感和欲望的熏陶,利用他們的藝術概括能力最充分地展現了時代心聲,且其中孕育著他們的同時代人所能理解、接受的文藝傑作的審美需求。在獲得不同時代間共鳴的每一種藝術中,經常可以清楚地發現前一個時代文藝高峰的偉大作品不僅在該時代得到廣泛認同,而且也使其他時代的人們對之產生極大興趣。伴隨這些認同、興趣而生的文藝發展、文藝進步反過來又推動文藝高峰的形成。這是文藝高峰的魅力所在,也是文藝傑作之於文藝發展的作用所在。
當然,相對各文藝高峰之間的關聯性而言,代表性的文藝家的生命力是貫穿其間的紅線。代表性的文藝家在不同層面上、不同時段上得到不同的理解與接受。這些理解與接受雖然有程度不同的差別,但無疑都與其構成文藝高峰的要素和條件緊密不可分。如果說文藝高峰是文藝星空最耀眼的星子,那麽那些因理解和接受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文藝“平原”、“高原”就是雖不那麽耀眼但閃爍光芒的群星,文藝星空因此而豐富。別林斯基曾就文藝傑作的生命力這樣評價普希金:“普希金不是隨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準上,而是要在社會的自覺中繼續發展下去的那些永遠活著和運動著的現象之一。每一個時代都要對這些現象發表自己的見解,不管這個時代把這些現象理解得多麽正確,總要留給下一個時代說一些什麽新的、更正確的話,並且任何一個時代都決不會把一切話都說完……”無疑,在中國文藝發展史上,文藝高峰的四個時期也存在這樣的文藝現象,文藝家創作的文藝傑作總是激發一代又一代的認同、興趣。比如,第二期的陶淵明詩歌就歷經擬陶詩、效陶詩、仿陶詩、和陶詩的各種形式,最後在蘇軾那裡達到鼎盛;又比如,從11世紀至16世紀興盛的文人畫潮流,這個潮流以蘇軾為開端者以董其昌為結束者,文人藝術家的文化理念及其實踐決定性地開創了中國繪畫新傳統;再比如,書聖王羲之行書《蘭亭集序》所張揚的生命精神、文藝精神幾乎成為後續文藝高峰包括書學在內的各種藝術門類的文化資源。
二、文藝高峰與“一代有一代之文藝”
1912年,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的“自序”裡開篇曾這樣論斷文學史上各類文體競相紛呈的現象:“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為強調其研究對象有元一代戲曲的文學史地位和研究價值,王國維從文藝發展的代際關係出發考辨戲曲在元代勝出的意義、價值,指出元曲和楚騷、漢賦等文體的並置地位。不唯王國維,生活在元代的虞集就曾依憑其當代人經驗評價戲曲作為“絕藝”之於文藝的貢獻:“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於後世者: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開於氣數音律之盛。其所謂雜劇者,雖曰本於梨園之戲中間多以古史編成,包含諷諫,無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為美刺之一端也。”虞集和王國維兩人都看到戲曲作為元代文藝高峰的最主要藝術形式在中國文藝發展史上與其他文藝高峰的比較優勢,才從“絕藝”、“後世莫能繼焉”的高度將這樣的文藝高峰地位充分肯定、甚至絕對化。這一研究為我們探析通向文藝高峰之路提供了啟示。但是,細究虞集、王國維的立論邏輯,不難發現他們無不著眼於文體形式自身發展的獨立性,著眼於文體形式的變革,從“美學內在的觀點”出發,才以王朝更替為背景討論文藝(文藝形式)和社會變遷的關聯性,將文藝發展恢復到王朝更替的背景中得到討論。他們的論述邏輯表明,“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藝)”觀得以成立的條件在於:文藝發展如果構成一張文藝演變歷史地圖,不斷更替的王朝政權必然地繪就地圖的時間邊界。文藝的代興背後其實是文藝的代衰,有某一種文藝形式的衰亡才會有另一種文藝形式的興盛,其標誌最終以為王朝政權的更替期被提出。或者簡要地說,文藝的代興代衰隨王朝的代興代衰而來。
但是如果從文藝與社會發展的總體的平衡關係與特殊的不平衡關係去看,這種肯定某一種文藝形式在某一個階段(比如王朝)的絕對地位的文藝觀其實是一種相對主義的絕對化的文藝發展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告訴我們:“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文藝高峰的出現或者說文藝的繁盛不必然體現為因王朝更替而致的文藝樣式的翻新(整體上王朝政權的更替表征著歷史的線性進步),恰恰相反的是,它以高品質的文藝作品的產生為標誌,高品質的文藝作品的產生才是文藝繁盛、文藝高峰的應有內涵。
當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藝)”說的學理基礎乃是建立在對文藝和時代、社會密切不可分關係的理解之上。強調文藝和時代的關係、強調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藝及文藝形式,這無疑說明文藝因時而異、因時而新。文藝之異、文藝之新不是朝夕可就的事物。惟其如此,文藝發展經常從一個較長時段得到反映,這也是人們願意以代為時間段來觀察文藝之新變的原因,即便文藝高峰在經歷長期的準備(經常體現為文藝“平原”、“高原”向文藝高峰的醞釀)偶爾在一個較短的時間段找到新變的突破口。“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不只意味著文學體裁因時更替,還意味著一種文體在它誕生的時代就達到了藝術創造的頂峰,令後人無法企及。換言之,文學的繁榮總是與新文體的形成相伴出現,而作家總是在接受新文體時爆發了最大的創造力”。從文藝自身推陳出新的演變規律去看,某一具體樣式的文藝達到高峰,其實與對以往文藝的借鑒息息相關。“一種文體在它誕生的時代就達到了藝術創造的頂峰”,這種達到文藝高峰的文體不可能離開它誕生的已有文體的基礎,離開那些可能表現於文藝“平原”、“高原”時期的已有成就。而文藝傑作愈是得到推崇愈是表明這樣的傑作是屬於時代、屬於社會,在在體現文藝創作主體的審美表達和社會進程關係的密切。或者說,即便在某一個時代藝術形式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闡釋這一突破也需要圍繞著形式自身的演進史和美學表達與時代之關係等方面進行。
藝術雖然與時代關係緊密,一方變化必然帶來另一方的變化,但時代和文藝不是簡單的對應、因果關係:“同一種藝術現象可能出自不同的社會條件,而同一社會條件又可以產生不同的藝術表現。”時代總是通過藝術得到折射,時代也可能因為藝術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特徵。時代作用於文藝,文藝也可以作用時代:“藝術和社會處於一種連鎖反應般的相互依賴的關係之中,這不僅表示它們總是互相影響著,而且意味著一方的任何變化都與另一方的變化相互關係,並向自己提出進一步變化的要求。”在這個意義上,“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藝)”說便有其成立的理由。但辯證地看,文藝和時代關係的互動性和複雜性又確實說明這樣的道理:“社會與藝術的互動關係不同於藝術中自發與習俗、表達意願與表達方式、內容與形式的關係。藝術既不是對社會的‘否定’,又不是這種‘否定的否定’。”之所以稱“藝術既不是對社會的‘否定’,又不是這種‘否定的否定’”,這與藝術傑作在自我完成之時連同對與之相隨的社會重構和主流價值塑造有關。一般說來,文藝高峰的藝術傑作就是通過濡染性力量引導人們進入自身的藝術實踐,進而在對藝術實踐的體驗中確認其功能和意義。文藝軟性濡染力量的釋放既來自藝術傑作所刻畫的藝術形象的引導又來自藝術傑作所產生的理解和接受。人們不難形成這樣的印象:當一個時代的文藝滿足時代的審美需要,這個時代的文藝也就繁盛;當一個時代的文藝繁盛,這個時代的文化精神也高漲;當一個時代的社會崇尚產生偏差,其相應的藝術也會存在偏差,反之亦然。在很多時候,藝術都發揮著類似哲學、宗教、道德、歷史乃至政治一樣的作用,推動著某一時代與社會文化精神的健康成長。所謂創造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作品,以優秀的作品感動人、鼓舞人就蘊含著這方面的樸素道理。
就文藝傑作之於具體時代、具體社會的文藝高峰的貢獻來說,文藝傑作所刻畫的藝術形象更是借助文化精神顯示出濡染作用、感召力的特殊性一面來,藝術形象雖然一經過藝術家的塑造便獲得自身的相對獨立性,但更是和藝術所折射的特定時代美學態度、文化精神息息相關。藝術形象總是將藝術所誕生的時代與社會文化狀況呈現於藝術魅力的釋放之中,這也是人們可以透過不同文藝高峰觀望不同時代的原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第四版序言中借人類學家巴霍芬《母權論》一書對古希臘文藝高峰的代表性作家埃斯庫羅斯的悲劇《奧列斯特》評價為例肯定了雅典娜、阿波羅、奧列斯特一類神和英雄的非凡藝術魅力和獨特認識價值:“埃斯庫羅斯的《奧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戲劇的形式來描寫沒落的母權製跟發生於英雄時代並日益獲得勝利的父權製之間的鬥爭。克麗達妮斯特拉為了她的情人亞格斯都士,殺死了她的剛從特洛伊戰爭歸來的丈夫亞加米農;而他和亞加米農所生的兒子奧列斯特又殺死了自己的母親,以報殺父之仇。為此,他受到母權製的凶惡維護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為按照母權製,殺母是不可贖的大罪。但是,曾通過自己的傳諭者鼓勵奧列斯特去做這件事情的阿波羅和被請來當裁判官的雅典娜這兩位在這裡代表父權製新秩序的神,則庇護奧列斯特,……雅典娜以審判長的資格,給奧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無罪”。在這裡,雅典娜、阿波羅和奧列斯特都成了父權製取代母權製這一社會制度更替過程的代言人,他們順應時代發展,從而體現了社會進步的必然性。恩格斯肯定了巴霍芬對《奧列斯特》的如此閱讀及對雅典娜、阿波羅和奧列斯特的如此肯定應證了文藝傑作所塑造的藝術形象的魅力之於人們觀望與體驗處於發展期的古代希臘民主製和民主精神的文化價值,進而也讓人相信“希臘的光榮”絕不只存在於神話當中——它存在產生輝煌文藝的雅典民主時代,沒有古典式民主的雅典便沒有如此反映歷史必然性的文化精神,沒有如此理性的文化精神便沒有輝煌的希臘文藝。可見,恰恰是通過文化精神的塑造滿足時代之需,文藝傑作在推動人們對文藝與時代相互關係的認識之時吸引著人們對藝術為何具有永恆意義的廣泛探討,對藝術以何種方式折射時代和折射時代何種事物的探討,而探討藝術的永恆魅力又不得不圍繞著特定社會文化精神的養成的中心議題進行,這原本是一個相反相成的極為有趣的過程。為什麽《詩經》會保留永恆的魅力?為什麽《紅樓夢》會保留永恆的價值?不難想象,我們正是因為基於華夏民族共同的心理、情感才認同《詩經》,認同《紅樓夢》,認同產生《詩經》的先秦文藝濫觴期文化精神的充沛與生命力,認同明清長篇小說豐收期文化精神的雍容廣大。從這個角度上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藝)”說其實又含有對時代與文藝高峰關係的辯證理解。
三、文藝高峰與文藝的“繼替”現象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藝)”既簡明地表明了文藝興衰的文藝史事實,又簡明地表明了文藝繼替之間的關係。然而,在看到文藝發展史上的繼承與革新關係時,不宜用“作品好一些壞一些”、“高一些低一些”為標準對這一關係作簡單、機械的判斷。文藝發展繼承與革新的複雜性決定了文藝高峰與文藝高峰之間關係的複雜性。這說明了文藝發展史上文藝高峰形成原因的複雜性。從前述的中國文藝高峰四個時期來看,各個時期的文藝傑作之間存在一個影響與被影響的過程,一個影響與超越影響的過程,但又很難說某一個時期的文藝高峰或高於或低於另一個時期。
一般說來,文藝高峰一旦形成便會具有穩定性和變化性的美學維度。穩定性是指文藝高峰的基本內容、特徵等等的穩定,變化性則是指文藝高峰的藝術魅力總是通過文藝發展的歷史長河不斷釋放、不斷豐富,彌散於文藝發展史,彌散於眾多文藝“平原”、“高原”,即文藝高峰的關聯地帶。正因為文藝高峰存在穩定性、變化性的東西,我們常常看到文藝高峰與文藝發展史之間的關係通過文藝珍品、傑作的效果史得到演繹、反映,於是文藝高峰之間的關係呈現為不同時期文藝傑作與文藝傑作的或隱或顯對話關係。
對於文藝發展史而言,繼承與革新是文藝在審美需要方面的突破的實際表現,突破的深度、廣度取決於構成文藝高峰的文藝傑作在每一個階段的示範作用和代表性,還取決於文藝高峰之間的文藝“平原”、“高原”的中介。“在藝術領域中,繼承關係並不僅僅局限於前一階段的經驗,某一種種類、類型的經驗。這種繼承關係可以在各個不同時代的、屬於完全不相似的思潮的藝術家們中間,也可以在各種不同的藝術種類的大師們中間發生。”正是因為通過構成文藝“平原”、“高原”的不同思潮的藝術家們的傳遞,正式因為文藝大師的所創作的文藝傑作決定文藝傳承的基本面,文藝的生命力才通過文藝傳承集中地在一代又一代文藝大師那裡得到體現,在一個高峰和另一個高峰那裡得到體現。“藝術、文學的本性是新,是以新的豐富已經有的,‘舊’的能夠存在,因為本來也新,所以有永恆的生命。因此,作為後來者也必須是新的,這是規律,不允許重複,重複十褻瀆,是犯罪。”重複是停滯,遑論文藝高峰的形成。文藝發展不是指文藝的線性發展,文藝繼承也不是指從前一類文藝直接通向後一類文藝的東西,前一時期通向後一時期的東西。它必須經歷文藝“先行者”和“後來者”的各個階段,文藝的“先行者”和“後來者”構成文藝作品的發展序列。在“先行者”那裡不一定具備後續的文藝高峰的要素和條件,但無疑又是為後續的高峰準備了條件、提供了要素。在這樣的發展序列,無論“先”與“後”對於文藝高峰都有著同等的意義。我們在前文述及的四個時期的文藝高峰與“三個中國”說就能表明文藝傑作在促進文藝的發展方面都有著同等意義,而貫穿其中的文藝“平原”、“高原”同樣不可忽視:這四個時期的每一個階段的文藝高峰都是經過長期的醞釀、鋪墊,文藝高峰就像浮於海面的高聳冰山,眾多文藝“平原”、“高原”沉於海面以下,而沒有海面下文藝“平原”、“高原”的力托,也就不會有浮出海面的高峰。
相對文藝“平原”、“高原”而言,文藝高峰不是製造偶像崇拜,但確實沒有高品質的文藝傑作便沒有文藝高峰。文藝發展是隨藝術家感受世界、藝術概括能力的發展而發展。文藝發展意味著變化,但更意味著新的內容與形式的賦予,舊的內容與形式的消褪。儘管我們無法精確地判斷文藝發展過程文藝作品的進步程度,對此更無法給出精確的計算模型,但是文藝發展史上的確存在繼替現象,即是藝術家的每一部文藝作品和前人的作品有著內在或外在的聯繫,有繼承與革新的現象便標誌著文藝的發展:“繼承關係和革新的相互關係不僅決定著藝術的歷史演化的連續性,而且也決定著那些在長時期內保持著本身的意義並標誌出人類藝術文化的發展的美學成果。顯然,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不是由於藝術的內在運動,而是由於這種相互關係反映出生活以及精神、美學需要的發展,是在其最好的范例中顯示出來的人的創造積極性和精神力量的重要表現之一。在藝術的前進運動中突出地表現出人和社會都不滿足於已經達到的、已經完成的東西。藝術思想努力追求新的東西,力求發現它,創造出前所未知的精神的、美學的珍品。”在一定程度上,文藝發展史總是通過藝術傑作之間的繼承與革新關係、文藝高峰對文藝“平原”、“高原”的不斷超越得到清晰體現,於是美學珍品的創造相應地成為文藝發展史繼承與革新的最佳代表。隻不過在某些時期,文藝傑作即使沒有在後續的文藝高峰中發揮其應有影響力,也常常轉變為對文藝高峰的關聯地帶的潛在影響力:通過作用於文藝“平原”、“高原”間接地作用於後續的文藝高峰。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一書裡回顧中華民族自遠古至明清綿延將近八千年的燦爛藝術成就,曾得出一個總體性的結論,“漢代文藝反映了事功、行動,魏晉風度、北朝雕塑表現了精神、思辨,唐詩宋詞、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懷、意緒……以小說戲曲為代表的明清文藝所描繪的卻是世俗人情”。在他看來中華文藝發展的這一態勢,民族審美發展的這一歷程與原始先民巫術宗教傳統、先秦儒道互補的理性傳統的奠基作用是分不開的。華夏民族的獨具魅力的藝術演繹了華夏民族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獨具魅力審美情感,這一審美情感“與今天中國人的心理結構有相呼應的同構關係和影響”,“心理結構創造藝術的永恆,永恆的藝術也創造、體現人類流傳下來的社會性的共同心理結構”。正因為藝術提供的審美世界和民族的心理結構的同構關係,華夏民族的藝術奇葩凝聚的審美趣味、審美風格不但曾經影響著文藝的發展,而且還與今天的我們的感受愛好相吻合,在我們的內心產生深刻的共鳴,從而引導新的藝術內容與表達形式的產生。李澤厚的解釋雖然只是就審美心理結構和文化積澱的關係而言,但的確說明了歷史上的文藝高峰的不同美學特徵及其對於民族文化傳承的巨大作用、特殊價值。民族文化的傳承離不開文藝高峰對民族審美情感的葆有和演繹,藝術文化史在這裡可以表現為民族審美精神的演變史、發展史,可以表現為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對“流傳下來的社會性的共同心理結構”的接受和理解,這通常構成文化傳承的主要內容,也構成文藝發展的主要內容。“文化史如何起作用的?是基於人的群體性即社會性。群體可以超越個體的局限,每個個體的人有生有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時生同時死;不同的人的生與死,是有時間差的,生不同時,死不同刻,而不同時間生死的人,不同代際的人,有共處的時間,在共處的這段時間裡,每個人的人生經驗、知識、感受、發明等等,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相傳遞,可以變成別人的東西,保存在別人那裡。……人和人可以跨越時間、太空的障礙,進行交流和學習,分享知識和經驗”。文藝高峰的“知識和經驗”倘若要得到分享,勢必導致文化的傳與承,文化的傳與承其實就是文藝在表現形式與內容方面的“知識和經驗”的分享,自然也造就“社會性的共同心裡結構”。惟其如此,文藝高峰才跨越時代得以傳承,文藝高峰才跨越文藝類型得以綜合,引導新的文藝實踐的開啟。
值得注意的是,文藝高峰在引入人們進入自身的文藝實踐時還體現出文化兼容性的一面。文藝高峰總是在借鑒本民族原有藝術和外來民族藝術的過程中走向藝術形式和內容的創新,甚至還走向諸種形式的新綜合,體現出一般藝術品難以達到的藝術概括能力,體現出超越文藝“平原”、“高原”的可能性。文藝傑作借鑒外來藝術也適當對其內蘊的文化價值做出選擇性的吸納,從而釋放出更為豐富、更為新穎的藝術魅力,引導它走向新的階段。當我們說大唐盛世產生燦爛輝煌的文明成就和創造絢麗多姿的藝術時,我們不會否認這個偉大的歷史時代在吸收外來文明一切先進成果方面表現出的空前開放姿態,這個時代的確“無所畏懼無所顧忌地引進和吸收,無所束縛無所留戀地創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傳統,這就是產生文藝上所謂‘盛唐之音’的社會氛圍和思想基礎”,這個時代在包括詩歌、繪畫、音樂、舞蹈、建築、雕塑在內的藝術實踐領域所做出的積極探索促成了新的藝術的誕生,為後世立下新的美學規範,而以李白等人為代表的藝術巨擘元氣淋漓的藝術創作差不多集中證明了文藝傑作的藝術魅力從來不是一種封閉保守的作用力。歷史地看,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高峰藝術越是得到充分發展,則這個時代、這個民族越是開放、越是充滿創造和革新的生機。文藝高峰被當作文明的精髓部分在文化傳承中所起的這一作用如此重要、特殊,以至於哲學家羅素會聲稱:“文化從一個文明到另一個文明,以及在該文化之中傳遞的連續性,更是由藝術而不是其他某事物所決定的”。
恩格斯在致出版商布洛赫的信中曾這樣指出歷史創造主體與歷史之間的聯繫:歷史“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社會的發展和伴隨社會發展而來的社會生活的豐富賦予文藝發展新的條件,賦予藝術家們新的創作契機,這似乎說明“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因社會進步是確定的。但恩格斯又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中國文藝四個時期文藝高峰的形成正如歷史的創造一樣,是文藝關聯領域多種力的平行四邊形的合力結果,存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因素的複雜運動。文藝高峰是文藝長時段積累的產物,離不開文藝“平原”、“高原”的共同塑造。這一狀況說明,探析通向文藝高峰之路需要考察文藝關聯領域多種力的合成條件、效果,在關注文藝高峰的同時,也要關注文藝“平原”、“高原”在通向文藝高峰的奠基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