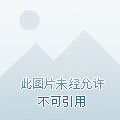“天府”一詞,在現在的媒體上,常是四川人的專利:說到“天府之國”,大部分人第一反應想到的便是四川,四川省會成都市中心有“天府廣場”,新城叫“天府新區”,在建的新機場也定名為“天府機場”。英國學者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一部對川菜的專著,書名就叫《天府之國》(Land of Plenty),英文原名直譯便是“富饒之地”。這一稱號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十年前《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選“新天府”,引起了許多四川人的不滿。然而在歷史上,“天府之國”一詞既非四川專有,最初也並非指四川,其意也不僅是說當地肥沃富饒——否則就很難解釋,為何像江南、江漢平原、珠江三角洲這樣歷史上肥沃富饒不輸於四川的地方,卻幾乎從未被稱為天府。在這個簡單稱謂的背後,隱藏著時常被人忽略的中國傳統文化理念。

釋“天府”
在現代漢語中,“天府”的含義常僅限於“天府之國”,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權威工具書《現代漢語詞典》就隻收錄了“天府之國”這一詞條,解釋為:“土地肥沃、物產富饒的地方,在我國一般把四川稱為‘天府之國’。”《古代漢語詞典》收錄了“天府”一詞,但同樣解釋為“謂自然條件優越,形勢險固,物產富饒的地方”。《辭源》中則列出了“天府”的四種含義:1)周官名,屬春官,掌祖廟的守護保管。凡民數的登記冊、邦國的盟書、獄訟的簿籍,都送天府保存。府,藏物之所;天,尊稱。後泛指朝廷的倉庫。2)肥沃、險要、物產豐饒的地區。3)星名。亢宿、房宿都有四星,並稱天府。4)人身部位及經穴名。實際上,“天府”的含義極為複雜,還遠不止這些,歷史地理學者王雙懷在《“天府之國”的演變》一文中共舉出九種之多,除了《辭源》所列之外,還指:人的“靈府”,表示思想深邃,富有智慧;國家圖書館或檔案館;朝廷或天廷;國庫或天子府庫;適宜人類生活的富庶之地。
這些含義乍看上去五花八門,但其實彼此之間是密切相關的。要理解這一點,就得先明白,中國傳統上是一種氣化宇宙論的思維模式,並相信“天人一體”,即人體在本質上是一個小宇宙。這和西方思維中認為“思維與身體是一部不同質而又相互作用的機器”的假設完全不同,儘管它也強調“心”和“頭”作為控制中心來控制其它部位,但采取的卻不是一種機械論的隱喻,而認為對“氣”的控制和導引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氣”不僅是宇宙中有規律流動的生命力,還是人的生命所系,是人體健康的基礎,漢語中說人死便是“斷氣”。因此,中醫、養生術和內功都強調對“氣”的吸納、導引、存儲(收入“丹田”),這些“氣”在體內沿著經脈流動,在人體的不同部位有“穴位”像關卡一樣可以疏通或封閉氣流,而當人體出現病痛時便被診斷為是氣流不暢所致,需要用針灸刺入穴位的方式來加以疏導,但最重要的仍是對能量的儲存、集聚、控制和運用。
由於這種思維模式在潛移默化中支配著中國人對不同領域的想象,因而我們常可以看到它作為一種隱喻出現在不同類別中:中醫和氣功中用以指人體特定部位的“穴”,在風水堪輿術中也使用同樣的術語。與古希臘的解剖醫學注重肌肉與神經不同,中醫在觀察時注重的是“五髒”和“經脈”。先秦時醫學原理常被用作政治文本中具有說服力的隱喻,因而人體髒腑的命名與國家政治基於相同的原理,所謂“五髒六腑”,《白虎通》明白指出:“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也就是說,內髒器官是宇宙結構在人體內的體現。“髒”與“腑”的聲旁分別是“藏”與“府”。《素問·五髒別論》:“所謂五髒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靈樞·本髒》:“五髒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而《周禮·天官·疾醫疏》稱:“六府,胃、小腸、大腸、膀胱、膽、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為府。”五髒是人體生命活動的中心,儲藏能量;而六腑則類似於“傳化物”,須“瀉而不藏”,“實而不能滿”,換言之,能量需要經此處流動、傳輸,來供給中樞的控制支配。在這樣的視角中,人體機能被設想為一個能量的儲蓄池,一個人可以通過對能量流入、消耗的控制來獲得力量並進行活動。
基於此,我們便能理解貫通不同事務的隱喻:“府”從造字上說本指藏放財貨之所,到後來則抽象化為比喻一切儲存。《周禮·春官》“天府”條賈公彥疏:“府,聚也。凡物所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莊子·齊物論》認為,要擺脫人們之間無盡的是非紛爭,最根本的辦法是棄絕智慧,藏其知於“天府”,收斂起智慧光芒(“葆光”),在此,“天府”就像“丹田”一樣是一個內在的積聚之所。漢語裡常說一個人處事有心機謂之“城府深”;風水術上宅第也講究“藏風聚氣”,要山環水抱,才能轉運生財,故宅第也稱“府”;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府,文書藏也”,這意味著對朝廷來說,文書本身就是行政權力的構成要件。原本內廷機構和人體器官隱喻的“府”,到唐代開元元年(713年)正式成為行政區劃名,唐玄宗升國都雍州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為河南府,這本身或許意味著國家權力的集中化與內廷權力外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府”的含義始終隱含著“儲存、支配、調用關鍵物資的中樞”這一層意義,因而天府星古稱“令星”,在相術中被稱為“南鬥星主”,主財帛、田宅及衣食。人體所說的天府穴,其位置在將手伸直,用鼻尖點臂上所到之處,其原理在於:中國人相信“鼻通氣象”,是生命的關鍵之處,而“人身諸氣之府”的肺借助鼻子“外通氣象”。

應用到政治理念中,這便是一種“貢賦經濟學”:一個國君如果想要成就帝王霸業,那就必須以贏得戰爭勝利為目的,借助官僚機構的力量來有效地調配各地的生產活動和人力物力。這接近於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說的“謀製”(Machenschaft),也就是迫使自己所統治的地域、人民順從管理的需要,乖乖地交出我們想要從他們那兒得到的東西。在這類關係中,能量不是經過播種、照料後,最終被收獲,而是被解鎖和轉換後,以某種不同的形式存儲起來,等待著被分配出去。海德格爾話語中隱含的軍事意象與中國傳統理念很契合:“一切都被命令要處於待命狀態,要立即就可以使用,事實上,就讓它站在那裡,好能隨時等待進一步的命令。”
按中國的傳統話語來說,這是一種“勢”:天地之間的力量是“氣”,而這種力量在作趨向性運行與轉化時便是“勢”,如果一個人能調動起這種力量也被認為有“氣勢”。“勢”的營造極為重要,無所不在:風水堪輿有龍勢,軍事打仗有陣勢,書畫運筆有筆勢,文章結構有文勢,而軍政大事也講究“形勢”,往往須佔據有利的“形勝之地”,這樣才能預先高屋建瓴,打下基礎。這樣一個能滿足政治需要的基地才是“天府之國”。
“天府之國”:一個軍國地理學術語
不難想見,當古人論述政治、軍事問題時,也借用了同樣的隱喻來說明問題。一如歷史學者陳蘇鎮所言:“從現代學科分類角度看,先秦諸子在理論層次、研究方法、觀察角度等方面往往不同,但它們闡述的大多是關於如何‘治’國、‘治’天下的學問。這些學問通常包括人性論、治國方略、歷史觀、宇宙觀等不同層次的內容。”也就是說,先秦時代計程車人最關注的還是從政治層面如何治國安邦的策略,只是他們會從宇宙論等不同層次來說明問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用“天府”一詞來隱喻某一地理區域的說法出現了。首創這一用法的是戰國時期著名的策士蘇秦。《史記·蘇秦列傳》記載他遊說秦惠王說:“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但秦王反應冷淡,於是他又北上遊說燕文侯,其措辭與遊說秦王時十分相似:“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裡,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
蘇秦在此從軍事地理學的層面為“天府”增添了新的內涵:形勢險固(山河作為屏障)、有軍事潛力(馬匹和人力)、饒有建立帝王之業的物資。像他這樣的思路,在當時各國策士中其實比比皆是,范雎在遊說秦王時的口吻與他幾乎如出一轍:“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他強調有了這樣的土地人民之後“霸王之業可致也”。而范雎受封應侯之後,接待來訪的荀子時問他“入秦何見”,荀子的回答也是類似模式:“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荀子·強國》)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治國術視角中,一個地方要能被稱為“天府之國”,不僅在於它能提供豐饒的戰略物資,還必須易守難攻、能據以立足來奠定強國基業。這一議論之所以在戰國時期萌生,恐怕正是由於當時的大國競爭走向了全面動員化,物資和人力消耗巨大,直接轉化為決定各國在爭霸戰爭中的生死存亡問題。
前代學者也已總結過中國歷史上的這些現象。1935年,冀朝鼎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一書中提出“基本經濟區”(key economic areas)的概念,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當時各地自給自足,經濟發展水準大致如舊,彼此互不依賴,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於提供貢納穀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

魯西奇認為,冀朝鼎的這一觀點深受當時地緣政治學說的影響,如果根據麥金德“地理樞紐”的觀點,也可以將冀朝鼎的觀點濃縮如下:“誰控制關中,誰就能控制中原;誰控制中原,誰就能控制中華帝國。”由此,他主張中國歷史上有“受到王朝特別重視,據之即足以控制全國的特殊地區”,即“核心區”,但他將這一原本經濟地理學的概念擴展為如下要素:1)應是兵甲所出之區,2)應是財賦所聚之都,3)應是人才所萃之地,4)應為正統所寄之望。不過,魯西奇還遺漏了一點,即這一核心區在地勢上的險固。葛兆光在引述其觀點後認為,這樣一個核心區其實就是上古的“中國”——“中國”一詞最原初的含義,本來就是指一塊能奠定政治基業的核心區。“核心區”與“天下之中”的概念其實都可用英文heartland來表達。
“天府之國”的論述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其含義乍看是經濟學意義上,實則卻是一個軍國地理學術語。因為“天府”本身就意味著一種非市場經濟的“貢賦經濟體制”,是通過賦役征派來汲取物資,著力於戶籍、地籍、田賦、差役、漕運、倉儲等,並最終用於建立強國基業。這顯然不是真正的商品貿易,貢賦的物資都是通過稅收或武力威脅強取來的貢品,因而這一商業體制是為政治性帝國效力,物資的流通內嵌在政治運作的框架內。在商品和貨幣經濟充分發展之前,這種實物形式的租稅、貢賦差不多就是物資流通的主要形態,“政府主要通過直接征發力役、兵役和各種實物維持戰爭”。大體上,這接近於經濟學上所說的“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也就是徑自掠奪他人資產和強迫他人付出勞力,而非通過生產技術和市場運作,只不過古代帝國這麽做的目的是為了調集資源供養強大的軍隊來進一步獲得政治權力的擴張——概言之,他們是政治家,而不是合乎經濟理性的市場算計者。也正因為古代交通不便,因而建立政治勢力必須要有一個就近的基地,否則遠處的物資不易調配。
在軍國地理學的意義上,“天府之國”強調的不僅是“物產富饒”,更重要的還在於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即便不能爭雄天下,至少也能割據一方。南北朝詩人庾信《蒜山被始興王命作詩》有一句“形勝信天府,珍寶麗皇州”,也指出“形勝”是“天府”的組成要素,不過他這裡所說的“天府”乃指蒜山所在的京口(今鎮江),當時這裡是南朝最重要的關隘。正因強調此地堅不可摧,故而在古代文獻中,“天府”常與“金城”並用,《陳拾遺集》卷五:“夫蜀都天府之國,金城鐵冶,而俗以財雄。”又如清乾隆《崇明縣志》載有清人名吳金城,“字天府”。
清初學者魏禧曾概括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的重點,第一條便是:“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為要害而彼為散地,此為散地彼為要害者。一以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也就是說,建都的“形勝之地”必須是一塊能夠控制天下、而不擔心天下可以反製的“根本之地”。
在治國術的視角下,這種論述幾乎是一種固定模式,雖然未必使用“天府”這一隱喻。如東漢末年荊州牧劉表死後,魯肅向孫權進言:“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裡,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吳國覆亡之後,陸機著《辨亡論》,談到吳國也是這樣一番形容:“地方幾萬裡,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製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禦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只不過吳國在這樣的條件下仍然亡國,陸機故而得出一個深合儒家觀念的結論:一個國家的興亡,“在德不在險”。
和“天府”這一戰國策士的術語相比,這一觀念甚至起源更早。《易·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陸機《辯亡論》:“《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國語·鄭語》:“虢叔恃勢,鄶仲恃險。”也就是說,中國政治家在極早的年代便已意識到地勢險要對自身安危的重要性;然而到戰國時期,隨著軍事征戰的激烈化,越來越多的人物開始意識到這並不是政治上獲得優勢最重要的條件。《史記·吳起列傳》記載魏武侯在西河上感慨魏國“山河之固”,但通曉兵家、法家、儒家學說的吳起卻說:“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在此他舉出歷史史實強調:即便據守地勢險要的形勝之地,但統治者“不修德”的話,仍會亡國。
秦代的覆亡證明關中之險固亦不足為恃,漢代儒家更強調“德義”、“仁義”的重要性。《史記·陳涉世家》褚先生曰:“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賈誼便反對西漢諸帝固守關中以防備、控制關東諸侯,認為“兼愛無私”足可消除天下敵意,使得防備失去意義。這樣的觀點對後世影響深遠,每每總有人抬出來。《魏書》卷五四高閭傳:“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這裡他雖然讚同修長城以備北方遊牧民族,但同樣將“設險”列為不那麽重要的一點。《北齊書》卷四〇唐邕傳,記載有人對北齊開國皇帝高洋說,並州城“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高洋卻說:“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以此表明自己重視的是人才而非城池。後世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發展了這一觀點:“圖王業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險要財賦之謂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謂也,得其賢也。”這也恰好證明,傳統觀念中王業正是要“得其險要財賦”。
基於這些歷史,儒家士人開始質疑經典中理想的“宅中圖大”、“卜居地中”之說,轉而強調人才、德性的重要性。唐末李庾《兩都賦》中最後總結:“則知鑒四姓之覆轍,嗣重葉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他認為王朝興衰還是因為人事,地勢不足憑恃,定都在哪裡都可以。北宋初期的976年,考慮到開封府在平原上無險可守,宋太祖有意遷都洛陽,於這年春巡幸洛陽,但其弟趙匡義(後來的宋太宗)反對遷都,理由便是“在德不在險”。明代人也常誇讚燕京適宜建都,但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後,劉溥在《感懷》詩中說到“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淚漣”,四塞山河之固顯然並未使國家免於這一冤罪殺機。

歷史上的“天府之國”
明白了這一套軍國地理學的治國術理念,我們才能理解最早稱四川盆地為“天府之國”的諸葛亮,是在什麽意義上提出這一說法的。按《隆中對》所言:“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在這裡他首先指出的是“險塞”而非“肥沃”,並緊接著指出劉邦曾以此為基地(漢代益州包括劉邦稱漢王的漢中盆地)成就帝業;至於“沃野千里”,只是因為在農業文明的條件下,這是物資供應富足的基本要件,但相比起地勢險要的“形勝”之勢,這是次要的。在此之前,兩漢之際公孫述割據益州時也是如此,重在所謂“地險眾附”。常被人忽視的是,諸葛亮在《隆中對》裡描述益州之前,在談到江東(“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和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時,其實也是出自相同的邏輯。現在還有一種流行的誤解,認為成都平原取得“天府之國”的稱號是在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灌溉良田之後,但從政治戰略的視角來說,在諸葛亮提出以巴蜀為根據地爭雄天下之前,這裡不可能被稱作“天府”,因為這一稱號僅在帝王建都時適用。
事實上,雖然現在很多人以為四川作為“天府之國”形容的是其“土地肥沃”,但歷史上談到時,強調的卻是其險要的一面。《周書·齊煬王憲傳》:“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也就是說,這裡地勢險要,故而北周太祖宇文邕不想讓宿將鎮守,以免此人趁機割據。從據地建業的視角來說,“地險”顯然比“肥沃”是更重要的考慮重點,故此杜甫在《諸將五首》中論述政治形勢時強調“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群材”。南宋樓鑰《送王粹中教授入蜀》一詩起首一句便是:“萬山四塞圍平陸,大為關中次為蜀。”另一位南宋詩人吳潛送人入蜀,在《賀新郎·送吳季永侍郎》中也形容四川是“四塞三關天樣險”。清人楊芳燦在談到四川作為“天府”時強調的也是其險要而非肥沃:“大易雲:主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言地利必資形勢也,蜀國如天府奧區,直坤維而疆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形勢之險甲於寰宇。”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便從軍國地理學的視角出發,強調:“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基於這一判斷,他認為“成都之險,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據蜀者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因而“巴蜀之根本實在漢中。未有漢中不守而巴蜀可無患者也。故昔人謂東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漢中”。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最早稱四川盆地為“天府之國”的諸葛亮,為何要強調東連荊州、北爭漢中,並連年出兵,六出祁山,因為不如此不但無法爭奪天下,甚至可能自身難保。
既然“天府之國”是一塊能成帝王之業的根據地,也就不奇怪為何像江南、珠三角這樣雖然肥沃、但不足以據險圖霸的地方極少會被稱作“天府之國”了。西晉代曹魏後,羊祜上表陳伐吳方略,其中強調“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然而,帝王建都之地無不都是“以一隅當天下之眾”,因而此地最好形勢險要,無須四面受敵。事實上,歷史上最早、也最頻繁地被冠以這一稱號的不是四川盆地,而是關中平原。原因很簡單,從中國的地形大勢和傳統政治格局來看,關中雖非最肥沃之地,卻被一再證明是建立霸業的極好基地。
在秦以關中為根本統一天下之後,這差不多是歷代士人的共識。劉邦建立漢朝後,在討論定都時,“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他定都洛陽,但劉敬和張良均極力主張定都關中,認為這裡才是“天府”,但所舉出的理由其實都側重關中“險固”的一面,也即關中比洛陽更適合成為控馭天下的“用武之國”。
秦漢之後,每當有人談及天下大勢,便有人主張關中是最適宜定都來掌控天下的“天府”,在詩文中出現頻率極高。唐人袁朗詩《和洗掾登城南阪望京邑》突出長安一帶自來是帝王之地:“奧區稱富貴,重險擅雄強。龍飛灞水上,鳳集岐山陽。神皋多瑞跡,列代有興王。我後膺靈命,爰求宅茲土。宸居法太微,建國資天府。”甚至在唐末長安被毀之後,仍有許多人堅信應建都關中以定天下。北宋滅亡後,當時一度考慮以金陵、南陽或長安作為高宗駐蹕之地,鄭驤認為“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三朝北盟會編》所謂關中“據山河百二之險,自古號天府之國。保關中所以衛京師”;紹興十年(1140)金人議和,考慮歸還關中之地,宋臣張闡力辯取得關中事關興複:“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

明初朱元璋原擬定都關中,終因當地數百年來殘破不堪,最終選擇建都於南京,靖難之役後,永樂帝又遷都北京。在議論遷都之時,群臣已明其意,紛紛將北京形容為適合控引天下之地:“公侯伯五軍都督及在京都指揮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此類形容,明清兩代出現極多。值得注意的是,其實早在元代就已出現,如楊維楨《重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詩》:“朔方聖人啟中天,天府之國宅幽燕。”並且,即便在明清兩代,仍有許多人在抒發懷古之思時,將關中視為天府,如明人薛蕙《長安道》一詩起首第一句便是:“神州應東井,天府擅西秦。”明末清初錢謙益《南征吟小引》則謂:“今長安關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甚至朝鮮人也深知這一點,14世紀朝鮮詞人李齊賢有《木蘭花慢·長安懷古》:“望千里金城,一區天府,氣勢清雄。”
明清雖建都於北京,關中殘破,但始終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關中就控馭天下形勢而言是最佳建都之地。明末林時對《荷牐叢談·論京都形勢》就認為定都北京雖比洛陽、開封好,但不如西周、西漢之定都關中:“本朝之燕都也,蓋與古不同,稍難於周漢而大勝於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想法,明末大儒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主張,明代危亡,都是因為“建都失算”,他認為金陵是最佳定都之地,理由是形勢已變,當時關中人才、經濟皆不如金陵,但在他心目中,除去金陵之外也就數關中最適合建都了。但清初的歷史地理學者顧祖禹卻明確主張關中是最佳建都之地:“人亦有言:‘建都之地,關中為上,洛陽次之,燕都又次之’……‘然則當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為創業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然則建都者,當何如?’曰:‘法成周而紹漢唐,吾知其必在關中矣。’”(《讀史方輿紀要·北直方輿紀要序》)
這個信念直至晚清都一直有人主張。1851年,太平天國起兵後攻佔永安,有道州舉人胡孝先求見洪秀全,而他提出的建議便是:“關中天府之國,周秦之所以興,欲爭天下,必先取鹹陽,然後出山右,定燕薊,天下可傳檄定也。”(羅惇曧《太平天國戰記》)其時列強進逼,尤其是在1860年北京被英法聯軍攻破之後,很多士人意識到北京的脆弱性,於是許多人再度提出關中才是最適合的建都之地。這些人的立論往往帶有戰國時期策士的影子,多從天下形勢著眼,如1890年湯震著《危言》自序的第一句以“吾欲為策士”來獻議,開篇第一卷“遷鼎”,起首便說:“未有三面臨邊,一面製敵,而足以控引天下,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他認為,雖然北京“內外蒙古依我肘腋,資我卵翼,踞三關、包渤海,此非所謂天府歟”,但現在已不適合建都,長安更適合:“長安,山河四塞,崤函重關,晉豫翼其左,疆隴蔽其右,俯瞷宛洛,前控襄鄧,旁襟黔蜀。”
四年後,鄭觀應所著《盛世危言》問世,同樣強調形勢已變:“世變靡常,今昔異勢。燕京自遼金元明以迄本朝,建都舊地,西南北三垂高山,東面距海,膏腴上壤,形勢天然,亦猶古人所稱關中天府四塞之國也。”而他開出的建議同樣是遷都關中:“求今日之地勢,可以居中馭外、雄長天下者,其惟關中乎?關中形勢,沃野千里,溝渠四達,耕漁畜牧可以廣事屯田。又有河東花馬鹽池可以為民利。天府陸海,今何必異於古所雲也。又況山河四塞,海外諸國舟楫不通,即陸路之鐵路火車亦未能遽到。重重關鍵,氣毓真王,南北東西無思不服。自古中興之主撫有西北,則可以蒞中國而有東南,雖時會使然,亦形勢之利便為之也。”又數年之後,1900年的義和團之變中,首都北京再度被八國聯軍攻破,兩宮西狩,證明北京在面臨來自海上的敵軍時相當脆弱,無險可守,遷都西安之說再度興起。周景勳便上書張之洞說:“都城不遷,建路於引寇招敵之地,雖一寸而不為建。陪都於長安,設路於有利無害之方,雖萬裡而不惜。”
這差不多也是西安、關中被視為適合建都的“天府之國”的最後輝煌,在那之後,隨著近代形勢的急劇變化,很少人再去從歷史典籍中去理解“天下形勢”,新文化運動之後國人對傳統理念的隔閡也日深一日,甚至連“天府”本身的含義也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其結果是,很少人還記得關中曾是“天府之國”,這個稱號似乎變成了四川的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