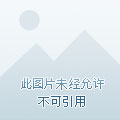本期話題圍繞《流浪地球》與中國科幻文學開展。我們特別約請了4位作者來暢談這部電影的得與失。他們當中既有科幻作家、學院派評論家、主流媒體人、新銳影評人以及影協負責人等多重身份。他們從不同立場出發對《流浪地球》這部現象級科幻電影的思想與文化價值、審美結構、類型探索,中國科幻文學和科幻電影的廣闊前景以及對中國電影工業生產的深遠影響等進行了探討與展望。
——小編
《流浪地球》:新主流電影發展的新方向
吳昊,新銳影評人,中國人民大學廣播電視學碩士。曾在《文藝爭鳴》《小說評論》《文匯報》等報刊發表文章多篇。

在這個春節,中國電影市場再次火爆起來,不但票價節節高升,而且幾部熱門電影還幾乎座無虛席。其中,《流浪地球》更是為這個春節檔注入了一針強心劑,成為中國科幻電影真正的里程碑式作品。很多人盛讚這部影片開創了中國硬核科幻片的新時代,讓2019年成為了中國科幻電影的元年。而在我看來,《流浪地球》不僅僅是一部單純的硬核科幻電影,它還同樣代表著中國新主流電影的探索方向。

首先,《流浪地球》最吸引人的就是它的特效。對任何一部電影來說,好看、視覺衝擊力,永遠是第一位的硬道理。《流浪地球》在視覺效果上無疑是出類拔萃的,衝擊力、感染力、震撼力都堪稱一流。長期以來,中國電影之所以遲遲不能邁出走向硬核科幻大片的步伐,就是因為國產電影的特效水準和好萊塢存在著巨大差距。這部電影的拍攝歷時四年之久,其間還歷經了種種挫折和不信任,但是其最終特效的呈現效果,卻幾乎能夠和好萊塢同類大片相媲美,這簡直讓人驚喜萬分。太空中流浪的地球劃出的美麗弧線、攜帶著30萬噸燃料的巨型“領航者號”空間站、機械化運作的地下城、高聳入雲的行星發動機和直衝天際的藍色強光柱、冰天雪地的地球表層、上海、杭州大樓坍塌的末日景象,等等,都令人驚豔且不由得對這部電影的製作團隊充滿敬意。

其次,《流浪地球》劇情和故事的精彩程度完全符合一部成功科幻大片的基本標準。也許單從這部電影呈現出的故事來講,可能不少小說迷會有些失望。它雖然改編自劉慈欣的同名小說,可其實電影除了保留了劉慈欣塑造的世界瀕臨末日的宏大背景及人類準備帶著地球逃離太陽系的宇宙觀外,對內核劇情進行了大幅度的改動。或者說,這部電影只是截取了原小說中很小的一部分,即最容易在銀幕上展現特效和烘托氛圍的一個段落進行了擴充和放大,而放棄了小說原有的高潮。在原著中,真正的高潮是反對地球作為載具的飛船派和堅持保留地球的地球派之間的鬥爭,由於世界末日沒有按時來臨,導致新派飛船派被殘忍地殺害,隨後世界末日真的來臨,地球依舊走上了流亡之路。然而,這樣複雜的故事線索需要更高超的表現手法、更成熟的場面調動水準和更優秀的故事講述能力,在中國科幻電影仍不成熟的今天,首部硬核科幻片就挑戰如此複雜的劇情,顯然有些強人所難,稍有不慎,還可能弄巧成拙。因此,在這樣一部開端性質的硬核科幻電影中,導演本身可能更側重於對技術的表現,刪去了原著中相對冷酷和複雜的劇情,將其改編成了一個具有模式化的、比較討巧的點燃木星拯救地球的故事。

但是,儘管如此,我依舊覺得這部電影中的故事是合格的,講述故事的能力和水準也是合格的。儘管深究的話可能會存在一些科學和邏輯的問題,整體故事也顯得略微簡單,但是它充滿了恢宏奇妙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是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學十分稀缺、十分需要的,所以整部電影依舊十分好看、十分激動人心。“帶著地球去流浪”這個想法,本身就充滿了吸引力。在長期以來的科幻電影中,似乎人類都會選擇要麽拯救地球,要麽逃離地球,而真正帶著地球逃跑的科幻片,少之又少,可以說是中國人獨特的思維方式的體現。除此之外,在影片中,存在著大量的反轉和高潮部分,比如在運輸火石途中爺爺的去世,又比如千辛萬苦拯救完全部發動機後卻發現這種拯救無濟於事,再比如全體救援隊眾志成城進行著“點燃火星”的努力,但最終仍有5000公里無法抵達,最後只能由吳京駕駛著飛行器犧牲自己去拯救人類。雖然情節略顯俗套,邏輯上也存在太多的漏洞,科學上可能也不可信,找不到科學依據,但是它完全符合一個科技商業大片的需求: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感受到持續的視覺、聽覺、情感、心理上的高潮衝擊。一個接一個的反轉,生與死,希望與絕望,困難和犧牲,總是會讓人看得熱血沸騰。

再次,《流浪地球》將家國情懷、英雄主義與人類意識、宇宙意識相融合,開辟了中國當代新主流電影的新方向。一般認為,中國的新主流電影就是主旋律電影與商業電影的結合,是嘗試著在類型化影片中構築中國的國家形象、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價值觀的電影實踐。相比於之前《戰狼2》和《紅海行動》采取的戰爭類型片的形式,《流浪地球》給我們拓展了新主流電影的更多可能:硬核科幻電影不再是好萊塢的專利,我們同樣可以依靠科幻類型片絢爛的特效和緊張刺激的情節來展現中國精神。只不過,問題在於,展現的手段能否更加巧妙。

事實上,針對這部電影的爭議也一直沒有停歇,有一種聲音始終認為,過多的煽情戲刻板而生硬,影片中刻意加入的大國情懷破壞了電影整體的節奏和美感,顯得並不必要。很多人形容吳京把《流浪地球》變成了《戰狼》,不可否認,這部電影並不完美,比如配角的角色似乎太過功能化,而且電影當中的幾段煽情戲,確實顯得刻意,尤其是吳京在空間站試圖說服聯合政府的發言,以及韓朵朵最後的喊話,都有一種用力過猛的感覺,就仿佛是刻意煽情,又或者是在背課文來拔高價值觀,讓人十分出戲。試想,面對世界末日,那種標準的書面語言你還說得出口嗎?而吳京飾演的劉培強,在空間站對自己是中國宇航員的強調也多少有些刻意,與電影所表達的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共同合作戰勝災難拯救地球的主題顯得不合拍。從這個角度來說,主流電影在克服習以為常的思維模式方面確實是任重道遠。

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寫道:“無論是現代國家、中世紀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規模人類合作的根基,都在於某種只存在於集體想象中的虛構故事。”人之所以能夠和陌生人保持合作和友好,就是因為人們之間相信共同的想象的現實,而實現這一點的方法,就是講故事,還要講好故事,讓你講的故事能夠被大家所接受。就拿宗教而言,宗教靠什麽來團結如此數量眾多毫不相識的人呢,靠的就是可信的富有邏輯的故事。而電影本身雖然沒有宗教或國家這麽大的影響力,但它也能夠對觀眾產生同樣的影響。對於電影而言,其講故事的內在邏輯並沒有變。電影要讓觀眾買單,要讓觀眾接受,首先它講的故事就要好看並令人信服,其次需要能夠反映出一種觀眾能夠通過故事所認可的價值觀和理念。作為電影,不可避免地會傳導某種價值導向,諸如著名的美國導演斯皮爾伯格,幾乎就是美式主旋律電影的代表人物,他所拍攝的《拯救大兵瑞恩》《阿甘正傳》,都展現著美國夢或者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只不過,他講故事的手法更加高明,以至於人們會願意沉浸在故事中並潛移默化地接受故事所反映的價值觀。美國主流大片《菲利普船長》也同樣如此,影片中沒有高喊美國萬歲的口號,也沒有妖魔化索馬裡海盜,甚至對海盜還充滿著人道主義的同情,但海盜不經意間說出的“我將來的目標就是去美國買套房,”“也許在你們國家可以這樣活著,但是我們不行。”這樣的話,展現的正是海盜對美國的自由、平等和美好的認同。沒有說教,沒有煽情,但價值觀的力量卻彰顯無疑。

《流浪地球》當然仍然有著中國主流電影的先天性的局限,比如:劇情演進存在一定的邏輯問題、拯救地球的過程顯得過於草率和簡單、影片中的人物性格張力不足、人物表演過於煽情用力過猛導致簡單化臉譜化等。但可喜的是,在這部電影中,我們看到了中國電影人尋求突破和改變的努力。其中最引人注目並將會重新塑造中國主流電影形象的地方在於:這部電影將主旋律和家國情懷與人類意識、世界意識、宇宙意識進行了有深度的哲學化的融合,開辟了中國主流電影敘事的新模式,實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故事在電影話語裡面的成功實踐。

整部影片因為關於人類命運的哲學思考的嵌入,而擁有了傳統國產商業電影少有的深度,也賦予了各國觀眾更多可以共同討論、共同思索的維度。比如,在面對世界末日的時候,我們是選擇自己的家庭團聚,還是選擇全人類的命運?大我和小我究竟誰更重要?英雄主義、犧牲精神和人性的力量是否是永恆的?雖然這些問題的表達還有些僵硬,但思考本身是令人欣喜且能引發共鳴的。當然,《流浪地球》最深刻的思考在於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博弈。很多人認為AI“莫斯”的設計是對《2001太空漫遊》的單純致敬,但我認為這不是簡單的致敬,而是一種延伸的思考與追問。在《流浪地球》的設定中,人工智能並沒有叛變,它只是按照算法所得出來的結果,采取最為理性的做法,它依舊需要得到聯合政府的授權。但問題是,看似最終的決定是由聯合政府所簽署的,可他們簽署的依據是什麽呢?是人工智能給予他們的演算結果,是人工智能告訴他們“成功的概率幾乎為百分之零”,所以聯合政府才推翻了以色列人點燃木星的理論。因此,最後做決定的到底是人,還是人工智能呢?就算人工智能沒有像《2001太空漫遊》中那樣叛變,決定人類命運的,究竟是人,還是人工智能?近年來很多人擔心人工智能會取代人類。可是通過這部影片我們會發現,人和人工智能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人工智能相信算法,也就是相信概率,而人更傾向於相信感受,相信奇跡。而相信奇跡,本就是創造奇跡的必要條件。只要人類保持著這一特質,人工智能就很難在真正意義上取代人類。

諸如此類的思考被嵌入影片之中,使得它關注的對象延展到了全人類的共同命運,它體現的是全人類共同關心的價值取向。事實上,通過《流浪地球》,我們已然發現,將關注中國國民的命運轉化為關注全人類的命運,並不會使得觀眾忽視中國的影響和貢獻,將家國情懷施加到世界範疇,不但並不突兀,還能更好地展現中國的大國擔當。我們甚至發現,“帶著地球去流浪”這樣有創意的劇情設定,本身就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思維與想象,是對中國人堅定的家國情懷的更精彩的表現。正因為有了故事講述方式的改變,我們看到中國的故事就成了世界的故事和全人類的故事,中國的情感、中國的價值就變成了全世界的情感、全人類共同的價值。這何嘗不是對主旋律電影的一種高級的升華,這與過去中國主流電影喊口號式的煽情和表達相比,不是更含蓄、更委婉、更自然嗎?

總之,《流浪地球》確實是中國電影的一大驚喜,它呈現了新主流電影全新的發展方向,使得新主流電影可以有勇氣披上各種類型電影的外衣。但是,對於新主流電影來說,問題也依舊存在,如何真正解決商業性和主旋律的融合,如何更好地平衡主旋律和講好故事之間的關係,如何真正處理好中國話語和世界話語的相通,《流浪地球》只是開了一個頭、破了一點題,離問題的真正解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顯然,在這方面,中國電影人仍然任重而道遠。好在,因為《流浪地球》,我們已經看到了希望。

《流浪地球》至少扭轉了
對“科幻美學”的一些誤解
“
許暘,85後,複旦大學新聞學院碩士,《文匯報》記者、編輯。

電影《流浪地球》的票房逆襲,不僅引爆了觀眾對國產科幻銀幕巨製的信心,也有效撬動了本土原創科幻文學土壤的活躍指數,科幻這一題材成功“出圈”。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是,科幻題材創作,不再是小圈子裡的孤芳自賞,伴隨著對影片、劉慈欣同名小說的持續熱議,不少讀者將會或已經刷新了對於“科幻美學”的定義。


要知道,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文藝界對於本土科幻的表達尤其是科幻小說語言的呈現,有諸多不滿,其中備受詬病的“原罪”包括但不限於:語言過於粗糙、人物塑造不飽滿、重“腦洞”輕情節……即便2015年夏天劉慈欣摘得雨果獎,成為亞洲首位問鼎世界級科幻榮譽的作家,對大劉作品的批評聲中,仍有大部分火力是對準他的文本語言的。有人吐槽:“不管劉慈欣的想象力如何,他的語言還是太差了;在遣詞造句、謀篇布局、人物塑造、情感深度發掘等方面,劉慈欣的問題顯而易見。”
那麽科幻小說,是否就天然在文字表達上略遜一籌?科幻的美與力,究竟怎樣才能調和出“黃金比例”,從而令人信服地再現宇宙之宏闊?《流浪地球》的熱映,給這一老話題帶來了新的衝擊和思考。
同為科幻作家,飛氘的一番話尤具代表性:如果把科幻作家的“語言”能力理解為準確、有效地用文字來言說他對世界的思考、想象和情感,那麽,如何用漢語去表現科學革命之後的時空之廣袤、探索之艱辛、定律之奧妙、技術之恢弘,抒發現代中國人的豪邁和悲憫,則是一個多世紀前才出現的全新任務。而劉慈欣的寫作,正代表了中國作家在嘗試承擔這一使命時的某種可能性。我讚同他的辯解——“在這個充滿挫折和挑戰的過程中,劉慈欣至少為漢語文學貢獻了生猛、奇崛、壯闊的意象,勇毅、果決、進取的氣質,崇高、悲愴、莊重的語調,而所有這些共同塑造了他的文學語言質地。”
是呀,誰說科幻美學只能由一種價值標尺來衡量?也許渴求從科幻作品中讀出主流文學氣息的讀者並沒有料到,那些看似乾巴巴的文字裡,其實蘊含著科幻獨有的殺傷力——當想象的尺度被無限擴大時,鴻蒙氣息、浩渺之感、攝人心魄的能量,反而由“樸素到了莊重地步”的語言所承載。

劉慈欣作品——《微觀盡頭》(插畫)
這種樸素與莊重,對於電影《流浪地球》而言,是無數扎實的細節組成。從全實景UI到六軸電動平台,從外骨骼到氣囊球,從地下城到運載車……這個劇組很務實,同樣在美術、服化、道具、特效等層面轉換了設計思路,從而確定了屬於《流浪地球》的場景美學體系。比如,不少觀眾觀察到,全片最奇怪的東西也許就是發動機,那個地球引擎。從設計上來說,偏工業化,機械一點,沒有那麽複古,但也是純工業的,帶著外露的、更硬的蘇式的那種感覺。
我想,這種感覺某種程度上,和科幻原著的美學是有一脈相承的地方。電影中一些道具或創意設定,並沒有一味模仿國外科幻片比如《獨立日》裡的極簡設計,或是走華麗路線,而是呼應了前面所說的“樸素到了莊重”。
評論家黃德海對這種科幻語言有過精準的描述,他以劉慈欣《三體》為例打了一組比方——像一個剛學會用語言表達自己複雜感受,陷入愛情的小夥子寫給姑娘的情書;像一個偶然瞥見了不為人知的罕見秘密,卻找不到合適語言傳遞回世間者的試探;或者像一個研究者發現了可以改變以往所有結論的檔案,試著小心翼翼把檔案攜帶的信息放進此前研究構築的龐然大廈。他接連用了三個“不”來進一步解釋——不流利,不雅致,不俏皮,略嫌生澀,時露粗糙,“如同猛獸奔跑之後,帶著滿身的疲累喘著粗氣,而生機還沒有完全停歇下來,其息咻咻然,偶爾有涎水滴落,在地面上洇開大大的一片。在這樣的情境下,劉慈欣的文字越具象,越有表現力,帶來的後果就可能越嚴重,聽慣搖籃曲和童話故事、習慣日常溫煦時光的人,會出現非常典型的發呆、憤怒、眩暈等症狀,感受力更為敏銳的,甚至會有明顯的惡心嘔吐感……”
換句話說,人們會漸漸懂得,科幻題材需要與之精準匹配的語言和質感。不是所有的藝術景觀都適合絲綢般細膩順滑,或是似錦繁花的絢爛,粗糲的、質樸的、平實的語言(包括電影的鏡頭語言),同樣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當然前提是,需要準確匹配的描述與構思。

如果說《流浪地球》的里程碑式意義溢出了科幻的類型邊界,成為中國電影工業化進程中的標誌性力作,那麽持續發力的本土科幻小說,在視野邊疆的拓展、題材手法、語言表達的更新上,也可視作中國正借助流行文化鋪展“仰望星空”的思考路徑,推動讀者不斷突破對未來想象的邊界。而作為中國科幻文學最知名的代表,劉慈欣始終探索著漢語表達宇宙、時空、技術的可能性,嘗試用科幻抒發當代中國人的豪邁和悲憫。他本人曾這樣讚美科幻的力量:“主流文學描寫上帝已經創造的世界,科幻文學則像上帝一樣創造世界再描寫它。”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期待,這種“再描寫”“再創造”本身就意味著不同的路徑,而嘗試著更加理解和擁抱另一種科幻美學?
即便是感性的人類情感,也能在冰冷宇宙中得以釋放溫度,卑小的個體與壯闊的時空同樣可實現聯結。而最能體現劉慈欣對“重量”感受的,莫過於《流浪地球》。有評論說,劉慈欣在他的科幻世界中,完成了對近現代中國核心命題在星際尺度上的再表達,即對生存的焦慮、對進化的執著和對科學的崇拜。

“隨著新一代讀者和作者思維方式的轉變,科幻文學和科幻電影會越來越接近它的本質。社會現代化進程飛速發展,為科幻創作提供了肥沃土壤。”恰如不少外媒為《流浪地球》點讚時所說的,這部電影及其原著小說,成功將極具東方色彩的家國情懷融入劇情,諸多本土元素不是生硬鑲嵌,而是如鹽化水般自然融合。這也點出了未來科幻的發力點,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和發展壯大,在對遼闊時空的想象中,本土作家生動代入了中國經驗,不再僅僅局限於對西方科幻名篇的粗糙模仿,或流於簡單移植現有的歐美模式。
而除了對科幻表達的影響,《流浪地球》在大銀幕上閃爍著的冷峻,也隱隱提醒著人們,我們周圍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像科幻小說了,這種進程還在飛快地加速。劉慈欣有一句扎心的比喻:未來像盛夏的大雨,在我們還不及撐開傘時就撲面而來。他很清楚,比起人們對語言表達的“指責”,更迫切的命題已經擺在科幻從業者面前了——“當科幻變為現實時,沒人會感到神奇,它們很快會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只有讓想象力前進到更為遙遠的時間和空間中去尋找科幻的神奇,科幻小說將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變成平淡生活的一部分,作為一名科幻作家,我想我們的責任就是在事情變得平淡之前把它們寫出來。”

文章的結尾,以飛氘的幾句話結束吧,他完美提煉了科幻美學的靈魂內核。在談及電影《流浪地球》讓他感到最不過癮的部分,並非所謂的情節或特效,而是“地球在無際長夜中默默前行的鏡頭太短。如果可以,我想久久地凝視這小小的蔚藍色行星,看著它在千萬簇幽微火焰的推動下,遲緩而堅定地告別故鄉。是的,太陽完了,太陽系完了,可是,地球還沒完。我們要用笨重可笑、破破爛爛的設備,拖拽著遍體鱗傷的母星,逃向新的家園。請不要問為什麽,這就是生存意志的最後表達。”
《流浪地球》是中國電影工業美學的勝利

“
饒曙光,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研究員(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1985年開始從事電影研究,主要研究領域為電影美學、中國電影史、當代中國電影電視、影視與大眾文化等。出版了二十多部譯著和專著,主要有:《中國文學理論》《新時期電影文化思潮》《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史》《中國少數民族電影史》《博影而思--饒曙光文集1、2、3、4》。現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電影通史》(首席專家)。

《流浪地球》拍攝用了四年時間,加上購買小說版權在內的籌備時間應該是超過了六年,它的上映,被認為是中國科幻電影的“里程碑”。回顧中國科幻電影發展的歷史,確實是讓我們感慨不已,往事並不如煙甚至是“往事不堪回首”。
中國科幻電影的起步貌似時間上也不晚,上個世紀剛剛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就有了科幻電影《珊瑚島上的死光》(拍攝於1979年,公映於1980年),曾經給人們帶來了中國科幻電影的“一線光明”。之後我們也出現過《大氣層消失》(據說當時的成本才40萬人民幣),以及大量的具有軟科幻元素的電影。但所謂硬科幻電影,一直以來都是中國電影人的期盼,同時也是中國電影人的“隱痛”。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時候筆者寫過一篇文章,在分析中國為什麽難以拍攝出真正意義上的科幻電影時,曾經指出過幾個原因:首先還是與我們的社會發展水準與個人的生活境遇、體驗分不開。那個時候我們還在竭盡全力解決溫飽問題,我們的想象力難以一下子就從“生活層面”跨越上升到“人類層面”“宇宙層面”。其二,中華文化是深深植根於農業、農耕文明,基因也好,無意識也罷,都不可避免地帶有農業、農耕文明的烙印。
雖然儒家主流文化“不語怪”“不語神”,但民間文化卻恰恰相反,對“神怪”可以說是極其鍾情迷戀,大約在小時候就通過故事、評書、戲曲的方式植入到了孩子的心理,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文化無意識”。《西遊記》《封神演義》《聊齋志異》作為魔幻小說的代表,可以說是伴隨著每一個中國孩子的成長……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魔幻類型電影,無疑是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中的類型拓展(不能說是新類型,因為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已經有,後來甚至是泛濫成災),成為中國電影的“類型增量”,為電影市場的繁榮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還有人進一步分析說,農業、農耕文明只能產生魔幻電影而不能滋長科幻電影。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艱苦創業與社會進步,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已經從10%左右達到60%左右(2008年年底城鎮化率為59.58%),整體性的社會形態也早已經從傳統的農業、農耕文明、文化跨越到了工業文明、科技文明、信息文明,因此我們終於誕生了以劉慈欣為代表的科幻文學,並且得到了國際科幻文學界的專業認可和推崇。
但是,科幻小說並不能自動生成、轉化為科幻電影,之前《三體》項目的倉促上馬及其“不知所終”,真的讓我們很糾結很揪心。可以說,《流浪地球》能夠有今天,是文明轉型、科幻想象力、電影工業體系及其技術水準、能力“綜合實力、綜合國力”合力形成的一個結果,水到渠成,渠成水到。毫無疑問,《流浪地球》是中國電影工業化的勝利,也是中國電影工業美學的勝利。六年的時間,六千多人的團隊,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一把辛酸淚誰解其中味”……包括科幻電影在內的電影,永遠也都不止是技術、不止是高科技、不只是視聽奇觀,而必須有好的故事、飽滿的人物、溫暖的情懷、幽默的語言,尤其是能夠與觀眾建立起對話溝通互動交流的渠道並且最終形成“共同體美學”。

電影除了商品屬性更有文化屬性、審美屬性,以及更重要的意識形態屬性。一部電影,首先必須要有大創意,否則巨額投資、高新技術、視聽奇觀都有可能成為沒有“1”後面的“0”。中外電影史上,缺乏好的創意、好的故事,巨額投資、高新技術歸於零或者說血本無歸的案例真的不只是個案。有了好的創意尤其是大創意,加上創造者人生經驗、積澱、情懷、境界的呈現和表達,並且最終與接受主體也就是觀眾群體形成“共同體美學”,一部電影才能在口碑上以及市場表現上無往而不勝。

關於《流浪地球》產生的社會基礎、文化語境、文學內涵以及電影工業、技術保障,筆者認為,《流浪地球》更是在一個正確的時間出現的更正確的電影。《流浪地球》不僅對於中國科幻電影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開創了中國科幻電影的新紀元、新景觀,而且作為中國電影升級換代尤其是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的標誌性作品,對於中國電影高質量可持續繁榮發展的意義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地顯示出來。從海外尤其是好萊塢對《流浪地球》的關注和評論我們也可以看到,《流浪地球》的想象力、創作和製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大幅度提升了中國電影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軟實力。
毫無疑問,近年來中國電影工業化推進、布局、完善出現了加速度的態勢,各種硬體設施建設、技術條件及其保障有效提升,可以與好萊塢正面抗衡也就是打“陣地戰”的“重工業電影”作品開始不斷湧現。但從整體上來看,中國電影工業化體系、工業化標準、工業化流程都仍然處於建構過程中,升級換代的任務依然是任重而道遠,與好萊塢電影大創意與工業化生產無縫對接相比仍然有比較大的差距,萬萬不可盲目樂觀,自我膨脹。客觀地說,《流浪地球》並不是一部完美無缺的電影,我們現在可能更多的是“鼓勁”而不是“泄氣”,畢竟“氣可鼓而不可泄”。或許,真正從建設性意義來說,認真分析、指出影片的某些不足更重要,更有利於中國科幻電影的質量提升、品質保證、可持續繁榮發展……

看《流浪地球》:中國科幻不再流浪
“
超俠,科幻、少兒作家,中國作協會員、中國科普作協會員。主要作品有《少年冒險俠系列》《深海驚魂》《決勝時刻:狙擊手們的戰爭》《小福爾摩斯》等,編劇作品有《高手》《皇城相府》等。作品多次獲得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

大年初二,我和家裡除了沉迷於打麻將的親戚們,一起去看了中國第一部重工業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儘管之前有種種的期待,也有種種的懷疑,當我在銀幕上看到將劉慈欣原著中宏大壯闊的科幻構想淋漓盡致地展現在面前時,禁不住懷疑,我們中國真的能拍出這樣的片子嗎,這真是我們中國人拍出來的嗎?儘管與好萊塢最先進的科幻大片還有一定的差距,但這部作品,已然突破了中國過去所有科幻片種種壁壘,它是如此天氣萬千,磅礴壯麗。這確確實實是一部有著好萊塢科幻大片氣質,卻又是純純的擁有中國人思想和內核以及文化底蘊的中國科幻大片。
隨著這部片子從排片量第四,逆襲為春節檔票房冠軍,除了本身片子過硬的質量外,還有眾多科幻迷、科學迷的推波助瀾,自發的宣傳,四處打Call,因為這部片子讓一個曾經被認為是小眾的群體——科幻迷們揚眉吐氣。而這時候,我們終於發現,熱愛科幻的人群,並不是小眾,有中科院院士,也有街頭小販,有八九十歲的老人,也有才剛剛會認字的小孩。科幻,科學加幻想,它是那麽純粹,但它又無處不在。因為,它代表著,人類在想象力方面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流浪地球》是中國熱愛科幻人群的井噴,是科幻迷的一次狂歡。
從此,中國科幻將不再流浪。

是的,中國的科幻壓抑了太久,不但是科幻電影,也是科幻小說,以及那些熱愛科幻的科幻迷,那些窮困潦倒的科幻作家,他們終於看到了曙光,也看到了中國科幻的崛起,科幻的崛起,是國家科技力量、國民素質提高的表現。曾幾何時,科幻在中國的土地上風靡一時,也有不少兒童科幻片大獲成功,比如“70末”“80後”都看過的《霹靂貝貝》《珊瑚島上的死光》《大氣層消失》等等,但20世紀80年代末,科幻作品慘遭打壓,中國人的想象力,被壓製得太久太久,20世紀90年代,唯一能夠發表科幻的雜誌,大概只有《科幻世界》。當我們看著好萊塢的《超人》《星際大戰》《大西洋底來的人》等科幻影視時,情不自禁被吸引,癡迷其中,但也逐漸認可了中國沒有科幻,中國人在科學上是沒有想象力的。許多科幻作者甚至從來不用中國人的名字進行科幻創作,認為那太過突兀和滑稽。
科幻原本就是建立在現實科學上的幻想,它不能如玄幻奇幻那般天馬行空,毫無科學依據,也不會像沉悶的科普作品那樣只有知識的堆砌,無法打開想象的翅膀。它是用科學的長線,放飛想象的風箏,無論風箏飛得多高多遠,都要有科學自洽的邏輯來牽連現實。《流浪地球》的原著小說,本身就是一部具有氣勢雄偉、震撼想象力的科幻作品,它的科技創意,是獨一無二,中國式的。要在銀幕上呈現,也必須有足夠高、足夠強的電影工業技術,才能將小說的文字完美地展現出來。經過郭帆導演團隊四年的努力,那些好萊塢電影裡出現過的世界末日以及科技產品,終於由中國人靠自己的方式和手段,完成度很高地成功實現。我們興奮地發現中國也有如此高明的科幻構想,更有能夠實現這些科幻構想的技術手段。這非但代表了中國人科幻想象的進步,也告訴世界,中國的電影在進步,可以不亞於好萊塢。

《阿麗塔:戰鬥天使》劇照
相比之下,好萊塢創意的枯竭與靈感的匱乏是顯而易見的。好萊塢的科幻片,已經越來越隻流於表面,我們無法看到他們獨一無二的科學創意和科學構想。因為無論多麽花哨多麽華麗的畫面,如果缺乏具有哲學性、具有深度和令人拍案叫絕的創意,它將會變得空洞而蒼白。但科幻創意的產生,除了因為科學的突破而引發的靈感外,還需要有對科學、對人文、對想象力的合理應用的天才,電影工業培養不出這樣的靈感來源。好萊塢沒有劉慈欣,也沒有更具有突破性的編劇和作家。反觀最近與《流浪地球》一起上映的,由卡梅隆監製、羅德裡格茲執導的《阿麗塔:戰鬥天使》,這部科幻片的電腦特技、細節、CG動畫,都比《流浪地球》高出不止一個檔次,然而其中的科幻內核,以及哲學思考,甚至情感的感動,都遠不如《流浪地球》。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一部成功的科幻大片,不但需要優秀的製作團隊和電腦特效,更需要一個絕妙的科學構想,需要更具邏輯,前所未有的科幻故事。故事是電影的靈魂、而故事的靈魂之源,來源於絕妙的創意,特別是科幻片,需要的不但是科學上的前沿想象,也需要文學上的人文幻想。源於劉慈欣原著的《流浪地球》,提取了劉慈欣小說的內核思想,並賦予了一個中國式的親情、感動,以及聯合全世界,集體戰勝困難的故事,這就是它引發了全中國人,甚至全球華人觀影熱潮的成功之處。

當然這部片子的成功也引發了種種爭議,包括對演員的,包括對裡面的科學邏輯硬傷,甚至是對其中的劇情轉折的。除去很大一部分沒有邏輯的亂罵之外,有不少真正的理智的科學家,確實提到了其中關於“點燃木星”“火石運輸”“交通運輸車”等方面有種種不合理之處,包括讓地球變為太空飛船,將要損失地球表面物質等等,這些問題說得有一定道理,但科幻並非是死板的科學實驗,它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思想實驗,曾經有一句哲學名言說的是:“當一位傑出的老科學家說什麽是可能的時候,他差不多總是對的;但當他說什麽是不可能的時候,他差不多總是錯的。”這就是科學與科幻的區別,科幻只是借助科學,呈現一種合理的可能性,科學則要找到種種可能性中唯一的確定性。除了科學硬傷引發爭議外,劇情以及台詞對白,還有進步的空間,包括人物性格的塑造,許多地方與好萊塢電影的劇情流暢度相比,還有差距。
總體來說,這是一部成功的,必將載入中國科幻史冊的科幻電影,它開啟了中國科幻大片之門。而科幻大片的成功,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一個國家科技進步、文化自信、教育水準提升的重大標。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整天沉溺於宮鬥,沉溺於整人與被整,沉溺於小鮮肉時,這樣的國家和民族,必將毫無前途和希望。當我們為了生活瑣事而煩惱,為蠅頭小利而苟且時,為何不能仰起頭來,看看美麗的星空,想想無限廣袤的宇宙,我們只是地球上的一個點,而地球,只是銀河系的一粒微塵,而銀河系在宇宙中,隻怕連微塵都算不上。可是因為有了科學,有了哲學,有了思想,所以有了科幻,我們能夠以思維探索的方式,來到宇宙邊緣,看到更多的宇宙和世界,那麽,為什麽,我們不能心胸開闊地微微一笑呢?
END
策劃/范黨輝
視覺設計/李羿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