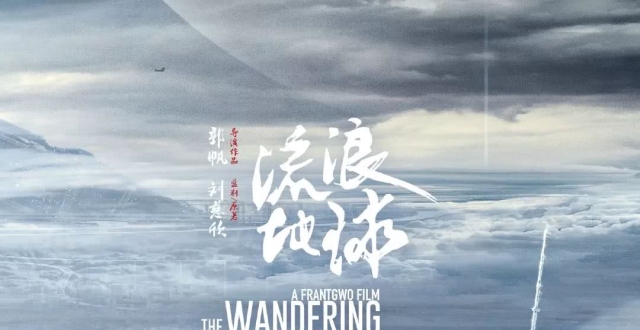最近,《流浪地球》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毋庸諱言,《流浪地球》的評價有家國情結的加持。
其實,《流浪地球》未必有多少家國情懷。好萊塢電影中美國人拯救世界,是為了美國國內市場,中國電影中,自然也是中國人拯救世界,沒其他國家什麽事,甚至被用來襯托中國人,這是正常的市場策略。
此外,吳京的意識形態色彩是自帶的,電影情節並未過多強調家國主義。所以,家國情懷很大程度上是粉絲、輿論自己加戲,電影的價值觀色彩被過度演繹了。
這並不奇怪,因為中國人懂科幻的很少,自然也不會從科幻角度去討論,而是強拉入自己熟悉的領域。於是,最初源於一個工程師頭腦中“太陽災變人類該怎麽辦”的頭腦風暴,在輿論中扭曲、發酵,變為了中國人“重土安遷”,變為了中國方案。不過,要想客觀理性的討論,還是先需回到本源。
一,20年前,中國也曾迎來“科幻元年”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中,中國科幻曾經有過短暫的黃金時期,之後,隨著科幻被視為“精神汙染”而陷入沉寂。此後十幾年中,《科幻世界》是唯一發表科幻作品的平台。
1999 年,高考作文的題目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同一年的《科幻世界》上正好有一篇相關內容的短篇小說。於是,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家長蜂擁而至,2000年,《科幻世界》的發行量激增到每月36萬份。
這是中國科幻繁榮的元年嗎?並不是。隨後,《科幻世界》的發行量逐年下降,2010年降到了16萬份。這個時候離三體獲獎,還有5年。
《三體》的流行,首先當然是因為它是一部優秀的硬科幻小說,但某種程度上,其在中國的流行,與科幻沒有多大的關係,而是中國互聯網創業潮的產物。
降維打擊、黑暗森林,這些理論的商業化解釋與應用,通過互聯網領袖的社交媒體,極大地促進了小說的傳播,使讀者從傳統的科幻讀者延伸到了更廣泛的讀者群體中,奠定了其在中國的名聲,然後向外傳播,最終反過來形成更大的影響力。

所以,《三體》的流行是一個互聯網現象。就如當年《假如記憶可以移植》讓《科幻世界》一時洛陽紙貴,只是一個高考現象。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當年的科幻熱是家長們的功利之舉的話,那麽,如今的三體何嘗不是另一種功利呢?這種功利,無非是家長變為創業人群,變為白領的知識焦慮,以及追隨短暫的流行文化而已。當然,互聯網創業潮本身也是工業化的產物,而工業是科幻的土壤。
但無論如何,中國硬科幻小說的閱聽人基礎薄弱是客觀存在的,科幻小說要有技術審美能力的門檻,如果不明白3K背景異塵餘生與宇宙的關係,就無法明白為什麽小說中的人物會因為背景異塵餘生閃爍而崩潰,反而會認為,天空閃爍算什麽,玄幻小說中道友渡劫那才叫天翻地覆。
但是,技術審美與教育有關,而中國的本科率才僅僅4%。所以,說今年是科幻電影元年或許不為過,但中國科幻是否要就此崛起,恐怕答案並不樂觀。
一個可以印證我這個觀點的現象是,劉慈欣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現象級作家,大眾還知道的另一個科幻作家可能是因為《北京折疊》獲獎而聞名的郝景芳。但是,中國科幻圈內的另一些長期持續創作的知名作者,比如與劉慈欣並稱中國科幻三巨頭的王晉康與何夕,在普通大眾中,仍然籍籍無名。
何夕的《傷心者》《六道眾生》,王晉康的《生死平衡》《七重外殼》《水星播種》都是非常優秀的科幻小說,與《流浪地球》相比,也不遑多讓。實際上,在電影之前,就連劉慈欣的《流浪地球》《鄉村教師》也並沒有多少人讀過。
所以,作為一部硬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引發熱議,但卻很少有人從科幻角度去談,太多的借這杯酒澆自己胸中的塊壘。雖然這有其必然,但從科幻角度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那麽,作為一個科幻小說愛好者,也為一個專欄作家,我權且拋磚引玉,希望在價值觀爭論之餘,引入更專業的討論。
二,說《流浪地球》是偽科學,言過其實了
科幻小說一般分為軟硬兩類。如果把軟科幻放在光譜的左端,最左邊的,應該是類似哈利·波特這樣的奇幻小說;星際大戰、銀河英雄列傳這類,儘管有了太空與科技,光劍與雷射,但僅僅是一個背景而已,也是典型的軟科幻,被稱為太空歌劇;《三體》、《基地三部曲》、《太空奧德賽》這一類小說,技術深度參與到情節發展中,則屬於硬科幻。劉慈欣的小說,在科幻的光譜上,已經接近最硬、最技術化的一端了。
人們對於硬科幻有兩種誤解:一種是只要不符合現有技術,就是偽科學。當年科幻被視為精神汙染,正是出於這種偏見。另一種誤解是只要是科幻,隨便怎麽幻,都是可以的。這兩種誤解,可以同時存在一篇文章中。
就有科普人士侃侃而談:科幻小說要設立科學顧問,防止偽科學,同時又說,“允許有虛構和文學化想象,這與武俠片裡飛簷走壁的輕功具有相似功能”。也有教授洋洋灑灑指出《流浪地球》的很多技術漏洞,視為偽科學。
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
超光速是偽科學嗎?的確是的,但是,把科幻的“科”,等同現有技術,這會壓抑科幻的空間。而把科幻的“幻“當做了奇幻的幻,又會降低了硬科幻的品質與魅力。這兩種誤解,有濃重的歷史痕跡。
長期以來,在官方話語體系中,科幻的地位一直不高,甚至一度被視為精神汙染,所以專業性缺失,大眾無法正確理解,即便在今天,也並不令人樂觀。這兩種誤解,必然體現在《流浪地球》電影以及後續評論當中。
比如,在流浪地球的劇本中,一開始就說木星引力增大,以及後面的點燃木星瑕疵,均是出於編劇缺乏對硬科幻範式的理解與尊重。同樣的,批評者認為,地球根本不可能推動,這是偽科學,同樣也是出於對硬科幻的誤解。
這兩個誤解會限制中國硬科幻電影、評論的發展,以及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阻礙中國硬科幻電影的進步。這個基礎性的方法論問題,值得被認真討論。
三,科幻科幻,“科“在何處,“幻“在何處
硬科幻小說中除了人文思考與文學性,還需要科學與幻想。與奇幻不同,“科”與“幻”應有邊界,遵循一定的範式,從而達到邏輯自洽。硬科幻小說的一般模型,可以用下圖表示:
硬科幻,不但有作為“幻”的構想的新技術,還有作為“科”的技術推理過程,後者是硬科幻小說獨具的技術審美魅力。比如,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定律,是“幻“的範疇,但由此進行的邏輯推導,卻屬於“科”的範疇。
同樣的,著名的“黑暗森林“理論之所以精彩,是因為它有著較為嚴格的推理過程。所以,科幻小說的範式以及評價硬科幻小說,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第一,幻想上要自洽。幻想的對象可以是新技術,也可以是新規律,甚至是新的物理、數學規律、常數發生變化,甚至1+1=3。物理、化學、生物等理工科之外,也可以對社會、經濟領域進行幻想。幻想不必符合科學原理,但卻要整體自洽,符合小說的整體世界觀。
比如,在《三體》中,雲天明的攻擊方式是改變引力常數。因為小說中本身就存在神一樣的文明,所以,改變物理常數與小說本身的世界觀是吻合的。再比如,在《計算中的上帝》中,一隻巨手包裹住了爆發的超新星;上帝射出的一束光使三個不同星球種族的DNA聚合。這些設定儘管都屬於超級技術,但與小說的世界觀是自洽的。
再來看《流浪地球》,電影一開始,《流浪地球》就毫無必要地犧牲了“幻”的世界觀來自洽。從世界觀上看,在《流浪地球》中,人類之所以這麽慘,或者說,小說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沒有神級技術,但劇本毫無解釋地引入了 “木星引力突然增大”,這個明顯違背常識的情節,導致了世界觀衝突。
“木星引力突然加大”,可以用“整個太陽系突然進入了引力異常區”去作為交代,但是,這屬於神級奇跡,放在《三體》中可以,放在《深淵上的火》中也可以,但放在《流浪地球》中就與世界觀發生衝突了。
其實,避免這個錯誤,也就一句字幕的事,比如改為:“受病毒影響,多台發動機停機,地球進入木星撞擊範圍”。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劇本幾乎沒有“硬科幻的‘幻’需要在世界觀上自洽“的概念。
當然也可以不用衝量定理。比如,王晉康在《天年》中,就引入了一種新的物理規律,即宇宙是由量子纖維組成,一旦破損就會扭曲空間,移動巨大的天體。這相當於替代了衝量定理。但是,這顯然也屬於神級技術,與世界觀不自洽。
第二,科學上要合理。硬科幻不等於一定不脫離現有技術。但如果技術過程是已知原理主導的,則要求過程有科學上的合理性。比如,在《三體》中,用核彈推動光帆飛船,雖然人類的技術現在達不到,但其原理光壓、衝量是合理的。
遺憾的是,《流浪地球》劇本為了追求反轉,犧牲了“科”的合理性。
電影需要 “危機——解決危機——失敗——絕處逢生”這樣反轉,所以,電影設定了點燃木星推動地球。這是一個衝量過程,更多地屬於 “科”的範疇,應該更嚴謹。但是,劇本完全拋開了定理,數值上的bug顯而易見,而劉慈欣小說又以技術過程中的技術審美著稱,這就產生了違和感。
四,科幻小說自洽與合理外,有一些例外原則
當然,科幻小說畢竟是小說,不是論文,自洽與合理都可以有例外。
第一,“科”範疇的推理過程,可以退而求其次,達到“接近合理”即可。我個人覺得,所謂接近合理,即需要查資料、動筆推算,才能發現的瑕疵,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望即知的錯誤是低級錯誤,硬科幻小說、劇本都應該盡量避免這一點。
第二,基礎框架的“科”範疇的技術設定,可以免於審視。在這個框架之下,離框架越近的技術設定,技術過程就越要嚴謹,遠一些的,則可以忽略。
比如,時間穿越這個技術設定,作為一部小說的初始邏輯基礎,應該免於審視,否則,多數小說都無法成立。
在《流浪地球》中,最主要的框架是行星發動機推動地球,這也存在地球地質結構經受不住、發動機推力不足等問題。這些問題本質上和點燃木星類似,但是,這屬於小說的基本框架、邏輯起點,應該免於審視。而且,這個瑕疵已經在普通人“動筆”這個底線之上。
再比如,《火星救援》小說以精確的數字聞名,對植物生長的數據、對航天員所需的水、電量、熱量都是有精確計算的。但是,相對來說,從地球到火星的大飛船的技術參數,中國飛船與美國飛船的銜接等問題,技術推導就少很多了。
行文至此,基本上可以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了:為什麽儘管行星發動機推不動地球,但是這個設定卻是精彩絕倫的。而木星引力突然增大,點燃木星推動地球的設定,卻是一個不應該犯的錯誤。
第三個例外是,作為背景的經濟、社會設定是可以忽略的。價值觀的角度,在科幻小說,特別是硬科幻小說中,比一般小說處於更次要的地位。
比如,在一個反烏托邦社會中,人民被奴役,就無需追問為什麽沒有反抗。所以,流浪地球的超級工程是否會引發經濟的崩潰,抽簽是否符合道德等議題,其實是可以忽略的。
科幻電影中出現這種場面,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這是人類文明緊急狀態的必然。實際上,美國人1998年拍的《天地大衝撞》也是采取的抽簽制度。糾結這些問題,往往是因為對技術審美無感,而強拉入價值觀範疇。
《星河戰隊》這部電影很多人都看過,很多人會覺得制服很像納粹制服,其實,其原著小說,即海因萊因的《星際傘兵》,講的就是人類擴張,殖民其他星球而遇到抵抗的故事。至於小說中的公民權需要爭取,更是政治不正確。但不可否認,這仍是一部好的科幻小說。
當然,並不是社會與經濟不重要。實際上,它們可以作為科幻的主體框架,這個時候當然就不能免於價值觀的審視。1993年雨果獎的獲得者《深淵上的火》就構造了一種三個個體共同思維的智慧物種,並構造了其文明的圖景。
在《三體》中,也有對三體人的社會的幻想。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中,也是對社會過程進行了“幻”的設定,“心靈歷史學”發人深思。實際上,劉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則對宇宙文明的抽象化就有“心靈歷史學”方法論的影子。
五,硬科幻電影《流浪地球》有明顯bug
有這些方法論幫助厘清“科與幻的邊界”,我們就可以去審視硬科幻電影了。
在《星際穿越》中,為了實現人類完全無法達到的星球,作者幻想了外星人放置的蟲洞的情節,這屬於“幻”。但從蟲洞出來之後,黑洞的模樣、黑洞引發的潮汐以及雙生子佯謬,都是嚴格按照已有的物理知識進行推理、構造的,這屬於“科”。
這正是科學顧問所做的事。由此可見,科學顧問不是用來限制所謂“偽科學”的,科學顧問沒有限制作為“幻”的這一部分的蟲洞穿越,而是幫助在“科”的這一部分更嚴謹。
電影在最後為了實現父親與女兒的通訊,又引入了從高維空間跨越時空的引力。這是改變了物理推導過程,但這在有著能夠放置蟲洞、構建高維空間的神級文明存在的世界觀中,是邏輯自洽的。
所以,《星際穿越》的幻與科,天馬行空的想象與嚴謹的推理同在,是一部優秀的硬科幻電影,也剛好契合筆者本文提出的硬科幻範式。
再來看《流浪地球》。正如前文所說,在一開始的“木星引力增大”中,劇本失掉了“幻“的世界觀自洽。在結尾的時候,又為了追求反轉,在點燃木星中,失掉了”科“的合理性。前者是非常輕率的,因為完全可以用發動機集體損壞作為理由。而後者,則有本質上的困難。
這源於硬科幻本身的限制:在沒有神級技術,只有既有技術的前提下,要達到絕地逢生的反轉,在幾分鐘內改變兩個星球的路徑,這本身就超出了嚴肅硬科幻力所能及的範圍,恐怕要修改整個故事。如果編劇對硬科幻有正確的認識,可能我們看到的故事就不一樣了。
其實,同期的《瘋狂外星人》結尾時,就是一個典型的硬科幻反轉。外星人附體是作為“幻“的一部分,而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是屬於“科“的既有原理,最後條件反射喚醒原本的猴子的意識,這是一個技術推理過程。作為電影,這是一個合格的硬科幻反轉。所以,對於硬科幻來說,劇本對於科幻的認識非常重要。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轉是克拉克的《星》。聖誕樹頂都有一顆星,在《馬太福音》等宗教書中,這顆星叫伯利恆星,是與耶穌一起誕生的,有科學家認為,伯利恆星是超新星爆發。
根據這個科學假說,克拉克創作了小說《星》,前去考察的宇宙飛船上的隨船牧師,在描述了一個文明預知超新星爆發所做的最後徒勞掙扎之後,最後一句是:“神啊,你有億萬顆星辰可供驅遣,何以偏偏選上這一顆?你用大火斷送了整個世界的人,就只是為了照亮伯利恆的早晨?“這是一個精彩絕倫的、震撼性的、巨集大的且合理的反轉。
《流浪地球》在“科”的範圍內失掉的嚴謹性還有很多例子。比如人推人的方式;為什麽火石那麽多,卻沒有就近布置;一把大火燒掉人工智能等。最後一個場景讓我想到了科幻電影史上經典的一幕。
《流浪地球》中的人工智能Moss的紅燈,是在向克拉克原著、庫布裡克導演的《太空奧德賽:2001》中的人工智能HAL致敬。順便說一下,HAL三個字,是對IBM三個字母的移位得到的。HAL同樣也被人類殺死了,但卻不是死於一瓶伏特加。
在電影中,人工智能HAL是負責飛船的一切的,後來航天員發現HAL殺人,就要毀掉HAL。怎麽毀呢?他躲過HAL控制下的重重機構,進入核心部位,一塊一塊地抽掉電腦板塊,這時HAL沒有機械可控制了,但還通過對話在勸說他,隨著板塊的抽出,HAL的語言越來越慢、越來越混亂,紅燈也慢慢黯淡下去,最後沒有聲音,燈也滅了。
這個過程暗示著HAL的運行原理是大規模的並行運算,毀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仍然能運行,直到低於一個閾值。對的,現在大熱的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正是基於並行運算的。《太空奧德賽:2001》拍攝於1968年,被譽為當之無愧的現代科幻電影技術的里程碑。
連劉慈欣都在說:“我所有的一切作品都是對阿瑟·克拉克最拙劣的模仿”。當然,這只是他的自謙之詞。
其實,好萊塢壞的例子也很多。在電影《獨立日》的情節中,電腦病毒竟然戰勝了外星人。根據常識,同為“馮·諾伊曼型結構”的電腦,安卓、蘋果,PC之間的病毒是不通用的。人類電腦的病毒能在外星人的電腦上發揮作用,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壞的技術推理過程。
硬科幻電影不存在偽科學一說,“幻”這一部分可以天馬行空,但“科”這一部分,卻需要循序硬科幻小說的幾個原則。
劉慈欣本身是很反感漫無邊際的幻想的。他舉了個例子——曾經有一位導演問他,按照劇本中的技術設定,從地球到木星要航行多久?他回答,至少要半個月。
導演又問,能不能再快點?比如用時空跳躍的方法直接到達?面對這個問題,劉慈欣回答問題的聲音都提高了:“可是,時空躍遷是一種超級技術啊!這種技術一旦誕生,改變的就不單純是從地球到木星的航行時間了,整個人類社會、人類文明都會發生改變啊!”
他解釋了他為什麽會激動,他說:“所謂科幻的思維方式,是指要把整個世界構建在一定的科技層次之上,這個世界是自洽的,是有一套自我邏輯的。”
其實,我覺得流浪地球劇組根本不需要科學顧問,有劉慈欣就夠了。專家雖然專業水準更高,但卻而不可避免的帶有對硬科幻的兩種誤解。科學家與科幻小說家是兩個不同的專業。
劉慈欣的小說對硬科幻的原則遵循得非常好。他的小說既恢弘瑰麗,又充滿各種奇思妙想的技術細節,已經是世界頂尖水準。雖然這些想象未必都正確,但都是在一定的技術範疇內進行的。
比如,《三體》中著名的納米絲切割船體情節。科技設定是納米絲,但推理過程卻是實實在在的物理過程:納米絲細、強度大,因而造成的壓強大,所以可以起到切割作用。
劉慈欣的小說有非常嚴密的邏輯,他連納米絲的墊片都想到了。因為納米絲對船的壓強大,同樣的,也沒有已知的材料能扛住納米絲的壓強,固定納米絲。所以,劉慈欣在已有的技術設定中,構造出納米絲(“有一些同類片狀材料可以墊片”)。這就是硬核科幻。
如果劉慈欣拋出神奇女俠的鞭子,或者鋼鐵俠的盾牌,或者突然發現一種堅固的材料,那就不是一個好設定。再比如,在《三體》中,面壁者的計劃之一就是用核彈炸飛水星,減速水星,使之墜入太陽,這個過程屬於衝量定理,但整個過程充滿了技術審美。
硬科幻的這種技術審美,甚至會反過來推動技術。比如,克拉克是第一個提出全球同步衛星的,而如今NASA也會找未來學家、科幻小說家去做谘詢。甚至於科幻作品中的產品形態會影響現實產品的發展。
比如,透明螢幕。透明螢幕其實從來不是真實的產品需求,人會用黑板、白板,但不會有人用透明玻璃當演示板,因為後面的物體與光線會產生干擾,但在科幻作品的影響下,人們都認為未來的產品就是這個樣子的。
對真正的科幻小說愛好者而言,劉慈欣小說的魅力,正是源於這種合理而恢弘的想象。說劉慈欣以一己之力提升了中國科幻,小說中這種對技術推導過程帶來的審美愉悅,佔了很大一部分。也正因為如此,在真正的科幻群體看來,《流浪地球》的錯誤特別讓人感覺到一種違和感。
這一次觀眾是用“中國人自己的科幻大片“”中國硬科幻元年”的地位來呵護《流浪地球》的,但是,第二部,第三部就不會有這個待遇。中國硬科幻應該在情節、劇本上投入更多。
實際上,這部片子能夠成功,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劉慈欣的基礎設定,所以,只有尊重原著,尊重這樣的智慧,中國科幻電影才能走得更遠。
可以想見的是,隨著電影的成功,劉慈欣的話語權會越來越大,後續改編電影在“幻”的自洽性與“科”的合理性上,都會有較大的提升。
六,《流浪地球》一邊倒好評的公共價值在哪裡
人類對技術的追求根植於作為自組織系統的人類發展的熱力學方向,這更加符合人類進化路徑的審美——比起家國主義、精忠報國,具有更高的審美價值。
但是,即便如此,強調純粹的技術之美,強調人類對技術無止境的追求,並不能越過道義的審視。所以,在硬科幻電影之外,價值觀的評價是有其意義的。
電影在兩次意義上完成藝術的生命。第一次是電影本身,第二次是電影引發的評價、發掘。無論褒貶,無論其在作者、導演本身的意圖之中,還是朝著始料不及的方向,都可以在更大層面、更深意義上完成電影與社會的互動,從而形成電影的藝術意義與社會意義。
劉慈欣可以稱為工業黨,在單純的字面意義上,這並非一個貶義詞。當然,應該看到,隨著社會化分工與科學的進步,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依賴於國家提供的財政預算支持,某種程度上,這使他們傾向於巨集大的國家敘事。這就造成了“工業黨”與觀眾敘事的第一波合流。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個脆弱行星的另一面,劉慈欣的這個思想內核,體現在《三體》中,並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解讀。
2013年時,美國科幻作家LarryCorreia認為,雨果獎受到美國科幻界“政治正確”氣候的影響,偏向獎勵女作家、年輕作家、少數族裔作家,使得部分白人保守派的作家和作品完全被忽視。所以他發起了名為“悲傷小狗”的運動,爭奪白人保守作家在雨果獎中的地位。隨後,悲傷小狗被Vox Day發展為“瘋狂小狗”。
《三體》中的一些描述契合了美國白人保守派科幻群體的意淫。甚至可以說,讓他們覺得遺憾的,“只是作者不是美國中年男性人”。隨後在瘋狂小狗的地下提名與刷票的支持下,《三體》獲獎。所以有人說:“《三體》是一個‘小狗式的勝利’。”
不得不說,這是圍繞《三體》的一個最大的誤會。或者說,《三體》在中美兩國獲得青睞背後的深層原因的差異,可能也孕育著新的矛盾。
但是,被忽略了的是,劉慈欣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寫科幻小說的知識分子。科幻小說價值觀中“科”的這一部分,在中美,乃至全世界都是互通的。
劉遠舉(專欄作家)
編輯 李冰冰 實習生 李文雋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