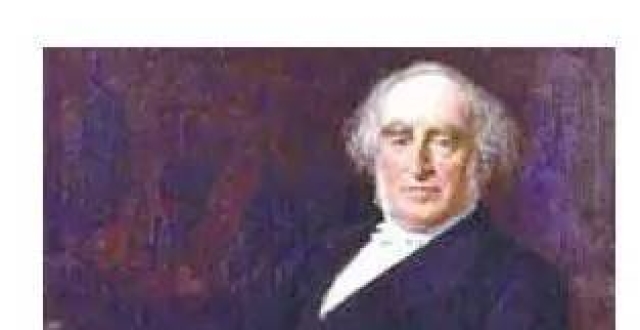隨著我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文學外譯出現了一些值得我們思考的關鍵性問題:中國文學外譯應該由誰來譯?是中國譯者、外國譯者還是中外譯者的合作翻譯?這三種類型的文學翻譯各有什麽特點?如何處理好文學翻譯與文化翻譯之間的關係?
原文 :《中國文學應該由誰來譯?》
作者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馬會娟
圖片 |網絡
國文學英譯的理想譯者
縱觀歷史上中國文化外譯的主體,可以發現,主要有三種類型的譯者模式:中國譯者的獨立翻譯、外國譯者的獨立翻譯和中外譯者的合作翻譯。這三種類型的翻譯因譯者生活的社會環境以及譯者的語言能力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點。從翻譯的國際慣例來說,譯者最好是譯入母語,也就是說,中國文學英譯的理想譯者應該是英語為母語的人士。

文學翻譯的關鍵是譯者譯入語語言的表達能力。翻譯家蕭乾先生認為,翻譯是三分理解,七分表達。但是,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母語是英語的譯者也存在著一個缺點,即他們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中的文化內容時經常會產生理解錯誤,導致文化誤譯。這使得一些專家和學者認為,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最好是中外譯者的合作翻譯。這是因為在合作翻譯中,中國譯者可以幫助外國譯者更好地理解文學作品中的文化內容,而外國譯者可以把好語言關,避免中式英語,保證譯文語言的地道和可接受性。對於以上觀點,我認為都有簡單化之嫌。如果不加以澄清,對國家或出版社選擇中國文學外譯的合格譯者會產生一定的誤導作用。
文學翻譯品質與譯者國別、翻譯模式無關
我以沈複《浮生六記》的三個英譯本中的譯例加以說明。

《浮生六記》是清末文人沈複的自傳體筆記,自20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受到了我國學界的歡迎。這本傳記目前有三個英譯本:一個是1935年出版的林語堂的譯本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一個是1960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Shirley M. Black的譯本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還有一個是1983年企鵝出版社出版的美國人Leonard Pratt(漢語名字為白倫)和台灣學者江素惠合作翻譯的譯本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這三個譯本恰好代表了中國文學外譯的三種類型:中國譯者(林語堂)的翻譯、外國譯者(Black)的翻譯和合作翻譯(白倫和江素惠),可以用來說明不同類型的譯者翻譯的特點。因篇幅所限,僅以三個譯本在傳達和再現原文的文化內容、文學語言的生動形象程度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我們看一下三個譯本的四位譯者對中國文化內容的翻譯是否準確。在卷一《閨房記樂》,作者談到自己晚上回家時,“腹饑索餌,婢嫗以棗脯進”。對於“棗脯”的翻譯,三個譯本的處理各有不同:林語堂的翻譯是“some dried dates”,Black的翻譯是“some dates and dried meats”,而白倫和江素惠的翻譯是“some dried plums”。很顯然,林語堂對這個詞的翻譯是正確的,而Black的翻譯出現了“dried meats”,是理解錯誤(將“脯”理解為“肉干”)和字字對應翻譯的結果。令人奇怪的是,白倫和江素惠將“棗脯”翻譯為“dried plums”(乾李子)。可見,林語堂的譯本在文化內容的翻譯上更為準確,而Black的譯本偶爾會出現一些因字面理解而導致的文化誤譯。中美譯者的合作翻譯除了文化誤譯外,主要採用了對文化因素的翻譯進行文外注釋的方法。

其次,讓我們看一下三個譯本在文學語言的形象再現上有什麽不同。還是在卷一《閨房記樂》,作者寫自己深夜歸家時,看到妻子燈下讀書的情景:(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醜末歸來,業已燈殘人靜。悄然入室,伴嫗盹於床下,芸卸妝尚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頸,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對於這段文字,四位譯者的譯文如下:
林語堂譯: She was bending her beautiful white neck before the bright candles, quite absorbed reading a book. (回譯:她低垂著優美、白淨的脖子,在明亮的燭光下,很投入地讀書。)

Black譯:She was sitting, in the light from a pair of tall silver candles, with her delicate white neck bent over a book, so completely absorbed in her reading that she was unaware I had come into the room.(回譯:她坐在那兒,在一對高高的銀燭燭光裡,低垂著優美、白淨的脖子,讀書,她如此認真投入,沒有注意到我走進臥室。)
白倫和江素惠譯:A candle burned brightly beside her; she was bent intently over a book, but I could not tell what it was that she was reading with such concentration.(回譯:燭光在她身旁明亮地燃燒著;她在投入地讀書,但是我不知道她那麽認真讀的是什麽書。)
對三個譯本進行閱讀比較,可以發現Black的譯文在語言表達上更為生動形象,在細節的再現上更為具體豐滿。漢英翻譯家劉士聰教授曾高度評價過Black翻譯的這段文字,“(Black的)譯文譯出了同樣的審美效果,句子組織勻稱、意義表達清晰”。可以說,在傳遞文學語言的審美形象方面,外國譯者的譯文比中國譯者的譯文、合作翻譯的譯文更具文學性,更好地再現了原作的文學審美特徵。
從以上例子來看,在回答中國文學外譯應該由誰來譯這個問題時,學界流行的一些觀點過於簡單化了。事實上,自中國文學外譯伊始至今,中國譯者、外國譯者和中外譯者合作翻譯這三種翻譯模式長期以來都是客觀存在的,它們都有可取之處,同時也存在著各自的問題。可以說,文學翻譯的品質與譯者的國別、翻譯模式無關,而與譯者的文學修養以及跨文化翻譯能力有關。對於任何譯者來說,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都是一項不完美的事業。任何譯本,包括上面提到的《浮生六記》的三個英譯本存在一些問題都是正常的。對於中國譯者的文學外譯,其譯本在文學語言的形象再現上存在一些問題是在所難免的。
文學翻譯要與翻譯文學、文化翻譯區分
此外,中國文學要成功外譯,還必須區分兩對概念:一是文學翻譯與翻譯文學,二是文學翻譯和文化翻譯。首先,文學翻譯不應該僅僅是將一國的文學作品(小說、詩歌、劇本)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更應該是文學(屬於翻譯文學),即翻譯的文學作品能夠恰到好處地再現原作的文學審美特徵,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如果說這很難實現,至少也應該成為中國文學外譯的目標。其次,中國文學要成功外譯,還必須區分文學翻譯和文化翻譯。這不僅牽涉到文學翻譯如何再現文學作品中的文化因素的問題,還涉及文學翻譯的目的問題。

下面我們仍以《浮生六記》中一個文化典故的翻譯為例。作者在談到自己不得不重操舊業時,使用了“不得已仍為馮婦”。這句話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翻譯:
林語堂譯:I was then compelled to return to my profession as a salaried man.
白倫、江素惠譯:I was obliged to be Feng Fu, and return to official work.
對上面兩個譯文中典故的翻譯,有學者曾這樣評論:“林語堂先生在處理這一典故時,僅將其引申意譯出;而白、江二人為了讓譯文讀者理解‘馮婦’這一典故,在書後加注……《浮生六記》之中還有很多這樣的文化含義很豐富的詞語,但在林譯中諸如‘蓬島’、‘沙叱利’等詞,或簡單音譯,或融入正文中加以解釋,全書注解僅有二十多條(白、江譯本有兩百多條注解)。由於相關注解的缺乏,原文的意思在譯文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傷。”以上的評論明確表示,林語堂對典故和含有文化涵義的詞語的處理不妥。給人的感覺似乎是注解越多,越能達到既保留原文的典故、意象等文化涵義豐富的詞語,又讓譯文讀者能夠理解的目的。但是,評論者似乎忽略了一個問題,即文學翻譯的目的是翻譯文學,而不是文化譯介,將文學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在譯文中作詳細、全面的介紹。

文學與文化密切相關。對文學翻譯中的文化現象進行注釋是正常的,但對於注釋到什麽程度,目前學界仍有爭論。德國學者霍恩比(Snell-Hornby)認為,對文化注釋的程度要依據翻譯的目的而定。從翻譯文學的文學性的角度考慮,文學翻譯中如果有過多的典故解釋,不僅容易打斷原文的敘述節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壞了讀者連續閱讀的興趣。所以,在談論文學翻譯中的文化注釋時,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注釋的多寡為標準來衡量和評價翻譯文學作品。文學翻譯和文化翻譯有著不同的目標:文學翻譯目標應該是“翻譯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而文化翻譯的目標是“譯介文化”,把一國的文化介紹給譯入語國家的讀者。孫致禮先生認為,“譯者並非為所有的讀者翻譯,而是為可能對作品感興趣的某個讀者群翻譯”。以再現文學性為根本的文學翻譯與以介紹原語文化為根本的文化翻譯,應該有不同的目標讀者群。

中國文學應該由誰來譯?答案應該是任何具有良好文學文化修養、具備跨文化適應能力的譯者。文學翻譯應該是翻譯文學,與文化翻譯的目標讀者不同。中國文化走出去是一個長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國家的支持,也需要對中國文學感興趣的譯者長期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