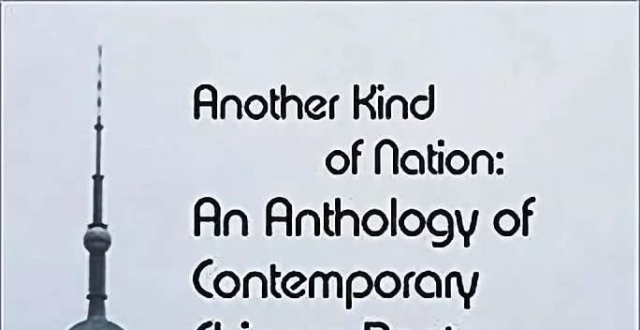作為西方漢學史上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理雅各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等經典翻譯成英文,並出版一系列著作,推動了中國文學文化在英語國家的傳播,在西方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19世紀英國漢學確立與發展的過程中,來華傳教士和外交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通過對中國的親身接觸和實地考察,翻譯中國經典,撰寫漢學著作,充當了中英文化交流的先鋒,為19世紀後半葉英國漢學的全面繁榮奠定了基礎。19世紀後半葉,英國漢學開始有了一定的突破和發展,促使了三位著名漢學家的誕生,理雅各(James Legge)、德庇時(John Davis)和翟裡斯(Herbert Giles)以各自獨樹一幟的學術建樹為英國漢學獲得世界的認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被譽為“19世紀英國漢學三大星座”。他們嚴謹的治學精神和豐碩的學術成果,在漢學領域獨領風騷。其中,作為西方漢學史上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理雅各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等經典翻譯成英文,並出版一系列著作,推動了中國文學文化在英語國家的傳播,在西方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為學數十載推動中西文化交流
理雅各是為英國漢學贏得國際聲譽的第一人,他的成就標誌著英國漢學從萌芽進入發展期的一個新高度。他是倫敦會傳教士,出生於蘇格蘭一個富庶的商人家庭,自小便聰慧過人,勤奮好學,有著極強的語言天賦和記憶力,1831年以第一名成績考入阿伯丁皇家學院,並獲得學院獎學金,四年後因表現出眾又再獲最高獎學金,以一人之力獲得兩項大獎是該校前所未有的,少年理雅各由此聲名鵲起。1835年他從阿伯丁皇家學院畢業,熟練掌握希臘語、拉丁語、數學、哲學等多門知識,這些都為他今後的漢學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理雅各於1838年加入倫敦會,被派往馬六甲傳教。在啟程前,他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漢語,投身於當時倫敦能找到的最好的漢學學者基德門下。1839年,理雅各以基督教傳教士身份前往遠東,任職於馬六甲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這裡,他努力布道傳教,兼管書院教育和報紙印刷的相關事宜,同時也開啟了自己數十年的漢學研究生涯。理雅各於1841年獲紐約大學名譽神學博士,並擔任了英華書院院長一職。1843年,英華書院遷至中國香港。此後30余年,除三次回英國處理事務外,理雅各一直在香港居住。在這裡,理雅各開始了他關於中國古代典籍的譯介工作,並從1861年開始陸續出版《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系列譯著。1873年理雅各返英,1876年就任牛津大學漢學講座首任教授,在此授課長達21年,開創了牛津大學的漢學研究傳統。在牛津任教期間,理雅各仍然筆耕不輟,繼續修訂完善已經出版的《中國經典》各卷。1897年,理雅各病逝於牛津,享年82歲。
在中國香港的數十年裡,理雅各不僅積極傳布教務,而且也投身於香港的教育制度改革、新聞出版事業和社會公益事業,成為一名慈善牧師、勤奮學者、教育家,以及公益事業推行者。他擔任了中國境內第一份中文鉛印出版刊物《遐邇貫珍》的編輯工作,其辦報理念和創新意識促進了中國報業走向近代化的進程。此外,他還推動了宗教教育向世俗化教育的轉向,改革了香港教育制度,推行了更符合社會發展的課程設定,因此也被譽為“香港教育之父”。
理氏譯本為中國典籍研究把脈
理雅各的最高成就在於他對中國學術的深入研究,以及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翻譯。理雅各認為,西方人要想了解中國必須從“十三經”入手,因為這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倫理道德的基礎。為了更好地傳教,他決定向西方譯介中國的經典。他曾說:“此項工作是必要的,因為這樣才能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們了解這個偉大的帝國,我們的傳教士才能有充分的智慧獲得長久可靠的結果。我認為將孔子的著作譯文與注釋全部出版會大大促進未來的傳教工作。”他最初是以傳教為目的開始了解和研究中國語言及文化體系,卻最終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偉業。
作為近代第一個系統翻譯介紹中國古代經典的外國翻譯家,理雅各從1847年擬定翻譯計劃開始直到1897年去世,在中國學者王韜的幫助下,歷經半個世紀,孜孜不倦地從事著這項偉大而又艱巨的工程,翻譯出版了數十部中國文化典籍,包括儒家、道家和佛教的諸多經典作品。譯著中不僅包括嚴謹簡潔的譯文,還包括研究性的導言和翔實的注解,故理氏譯本一出,轟動了當時西方漢學界,一時無人能出其右。東方學家、語言學家繆勒主持編撰的大型叢書《東方聖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共51卷,其中也收錄了理雅各翻譯的《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太上感應篇》等譯著。可以說,《中國經典》與《東方聖書》裡中國經典的翻譯成為理雅各一生漢學成就中的兩座豐碑。
在翻譯中國經典的過程中,理雅各得到了不少中西學者的幫助,除了他的合作夥伴王韜以外,還包括何進善、黃勝、羅祥等華人,以及湛約翰、合信等西方漢學家。他們或答疑解經、或助譯部分章節、或共同探討中國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給予譯書不少幫助。其中,理雅各與王韜的合作歷時十餘年,兩人成為摯交好友,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王韜為理雅各廣泛收集各家評注和詮釋,提供《皇清經解校堪記》作為參考,並協助其引經據典、答疑解惑,深得理雅各讚賞。他曾說“王韜之助大矣”,又言“他為我提供了一個圖書館,藏書豐富”。另外,王韜本人與傳教士多年交遊,為理雅各的為人和學識所折服。合作譯經及前往歐洲的遊歷對王韜自身也產生了影響,並促使其成為中國近代有名的改良思想家。因此,理雅各與王韜兩位中西學者在翻譯中國經典上的成功合作成就了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在翻譯中,理雅各的一個原則是堅持參考官學、博采眾長的方法。他精選了上百種最有價值的參考文獻,取其精華,平衡各家注釋,力圖保持不偏不倚的客觀態度。王韜曾說理雅各“其言經也,不主一家,不專一說,博采旁涉,務極其通,大抵取材於孔、鄭而折衷於程、朱,於漢、宋之學,兩無偏袒”。因此,理氏譯本早已超出了單純的文學翻譯,而是力求在紛繁浩大的書海中為西方讀者整理一條閱讀理解中國古代經籍的線索和脈絡。
理氏譯本的另一大特色是忠實原著、強調直譯、反對意譯、風格平實。為盡量傳達原文精神,有時難免會犧牲語言文字的流暢,於是“忠實為主,典雅次之” 成為理氏譯本遭受某些批評的原因。然而仔細閱讀他的譯本,我們也可發現其在努力貼近原文的基礎上,亦盡可能地注意翻譯語言的優美押韻。以《詩經》的翻譯為例,他在英譯時採用了英詩的格式來還原中詩的韻律和意境,力求兼顧中國古代詩歌的語言特點,這種努力亦實屬不易。
理雅各不僅僅是單純的翻譯,而是在譯介中加入了自己多年研究中國典籍的心得,屬於“學者型”翻譯。每個譯本都附有長篇序言和詳細注解,以便讀者在閱讀中國經典的同時還能補充百科全書式的背景知識,他認為這些知識可以拓展學習者視野,為今後的進一步研究打下基礎。
理氏研究開創近代西方漢學新紀元
理雅各關於中國經典的系列譯著開創了近代西方漢學的新紀元,為國際漢學界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研究材料,促進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優秀成果走向世界。理氏的英譯本雖歷經百餘年,仍被奉為中國古代經典的標準譯本,成為西方了解中國文化和文明的基石。英國漢學家翟裡斯曾說:“理雅各所翻譯的《中國經典》,在漢學研究方面乃是一種空前的貢獻。他的那些譯作將長期為人民所銘記和鑽研。”翟裡斯的兒子翟林奈也曾評價理氏的譯介工作,“五十餘年來,使得英國讀者皆能博覽孔子經典者,吾人不能不感激理雅各氏不朽之作也。”
理雅各的學術譯介與研究結束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獻業餘水準的研究,走向了專業化的路線。由於其傑出成就,他成為1876年獲得西方漢學研究最高榮譽獎——儒蓮漢籍國際翻譯獎的第一人,並與法國的顧賽芬、德國的衛禮賢並稱為“漢籍歐譯三大師”。理雅各在漢學領域特別是漢籍翻譯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被中國學者稱為“英國漢學界的‘玄奘’”是當之無愧的。2015年恰逢理雅各誕辰200周年,在中國大陸、香港以及他的家鄉愛丁堡的多個研究機構都將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隆重紀念這位偉大的漢學家對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