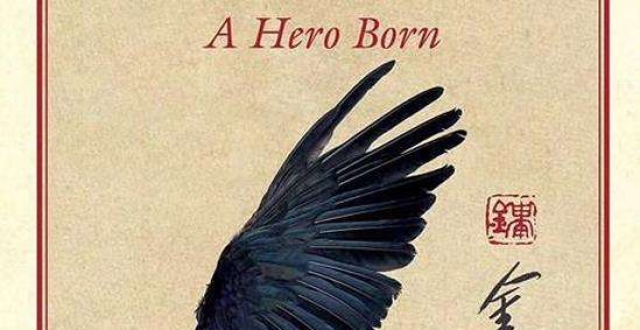如今,機器翻譯日益接近現實,不同語言間的零距離交流看似不再遙遠。據悉,國外某網絡公司曾推出一個翻譯網絡,準確率已高達86%。但就文學翻譯而言,機器翻譯即便能趨近準確層面上的“信”,卻未必能做到“達”和“雅”。
什麽是好的文學翻譯?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糟糕的譯文還是容易辨別的,就像一個喝醉的人揮舞著剪刀,剪出來的東西歪歪扭扭。比如下面這段見於市面的《百年孤獨》開頭:
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蒂亞上校還無法忘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那麽,很好的,和同樣很不錯的放一起呢?
多年以後,奧雷連諾上校站在行刑隊面前,準會想起父親帶他去參觀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高長榮譯)
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裡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范曄譯)
哪一段更好?
總體看來,范曄的翻譯更“時尚”一些,深得當下文學青年的追捧。高的譯本也很不錯,兩段譯本看似不分伯仲,究竟更喜歡誰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據估計,中國每年的各類文學譯本超過一百種,可謂良莠不齊,泥沙俱下,共識是,好的譯本越來越少了,大家都在懷念李文俊的福克納、汝龍的契科夫,草嬰的托爾斯泰,王永年的博爾赫斯,傅雷的巴爾扎克……他們,這些翻譯大師們,是真正做到了“信、達、雅”。

文學翻譯環境“清苦”,很少有人用“愛”堅持
一部偶像劇《親愛的翻譯官》讓翻譯這個職業進入到大眾視野。周遊列國,出訪於高端會所,遊刃於名流大家,再加上“日進鬥金”,許多人都對劇中高翻們的生活充滿向往。
其實翻譯哪有如此風光,尤其身處翻譯金字塔頂端的另一批人——“文學翻譯者”的生存狀態卻是另一番景象:“吃力不討好、報酬低、不招待見”是翻譯界共識。中國有出版商曾透露,付給譯者的稿酬千字不超過 70 元。什麽概念?現在中國縣級的文學刊物稿費,也大多百元每千字了。(我們“大益文學”書系,千字千元,為全國之最。翻譯作品亦開出了千字四百-五百的高稿費)即使是在美國,情況也大同小異:去年年底 Author Guild 發布的一項報告顯示,調查中僅有 7% 的人能夠靠文學翻譯所得的報酬養活自己。專職的文學翻譯家數量少也就不足為奇了。對大部分譯者來說,翻譯文學作品並沒有那麽多“詩與遠方”,更多的是時間緊、任務重、稿酬低的現實“苟且”。
文學翻譯耗費大量精力,低報酬,削減了優秀譯者參與文學翻譯的熱情,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很難像前輩那樣一絲不苟了。著名翻譯家李文俊就從1980年2月開譯《喧嘩與騷動》直到1982年6月才將全書譯出,他曾說:“在這兩年中,這本書日日夜夜糾纏著我,像一個夢——有時是美夢,有時卻又是噩夢。而最難譯的是《押沙龍,押沙龍!》,那個時期,剪不斷理還亂的長句便讓人擲筆興歎。我往往一天只能譯一小段甚至一個長句,第二天再將之改定。”
隨著楊絳、傅惟慈、汝龍等翻譯大家的辭世,李文俊、榮如德等大家的力衰,“文學翻譯的黃昏正在來臨”。目前文學作品翻譯人才凋零,翻譯品質良莠不齊。如今外國文學作品(我們僅以小說為例)的譯作出版雖有所增多,但精品卻愈來愈少。除上海的黃昱寧,北京的范曄,自由翻譯家小二等備份,你能記住的中青年,還有多少?
德國漢學家顧彬曾在一次採訪中給譯者這樣的建議:“中國的譯者和德國的譯者區別很大。你們的譯者基本上是年輕的,基本上到了30歲以後不再翻譯,如果一個人20歲開始翻譯,他沒有經驗,語言水準可能也有問題,所以一個認真的翻譯家不應該到了30歲以後停止搞翻譯。”顯然,在國內這樣“清苦”的環境下,很少有人用“愛”堅持文學翻譯一輩子。

翻譯不僅僅是技術活,還是不斷生成的過程
“以甲國文字傳達乙國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點,必須像伯樂相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傅雷談到文學翻譯時,這樣解釋。“即使是最優秀的譯文,其韻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或不及。翻譯時只能盡量縮短這個距離,過則求其勿太過,不及則求其勿過於不及。”而目前,人們對翻譯普遍存在誤解,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只要是學外語的,就能翻譯。
對於文學翻譯個人而言,許鈞給出這樣的建議,“要處理好文字、文學和文化這三個彼此有別而又相互關聯的層面的關係。”我們在翻譯研究中要力求克服“狹隘的、技術性的傾向”,不要停留於“文字翻譯”層面的爭論。如果文學翻譯隻停留在“技”的層面永遠得不到令所有人滿意的答案,文學翻譯能夠給予文學創作什麽樣的支持,同樣是譯者必須思考的。
“翻譯是一種文學的創造和思想的創造,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的過程中,在文本的背後隱藏著作者、讀者。而且文學翻譯是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出版者、研究者都穿插在翻譯的過程中。只有將這些綜合聯繫起來,翻譯的世界才真正打開。”(許鈞)
然而,現在諸多譯本經常遭到讀者、原作者、甚至學術界的一片聲討,出版社彌漫的急功近利更是重要原因,“市場上扎堆出版的通常是銷量有保證的世界名著,它們往往已經有大量現成譯本,複譯可以借鑒前人,難度大大降低。”許多“影子翻譯”紛紛出現,搶佔了真正好譯者的太空。
這些蠻乾者、急功近利之輩大大加劇了全行業的惡性循環。不過,文益君的心得是,像上海譯文,人民文學這樣的出版社的作品,還是有翻譯保障的。除此之外呢?也許,真的一片哀鴻。

那些翻譯大家留下的傑作與心得
汪湧豪曾在《什麽是好的文學翻譯》一文中強調:“翻譯品質不斷下降,翻譯人才青黃不接,翻譯大賽連續幾屆一等獎空缺,最大原因在於中文不能達意。與西語不同,中文更重視內在的語義生成。中文的靈活和意蘊多面延展性是西語做不到的”。
除去這些技術上的考校,更重要的是要在觀念層面上確立,最大限度地遵從漢語的表達習慣。石黑一雄的譯者郭國良,邁克爾·翁達傑《遙望》的譯者張芸,契科夫的譯者汝龍,博爾赫斯的譯者王永年,前輩如傅雷、朱生豪、梁實秋、梁宗岱、夏濟安、呂同六、馮亦代、梅少武等人已作出了很好的示範。再往前推,“林紓的翻譯更顯中國氣派,可謂將漢語的特性發揚到淋漓盡致。錢鍾書先生稱讚他所譯的《塊肉餘生記》好過狄更斯的原作”。
他還沒到四十歲,可是已經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和兩個上中學的兒子了。他結婚很早,當時他還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如今他妻子的年紀仿佛比他大半倍似的。她是一個高身量的女人,生著兩道黑眉毛,直率,尊嚴,莊重,按她對自己的說法,她是個有思想的女人。她讀過很多書,在信上不寫“b”這個硬音符號,不叫她的丈夫德米特利而叫吉米特利;他呢,私下裡認為她智力有限,胸襟狹隘,缺少風雅,他怕她,不喜歡待在家裡。他早已開始背著她跟別的女人私通,而且不止一次了,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一講起女人幾乎總是說壞話;每逢人家在他面前談到女人,他總是這樣稱呼她們:“卑賤的人種!”
——汝龍譯《帶小狗的女人》
西奧多·薩瓦利在《翻譯的藝術》一書中提到兩條爭鋒相對的翻譯方法:1)譯文應該讀起來像原文,2)譯文因該讀起來像譯文。
很長時間以來,這兩種翻譯方式一直並存,很難說出哪種更好。1981年發表的《林紓的翻譯》中,錢先生提出了“化境”說,他指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為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這種精神人們常用“信、達、雅”來概括。傅雷則認為:“不妨假定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那麽原文的意義與精神,譯文的流暢與完整,都可以兼籌並顧,不至於再有以詞害意,或以意害辭的弊病了。”
他一生翻譯外國文學名著三十三部。其中絕大部分是巴爾扎克的作品,而傳世的十四部巴爾扎克作品中,又以《高老頭》用力最深,達到了相當高度的“雅”;
文明好比一輛大車。和印度的神車一樣,碰到一顆比較不容易粉碎的心,略微耽擱了一下,馬上把它壓碎了,又潔浩蕩蕩的繼續前進。你們讀者大概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這本書,埋在軟綿綿的安樂椅裡,想道:也許這部小說能夠讓我消遣一下。讀完了高老頭隱秘的痛史以後,你依舊胃口很好的用晚督,把你的無動於衷推給作者負責,說作者誇張,渲染過分。殊不知這慘劇既非杜撰,亦非小說。一切都是真情實事,真實到每個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者心裡發現劇中的要素。
——傅雷譯《高老頭》
70後范曄翻譯的《百年孤獨》同樣受到一致好評,人們評價他的譯本:語句明快、簡潔、詩意、流暢。在很多文學愛好者眼中,范曄翻譯的科塔薩爾《萬火歸一》更加經典。在接受採訪時他曾坦言,“一切所有的翻譯都是在規化和異化中找平衡點,因為翻譯本身是一個妥協的藝術或者說是一個平衡的藝術,永遠在張力之中,但是要在張力中找到一個相對的平衡點、一個動態的平衡。我要體現的是馬爾克斯的風格,當然我自己的風格也會流露出來”。由此可見,一個好的譯者比任何人都清楚並能恪守再創造的基點。將母語的特性發揚到極致,忠於原文,又能服務讀者。
瑪利尼很高興被派來飛“羅馬——德黑蘭”班機,因為不像北方的航線那樣陰鬱,姑娘們總是興高采烈,因為能夠去東方獵奇或者去見識意大利。四天后,一個小男孩丟了杓子,難過地衝他端起甜食盤,他去幫忙的時候又一次看見島嶼的邊際。時間上差了八分鐘,但當他在機尾的小窗裡俯身下望的時候,他確認無疑。小島的形狀獨一無二,好像一隻海龜正從海裡露出四肢來。他看著直到有人叫他,這回他肯定那鉛灰色的斑點是一組房屋,甚至分辨出幾處稀稀落落的農田,一直延伸到海灘。那個島成了瑪利尼的一個牽掛,一想起來或者身邊有舷窗的時候,他就看著它,最後幾乎總是聳聳肩作罷。
——范曄譯《正午的島嶼》

未來會好嗎?
如今,不計時間成本,精益求精地翻譯文學作品的精英譯者越來越難以靠翻譯謀生,而以快速交付稿件、按客戶滿意度衡量翻譯產品品質的職業譯者越來越多。
曾獲蘇聯文學最高獎“高爾基文學獎”、魯迅文學翻譯彩虹獎的著名俄語翻譯家草嬰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不無感慨地說“(現在)靠翻譯養家糊口很困難”,“像我這樣的譯者,在這個時代是活不下去的”。
但無論你承認還是不承認,中國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文學輸入國,每年,除了大量的再版經典,還有各種各樣的獲大獎的文學作品,如諾貝爾獎、布克獎、國際布克獎、美國普立茲獎、美國國家圖書獎等等,都需要大批的優秀的譯者操刀,市場化的力量也讓一小部分譯者逐漸獲得了經濟和社會身份的雙重保障,他們也許不必非得靠翻譯養活自己,翻譯,只是他熱愛的事業之一,而非全部。范曄如此,近年來翻譯卡佛的小二也如此。
另有一些很年輕的翻譯家由於自己也寫作,外語又不錯,難免會一時技癢,對翻譯經典作品投入了極大熱情。比如漓江出版社的編輯陸源,比如孔子學院拉美中心的范童心,原吉林出版集團的胥弋……還有更多默默無名的文學愛好者,堅持著自己的文學翻譯夢。
但顯然,文學翻譯行業光靠熱愛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全社會認識到文學翻譯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除大幅提升稿費,高校也可加大對文學翻譯及其研究工作的投入。好的譯作不能用金錢衡量,但好的譯者必須得到應有的尊重。
從前中國的譯者是“計劃的”,現在轉向“市場的”,希望這種轉軌,只會帶來更大的輝煌。

再談談中國文學的譯出
談到中國文學的譯出,各國對中國文學翻譯的奇缺。那是另一個更大的話題。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瑞典漢學家安娜功不可沒,他們是莫言作品的英文、瑞典文譯者,沒有他們的精心付出,很難想象莫言能摘得諾獎。而現在,安娜甚至辭去了教職一心翻譯中國作家作品,因為心急的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們已經在她的門口排起了長龍。
然而,《中華讀書報》發表的《葛浩文式翻譯是翻譯的“靈丹妙藥”嗎?》在網上引發了眾多網友的議論。翻譯是否可以“連譯帶改”這場爭議,稱得上是我國翻譯界近些年來最受關注的話題。
葛浩文在自己的翻譯理論中往往將讀者接受性置於首位。而英美讀者更喜歡沒有外國語痕跡的譯本,這使得葛浩文不得不對原語文本進行改寫和背叛。同樣,在西方最有名的《紅樓夢》譯本不是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而是牛津教授霍克斯的,後者一樣有基於西方語言習慣的改寫。
從嚴肅的翻譯學術來說,“連譯帶改”背離原文,難免有異端之嫌。但從市場翻譯傳播來看,那樣譯,有時又是成功的。
毫無疑問,中國文學“走出去”譯者是關鍵,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許多出版社對國外漢學家一直心存芥蒂,認為其無法原汁原味地再現作品的中國元素。加之本土譯者對英美文化和英語文學創作的功力欠佳,對異域讀者閱讀習慣的不了解。好的中國文學作品很難得到異域行家和讀者的認可。
這還不是最關鍵的問題。最大的困難在於,一,精通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們少之又少,二,能兼職翻譯的漢學家更是鳳毛麟角。中國文學,尤其中國當代文學的對外輸出工作,說白了,居然就肩負在全世界範圍內屈指可數的幾個漢學家的身上。這讓人情何以堪!
中國文學要更好地打入西方主流社會,真的太難了。也許,我們需要為此等上幾十年,上百年。
是的,那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歡迎分享到朋友圈?
評論功能現已開啟,我們接受一切形式的吐槽和讚美?
大益文學
文學 | 品位 | 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