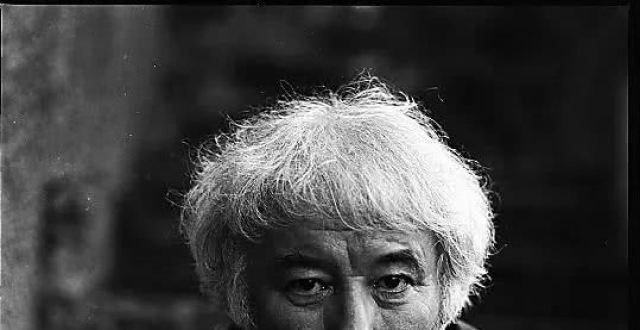在一個可以隨意在社交媒體上看到詩的時代,你是不是也會有這樣的疑惑:現代詩到底是什麽?詩人是不是江湖騙子?詩究竟能不能被理解,被解釋?感受力的無所憑依導致了讀者普遍的失語。緊接著,懷疑變成不安和焦慮,阻礙我們全身心去體驗詩歌。
今日文章節選自《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詩》的引言部分。在書中,作者張定浩拋出邀請,並將“詩歌是可解釋的”這一許諾帶給讀者。藉由那些優秀的現代漢語詩人,我們得以治愈分析手段缺席和對譯詩的依賴帶來的感受力退化,重建與母語、與詩歌的親近關係......

《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詩》
張定浩 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
什麽是新詩?如何理解新詩?
文|張定浩
在威廉·燕卜遜《朦朧的七種類型》的結尾處,他說:
今天所有的詩歌讀者都會一致認為,某些現代詩人是江湖騙子,儘管不同的讀者會將這遊曳不定的懷疑加在不同的詩人身上,但這些讀者沒有肯定的辦法能證實自己的懷疑。
……人們無論讀什麽詩,總感到有某種不滿足,心中永遠有疑團,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正確地理解詩句,而假如應該這樣理解,又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感到滿意。
很明顯,缺少分析手段,比如缺少那類穩健可靠的手段來判定自己的態度正確與否,就會導致情感的貧乏,而缺乏情感不如不讀詩。難怪,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就算不是對某一種詩的解釋,也應該是一種有普遍說服力的信念,即堅信所有詩都是可解釋的。
這種由新批評派在上世紀初帶來的有關詩歌的珍貴信念,即“堅信所有詩都是可解釋的”,是這本小書的起點。
這種“可解釋”,並非意味著每首詩都如語文閱讀理解試題一般在背後隱藏一個標準答案,更不是意味著一首詩就此可以等同於有關這首詩的各種知識,而是說,這首詩正在向我們發出邀請,邀請我們動用自己全部的感受力和分析力進入它,體驗它,探索它,被它充滿,並許諾,我們必將有所收獲,這收獲不是知識上的,而是心智和經驗上的,像經受了一場愛情或奇異的風暴,我們的生命得以更新。

▲威廉·燕卜遜(後排右一)與喬治·奧威爾(後排右二)等在 BBC 共事
這種“可解釋”的信念,同樣也是對詩的巨大考驗。既然它要求我們對一首詩完全信任,那麽,這首詩也一定要有足夠的力量配得上這種信任,這首詩需要像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裡所闡明和示範的那樣:
……而每個短語
和每個句子都恰當(每個詞各得其所,
在各自位置上支撐其他的詞,
每個詞不膽怯也不賣弄,
新詞與舊詞從容交流,
日常詞語準確又不粗俗,
書面詞語精細且不迂腐,
整個樂隊和諧共舞)
每個短語每個句子是結束也是開始,
每首詩一座碑文……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詩都能抵達這個高度。當我們這麽說的時候,我們是從描述性的角度去定義“詩”這個詞作為一個文類的存在,我們隨即自然將詩分為好詩和壞詩。好詩擁有經得起解釋的堅定秩序,像碑文和樂隊一樣,即便有偶然性的介入,最終也字字句句不可隨意替換地構成一個完美整體;壞詩和相對平庸的詩則會在逐字逐句要求解釋的重壓下垮掉。

▲年輕的 T·S·Eliot 肖像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須記得,當新批評派使用“詩”這個名詞的時候,他們取的是其規範性而非描述性的定義,也就是說,只有好詩可以被稱作“詩”,壞詩根本就不是詩。所以新批評派談論的詩大多都是已有定論的經典作品,他們覺得這些經典作品中有一部分美被忽視了,或者說被冰封在某種似乎不可表達的文本凍土層中,他們希望用分析性的言語去開掘那些看似不可表述、一觸即碎的美。
倘若忽視這個描述性和規範性的區分,將新批評的文本細讀僅僅當作一種獨立的批評方法引進,且不加揀擇地應用在任何一首從描述性角度被定義的詩身上,文本細讀就會變成一種類似點金術的學院巫術,一種俯身向公眾解釋詩歌的謙虛姿態會迅速與一種特權話語般的學院傲慢合謀,進一步撕裂而非彌合詩和普通公眾之間的距離。
詩是可解釋的,但解釋的前提、路徑和終點,應當仍舊是廣義的詩。而目前中文領域常見的釋詩,往往是在非詩的層面展開的,這種“非詩”體現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散文化,把詩句拆成散文重新逐段講述一遍,疊床架屋地告訴我們詩人在說什麽,想說什麽;
另一種是哲學化,從一些核心詞匯和意象出發,借助不停的轉喻和聯想,與各種坊間流行西哲攀上親戚,在八九十年代或許是海德格爾克爾凱郭爾,接著是福柯德裡達,如今則是阿甘本和朗西埃。這兩種非詩的解釋,一種把詩拖進散文的泥濘,一種將詩拽上哲學的高空,無論我們從中獲得的最終感受是什麽,是好是壞,它都和原來那首詩喪失了關係。
 ▲遊行中的米歇爾·福柯(前排左一)
▲遊行中的米歇爾·福柯(前排左一)
而這種情況之所以習焉不察,和漢語新詩作者、讀者長久以來對翻譯詩的嚴重依賴有關。在一首詩從源語言向著現代漢語的翻譯中,能最大限度保存下來的,是這首詩要表達的意思、意義和大部分意象,也即一首詩中隱含的散文梗概和哲學碎片,而所謂語調、句法、節奏、音韻等需要精微辨認和用心體驗的內在關係,以及依附於這種內在關係的情感和思維方式(現代語言學證明我們不是用單詞而是直接用短語和句子進行思維的),大部分情況下在翻譯中都喪失了。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習慣通過翻譯詩接觸現代詩的讀者和寫作者而言,囫圇吞棗和斷章取義,似乎就成了理解詩歌的唯二方法。
這麽說,並非要拒絕翻譯詩,而是要認識到,在詩的解釋和翻譯之間存在同構關係。解釋一首詩就是翻譯一首詩,反之亦然。而當我們照著一般翻譯詩和閱讀翻譯詩的習慣去解釋一首詩的時候,我們或許正在丟失一首詩在傳達和交流的過程中最不應該丟失的體驗。
詩所帶來的體驗,首先是聽覺上的,其次是視覺上的,更直接的反應則是身體上的。這種身體反應,在傑出的詩人那裡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表述,“如果我從肉體上感覺到仿佛自己的腦袋被搬走了,我知道這就是詩”(艾米莉·狄金森);“一首好詩能從它沿著人們的脊椎造成的戰栗去判定”(A·E·豪斯曼);“讀完一首詩,如果你不是直到腳趾頭都有感受的話,都不是一首好詩”(羅伯特·沃倫)。一首好詩,帶給我們的,首先是一種非常強烈和具體的肉身感受,一種非常誠實的、無法自我欺騙的感受。這種感受,類似於愛的感受,我們起初無以名狀,如同威廉·布萊克遭遇彌爾頓時的感受:
但是彌爾頓鑽進了我的腳;我看見……
但我不知道他是彌爾頓,因為人不能知道
穿過他身體的是什麽,直到太空和時間
揭示出永恆的秘密。

▲1727 年版本《失樂園》的封面
所謂“道(word)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這種感受,一定是來自母語的。希尼曾談到他在學校所讀到的幾行丁尼生的詩,
老紫杉,抓住了刻著
下面的死者名字的石頭,
你的纖維纏著無夢的圓顱,
你的根莖繞著骸骨。
——《希尼三十年文選》中譯本
單看譯文,我們大概會奇怪於希尼接下來所說的那種“有點像試金石,其語言能夠引起你某種聽覺上的小疙瘩”的身體感受,我們需要回顧一下原詩,它來自丁尼生《悼念集》第二首的開頭幾行:
Old Yew, which graspest at the stones
That name the under-lying dead,
Thy fibres net the dreamless head,
Thy roots are wrapt about the bones.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雕像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雕像
在心中默讀幾遍,我們或許才能對希尼的話稍有所感,並隱約領會艾略特曾經發出的讚詞,“自彌爾頓以來,丁尼生擁有最靈敏的聽覺”。這裡或許還可以嘗試翻譯如下:
老紫杉,你設法抓緊那些石碑,
它們講述躺在下面的死者,
你的細枝網住沒有夢的頭顱,
你的根莖纏繞在那些骨頭周圍。
我所做出的翻譯和原詩相比,當然還相距甚遠。舉這個微小的例子是希望強調,當我們閱讀譯詩的時候,要隨時意識到譯詩在我們心中所產生的體驗和原詩應當產生的體驗之間的、或大或小的誤差,我們需要隨時調校這個誤差,而來自與原詩作者相同母語的一些作者被翻譯過來的文論,將會是很好的調校工具,如在這個丁尼生的例子中希尼和艾略特所起到的作用。
這裡指的“被翻譯過來的文論”,來自那些最好的詩人和最好的批評家——艾略特的三卷本文論集,埃茲拉·龐德的《閱讀ABC》,布羅茨基《小於一》和《悲傷與理智》中有關奧登、哈代和弗羅斯特的文章,希尼有關艾略特、奧登、畢肖普和普拉斯的文章,帕斯的《弓與琴》,特裡·伊格爾頓的《如何讀詩》,詹姆士·伍德的《不負責任的自我》,阿蘭·布魯姆的《愛與友誼》……是這些由辛勤的譯者帶給中文世界的典範文論在反覆賦予我信念,相信在神秘主義和庸俗社會學之間,存在某種談論詩歌乃至文學的更優雅和準確的現代方式。

《小於一》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 著
黃燦然 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
這種作家批評,不同於學院教材,它始終是從具體出發的,並強調感受力和學養的相輔相成。在《不負責任的自我》的引言中,伍德談到那些抗拒評論喜劇的人,“那些人似乎太害怕自我意識,或者說太不相信言詞,尤其不相信闡釋的可能。事實上許多喜劇不但可以闡釋,而且完全可以闡釋,有點兒荒唐的倒可能是喜劇理論”。伍德應當不會反對將這段話裡的“喜劇”置換成“詩歌”,因為他也說到,“那些抗拒批評入侵喜劇的人往往也聲稱難以真正談論詩歌、音樂或美學觀念”。
與之同仇敵愾的,是特裡·伊格爾頓。在《如何讀詩》的開頭,他憤怒於那種認為是文學批評殺死詩歌的陳詞濫調,他舉巴赫金、阿多諾、本雅明等諸多批評家為例,證明文學感受力是一種需要時刻熏習在傑出批評中方可艱苦獲致的語言表達能力,“面對艾略特的幾行詩,有批評家評論說,‘標點中有某種很悲傷的東西’,大多數學生可說不出這樣的語言。相反,他們把詩看作:其作者仿佛為著某種古怪的理由,以不滿頁的詩行寫出他或她有關戰爭或性活動的觀點”。
他認為,令大多數學生在詩歌面前失語的,不是文學批評,而恰恰是文學批評缺失帶來的相應感受力的缺失,這可以回應本文最初所引的燕卜遜那段話,正是“缺少分析手段”導致了“情感的貧乏”。他們共同期待文學批評可以有效地帶給普通讀者之物,在喬納森·卡勒那裡,則被正確又警醒地稱之為——“文學能力”。

▲美國學者、理論家喬納森·卡勒
而所謂“文學能力”,與其說是用一種屬於讀者的主觀能力闡釋某首作為客體對象的詩,不如說是在讀者和這首詩之間建立起一種類似於愛的積極關係。這也就是伊格爾頓所說的,“詩是某種對我們所做的東西,而不是某種僅僅對我們說話的東西,詩的詞語的意思與對它們的體驗緊密相關”。
帕斯也說過類似的話,“詩的體驗可以採用這種或那種方式,但總是超越這首詩本身,打破時間的牆,成為另一首詩”(《弓與琴》)。於是,要想有效地談論一首詩,這種談論本身就要有能力成為一首新的詩,或者說,新的創造。
這種談論本身當成為一種印證,以詩印證詩,用創造印證創造,在愛中印證愛。這種印證又不是脫離原詩的,相反,它要呈現的,正是伽達默爾曾經揭示給我們的“藝術真理”——“作品只有通過再創造或再現而使自身達到表現”,我們對一個過往作品的理解和熱愛,本就是它作為存在的一部分,如我們所見到的星光之於星辰。
......
(文章系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