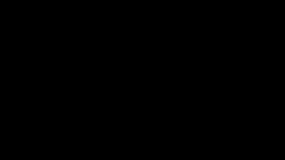有學術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地方性的生產:《繁花》的上海敘述
曾軍 |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首屆長江學者青年學者
本文原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經作者授權推送
文中圖片未經注明均來自網絡

內容摘要:對金宇澄《繁花》地方性生產的分析必須將“內容”、“形式”及其“生產機制”的研究綜合起來。其首發之地“弄堂網”中的分論壇“文字域”所形成的“上海人講述上海人自己的故事”的文學場決定了《繁花》用上海閑話講述上海記憶的特點。在“收獲”版《繁花》中,金宇澄將主人公確定為“滬生”(而非“弄堂”版的“膩先生”和“滬源”),顯現出著意強化“滬生”們的上海城市市民意識,使之成為“當代上海寓言”的努力。金宇澄在“文藝”版《繁花》中新增17幅手繪插圖,建構“上海人的上海地圖”,展現了上海市民的太空意識。
早在20世紀80年代,詹明信就在其《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文中就專門論述過“後現代主義與都市”的問題。他通過對美國洛杉磯鴻運大飯店的太空分析,認為“後現代的‘超級太空’乃是晚近最普及的一種太空轉化的結果”,但我們的視覺感覺“始終無法擺脫現代主義高峰期太空感設計的規範”。
當代許多城市(都市)文學都遵循著這種具有烏托邦性質的、帶有強烈震驚體驗的、但同時又采取田園牧歌式(具體到中國當代,就是強調“鄉土中國”語境的“城鄉二元對立”)的價值立場的敘述邏輯。在他們看來,由於城市規劃布局、建築風格、生活方式及城鄉流動等各方面所具有的一致性,帶來了城市(都市)文學在太空生產方面的一致性,也帶來了“地方性”的消失。因此,他們甚至主張用“在地性”(與之相關的,還有一系列相關表述,如“跨地性”、“多地性”等)來取消“地方性”。不過,這個維度並不能涵蓋當代中國城市文學的全部。
近兩年引起廣泛閱讀和討論的金宇澄的《繁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致力於“地方性的生產”的上海敘述。

《繁花》的文學生產刻上了鮮明的“上海”地方性。作家是《上海文學》的資深編輯金宇澄,首發之地是上海的“弄堂網”,正式發表是在另一份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上海文學期刊《收獲》,而專著版則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所有這些外部因素均與上海有關,絕非偶然。就內部因素來看,小說展開的是從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將近半個世紀的上海敘述,所涉及的人物,從資本家到商人、從地下黨到工人、從知青到律師,涵蓋了當代上海各社會階層的變遷;《繁花》自覺接續並擴展了從《海上花列傳》到張愛玲以來的“上海文學傳統”,“上海話”的方言敘述同樣也強化了這部小說的“上海味”。
這些從內到外的“地方性”,使得《繁花》成為近兩年來最受關注和歡迎的上海文學作品,也使得我們對於《繁花》“地方性”如何形成的研究不能局限於“內容”層面,而必須將“形式”以及“文學生產機制”等諸多層面的因素納入進來一起討論。
“弄堂”《繁花》:成為場的“文字域”
《繁花》有著與中國早期網絡文學《第一次親密接觸》極為相似的生產機制。它最早是從2011年5月14日開始出現在弄堂網的論壇“文字域”之中的,作者署名是“獨上閣樓”(金宇澄的網名)。在隨後數月間,長長短短的《繁花》章節便以帖子的形式陸陸續續貼了出來,並與論壇中的其他網民展開積極的交流互動、闡釋修改。但《繁花》又與當前的網絡文學工業中的作品很不一樣。
網絡文學經過十多年時間的迅猛發展,其生產機制和文學形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說《第一次親密接觸》時的網絡文學還多少具有個人性、娛樂性和手工作坊式的初級形態的話,那麽現在由盛大文學等所主導的網絡文學平台則已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工業。因此,與當前這些具有支配性的網絡文學生產方式相比,《繁花》所具有的網絡性毫無疑問已經太過古典,幾近文物了。這構成了《繁花》獨特的文學生產“場”。
首先,弄堂網的地方性強化了《繁花》寫作的上海性。弄堂網只是一個極為小眾的地方性網站,它的定位很簡單,就是“上海人講自家身邊的故事”。它分為“上海歷史”、“上海話”、“新老照片”、“小人書”、“亭子間”、“弄堂小菜”、“流金歲月”、“古董攤”及“客堂間”等幾個板塊組成。其中的“客堂間”是該網站的論壇板塊,又分為“我愛上海”、“關於上海”和“弄堂水城”等二級板塊,發表《繁花》的“文字域”是“我愛上海”板塊中的三級分論壇。
從弄堂網的這些特徵不難看出,它首先不是一個網絡文學網站,因此與曾經的“榕樹下”、“起點中文網”以及現在的“盛大文學”等知名網絡文學網站相比,它的目標並非“文學”,並不擁有數量龐大的致力於網絡文學寫作的作者和讀者群體。因此,無論是“弄堂網”和作為作者的“獨上閣樓”,還是其他論壇網民,都沒有陷入追求點擊率、追求文字量、追求轟動性等一般網絡文學的俗套,沒有陷入注水文學、討好文學、庸俗文學的怪圈。
尋找“最上海”、“最閣樓”的“過去的味道”,是“獨上閣樓”進入這個論壇的初衷,也是其“發帖”(“寫作”)的源動力。在5月10日到14日期間,“獨上閣樓”間斷性地寫了不少與上海有關的個人回憶——涉及從1960年代直到1980年代上海的諸多細節,如伸出老虎窗外看到的上海屋頭頂、1980年代上海新開小飯店如何挖地三尺“再造”太空、1970年代能講《簡·愛》《傲慢與偏見》的高職老阿姐、大自鳴鍾附近E君家的三層閣以及想享受悠閑滬上時光、體驗上海味道的W先生,等等。這些段落有一部分後來成為小說“引子前的引言”,並奠定了小說《繁花》的諸多特點:(1)與上海有關的個人回憶;(2)片斷式、非正式的上海閑話;(3)基於“上海認同”和“上海懷舊”的文學場域。
弄堂網保持了不直接暴露自己現實生活真實身份的慣例,但是其中的網民已形成了一個新型的具有網絡匿名屬性的熟人社會(“社群”形態的出現正是以這種共識和認同為基礎的)。他們共同回憶、分享、完善個人經驗和記憶,品味殘存的上海味道。因此,網絡之於金宇澄的《繁花》恰如同小說中頻繁出現的飯局一樣(雖然大家絕大多數並不認識,即使認識也保持網絡的遊戲規則,並不相認),它的遊戲規則是趣味相投。
從《繁花》的寫作開始直到現在,論壇中出現的與金宇澄交流的網民身份儘管不是很確定,但從其發言來看,主要有文學研究者、出版編輯人、上海文化人以及其他較高的文化層次和認識水準並且對上海文化有強烈的認同意識的“上海人”。弄堂網並沒有將《繁花》一下子投入“無名而匿名的網絡汪洋大海”,而是將之引入一下倍感溫馨的“上海人小圈子”。用傳播學的術語,弄堂網中的這些“熟悉的陌生人”做到了“分眾化”,也由此而“小眾化”了。
其次,“獨上閣樓”(金宇澄)的作者身份也是形成《繁花》獨特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獨上閣樓”有別於已自覺被納入網絡文學產業的生產機制之中的寫手:他“碼字”,一旦開始寫作,就形成了每天一小段、一小節的寫作慣性,但他不受網絡文學的“類型”束縛,由此也與當前流行的“玄幻”、“穿越”、“官場”、“青春”等絕緣;他也“討好讀者”,自稱“我的初衷,是想做一個位置很低的說書人,‘寧繁毋略,寧下毋高’,取悅我的讀者”,努力挖掘記憶中那些“最上海”的味道和細節,但他並不因此而追求點擊率和閱聽人量,也由此在寫作過程中始終能夠保持住自己的寫作初衷,形成“討好但不媚俗”的特點。
而另一方面,作為資深的紙質文學把關人(《上海文學》雜誌社的副主編)、一位有著長期寫作經歷的創作者的身份,“獨上閣樓”(金宇澄)既不像某些嚴肅文學作家自覺拉開被視為通俗文學的網絡文學的距離,又不像陳村那樣以專業作家的身份“實名”展開網絡寫作,他選擇了“匿名”的網絡文學寫作的慣例,並充分享受了這種寫作的自由。
從這個意義上講,“獨上閣樓”(金宇澄)正是充分調用自己作為專家作家和文學把關人的幾十年的文學積累,以長篇文字、上海閑話的網絡化碎片式寫作的方式,成功實現了嚴肅文學對網絡文學的逆襲。

再次,“弄堂”版《繁花》具有網絡文學生產最為重要的“互動性”,即自始至終都與“讀者”保持著密切的交流。這一互動性因“弄堂網”的小眾化和“上海趣味”以及金宇澄自身的文化積累,使得這一互動儘管“非正式”,但並不落俗。儘管金宇澄從一開始就自謙說將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但他的整個文學水準和藝術旨趣卻相當之高。整個“弄堂”版《繁花》從5月10日(而非5月14日)開始的互動內在地構成了“關於《繁花》的《繁花》”,即所謂“元小說”成分,它通過與各位網友之間的討論、爭論,不僅交代了《繁花》寫作的最初動機,藝術表現形式的選擇,人物身份、情節設定、主題結構等重大問題的思考,而且還包括作者自己和讀者對小說的評論。
比如有關《繁花》的創作緣起,先是“獨上閣樓”與網友們有關上海城市文化意蘊的討論,從宜山路地鐵3號轉9號線的設計開始,突然聯想起張愛玲;從老電車公司,講到現在的香哥裡拉酒店,從常德路的弄堂想起此前1970年代認得的一位美人小金寶(——特意寫到1990年代末再次碰見小金寶,看到伊在陝西路延安路轉角天橋下擺服裝攤,這一細節直接轉化為小說《繁花》中陶陶及其老婆芳妹、情人小琴之間的職業身份);5月13日,“獨上閣樓”的帖子標誌著《繁花》寫作真正的醞釀,“慢一點寫”、“老老實實地回憶”、“複式腔調”以及“近看遠眺”的姿態,尤其是“現在是啥時代,還有這樣講話的?”對上海話方言敘事的異乎尋常的敏感和嘗試的衝動,正是我們理解《繁花》的關鍵所在。“馬路菜場唱市面,各位阿記得。”《繁花》正是從此處開始著墨的。
在隨後的寫作過程中,還有數次直接關係到《繁花》寫作藝術特色的討論,如5月19日有關“如何進行上海話寫作”的討論、5月29日至6月1日有關“是否進行分行寫作”的討論、7月22日開始主人公從“膩先生”改為“滬源”的聲明及其引發的討論,8月3日有關《繁花》與王安憶《長恨歌》的比較,8月5日與《海上花列傳》的比較以及網友對故事兩條線索何時和如何交匯的期待。
這裡最為重要的事件是,9月10日寫到20萬字時,“獨上閣樓”作了一個總結,同時網友也表達了“巨集著早日出版”的祝願,這一細節標誌著“獨上閣樓”在寫作一半左右的時候,已經開始著手考慮紙質文學的出版了。到10月17日,小說寫到三十幾萬字時,“獨上閣樓”接受朋友的關照(“最好不要全部貼出,對書有影響”)正式準備撤出“弄堂網”。10月31日,“獨上閣樓”正式告別。很顯然,如果說5月14日的起點算是《繁花》網絡寫作的開端的話,那麽,從9月10日起,無論是“獨上閣樓”(金宇澄)還是網友們,都開始將之作為“嚴肅文學”來看待了。
“收獲”《繁花》:
“滬生”們的市民意識與當代上海寓言
《繁花》在《收獲》雜誌發表,是其獲得嚴肅文學認可的重要標誌。如果說寫作之初,金宇澄多少是帶有遊戲性、自娛性、片斷式的偶一為之的“非文學”的“虛構類長篇文字”的嘗試的話,那麽,當《繁花》中的各色人物一一登場亮相,虛構性人物已經形成了自身的生命發展軌跡的時候,金宇澄的寫作也便開始變得自覺,嚴肅文學的標準和要求也開始內在地影響寫作活動。

作家寫作中這一重要的變化資訊在“弄堂”版《繁花》中多少被保留了下來。其中最典型的是《繁花》主人公命名的變化。“弄堂”版《繁花》的主人公一開始叫“膩先生”。這個名字的來歷是主人公小時候上學時經常被罰作業,老是逃學,於是被王老師取的綽號,意思是“失敗,逃跑、害怕的蟋蟀,不想奮鬥的蟋蟀,上海叫‘膩先生’”。不過,這一明顯帶有貶義的具有失敗主義的特徵並不能涵蓋人物的全部特點。
文革造反派大行其道時,膩先生充當的是逍遙派角色。在隨後的命運轉折中,他既沒有像阿寶一樣,全家被發配到曹楊新村“兩萬戶”,從一度養尊處優的資產階級淪落為需要接受改造的工人階級,也沒有像小毛那樣,始終都是工人階級的社會身份,到後來甚至還掙扎在生存的底線上;相反,他在父母的運作下,到了某五金公司做採購(直到1970年代才受到衝擊);到了1980年代,他哥哥成為到溫州下海經商的第一批上海人,而膩先生自己則轉型為律師,過上了中產階級生活。正是這一人物性格及命運的形成,使得“獨上閣樓”認為“膩先生”不足以概括人物的特點了,於是嘗試用“滬源”這一曾經出現過的稱呼來命名。
到2011年7月22日,“膩先生”正式改名為“滬源”。“獨上閣樓”如此解釋:“幾位讀者認為膩先生名字不妥,今改名‘滬源’,南昌大樓姝華稱呼過。抱歉”。在“弄堂”版《繁花》中,滬源還有一哥哥叫滬生。但是等到“收獲”版《繁花》正式出版時,兄弟倆的姓名再次做了調整。弟弟“滬源”正式定名為“滬生”,而哥哥“滬生”則換名為“滬民”。將“滬生”確定為主人公之名,暗含著以滬生成為當代上海寓言的意味。從字面意義上講,“滬源”意為“滬之源頭”,顯然不符合《繁花》的原意,而“滬生”則是“上海所生”,“滬民”當然也是“上海之民”,完全貼合小說展現上海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近半個世紀上海城市社會文化變遷的主旨。
不過,這裡比較麻煩的問題在於,滬生只是一個大概與新中國同歲(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出生)的一個普通上海市民。無論是出生背景,還是人生經歷,他都遠遠沒有《海上花列傳》通過煙花女子觀察上自達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式的“傳奇”,也沒有《子夜》《上海的早晨》那樣直接將視角聚焦於上海社會變遷的重要人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及其沒落)那樣的“史詩”,同樣也沒有像《長恨歌》中王安憶直接以作家兼敘述者的口吻直接將王綺遙等同於“弄堂”、“閨閣”、“上海”的那種“隱喻”。
《繁花》中的“滬生”們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上海半個多世紀的風雲際會,但他們並沒有作為時代的弄潮兒以英雄的形象置於精神高地的頂點。恰恰相反,他們更多是以隨波逐流的方式被裹挾到大時代洪流中,沒能夠對歷史和時代產生重要的影響,只能自我適應、自我調整,於逍遙中獲得暫時的喘息,於被動中尋找生存的希望。
因此,要將“滬生”理解為“當代上海的寓言”需要重新尋找一個認識的基點,這就是“上海城市市民意識”。市民化進程是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標誌,這一過程包括兩個重要的階段:其一是身份的市民化,即城市化進程中,大批外來移民獲得城市居住權、職業以及各項城市權利;其二是意識的市民化,即獲得市民身份後,與城市形成認同感,產生市民文化,形成市民社會。但後者是一個極為複雜而漫長的過程,因此在市民化過程中始終存在各種文化矛盾。而市民意識的獲得是以市民個體性的自覺和獨立為前提的。
因此,我們要判斷“滬生”們是否具有“市民性”,首先看他是否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他是否有自己的人生軌跡、性格情感、欲望追求;第二,是以個體為中心,他是否也有與他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是以家庭、鄰裡、同學、同事為同心圓逐步擴散的;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由此確立了他與“大時代”、“大歷史”的關係,這些都將決定小說的敘述形態。
但是,在整部小說中,作為主人公的滬生並沒有充分成為小說敘事的中心。他更像一個參與者、旁觀者的角色,參與到他的同學、朋友們的悲歡離合之中。以滬生為中心,人物可以分為兩組:一組是男性,即滬生從小到大的好朋友,阿寶、小毛、陶陶,他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如康總、徐總、蘇安等。另一組則是在不同時期、分別出現在他們周圍的女性:蓓蒂、姝華、銀鳳、小珍、春香、蘭蘭、雪芝、菊芬、白萍、梅瑞、潘靜、汪小姐、李李、小琴等。
她們或是這“滬生”們童年的鄰居、玩伴,或是他們長大成年之後的戀人(或者是朋友的戀人)、同事。彼此的關係也頗為複雜,如姝華,既是小毛的姐姐,也是滬生的初戀;梅瑞則曾經是滬生、阿寶的戀人,又是後來康總的情人;陶陶是梅瑞的鄰居,也是滬生和阿寶在1980年代之後認識的新朋友。透過各位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不難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事實:《繁花》試圖向讀者展示一個“熟人社會”的上海敘事。
一般的城市社會學往往認為,“城市就是一個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因此,在許多城市文學中,“陌生人世界”往往成為觀察城市、反思城市的視角。但《繁花》花了數十年的,向我們呈現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上海的城市發展中,上海人(或者再普泛一些,所有的“城市人”都具有這個特點)始終生活在一個“熟人社會”之中,其中親戚鄰裡關係構成了市民交往的核心,其次是戀愛和工作的交往構成了其交往圈的外圍;再其次才是陌生人世界。但是這個陌生人世界如果不與人發生關係,其實是毫無意義的;而一旦與人發生關係,陌生人也就會轉化為熟人。這就是《繁花》為我們確立的“城市人‘陌生/熟識’的辯證法”。
小說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兩個場景:其一是阿寶全家搬到曹楊新村的“兩萬戶”,一下子被置於一個陌生人世界。但很快,他們便建立起新的鄰裡關係,彼此開始嘗試和諧相處互幫互助起來。其二是梅瑞在與康總的交往中,頻繁接觸生意場上的各色人等,到第二十八章梅瑞籌備大型懇談會時,與梅瑞有關的康總、李李、滬生、阿寶等均被邀請,總人數近四十桌。小說詳細開列了各桌的排位,完全就是根據關係親疏、彼此間的遠近進行了組合。這份座次表正是以梅瑞為中心的上海熟人關係網。從陌生人世界到熟人社會的轉變並不是上海城市市民自身的“熟悉化”過程,而是文藝作品通過想象再現的方式,對城市社會學長期形成的建立在與“鄉土社會”對立的基礎上所強化的對城市片面認知的糾正。
有了這個基礎,才有可能展開“滬生”們的精神世界——上海這座城市,究竟是如何塑造“上海人”及其市民意識的?在以往的城市社會學的描述中,上海一方面被指認為“移民城市”,這當然基於上海城市發展史上大量城市移民的事實,另一方面又被認為“排外”意識最強的城市,這是指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戶籍制度的影響,逐步形成了“上海人”的意識,所謂“新上海人”和“老上海人”之爭即此。但是《繁花》中所塑造的“上海人”,卻是一個並沒有明顯“排外”意識的精神世界——或者說,《繁花》的敘事重心並不指向是否“排外”,而是更加側重於“上海人講述上海自己的故事”的這種相對封閉的敘事系統。而這一來源於“弄堂網”的宗旨,恰恰成為金宇澄《繁花》找到了重新講述“當代上海寓言”的視角。

以“個體”為中心,依其社交圈子而形成“熟人社會”,但這並非“上海城市市民意識”的全部。在此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需要引入,這就是“歷史”。這裡所謂的“歷史”更準確地說是相對於“滬生”們等個體人生的“小歷史”之外的屬於民族國家的“大歷史”。此前巨集大歷史的敘事多以帝王將相、革命英雄為主人公,正是因為他們是巨集大歷史的製造者或參與者,敘述他們的經歷,也就完成了巨集大歷史的敘事。這也是中國歷史小說從《史記》等中形成的敘事成規;新歷史小說中,對巨集大歷史的解構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是歷史人物的調侃,用野史解構正史;二是選擇巨集大歷史中的邊緣性人物,通過其偏離歷史的常軌,來反思巨集大歷史敘事的有效性。
但是,《繁花》的個人史敘述,既不像正統歷史小說那樣,主人公就是巨集大歷史的弄潮兒,也不像新歷史小說那樣,主人公與巨集大歷史之間存在強烈的緊張關係。無論是人物,還是敘述者,並不以“個人與歷史之間的張力”作為關注的重點。人物的命運固然受到大歷史的巨大影響,諸如家族衰敗(作為資產階級的阿寶家被拆散,“阿寶”們被改造為工人階級)、親人離散(如蓓蒂的下落不明)、朋友反目(阿毛一度與滬生、阿寶決裂),不同的歷史時期,分別上演著不同的人生悲喜劇……但是,小說中,無論是人物還是敘述者,都沒有將反思、批判之矛指向歷史、政治、文化,而是有意克制住了這種“直抒胸臆”的表達。人物首先關注的是個人的生存、生活問題,他們的關注的問題局限在親情、友情和愛情上面。
作為一種典型的個人史的敘述,文本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敘述者和人物的時間意識。相對於完整而精確的具有歷史感的時間意識,其規範性的形態是“某年某月某日,星期幾,幾點幾分”。這種規範性的時間越精確,越表明敘述者或人物的歷史意識、時間意識的自覺,也越表明小說與“大歷史”之間關係的緊密。但是在《繁花》中,隨處可見的是“某天”、“那天”等非確指的時間標識。
小說中的“時間標識”大體可以歸為下面幾類:其一是完全的虛指,即只有一個大概的時代範圍,但沒有準確的時間節點。這又可分為兩小類,一類是顯示一種發生過多次的狀態,即熱奈特所說的“綜合性敘述”,如:“每次經過國泰電影院,阿寶就想到這段對話。”“小學時代,滬生每次經過這座老公寓”,如何如何。另一類是顯示發生過一次的事件,具體時間卻無法精確。如:“某日”蓓蒂爸爸帶回一隻兔子。阿寶“有一天”意外接到去了香港的哥哥的來信。“有一次”,祖父說爸爸“一腦子革命”。“有一天上班,阿寶發覺5室阿姨眼泡虛腫”。
其二是部分的虛指,即有一部分時間的標誌,但不完整。這又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突出“時代”標誌的,“六十年代上海,重視生日的家庭不多。滬生父母同歲同生日。”“1967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滬生、姝華到中山公園看梧桐。“1970年代的上海”,馬路遊戲如何如何。二是突出“季節”特徵的,如“早春的一夜”,汪小組與巨集慶吃夜飯。“這一日江南曉寒”,康總、梅瑞、巨集慶、汪小姐等去雙林古鎮春遊。“某年秋天的夜裡,芳妹陪了陶陶”去大碟黃牛孟先生那裡。
三是突出“年、月、日”或“星期幾”等某一單個時間元素的,如“禮拜天下午”,滬生來找小毛。李李經營至真園飯店,“某個周五,邀請阿寶、滬生、汪小姐巨集慶夫婦,康總夫婦吃飯。”“9日下午”,滬生到至真園。四是突出兩件事情之間的時間關係的,如:“此後某日,梅瑞打來電話,告訴康總,梅瑞娘終於離婚了……隔了三天,梅瑞再來電話說,我姆媽真的走了,不可能回上海了”。“幾天以後”,阿寶收到姝華的信,阿婆和蓓蒂失蹤了,等等。
在各種時間標識中,唯獨沒有規範性的歷史性的時間標誌。這一現象揭示出《繁花》所具有的基於“個人史”的時間意識: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其人生經歷並不具有大歷史所謂的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因此,“滬生”們的人生軌跡並不需要精確化、規範化到歷史時間序列之中去。所有這些“不完全的”、“非確指的”時間標識恰恰是普通老百姓基於個人記憶的時間意識——對於普通百姓(在小說中就是上海城市市民)而言,其所經歷的事件的意義或具有某個顯著的時代特徵,或隻具有某個季節性、日期性的屬性,或者隻與自己所經歷的前一個事件有某種關係,遵從這種時間意識的表現,用這種非確指的虛化的時間標識,正好準確地揭示了“滬生”們的歷史意識和時間觀念。
明確了《繁花》所堅持的以個人為中心的歷史意識和時間觀念,那麽下一個問題就是《繁花》如何處理“大歷史”和“小歷史”之間的關係?《繁花》處理“大歷史”的兩種方式:
一種是在敘述者的敘述層面,僅僅用概述的形式,以交待結果,而非原因和過程的方式。也就是評論家們已經注意到的,金宇澄的“話本”體,擅長以白描的方式,並不過多透露作家個人的判斷。如“引子”中講完滬生與梅瑞的戀情後,“兩個人關係,就此結束”,一句話交代了結果。如在第一章中,介紹人物關係和相關背景時,大多採用的是純客觀敘述的方式。客觀地概述人物及其關係的變化,顯示的是敘述者與人物之間所保持的某種客觀性歷史距離。此時儘管沒有出現“大歷史”,但這種表述方式正是“大歷史”在場的一種表現。
另一種更主要的,則是在人物的敘述,即人物的交談和對話中透露。但這裡的講述方式也不像以往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小說,通過人物之口,對其所經歷事件的完整講述,而是化解到日常的散漫的對話中。也就是說,以人物的講述為意識中介,將“大歷史”和“小歷史”並置地投射到人物大腦的意識螢幕上。儘管從歷史學的角度,其中所涉的“大歷史”事件可能具有風雲際會的性質,其意義有堪稱星雲、星系的大小,但是由於其與人物關係的遠近,投射到人物意識螢幕之中後,相反成為夜空中的繁星。“大歷史”和“小歷史”不再具有客觀真實的“大”或“小”的區分,而成了極為相似的繁星點點。
在近半個世紀的上海城市變遷中,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重大歷史事件都對上海城市及其市民帶來巨大影響,如“社會主義改造”、“破四舊”、“上山下鄉”、“造反”、“改革開放”等,但《繁花》並沒有將筆墨用於“歷史場景的還原”和“史詩性敘述”,而是將之投射到“滬生”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如第九章寫“破四舊”,則完全從滬生作為一個中學生的眼光來寫,既殘酷又有趣:“長樂中學大門口,兩個同學,發覺了滬生的新軍褲,上來搭腔攀談。此刻,淮海路方面,忽然喧嘩作亂,三個人奔過去看,是外區學生來淮海路‘破四舊’。”“滬生”們以好奇、旁觀者的心態來參與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小說寫滬生和他的這兩個同學,一直跟到陝西南路口,“看夠熱鬧,方才往回走。滬生說,實在太刺激了。”於是在身邊同學的教唆下,一起去剪香港小姐的褲腿,演化成一出令人觸目驚心的鬧劇。再比如,寫到文革,“停課鬧革命,滬生的父母,熱衷於空軍院校師生造反,一去北京,幾個禮拜不回來。姝華父母,‘靠邊站’,早出夜歸。滬生不參加任何組織,是‘逍遙派’,有時跟了姝華,出門亂走。”
本雅明在其《拱廊研究計劃》中,曾發展出一套獨特的方法論——“辯證意象”,又被稱為“凝固的辯證法”或“靜止的辯證法”(DialecticsataStandstill)。論者往往比較注重其“辯證法”與馬克思的發展運動的辯證法、盧卡奇的辯證的總體性、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之間的異同。不過,在筆者看來,本雅明方法論的重心並非“辯證法”而是“意象”。本雅明有意用“意象”替代“概念”,他的辯證法亦非抽象的“概念的辯證法”,而是極富形象性的“意象的辯證法”。
本雅明特別強調“當下”之於認識歷史的意義,認為是凝固的歷史瞬間,倡導一種立足於當下書寫歷史、透視未來的“凝固的辯證法”。他曾有過一個非常精彩的比喻:“因為意象的歷史標識不僅僅說它們屬於某一特定的時刻;而是說,首先它們僅僅在某一特定時刻才達到可理解性。……意象是那種來自星座的閃光在當下的集合。換言之,意象就是凝固的辯證法。”來自星座的閃光可能早已在太空飛行了數百萬光年,但直到映入地球上人們的眼簾的那一瞬間(當下)才顯現出意義,成為“意象”。很明顯,這種意象是當下對歷史的凝固,透過意象的分析,我們可以立足當下,反思歷史。
在《繁花》中,所有的“大時代”、“大歷史”正是以這種“星座的閃光”的方式,對人物(“滬生”們)和敘述者(或可在一定意義上視為作家本人)意識的投射。“大時代”、“大歷史”之於“城市市民意識”的關係,或可如是觀。
“文藝”《繁花》:上海人的上海地圖
2013年3月,《繁花》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立刻進入暢銷書行列,位列2012年中國小說學會“小說排行榜”的榜首;2014年1月,又出《繁花》的新版,這個版本最重要的變化是增加了由作者手繪的十七幅插圖(一共二十幅,其中三幅手繪地圖在“收獲”版《繁花》中出現過)。
二十幅插圖只有三幅與“現在上海”有關(一幅是十二章寫到玲子時,插圖反映的是上海人“貶日”情緒,一幅是花園飯店、一幅是關於小毛夢境“江鷗”的虛構),再加上一幅與作家創作有關(第二十七章部分,插入“本書出版於2013年,蛇年,畫蛇憶舊”)外,其餘十六幅插圖全部是有關“過去上海”的:其中包括四幅手繪“滬生”們活動區域的地圖(包括1960年代盧灣的局部、1970年代滬西的局部、1960-1970年代大自鳴鍾附近以及整個上海浦西的地圖概貌)、其他均為對1960-1970年代上海典型的居住太空的描繪(阿寶家、小毛家、春香家、“兩萬戶”)、青少年時代的活動太空(國泰電影院、君王堂、國營舊貨商店)以及成為記憶的城市生活習俗(物質匱乏時代的夢幻郵票、小毛們練功的器械、林林總總的開瓶器、1960年代的時尚穿著、阿寶和雪芝鏡破人散)等。

插圖形式的補充一方面固然體現出“讀圖時代”對讀者閱讀興趣和品味的某種迎合,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其實是對1960-1970年代上海城市市民居住、生活太空的某種複原。與老照片的真實再現不同,插圖的繪製可以更加充分地體現作者對太空關係的某種理解和圖示化,從而更好地重建“上海人的上海地圖”。因此,理解繼“弄堂”版《繁花》和“收獲”版《繁花》之後,“文藝”版《繁花》的地方性生產方面出現的新質,正在於進一步強化“上海市民城市太空意識的建構”。
《繁花》究竟建構了怎樣的“上海人的上海地圖”,它又是如何通過虛構性文本建構起來的?要想厘清這個問題,同樣必須將小說的“內容”(“滬生”們的人生軌跡)、“形式”(小說的結構及其敘述方式)以及“生產機制”(手繪插圖的增補)結合起來綜合考慮。
從內容上看,《繁花》的敘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受大時代影響,“滬生”們所遭遇的命運轉折,他們的數次搬家經歷正是其命運轉折的表征。其二是與“滬生”們日常生活的切身性相關的,以其居住生活之地為圓心,以親戚同學朋友的交往為半徑的“活動太空”。
從形式上看,小說以雙線並行的結構展開,繁體字的章節寫過去,分別從1950年代末一直寫到1980年代;簡體字的章節寫現在,主要圍繞滬生、陶陶、梅瑞等人物展開,集中在1990年代。其中從第二十八章起,改為1990年代的單向度敘述,直到結尾。

這種雙線並置的結構建構起了“過去上海”和“現在上海”兩種不同的太空意識的對比。這一形式並不只具有純粹的形式意義,更重要的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承載著作家或敘事者的情感價值語調,因此具有“上海市民太空意識價值”的分析維度。從生產機制角度來看,手繪插圖的增補成為《繁花》小說的“新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手繪插圖既非“老照片”,也非“舊地圖”,後者依據其生產媒介具有某種科學性和客觀性,而手繪插圖仍然屬於藝術創作領域,其實是作家依據其上海太空記憶,以插圖形式(它有別於現在流行的“卡通”、“漫畫”或者“寫生”、“素描”,其繪畫風格上體現出對早期印刷術時代的“繡像”和現代上海“連環畫”風格的致敬)對太空意識的建構產生強化作用。正如“弄堂”版《繁花》中那些與網友交流互動的“元小說”性質的文字那樣,“文藝”版《繁花》中的這些手繪插圖則形成緊密的“圖文關係”,豐富小說意蘊的傳達。
根據“滬生”們的生活太空及其在半個世紀的變遷,可以勾勒出“上海人的上海地圖”,即上海人自己對其“所在”和“所活”太空的感知、情感和觀念。從小說所展現的太空形態來看,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分類方法:其一是根據上海城市太空的物理屬性,分為“上海內”和“上海外”,其二是根據“滬生”們的活動太空的特徵,分為“居住太空”(私人太空)和“居住外太空”(公共太空)。將這兩種分類方法進行疊加,可以細分為三個子類型:“居住太空”、“上海內活動太空”和“上海外活動太空”。
從居住太空來看,《繁花》中的“過去上海”部分主要有三家:滬生家(1971年之前住在拉德公寓,1971年之後搬到武定路舊公家宿舍)、阿寶家(1966年之前與蓓蒂一家合租的盧灣司南路附近的洋房,其祖父在相鄰不遠的獨幢洋房;1966年之後是曹楊新村“兩萬戶”)和小毛家(大自鳴鍾弄堂三層閣的第三層,下面分別是一樓的理發店、二樓的爺叔家和銀鳳家)。
三家分別對應於革命家庭(作為新中國上海的首批外來移民,滬生的父母是空軍幹部,既是新中國的功臣,又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響應者)、資產階級家庭(阿寶家其祖父曾是擁有多家工廠的資產階級,但其父親曾是革命青年,與祖父決裂,上海解放之後又被審查關押,釋放之後被剝奪一切待遇,安排到雜貨公司做會計)和工人階級家庭(小毛爸爸是上鋼八廠的工人,1960年代末1971年之前的某個時間,小毛搬到莫乾山路春香家做上門女婿)。如果再加上小毛家繼續向北看到的棚戶區,《繁花》為我們建構起了“上海人”因不同社會階層歷史上所形成的四種居住太空的類型,這種並置性以及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階層居住太空的轉換,構成了多元、複雜、流動的“上海居住太空地形學”。
太空內充斥著差異、折射著人際關係——金宇澄插圖中“阿寶和蓓蒂”童年時代爬上屋頂時的溫馨與1970年代阿寶與雪芝不得不分手的傷感形成鮮明對比;小毛家位於三層閣樓的擁擠與春香家兩室戶婚房的殷實也透露出工人階級內部的生活水準的不同;當然還包括君王堂被拆,改建毛澤東像,然後再改建為錦江飯店的同一地點的歷史變遷。滬生、阿寶、小毛家由曾經有天壤之別的居住太空到1970年代後居住太空差異的縮小(其實是滬生和阿寶社會地位的降低而導致的居住環境的“惡化”),呈示出上海一系列政治運動、社會改造最終形成了“均一化”(看上去“平等化”了)的上海城市市民結構。
到了“現在上海”的寫作中,滬生、阿寶和小毛的居住太空不再成為《繁花》關注的焦點,取而代之的是“滬生”們的鄰裡、同事及朋友們的居住太空。依人物社會身份的不同,《繁花》描繪了1990年代上海市民居住太空的基本狀況:梅瑞原住虹口北四川路,房間大,後離婚搬出。於是賣掉新閘路老房間,買進延安中路底層的兩室一廳;李李的住所位於南昌路,走進沿街面一間老洋房底樓,獨門進出,外帶小天井;小琴的住處位於延慶路一條弄堂,“講起來新式裡弄,其實是底樓圍牆改造的披屋”;陶陶和小琴的同居之所是“六十年代老公家宿舍,四樓一室半”所有這些都是在新式居民小區改造和建設之前,上海市民的主要居住太空形式:其來源一方面是合租的老洋房、舊公寓,另一方面舊式老公家宿舍,居住太空都很局促,這也決定了上海市民長期以來形成的人際交往習慣:除非極為熟識的親戚同學朋友,一般情況下都不會“登門拜訪”,而會在市裡尋找一處碰面的地方——私人太空(居住太空)和公共太空(交往活動太空)的區分形成上海市民文化的城市景觀。

在上海市民的“活動太空”中,可以分為“上海內的活動太空”和“上海外的活動太空”,通過對《繁花》“過去上海”和“現在上海”的比較,我們不難構建出上海市民從1960年代直到1990年代以來的活動區域及其交往方式。
從活動區域來看,“滬生”們“上海內的活動太空”主要圍繞其居住之地展開。首先,其居住太空具有“家庭聚居”和“同學相鄰”的特點。所謂“家庭聚居”就是指親緣關係的聚居性質,類似阿寶那樣的資產階級大家庭祖孫三代住所相距甚近、彼此之間守望相助。所謂“同學相鄰”是指“滬生”們少年時期所建立起的朋友夥伴主要來源於同學關係,而“就近入學”一直是中國的入學傳統,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造期間,社會階層的區隔被打破,這才形成了滬生、阿寶、小毛三個不同社會階層的同學能夠相識相知的現象。
其次,其活動半徑因交通方式以步行為主、公交為次(僅阿寶祖父能夠有私車接送)主要集中在三塊地方:“文革”之前,集中在盧灣北至巨鹿路、南至複興路、東過思南路、西達陝西路方圓這片區域;“文革”之後,新增兩塊區域:曹楊新村“兩萬戶”附近,經過中山北路、穿過蘇州河、南抵長壽路這片區域以及大自鳴鍾、玉佛寺附近北抵蘇州河、南達南京西路、東到石門路、西近西康路的一片地方;再次,還因阿寶祖父搬到閘北,大伯搬到提籃橋,《繁花》的“上海地圖”也延伸到了閘北、虹口、楊浦等東北方向,但只是呈點狀分布。
最後,到了“現在上海”時期,“滬生”們各自成家立業,家庭、同學之間的交往更多地被同事、朋友間的聚會所取代,但從金宇澄所繪地圖顯示,其活動領域仍相對集中在南達盧灣、西抵普陀、東北到黃浦的這片“上海老城廂”。金宇澄的四幅手繪記憶中的上海地圖拚在一起,正好涵蓋了“上海浦西”的全部。
“滬生”們“上海外的活動太空”則體現出明顯的江南特色,童年時期,蓓蒂阿婆帶阿寶和蓓蒂到紹興鄉下,交通不便,歷經坎坷;成年之後,“滬生”們動輒到江浙遊玩,先後去了雙林古鎮、蘇州、常熟、昆山等地。這些活動太空突顯的,是上海市民對於江浙城鄉的雙重意識:一方面是“鄉土中國”(在上海人意識裡,“外地人”就是“鄉下人”),另一方面則是“消費社會”(蘇州常熟等地歷來被視為上海的“後花園”,吃喝玩樂、休閑度假的地方)。
此外,還有一類太空意識也頗為重要,即通過不同人物的經歷所建構起來的“上海人的全國地圖和全球地圖”,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地方在上海市民意識中的位置。如在“過去上海”時期,小說寫姝華知青到東北,阿寶哥哥在香港,上海人對東北和香港的複雜情感;到了“現在上海”時期,李李來自深圳、白萍出國(先後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玲子與日本人的關係、林太來自中國台灣,並由此展現出上海人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刻板印象,等等。
特定的活動太空是與特定的交往方式相聯繫的。在《繁花》寫作過程以及此後的評論中,“飯局”成為倍受關注的問題,正在於“滬生”們的交往方式主要是通過吃飯來完成的。但這並不是太準確。在少年時代,“滬生”們還有另一種更主要的交往方式:“蕩馬路”。《繁花》的第三章第三節詳細描寫了一個禮拜天下午滬生去大自鳴鍾弄堂找小毛玩,然後一起“蕩馬路”的過程。從滬生的視角描述了小毛家的居住狀況,依次從底樓的理發店,寫到二樓的銀鳳,再到三樓小毛家,“看老虎窗外,滿眼是弄堂屋頂”。然後下樓,開始漫無目標的“蕩馬路”。
還有第五章第三節,小毛來找滬生玩,兩人一起去南昌公寓找姝華玩,然後兩人繼續“蕩馬路”;第十一章第三節,滬生和姝華再次經過瑞金路長樂路轉角,看見被拆掉的君王堂上搭起了一座四層樓高的大棚;第十五章第三節,滬生與姝華、阿寶以及阿寶在曹楊新村的新鄰居小珍和小強,五人一起去長風公園,然後到華東師范大學,蘇州河等。
與“蕩馬路”相比,“滬生”們成年之後的交往方式“飯局”(吃飯、喝茶)具有了不同的特點:首先是“地方性”的地理特徵不再突出,對於“滬生”們來說,只有“終點”意識,不再有“蕩馬路”的過程感覺,因此,所有的飯局,幾乎都是“到了某某飯店”這樣極為簡潔的敘述;其次是交往對象開始複雜,既有朋友聚會,還有商務宴請,既有私密交往,還有大擺宴席,正因為如此,飯局才成為《繁花》濃縮上海市民社會關係,展開矛盾衝突的最佳選擇。
但是,“蕩馬路”和“飯局”還只是上海市民交往方式的外在表現形式,“蕩馬路”並不在乎從哪裡出發,蕩到哪裡去,或者在路上發生了哪些事情(如公路電影、流浪漢小說等的常見套路),而在於“蕩”這一過程本身中,小夥伴們通過話題散漫的閑聊,消磨了時光,加深了感情。“飯局”也不在乎吃了什麽菜、喝了什麽酒,而在乎是跟誰一起吃的,在吃的過程中的聊天。因此,《繁花》最為精彩的,也是最為重要的寫作特色即在於幾乎所有的章節,都充斥著“話題散漫”、“無軌電車”的“上海閑話”。這種“上海閑話”不僅僅成為《繁花》塑造人物、推動情節發展的“描寫對象”,更重要的,也成為金宇澄作為敘述者的“敘述方式”。
首先,聊天作為人類日常交往方式,不像嚴肅正式的談話,會有明確的主題、意圖;有時聊天甚至只是正式談話的前奏、插曲或者調劑。但是在《繁花》中,金宇澄賦予其“核心”、“主體”的具有支配性的地位:按普羅普民間故事形態學的分析方法,《繁花》中的“行動”可以分為一些核心功能:“蕩”、“吃”、“性”以及“聊”,而“聊”可謂“核心中的核心”。正因為如此,有一搭沒一搭,講完張三說李四,成為《繁花》聊天式敘述的基本特點。
這種敘述方式形成了與一般通俗小說巨大差異的敘事風格:一方面,所有的“聊”——不管是長聊還是短聊,無論是兩個人私聊,還是一桌人群聊——本身不具有推動情節、激化矛盾、設定懸念等敘事功能,隨著話題的轉換,聊過也就“忘”了,以前聊過的內容對後面情節的發展不再具有推動作用;但另一方面,聊的特點是追求“即時的快感”,即聊的當時非常熱鬧、不冷場,讀者也會覺得聊得有趣,所有單個的聊都構成一個個精彩的小故事,極富質感地反映著上海風格。
其次,聊具有“對話性”,即所有的聊一定是針對具體對象的聊,如“引子”中滬生與陶陶的聊,陶陶所有的講述,都是講給滬生聽的,此時,陶陶是敘述者,滬生是聽眾(讀者)。聽眾有“應答”,有積極性應答,也有消極性應答,於是就有了最極端的消極性應答方式——“不響”。在小說中,“不響”出現次數頻繁,達千次之多。全書引言前的題記:“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也將“不響”置於核心地位。從接受者而言,“不響”的原因很複雜:沒話說、不想說、沒法說、不能說……針對具體的情境及其所涉及的聊天的主題,“不響”亦可引申出更為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或者說,“不響”成為一種極具標誌性的行為,成為普通城市市民在面對諸多社會矛盾、文化衝突、人生命運時“以不變應萬變”的策略。
與“不響”相配套的,就是講述者的極端情況:“獨白”,即“對話的不可能性”,如十八章,李李與阿寶的聊天,阿寶始終處於“不響”,偶爾應付性的哼哈“應答”的狀態,這就使得李李的講述相對完整。李李有強烈的傾訴的欲望,講述了早年做模特時的辛酸,而阿寶則不想讓李李沉浸在過去的痛苦回憶中。於是出現了李李大篇幅的自述場景,如過電影一般。由此,《繁花》的聊天具備了展現人物性格、人際關係、人情冷暖的敘事功能。
第三,“聊”的敘述倫理。《繁花》的敘述結構很特別。此前的“過去上海”和“現在上海”的交叉性只是外在性的屬於“情節結構”的特點。從敘述結構來看,《繁花》所敘述的故事可以分為多個層面:第一層次是由作家敘述的故事。滬生等各色人等在1950年代末到1990年代近半個世紀的人生變遷。其敘述特點是白描、滬語、話本體以及太空的具體化和時間的模糊化(即此前所分析的,絕大多數的時間標記都是基於個人經驗的“記憶時間”)。第二個層次是在各種“蕩馬路”、“飯局”、“喝茶”等場景中由人物所講述的故事:小說不以人物的行動為主,而是以人物之間的講述為主,形成“關於人物敘述的敘述”的套層結構,這構成了《繁花》敘述內容的主體部分。

“所敘之事”通過人物之口來“講述”,而且均有特定的具有應答能力的聽眾(聊天的對象),都附著上了人物獨特的情感、價值、語調。任何人物的“事之所敘”也同時包含雙重目的:一方面是對“事”的講述,另一方面則是與他者交流的需要,要達到交流的目的。由此,人物的講述部分具有了散漫性、對話性、未完成性等可供敘事倫理分析的諸多層面。對於《繁花》的讀者而言,我們只能憑借作家的敘述、人物的敘述來重建對“滬生”們大半生以及上海城市近半個世紀的認識了。
正在於對“過去上海”和“現在上海”的精確複原(通過文字的,包括語音的,影像的,也包括地圖的),《繁花》才具有了記錄上海歷史文化和社會變遷的“民族志”的意義和價值。通過對《繁花》地方性敘述的分析,一個更大的問題產生了:如果說《繁花》中“滬生”們始終都生活在熟人社會之中,並因社會階層的差異而形成差序格局的話,那麽,《繁花》及其所再現的上海城市仍是費孝通“鄉土中國”的一部分,還是內在地構成了對“鄉土中國/現代中國”二元關係的解構?
《探索與爭鳴》人間體
聯絡員小探
xiaotanxiaosuo
轉載 | 合作 | 谘詢 | 建議
長按掃碼加好友
END
人文社科學者的平台
《探索與爭鳴》
唯一官方微信平台
版權所有。歡迎個人轉發,媒體轉載請聯繫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