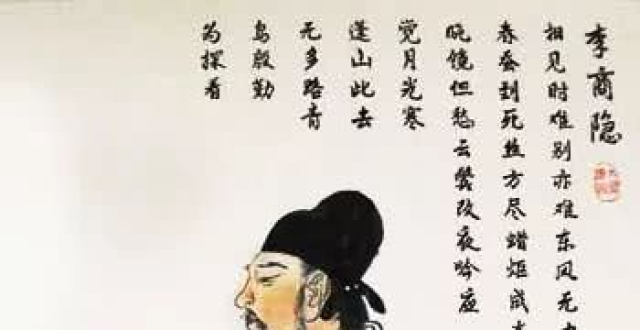內容摘要:樂府題解是“題解類批評”最重要也是最常見的一種樂府詩批評方式。與樂府題解始終相伴而行的是“四本”。“四本”是指存在於舊題樂府(古樂府)中的“本事”、“本題”、“本文”、“本義”,前三者均是為“本義”服務的,“本事”則為弄清楚一首樂府詩題旨的關鍵所在,故而,大凡從事“題解類批評”者,都在探討“本事”上下功夫。但從總的方面言,“四本”是各有其功能而又各具特點的。
關鍵詞:舊題樂府 樂府題解 四本特點

樂府詩雖然是詩歌大家庭中的一個重要成員,但從樂府詩批評的角度言,其卻是與詩歌批評有著許多之不同的,比如,關於是否可以配樂傳唱的問題,即為其一。又如,對樂府詩題(此主要指舊題樂府,下同,不另注)“本事”的勾勒與箋釋,甚至是考證等,則更是詩歌批評之所無。凡此等等,所表明的是樂府詩批評自有其規律與特點的,若不諳此,或者將樂府詩批評等同於詩歌批評,就有可能鬧出許多笑話來,更有甚者,則是對時人與後人之誤導。所以,從事樂府詩批評,是大不可以詩歌批評的方式、方法進行的。

在《中國樂府詩批評史》一書中,我曾根據歷代樂府詩批評的特點,將三千年的樂府詩批評分為六種類型,即“整理類批評”、“選擇類批評”、“題解類批評”、“品第類批評”、“專論類批評”、“注釋類批評”,並對每一種批評類型的概念或者定義在有關章節中進行了界說。僅從這些名目即可知,樂府詩批評的類型也是很有特點的,如“題解類批評”中的“四本”即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什麽是“四本”?“題解類批評”與“四本”的關係又是如何?“四本”之間的相互關係又是如何?而所有這些,卻構成了一個從無研究者涉及的文學問題,本節即重在對此進行考察與討論。
1、樂府題解與本事

樂府詩批評最常用的方式、方法之一,就是“題解類批評”。“題解類批評”是指以“題解”為主要批評對象的一種類型,其重點是對樂府詩題的箋釋,其中,對“本事”的勾勒與對所涉“人”或“事”的背景交代,則又為其主要者。“本事”,又稱“故事”、“故實”,是“題解類批評”中的“四本”之一(另外“三本”分別為“本題”、“本文”與“本義”),其既有指事之逸者,亦有指事之真、之虛者,而探其原委與始末,即為“題解類批評”表現在“本事”方面最核心的內容。一般而言,樂府詩中的“本事”,雖然“虛”、“實”均有,但以“真事”、“實事”為主,“虛事”則次之。所謂“虛事”,亦即“幻事”之謂,主要與神話傳說相關聯,也有出自小說家之言者,雖甚荒誕,但題解者卻多在“窮其原”上下功夫。如《樂府詩集》卷十六有《上陵》一詩,為《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之一,郭茂倩所撰題解在引智匠《古今樂錄》、范曄《後漢書·禮儀志》之後,乃雲:“按古辭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畢曲同否?”其中的“言神仙事”雲雲,即屬“虛事”之列。又如《樂府詩集》卷五十七《神人暢》題解引謝希逸《琴論》有雲:“《神人暢》,堯帝所作。堯彈琴感神人現,故製此弄也。”《神人暢》是否為“堯帝所作”,這裡不作討論,但謝希逸《琴論》之“堯彈琴感神人現”者,則顯屬“虛事”。
而“真事”、“實事”,乃為樂府詩“本事”之最重要者。以蔡邕《琴操》為例,便可對此有所認識與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續修四庫全書》本《琴操》,凡上下二卷,共收錄“前樂府”四十七篇(首),其中為:(1)有詩題、題解、琴辭(即樂府詩本文)者二十四篇;(2)有詩題、題解者二十篇;(3)有詩題而無題解、琴辭者三篇.在此四十四篇題解中,所涉之“本事”皆屬“真事”、“實事”,即皆可在左丘明《左傳》、司馬遷《史記》等史籍中找到出處。而且,有的題解之篇幅還相當大,因而所涉內容也甚為豐富,如上卷《履霜操》的題解即屬如此。其題解全文為: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奇編水荷而衣之,采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詞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遂射殺後妻。
全篇題解凡二〇余字,既交代了《履霜操》的作者,又將尹吉甫之子尹伯奇的遭遇一一道來,故事較為完整,且不乏戲劇性情節,儼然一篇質量上乘的人物傳記。而更為重要的是,尹吉甫、尹伯奇作為周宣王時期的兩位“本事”人物,在相關著述中均有記載,可確證其所言事乃“真事”、“實事”之屬。又如《別鶴操》所言陵牧子之“事”,崔豹《古今注》卷中、徐堅《初學記》卷十六之所載,則可與之互為印證,表明其亦為“真事”、“實事”之屬。其他如《拘幽操》之周文王、《周太伯》之周太伯、《箕山操》之許由、《將歸操》之孔子等,司馬遷《史記》均有載,所表明的是這些詩題中的“本事人”及“本事事”,都是有所依據的。
“本事”之於樂府詩,要而言之,其作用主要有二。其一是規範樂府詩的本真用意之所在,即什麽樣的樂府題,寫什麽樣的內容,否則,即有“越軌”之嫌。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序》有雲:“歷代文士,篇詠實繁。或不睹於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夫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彼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斑者,但美繡項綿臆;歌天馬者,唯敘驕馳亂踏。類皆若茲,不可勝載。”在這裡,吳兢雖然是就其所撰《樂府古題要解》之動機而言,其實際上是已涉及到了樂府詩與“本事”的關係問題。吳兢認為,《公無渡河》與“贈夫利涉”毫無關係;“慶彼載誕”亦非《烏生八九子》之所寫,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在於“後生”們不明樂府題所蘊含的“本事”之所在。所以,其於《烏生八九子》之“要解”中寫道:“右古詞:“‘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出岩石間,而來為秦氏彈丸所殺。……若梁劉孝威‘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但詠鳥而已,不言本事。”所謂“不言本事”,是指劉孝威《烏生八九子》(參見《樂府詩集》卷二十八“相和歌辭三”)之所寫,與《烏生八九子古辭之“本事”了不相涉。
“本事”之於樂府詩作用的第二個方面,是可增強詩中所寫人或事的真實感與可信度,清人朱乾《樂府正義序》之“事則案諸史”雲雲,即與此甚為關聯。其中有雲:“乾以為既曰詩,未有不可被之弦歌者。……今以《三百篇》例之……則見其中美者,可以勸善惡者,可以懲尤,夫三百也。……義則本之經,事則案諸史。”所謂“事則案諸史”,是指“本事”所涉之“人”或“事”, 即都要真實可信,經得住史籍的檢驗。也即在朱乾看來,樂府詩所寫之事或人,只要能“案諸史”,讀者就自然會對其信而不疑。正因此,朱乾於《樂府正義》之中,雖然重點是對樂府詩“正義”,也就是對他人之“義”予以辨駁,但於“本事”所涉及之“人”或“事”,即皆以“案諸史”的方法而為。此則表明,朱乾《樂府正義》之“正義”,都是可以“案諸史”的(對於朱乾《樂府正義》,另可詳下)。
以上之所述所論,所表明的是“本事”在樂府詩中的重要性。正因為重要,故自西漢揚雄《琴清英》始,歷朝歷代的樂府詩批評著述皆於“題解類批評”中,乃將對“本事”的勾勒放在首位,其目的自然是對其重要性的強調。
2、樂府題解與本題
由於戰爭與歷史久遠等多方面的原因,樂府詩在流傳的過程中,其詩題與其它文學品類的題目一樣,均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變化”,因之,與原詩題的差異性也即由此而得以突顯。此外,不同的集本與不同的版本,所著錄之同一作者的樂府詩題,也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之差異的,如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七“相和歌辭二”收有李白《登高丘而望遠》一詩,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卷四、宋鹹淳本《李翰林集》卷四,均作《登高丘而望遠海》,即一有“海”字,一無“海”字,二者孰是?若從版本學的角度審視,兩種宋刊本李白集,顯然是均較《文苑英華》為後的,則當以無“海”字為是,但是否如此,尚需進行具體考察。又,有一些樂府詩題在傳播的過程中,還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式的詩題,如《箜篌引》即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辭一”著錄李賀《箜篌引》一首,並撰題解雲:“一曰《公無渡河》。”《箜篌引》在其發展的路途中,是如何演變為《公無渡河》的,研究者對其之孰是孰非卻缺乏具體的考察,因而使得這兩種樂府詩題一直並行至今。其它如《黃鶴吟》一作《黃鵠》,《隴頭吟》一作《隴頭水》、《豔歌何嘗行》一作《飛鶴行》、《步出夏門行》一作《隴西行》、《薤露歌》一作《薤露行》、《相逢狹路間行》一作《長安有狹斜行》、《怨歌行》一作《怨詩行》、《思婦分》一作《離拘操》,《銅雀台》一作《銅雀妓》等,亦皆具有相當的差異性。
以上之所述,實際上涉及的是樂府詩批評、特別是“題解類批評”中的“本題”問題。題解類批評”中的“本題”,指的是樂府詩最原始、最本真的詩題,也即具有明顯的原生態特徵的詩題。而樂府詩的詩題,與其它類別的詩題如聲詩、歌詩、徒詩等詩題相比,又有著一種與眾不同的特點,即其首先是音樂之題(曲名),然後才是樂府詩之題(辭名),而從演化的角度考察,只有這種早先的音樂之題,才能成為樂府詩的原始詩題,也就是“本題”。如上所述,樂府詩中的“本事”固然重要,但“本題”之於樂府詩則也是重要的。這是因為,如果“本題”不明確,其“本事”、“本義”或者“本文”,也就有可能因此而模糊,不明就裡,難以藉之作出準確、中的之題解。所以,品評一首樂府詩,既要熟悉其詩題之由正格向變格演變的過程,又要知曉其“本題”與“非本題”的區別。為便於認識,下面茲以《釣竿》一題為例,以略作論析。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八著錄曹丕《釣竿》一首,並於題解開首引崔豹《古今注》雲:“《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為樂曲。”據此可知:(1)《釣竿》古辭是一首妻子思夫的愛情詩;(2)其作年在司馬相如《釣竿詩》之前。據三秦出版社版《中國文學辭典·古代卷》,司馬相如卒於公元前一一七年,其時距漢武帝“乃立樂府”的元朔五年即公元前一二四年,乃有七年之隔,則《釣竿》古辭的問世,當在漢武帝元朔五年之前,也即《釣竿》當為一首“前樂府”。但值注意的是,《樂府詩集》同卷並沒有司馬相如的《釣竿詩》,而是將劉孝綽《釣竿篇》收入。又,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上卷於《釣竿》之題解後有“總評”雲:
以上樂府鐃歌。案漢明帝定樂有四品,最末曰短簫鐃歌,軍中鼓吹之曲。……又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等十八曲,字多紕繆不可曉。《釣竿》一篇,晉代亦稱為漢止於十八,恐非是也。
按,《樂府古題要解》認為“《釣竿》一篇,晉代亦稱為漢止於十八,恐非是也”的認識,實則為誤。檢房玄齡等《晉書》卷二十三《樂下》有雲:“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台》、《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入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其中明言漢《短簫鐃歌》有二十二曲,而非“晉代亦稱為漢止於十八”。正因為晉代沒有“稱為漢止於十八”,故而在晉武帝司馬炎即位後,即命傅玄依漢製仍“製為二十二篇”,以述“功德代魏”,且二十二的最後一篇,又恰為《釣竿》。還值注意的是,在傅玄所製之晉《短簫鐃歌》二十二篇中,有二十一篇的曲名全改為新名,如《朱鷺》改為《靈之祥》等,唯“《釣竿》依舊名”(《晉書》卷二十三《樂下》)。其中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上述之論之析表明,為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八所收錄之曹丕《釣竿》,乃系依崔豹《古今注》所載之《釣竿》而作,而《古今注》所錄載之《釣竿》,即為此樂府題的“本題”,其後的《釣竿詩》、《釣竿篇》等,乃皆非“本題”之屬。又,《釣竿》既為“本題”,則其之“本事”,就理所當然應以崔豹《古今注》所載為是,而《晉書》卷二十三《樂下》之“列入鼓吹,多序戰陣之事”者,顯系後來因演變而使然之結果。而此,則又可表明,作為“前樂府”的《釣竿》一題,其“本事”是關於“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者”的故實,而非房玄齡等《晉書》卷二十三《樂下》所言之“多序戰陣之事”雲雲。
正因為“本題”在樂府詩題解中具有與“本事”直接關聯的特點,所以,歷朝歷代的樂府詩批評家均於“本題”極為重視,如明人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即曾如是寫道:“用本題事而不失本曲調,上也。”所謂“本題事”,就是“本題”所蘊含的“本事”。又,上舉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於所收錄“古題”下的十數例“一作×××”之注,所反映的亦是吳兢對“本題”的重視。不獨如此,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中的這些“一作×××”之注”,其絕大部分“古題”皆為“本題”之屬,而其所“要解”的亦幾乎全為“本事”,因之,僅就此而言,《樂府古題要解》實為“本題”與“本事”相結合的一部佳例。如此,其於後世樂府詩批評的影響之深之遠,也就不言而喻。
3、樂府題解與本文
“本文”是樂府詩的最重要部分,故而,大凡研究樂府詩者,“本文”即成為了其研究的關鍵所在,而一首樂府詩的文學價值如何,或者其文獻學價值如何,“本文”亦自然為其關鍵之所在。所以,只有“本題”而沒有“本文”的作品,研究者是很難藉之以窺探其文化背景的,也是很難去認識作者寫作動機的真面目,以及所要表達的思想與情感的,如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誌第十》之所著錄者,便是這樣的一批作品。其具體為:

《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十四篇、《出行巡狩及遊歌詩》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儒子妾冰未央才子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歌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洛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這是由周而漢的“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歌詩的“本題”。雖然如此,但後人卻很難從這“三百一十四篇”歌詩的“本題”中,對歌詩在周、漢時期之發展與繁榮的真實情況作一具體描述,原因是其只有“本題”而無“本文”。
正因為“本文”是如此的重要,故其在“四本”中所佔的地位,於樂府詩批評中所起的作用,也就非其它“三本”可以相比。而研究者在對樂府詩進行“整理類批評”或者“選擇類批評”時,首先所考慮的對象即為“本文”者,又可為之佐證。雖然如此,但“本文”之於樂府詩的“題解類批評”中,又往往與“本題”一樣,即由於戰爭與歷史久遠等多方面的原因,而於流傳的過程中,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有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綜而言之,“本文”所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具體為:
一是字詞訛誤。如王維《隴頭吟》的最後一句,殷璠《河嶽英靈集》卷中作“節旄落盡海西頭”,李昉等《文苑英華》一二五作“節旄零落海西頭”,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一、宋蜀刻本《王詰摩文集》卷一,皆作“節旄空盡海西頭。”在這三種著作中,殷璠《河嶽英靈集》為唐人著作,最具版本學上的權威性;李昉等《文苑英華》為官修著作,權威性是無須懷疑的;而郭茂倩《樂府詩集》為樂府詩專書,具有極強的可靠性。雖然如此,但“落盡”、“零落”、“空盡”三者孰是,則尚須作具體考察後方可回答。
二是有曲名(詩題)而無曲辭。如蔡邕《琴操》卷上之《鹿鳴》、《伐檀》、《雛虞》、《白駒》、《鵲巢》,卷下之《梁山操》、《諫不違操》、《三士窮》等,即皆為其例。而在現所存見的“前樂府”中,如《鹿鳴》等之有題無辭者,則並非少許。
三是文字脫衍。為便於認識,茲舉“脫”字例如次。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一九三盧思道《升天行》一詩雲:“尋師得法訣,輕舉厭人群。玉山候王母,珠庭謁老君。刻作長生文,飛策乘流電。……不學蜉蝣子,乾侶何紛紛。”最後一句的“乾侶”下有注雲:“一作迢,一作葬。”如果依這兩個“一作”,“乾侶何紛紛”就成為了“迢何紛紛”,或者“葬何紛紛”,此詩為五言,則“迢何紛紛”或者“葬何紛紛”,就明顯地脫一字。而郭茂倩《樂府詩集》六十三“雜曲歌辭三”收錄此詩,最後一句正為“葬何紛紛”,即與“一作葬”同,顯為錯誤,所以,中華書局版校點者即據《百三名家集》,將其補改為“生死何紛紛” 。
對於 “本文”所存在的上述之問題,一般而言,樂府詩批評者大都盡量予以解決,而解決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在題解中進行訂正,一是於“本文”錯誤處予以校補。但也有將此二者融入一首詩者,如蔡邕《琴操》所收之“前樂府”即皆如是,因文字較繁,讀者自可參看,此不具引。
題解之於“本文”還存在著另一種情況,即題解中往往夾雜著某一樂府詩的“本文”(其或為整首詩,或為某一名句等),而使之得以保存並流傳於世,如上引蔡邕《琴操》卷上之《履霜操》題解,即為其例。其中有雲:“(尹伯奇)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經與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五十七所收錄之尹伯奇《履霜操》比對後可知,此六句乃為《履霜操》“本文”的全文。又如《箜篌引》之題解:
《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裡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刺船而濯,有一狂夫被發提壺,涉河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河水死。乃號天唏噓,鼓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曲終自投河而死。子高聞而悲之,乃援琴而之,作《箜篌引》以象其聲,所謂《公無渡河》曲也。
其中的“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河死,當奈公何?”四句,即為《箜篌引》全詩之“本文”。而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下卷於《公無渡河》題下的“本《箜篌引》”之注釋,系據此而為者,乃可論斷。又宋人劉次莊《樂府集》之於《將進酒》的題解為:
《將進酒》,魏謂之《平關中》,吳謂之《章洪德》,晉謂之《因時運》,梁謂之《石首扃》,齊謂之《破侯景》,周謂之《取巴蜀》。李白所擬,直勸岑夫子、丹丘生飲耳。李賀深於樂府,至於此作,其辭亦曰:“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嗟乎,作詩者擺落鄙近以得意外趣者,古今難矣。
這條題解,不僅較詳細地列舉了《將進酒》的別名(其實也與“本題”相關,這種於“本題”之外詳列非“本題”的舉措,在宋、元、明、清各朝的樂府詩專書中,是很少見到的),而且還涉及到了李賀《將進酒》的“本文”問題。此則表明,“本文”與“本題”之於“題解類批評”中,乃是多為批評者們將其融合在一起的。而這樣的例子,在自漢而清的樂府詩批評著作中乃甚多,對此,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各章節所引之例文,已有所涉及,可參看,此不具引。
4、樂府題解與本義

樂府詩“題解類批評”的範圍雖然甚為廣泛,但其終極目標則是對一首樂府詩的“本義”(或寓意)的準確探討,因此之故,也就有了諸多樂府詩批評者對樂府詩“本義”探討的介入。更有甚者,則是有研究者推出了探討樂府詩“本義”的專書,如明代徐獻忠、清代朱嘉徵、朱乾等人,即為其例(具體詳下)。如此,就涉及到“題解與本義”的問題了。“本義”又稱“本意”,指的是一首樂府詩所要表達的實際意義,也即一首樂府詩的題旨之所在。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九有雲:“太白於樂府最深,古題無一弗擬,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出其新意,合而若離,曲盡擬古之妙。”在這裡,胡震亨雖然是對李白的“擬古”樂府進行了評論,但其中將“本意”與“新意”對舉,則“本意”之於樂府詩者,已是甚明。
而正是因了“本義”在樂府詩中的重要性,故在明、清兩代即問世了多種專門探討樂府詩“本義”的著作,如徐獻忠《樂府原》、朱嘉徵《樂府廣序》、朱乾《樂府正義》等,即皆為其代表。《樂府原》主要在於“原”樂府詩之“本意”,而《樂府正義》所“正”之“義”,則為一首樂府詩最本真之“義”。 朱嘉徵《樂府廣序》之所指,則是謂以多種方法“序”(探求)樂府詩之“本義”。總而言之,三書均在探討樂府詩的“本義”上,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以徐獻忠《樂府原》為例,如卷三《有所思》的題解為:
此以思歸比君子也。言我思所在遠方,而以珠玉玳瑁問,遺之以寄情也。奈何君有他心,而不專於我,則以所欲遺者,擢之使毀,燒之為灰,且當風揚散以滅其跡,以寄情也。從今以往,勿複相思而與君絕矣。君若再來,則雞鳴狗吠,兄嫂必知之,夜中妃且呼豨不睡,秋風且起,東方且白,決無見君之期,甚言決絕之情也。
徐獻忠《樂府原》題解的最大特點,就是於開首直言其“原”之所在。在這段題解文字中,徐獻忠首先開門見山地托出了其於《有所思》“本義”的認識:“此以思歸比君子也”;繼之則認為這是一首“寄情”之作,其“本意”是指女子稱男子“不專於我”,而“從今以往”,“決無見君之期,甚言決絕之情也”。經過比對可知,徐獻忠的這一認識,雖然是以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六所引《樂府解題》之“從今以往,勿複相思而與君絕矣”為基礎的,但卻較其更為精準。又如卷四《折楊柳》題解:“折楊柳者,邊塞戍征之士見春光再榮,別離難合,折之以寓悲感之思也。其或閨中思婦縫衣欲寄寒信,忽回春柳,複變感而悲焉,亦其情也。”徐獻忠的這一認識,較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二於此詩所撰題解而言,顯然是更加接近是詩意旨之真實性的。而綜徐獻忠《樂府原》十五卷又可知,其於題解中“原其本意”(徐獻忠《樂府原序》)之所獲,較前人如左克明《古樂府》等,則是更勝一籌的,對此,拙著《中國樂府詩批評史》第八章第二節已言之甚詳,此茲罷論。
再看朱乾《樂府正義》。《樂府正義》凡十六卷(含論文一卷,二十二篇,連同書末“附論”中的九篇,共三十一篇),其最令人矚目之特點,是採用考證的方法以“正”前人之“義”,即在辨駁前人“義”的基礎上提出屬於自己的“義”。為便於認識,茲舉卷九對陸機《泰山吟》所“正”之“義”如次:
按左思《齊都賦》注雲:《東武》、《泰山》,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其非喪歌亦明矣。士衡《泰山》,適感幽塗,武侯《梁甫》,偶悲三墓。自開三圖有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主死之說。而《樂府解題》,遂謂《泰山吟》,亦《薤露》、《蒿裡》之類,郭氏附會之,謂《梁甫吟》亦葬歌,不聞歌土風者,歌虞殯也。《解題》一書,但依樣模形,不識古義類如此。
這是對陸機《泰山吟》“本義”所進行的考辨,故在開首即引左思《齊都賦》之注,以為立論的依據,繼而則認為,《泰山吟》與《東武吟》一樣,“皆齊之土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其非喪歌亦明矣”。這是對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一引《樂府解題》所持“喪歌”說的辨駁。所以,接下來即有“而《樂府解題》,遂謂《泰山吟》,亦《薤露》、《蒿裡》之類,郭氏附會之,謂《梁甫吟》亦葬歌,不聞歌土風者,歌虞殯也”一段文字,其中的“郭氏附會之”雲雲,所指即《樂府詩集》於《泰山吟》題解引《樂府解題》之“喪歌”所言。而“士衡《泰山》,適感幽塗”,即為朱乾對陸機此詩“本義”的認識。
最後看朱嘉徵《樂府廣序》。《樂府廣序》三十卷,將所收三五〇首樂府詩分為十類,黃宗羲等人為之序。《樂府廣序》重在“序本意”,其特點是簡明、直接,如認為“《雞鳴》,刺時也”(卷一),“《陌上桑》,婦人以禮自防也”(卷一),“《箜篌引》,歌置酒宴樂也”(卷八),“《東都五詩》,歌明堂、辟雍、靈台、寶鼎、白雉,漢中興頌也”(卷二十二)等等。如上所言,《樂府廣序》重在從“廣”的角度“序”樂府詩之“本義”,故其除了“題解類批評”外,還對三五〇首樂府詩進行了“箋釋類批評”,即其“廣序”是集這兩種批評形式於一書的,但僅就“題解類批評”言,其於樂府詩“本義”的探求,卻是要較徐獻忠《樂府原》、朱乾《樂府正義》遜色許多的。
注釋:
具體參見《中國樂府詩批評史·自序》,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頁。
蔡邕《琴操》卷上,《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第1092冊,第149頁。
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卷首,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郭茂倩《釣竿》題解,《樂府詩集》卷十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62—263頁。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上卷,《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8—39頁。
房玄齡等《晉書》卷二十三《樂下》,中華書局1967年版,第701頁。
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誌第十》,嶽麓書社1993年版,第776—777頁。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六十三,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21頁。
蔡邕《琴操》卷上,《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第1092冊,第151頁。
劉次莊《樂府集》之於《將進酒》的題解,據阮閱《詩話總龜》卷七引,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頁。
徐獻忠《有所思》題解,《樂府原》卷三,《明詩話全編》本,鳳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頁。
朱乾《泰山吟》題解,《樂府正義》卷九,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本文原載《聊城大學學報》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