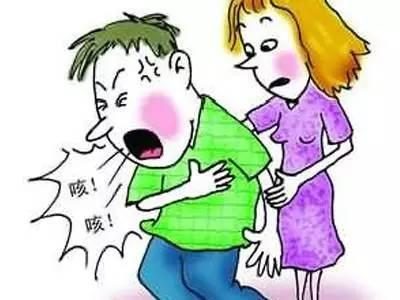周平安
(1939-2017)
我國著名呼吸病、熱病、疑難病專家,長期擔任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專家委員會專家,傳染病防治專家組核心專家,北京中醫藥薪火傳承名醫工作站名醫,第四批全國老中醫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國務院專家保健委員會專家,第三屆首都國醫名師。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高等中醫院校培養的第一代中醫,周平安先生52年來一直奮戰在中醫臨床第一線,曾長期擔任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及東方醫院急診科主任、呼吸病科主任、大內科主任、疑難病會診首席專家。在長期臨床實踐中,他在強調完整繼承、熟練運用中醫辨證論治思想和方法的基礎上,充分借鑒現代醫藥學乃至現代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主張中西醫結合是中醫藥學術發展的重要途徑。晚年進一步凝練其學術思想,以「和法」統領臨床諸法諸病,診療範圍逐漸擴大至傳染性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消化系統疾病、風濕免疫病、腫瘤等多種疾病並取得良好療效。2017年8月20日,先生病逝於北京。值此先生逝世周年之際,謹作此文以資紀念。
一
以「和」思想
通觀生命觀、疾病觀和治療觀
周平安教授曾得到秦伯未、董建華、顏正華、宋孝志、印會河、方鳴謙、焦樹德等大師的悉心傳授,在長期實踐基礎上,周平安教授認為中醫學即「中和之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道、法、術」的各個層面同樣體現出「和」思想。「和」是對正常的天人關係與人體正常狀態的總概括。「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闡釋了人體生命活動中存在的對立、統一規律。無論是形體結構還是生命活動,人體生命整個過程就是陰陽對立雙方在矛盾運動中此消彼長、此盛彼衰,不斷維持動態和諧的過程。「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是對正常生理活動的概括。
「法於陰陽,和於術數」
「和法」的本質是通過健運人體樞機、調和病機構係,針對錶裡上下失和、陰陽氣血營衛失和、臟腑氣機失和、寒熱互結或寒熱格拒等病機矛盾的一類治法。樞機是氣之升降出入有序運行的關鍵。表裡出入、上下升降、氣血調達、水火既濟、臟腑安和,皆本於「樞機」。樞機一旦失利,則破壞陰陽氣血、表裡上下的和諧關係,往往表現為:少陽表裡失和、太陽營衛不和、肝膽脾胃臟腑氣機失和、心腎水火升降失和、氣血失和、寒熱不調等。無論治療還是預防、保健、康復、養生,無論採取藥物內服還是針灸、導引、推拿、外治等不同手段,其基本的原則就在於恢復或促進人體「和」的狀態。不同於汗、吐、下、清、消之法專主攻邪,亦不同於溫、補之法的專主扶正,「和法」包括「和解法」與「調和法」,和解法主要有和解少陽法、開達膜原法、和解營衛法;調和法包括調和臟腑法、調和氣血法、平調寒熱法。和法適用於少陽病樞機不利、太陽病營衛不和、肝膽脾胃氣機失調、心腎水火升降失常、氣血失和、寒熱互結於中焦或寒熱格拒於上下等多種病變。
「和法」立足調和人體處於一種陰陽、表裡、氣血、臟腑之間關係相對穩定的狀態。周平安先生認為健運樞機,調和升降出入,是「和法」的理論內核和基本原理。「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是「和法」的內在要求。
北方流感「表寒裡熱」
1998年北京地區流感大爆發,根據北京地區的氣候和人群生活習慣特點,先生創造性地提出北方流感「表寒裡熱」的基本病機,力倡「表裡和解」的治療方法,創製「感冒雙解合劑」、「預防感冒合劑」,以麻杏石甘湯合柴葛解肌湯、銀翹散合用,療效卓著、享譽京城,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將1998流感中醫的救治譽為「中醫防治急性傳染性疾病的範例」。2009年甲型H1N1全球大流行,以周平安教授為主創製的「金花清感」也脫胎於此。針對甲型H1N1流感重症早期即有咯血,很快出現呼吸衰竭的臨床特點,先生根據《溫病條辨》上焦篇第十一條「太陰溫病,血從上溢者」、「若吐粉紅色血水,死不治,血從上溢,脈七八至以上,面反黑者,死不治,可用清絡育陰法」,提出流感或禽流感重症,應氣血並治,早期扭轉截斷,從而完善了流感的中醫論治體系。
中醫藥分期論治SARS
2003年4月,SARS肆虐京城,他深入東直門醫院、佑安醫院、地壇醫院等臨床一線診治重症病例,並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委託起草了全國第一個中醫藥防治SARS草案。5月8日,他在吳儀副總理主持召開的防治SARS座談會上,主動請纓:「中醫治療瘟疫病有兩千年的歷史,有其獨特的理論和治療方葯,在SARS的防治戰役中,中醫應大有作為」。繼而,他創造性地提出中醫藥分期論治SARS的救治方案,不僅可以改善急性期患者發熱、喘憋等癥狀,減少激素用量,而且通過長期治療,可以減少患者肺纖維化、肺功能損害等遠期併發症,在長期的熱病臨床實踐中,周平安注重外感熱病的內傷病理基礎及由內傷引起的病機、證治特點和轉歸的差異,強調「三因製宜」;內傷發熱則在明辨虛實、緩急基礎上,注意外感邪氣誘發加重的情況,扶正達邪,以「清」、「透」、「泄」三法給邪以出路,善以益氣解毒清熱透邪法治療結締組織疾病、腫瘤發熱以及現代醫學未明熱。
「三期二十一候」外感熱病理論體系
周平安教授曾得到秦伯未、董建華、宋孝志、印會河、方鳴謙等大師的悉心傳授,在董建華院士的指導和啟發下,周平安教授力倡寒溫統一,以「和法」為核心,形成了以表裡辨證為綱領獨具特色的「三期二十一候」外感熱病理論體系,在呼吸熱病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二
辨病與辨證有機結合
賦予西醫病理生理以中醫病證內涵
周平安教授對中西醫結合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 強調正確評價辨病與辨證在認識疾病本質方面的不同作用和二者的互補,倡導借鑒病理生理學等現代醫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更深刻地認識病人各種臨床表現的發生機制,將辨病與辨證有機結合,賦予西醫病理生理以中醫病證內涵,堅信辨病與辨證的有機結合將會促進中醫學術的發展與進步。
1、借鑒西醫病名系統和病機理論,
深化中醫病證認識
「法於陰陽,和於術數」
中醫藥在其發生髮展的過程中孕育了豐富的有關「病」的理性認識,從歷代中醫著作中可以看到龐雜的病名系統以及很多因病而設的方法和方葯,體現出古代醫家以「病」為綱研究疾病實質,進而把握共性、探索規律的努力和成就。其中漢唐醫學治療雜病,大多是在針對專病設立專方、專葯的前提下,進一步分析陰陽、表裡、寒熱、虛實特性,進行相應的藥物加減。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共記載疾病52類,100餘種;《黃帝內經》中論述的病名有300多個,以病名為篇名的有「瘧論」、「痹論」、「痿論」、「熱論」等;《神農本草經》中所載的常山截瘧、海藻治癭、黃連治痢等,都是針對「病」治療;張仲景《傷寒論》則將外感疾病分為太陽病、陽明病等6大類,《金匱要略》以病名篇,成為辨病論治的典範;《千金方》、《外台秘要》集隋唐經驗方之大成,專方專葯見有「治癭方」、「治消渴方」、「瘧疾方」等。辨病系統在明清又得以發揚,對於不同溫病的治療,首先應區分暑溫、濕溫、溫毒、秋燥等不同的病種,辨病論治。古人眾多關於「病」的科學認識和歷代醫籍中大量針對專病的專方專葯,值得後人認真總結和發掘。中醫學著作中關於瘧疾的記載,即使現在看來仍然是基本正確的。但由於歷史條件和中醫學對疾病認識方法的限制,中醫藥有關「病」的認識水準未能普遍達到與瘧疾認識同樣的高度。作為疾病的歸納方法,中醫學所稱的「病」,如「黃疸」、「咳嗽」、「傷寒」、「中風」等,常常是以典型的體征、癥狀或病因命名的,除少數明顯由特定病因所致者外,大多不夠具體、準確,內涵模糊,外延寬泛,不能全面反映病因、病位、病變、病程等臨床特徵,不能深刻揭示特異性疾病的本質屬性。因此,中醫的辨病系統需要甄別和完善。
西醫病名系統
西醫的病名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變器官的病理變化、整體機能的反應狀態、病程演變的階段和預後等多方面的本質問題,人們可以通過病名基本了解病情輕重、病程演變、預後轉歸,從而可以採取更加有效的方法,積極主動地治療、預防甚至消滅某種疾病。
二者互相融合
周平安先生堅決反對拋棄中醫學傳統的疾病理論體系,單純或主要採用西醫辨病的中醫臨床模式,但也不贊成隻知中醫辨證、排除西醫知識的「純中醫」臨床模式。他認為現代中醫應該在嫻熟運用中醫傳統理論和方法的同時,借鑒必要的西醫西藥知識,中醫藥治療疾病,不只是改善疾病癥狀,讓患者感到舒適,更重要的是針對疾病的病理改變,使疾病從根本上得到好轉。因此現代中醫不僅應學習現代醫學疾病的診斷體系,更應努力學習病理、生理等方面的知識,努力探索疾病癥狀、體征的發生機制,這樣才會有助於充分挖掘中醫學對於疾病認識的科學內涵。西醫疾病理論與中醫疾病理論相互融合、相互借鑒,才能有助於汲取中醫幾千年來寶貴的臨床經驗,從而在更深層次上把握疾病的本質,真正達到治病求本的目的。
以瀰漫性肺間質病為例
瀰漫性肺間質病是呼吸系統的疑難疾病,周平安教授認為本病應從肺痹論治。肺痹病名肇始於《內經》,《內經》以降,代有學者論及本病,立本於宋元,敷揚於明清。《素問·痹論》論述肺痹為臟腑痹之一,其主要表現為皮膚不仁,腫痛,隱疹,煩悶喘而嘔,喘息,發喘上氣,其脈浮、微大,各代醫家將肺痹另立一門,與哮、喘、咳嗽、肺痿毗鄰、並列,不僅豐富了肺痹內容,而且在方葯上補《內經》之不逮,但其疾病表現基本未超出《黃帝內經》論述的範疇。周平安總結了歷代關於肺痹的論述,借鑒現代醫學關於咳喘類疾病的認識,認為肺痹與哮證、肺脹、喘證不同,是一獨立的疾病,大致與肺間質疾病相當。從中醫角度分析肺間質纖維化,從西醫角度看肺痹,可以發現中西醫在病因、癥狀、體征、預後等的認識具有顯著的一致性。從病因學角度,繼發於硬皮病之肺間質纖維化,類似於皮痹久舍於肺之肺痹,而特發性肺間質纖維化則與本臟自痹相當。他從歷代中醫古籍中搜集了很多肺痹醫案和20首以肺痹為名的古方,並對近70味藥物進行了歸納分析,認為就肺痹而言,肺氣虧虛,為其病之根本,氣虛氣滯(虛氣留滯)、氣虛血瘀、氣滯血瘀、脈絡閉塞、痰濁濕熱阻滯等病機的相繼出現,導致了肺痹的持續發展。據此,先生創製益氣活血通絡開痹系列方葯,在特發性肺間質纖維化和硬皮病合併肺間質疾病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2、辨病與辨證有機結合,
提高臨床診治水準
辨病論治
辨病可以把握疾病的本質、特點、轉歸、預後,以解決疾病的主要矛盾。疾病狀態下,病的本質從根本上決定著證的變動和表現形式,辨證的目的是認識和解決疾病某一階段的主要矛盾,而解決疾病某一階段主要矛盾,必須服從於解決疾病整體過程的主要矛盾,因此辨病是綱,辨證是目,臨診時不能停留於辨識證候層面。周平安堅持先辨病、後辨證的臨床診療原則,每每取得顯著的療效。
辨證論治
西醫的病名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變器官的病理變化、整體機能的反應狀態、病程演變的階段和預後等多方面的本質問題,人們可以通過病名基本了解病情輕重、病程演變、預後轉歸,從而可以採取更加有效的方法,積極主動地治療、預防甚至消滅某種疾病。
兩者結合
辨病可以把握疾病的本質和發展變化規律,有助於提高辨證的預見性、準確性,重點在全過程;辨證可以抓住疾病現階段的具體特點和個體內環境狀態,又有助於辨病的個體化、針對性,重點在現階段。辨證與辨病相結合,在辨病的基礎上進一步辨證,既有全局觀念和整體認識,又有階段性、現實性和靈活性認識,從而可以動態把握疾病發生、發展的變化規律,準確辨別疾病性質、病位,明確所患何病、何證,據此進行有針對性的個體化治療。
以治療原因不明的慢性咳嗽為例
原因不明的慢性咳嗽(除外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肺癌等疾病),是呼吸科門診最常見的病證。俗語稱「諸病易治,咳嗽難醫」,而慢性咳嗽尤為難治。周平安認為,《黃帝內經》所言「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即言咳嗽病因繁雜,而且涉及病種頗多。他在實踐中發現,慢性頑固性咳嗽大多為咽喉源性咳嗽,表現以乾咳少痰為主,中醫歷代治療咳嗽的辨病處方中,治療乾咳的方葯也大多明確提出突出的咽喉部癥狀,如止嗽散和金沸草散。結合現代醫學慢性咳嗽的疾病譜系可知,鼻後滴綜合征、咳嗽型哮喘、變應性咳嗽、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等疾病,多以咽喉部癥狀為突出表現,緩解咽喉部不適,消除咳嗽的誘因,是治療此類疾病的關鍵環節。西醫辨病可以了解鼻後滴綜合征、咳嗽性哮喘、食管返流性咳嗽等形成的病理生理機制,而中醫辨證則認為病位有在肺、肝、脾、胃的不同,在辨病的基礎上,加強咽喉部的寒熱虛實辨證,注重調肝、和胃、健脾,可首先使咽喉部刺激感減輕,之後痰塊順利咯出,咳嗽也隨即迅速緩解。
周平安先生臨床治療慢性咳嗽時,還特別注重患者的體質因素和既往病史,如糖尿病患者感受邪氣之後易化燥傷陰,陰虛燥咳常見;高血壓病患者咳嗽則多表現為氣火;肥胖患者痰濕突出;慢性胃病患者在外感邪氣襲肺致咳嗽的同時,胃腸癥狀加重,肺胃失和較著;冠心病患者發生咳嗽之後,胸部悶脹、夜間咳重等氣滯血瘀特點也較明顯;兒童咳嗽,或肺氣偏虛,易感外邪,或飲食不當,食積化火者。針對體質因素和宿疾制定比較全面的治療方案,也是提高療效的重要環節之一。
在大量實踐的基礎上,周平安先生認為肺主氣,司呼吸,其性輕虛,肺病病機總體為氣機失調,氣血不和,故用藥宜以調理氣機為主;同時主張肺居上焦,其位最高,用藥宜輕,令藥力輕清上行易達病所,不宜重濁;肺為嬌臟,不耐寒熱,用藥宜平,不宜大寒大熱、偏過偏峻。
三
精熟本草理論,結合藥理知識
準確把握用藥指征
周平安教授是國內首屆中藥藥理學碩士,師從顏正華先生。由於中醫論治主要體現在方葯的具體運用方面,因此周平安教授多年來對本草學的鑽研精勤不輟,獨具心得,認為現代中醫必須全面繼承古代本草學知識,熟稔常用藥物的性用特長,同時還要將中藥藥理知識與傳統本草理論相結合,甚至應當著力建立中藥臨床藥理學新學科。臨證時應當以臨床藥效學及毒理學為指導,注意從同類藥物中選擇對患者個體最適宜的高效低毒藥物盡量做到用藥品種和劑量的個體化。周教授還倡導通過現代中藥藥理學的研究探尋中藥及方劑的新功效,開闢新用途,逐漸在臨床實踐中形成中醫藥治療的時代特色。
1、正確認識傳統本草學的
科學性與局限性
本草學是中醫藥學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本草藥物的作用機理,在於通過性味特性,扶正祛邪,糾正陰陽氣血的偏盛偏衰,恢復臟腑經絡的正常生理功能。古代醫藥學家以中醫學臟腑、經絡、病因、病機、治則等理論為指導,在長期實踐中逐漸總結出了以藥物性味、歸經、引經報使、升降浮沉、功用主治、七情和合、君臣佐使等組成的傳統本草學理論,從不同角度和層次,揭示了藥物於患病機體的特異聯繫和臨床應用的一般規律。自《神農本草經》重視四氣五味伊始,魏晉隋唐時期多以藥性與功用相結合,偏重於藥物的主治病證,而對功能的論述較為籠統;宋代開始以藥物法象理論(外在表象)為主解釋藥物奏效的原理,往往以形色、生態、習性乃至傳說附會作為釋葯的依據,如《聖濟經》解釋蜂房成於蜂,故以治蜂蜇;鼠婦生於濕,故以利水道等等,即帶有明顯的臆斷性和局限性。明代醫家常以儒理、佛理、道學來闡明中藥藥理,影響了中藥理論的真實性。清代仍然從藥物的形、色、氣、味等外觀特徵解釋藥物的藥性、藥效,如皮以治皮、節以治骨、藤蔓治筋骨、血肉者補血肉之類。以藥物性味及藥物法象為主闡發和解釋功用主治的方法具有明顯的缺陷,加之歷代醫家個體臨床實踐的局限性和主觀片面性,常常使得眾多醫家對於同一藥物性用主治的認識產生嚴重分歧,如丹參,《神農本草經》言其「微寒」,陶弘景言其「性熱」,《藥性論》則稱「平」;又如黃連,有瀉心說,有瀉脾說,有瀉心下虛熱說,有去上焦之火說,有去中焦之火說,有平肝、鎮肝說,有益肝膽或益膽說,可謂形形色色,使人莫衷一是。現在看來,某些傳統本草理論明顯滯後於臨床實踐已是不容諱言的事實。

周平安教授認為,古代本草學是總結、整理實踐中發現的藥物知識而逐漸形成的科學體系,其中心思想是通過藥物的四氣五味之性,糾正人體陰陽之偏,從而體現其治療功能,使患病機體恢復相對平衡。但藥物的「四氣五味」不過是藥物功能的抽象概括,與治療功能之間並不一定存在必然聯繫,單憑藥物的性味並不能真正闡釋藥物的療效,引經報使、四氣五味、升降浮沉為內容的本草學理論難以將藥物的藥效備述周全,其中牽強的比附之論,往往有礙藥物的正確使用,不宜全部盲目遵從。大量臨床實踐證明,藥物有專能,性同而用異,所以本草學應該著重研究藥物的功能主治,揭示藥物性同而效殊的內在機理,洞察和分析各種藥物獨具的特殊功效,尤其是傳統本草理論所不能概括和解釋的藥物作用。醫生臨證遣葯組方,應在深明藥物本草學特性的同時,注意區分性氣相同藥物之間的多方面差異,厚其能,薄其性,以藥性專能為選擇藥物的主要根據。同時,還須認識到現代中藥藥理研究闡明中藥功能的重要手段,中醫臨床醫生應當注意對相關研究成果的借鑒和利用。
2、熟諳傳統本草理論,
借鑒中藥藥理研究,
發掘中藥臨床新用。
傳統本草理論多建立在歷代醫家個體臨床經驗的基礎上,儘管有著合理的內核,但事實依據往往不夠充分,時代、地域、學派的不同,使得醫家們闡述中藥功能主治所用的術語不夠統一和規範,導致本草學對於藥物功能的論述不夠準確和穩定。而逐步建立起來的中藥藥理學,通過試驗研究探索藥效學規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方面和層次,深刻闡釋中藥本質和發揮功能主治的途徑。周平安教授師從顏正華先生,受其影響頗深。他認為中醫藥理論和經驗是現代中藥藥理學研究與學科發展的基礎、前提和動力,現代臨床實踐則是檢驗藥物藥效功能的唯一標準,中藥藥理研究與臨床中醫藥實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現代中藥藥理研究與本草理論相結合,可以在臨床實踐中建立起中藥臨床藥理學科,指導更科學合理的臨床用藥規範的逐步制定和實施。
用藥精當
謹守證據和指征
周平安教授強調,運用中藥必須依從證據、把握指征。所謂「證據」,就是本草學關於藥物功能主治的傳統論述與現代中藥藥理研究的綜合資料;所謂「指征」,則是針對此人、此病、此證的辨病辨證結論。與化學合成藥物不同,中藥所含天然成分的複雜性,決定了藥物作用的多樣性。舉甘草為例,歷代本草著作對甘草功能的描述達十餘種之多,如《神農本草經》言其「主五臟六腑寒熱邪氣,堅筋骨,長肌肉,倍力……解毒。」《名醫別錄》則謂:「溫中下氣……止渴,通經脈,利血氣,解百葯毒。」《日華子本草》曰:「安魂定魄補五勞七傷,通九竅,利百脈,益精,養氣,壯筋骨,解冷熱。」《湯液本草》謂:「生用大瀉熱火,炙之則溫,能補上焦、中焦、下焦元氣,性緩,善解諸急,熱藥用之緩其熱,寒藥用之緩其寒,去咽痛,除熱,緩正氣,緩陰血,潤肺。」《本草綱目》又補充「解小兒胎毒,降火,止痛。」

周教授認為,應該全面繼承歷代醫家描述的單一藥物的功效主治,與中藥藥理學相結合,認識藥物各種成分的功效與主治病證之間的必然聯繫。例如:甘草含有甘草次酸、甘草苷、甘草素、異甘草苷和異甘草素,這些成分具有抗潰瘍作用,而甘草在小建中湯治療腹痛;甘草的抗桿菌作用與葛根、桂枝、白頭翁、黃芩等相配治療下利;甘草含多量黏液性物質,能阻礙水液的吸收而有緩下作用,與大黃、芒硝配伍可治療便秘;甘草促進咽喉及支氣管黏膜的分泌而有化痰作用,所含甘草次酸具有中樞性鎮咳作用、對抗5-羥色胺等物質引起的支氣管痙攣作用,配合桔梗、麻黃、石膏治療咽痛、咳喘;甘草製劑具有去氧皮質醇樣作用,可以加重水鈉瀦留,甘草甜素有類似於腎上腺素的強心作用,從而增加血容量和升高血壓,改善血液循環,因而甘草與附子、桂枝配合,對氣血虧損的厥逆、心悸、脈結代等症有效;甘草有鎮痛與抗驚厥作用,說明甘草善緩急,補心陽,益心血,寧心神,與酸棗仁、茯神、當歸、棗仁、龍牡、桂枝等相配,治療臟躁、失眠及神經官能症,對於神經急迫症有緩解作用;甘草有殺菌消炎,尤其對熱痛過程中的細菌毒素有較強的解毒作用,因而可與麻黃、桂枝、石膏、知母、麥冬、柴胡等配伍治療各種熱症;甘草甜素對毒物有吸收作用,水解產生的葡萄糖醛酸能與毒物相結合,且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增強肝臟的解毒能力,故可用於解藥物食物之毒。《傷寒論》所載112方中有甘草70方,《金匱要略》184方中有甘草者85方,這些方劑被用於消化、呼吸、循環、神經等系統的多種病證。現代中藥藥理研究有助於理解仲景廣泛應用甘草而取效的機理,並可指導把握甘草治療不同病證的用量。以這種方法,周平安教授結合現代中藥藥理究成果,總結了歷代醫家應用甘草治療外科、皮膚科疾病等的經驗,闡明了藥效機理,深化了對傳統本草學臨床經驗的認識,揭示了在遵從古代本草理論基礎上,辨證應用甘草於各系統疾病的規律。
辨證認識藥物的
治療作用與毒副作用
中藥成分的複雜性要求醫生清晰地了解中藥的治療作用和毒副作用。如麻黃有發汗、平喘、利尿的治療作用,而歷代本草著作大多不言其毒。周平安教授認為麻黃並非無毒,毒性大小取決於生葯中總生物鹼的含量以及臨床用量和配伍情況。麻黃引起中毒的機理主要是麻黃鹼抑製單胺氧化酶的活性,使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素能神經的化學傳導物質降解的速度減慢,從而引起交感神經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對呼吸中樞和血管運動中樞帶來顯著影響,一次口服麻黃30~45g即可中毒,一般在服後30min至2h出現癥狀,表現為煩躁不安、焦慮譫妄、失眠、心悸氣短、頭暈震顫、噁心嘔吐、血壓升高、大量汗出、鼻黏膜乾燥、心前區疼痛、排尿困難、瞳孔散大等;重度中毒者,視物不清、休克、昏迷、呼吸困難、驚厥、心律失常,最後死於呼吸衰竭和心室纖顫。不同個體對麻黃毒性的耐受性存在者明顯的差異,對麻黃過於敏感者,3g麻黃一次煎服即可出現心動過速和失眠。事物總是辯證的,治療作用和毒副作用是藥物之劍的兩個利刃,必須具體分析,合理利用。麻黃髮汗、平喘、利尿時興奮交感神經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的毒副作用,也可成為治療作用,對於病竇綜合征、嗜睡症,可以收到良好的治療效果。
探索發現藥物的
最適用量
臨床藥物的用量是否適度,直接關係到藥物的療效,中藥成分的複雜性也導致中藥劑量和效應之間的關係遠較化學藥物複雜,而同一中藥或方劑,對不同個體,其藥物反應也可不同。應注意中藥藥效與用藥時間、劑量的關係,與個體體質差異的關係。在治療中應堅持辨病、辨證相結合的原則,因病、因人、因地、因葯而異,注意根據中藥藥理研究,確定療效最佳、毒副最低的用藥劑量,制定較為合理的治療方案,同時注意劑量的個體化,方能取得較為滿意的治療效果。仍舉甘草為例:甘草的用量古今中外的記述差別較大,《傷寒雜病論》中,治療呃逆的橘皮竹茹湯,用甘草五兩(相當於70g左右);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甘草瀉心湯、炙甘草湯等,均用甘草四兩。因甘草甜素的甜味約為砂糖的50倍,在國外被廣泛而大量的用於醫療和食品,但對其毒副作用已經引起廣泛重視,日本厚生省明確中藥方劑中配備甘草的劑量為一天1~4g。周平安教授則提出我國甘草的常用量大於日本和歐美,單用、偶用量可稍大,常服、久服量要漸小;補氣宜輕用,養陰宜重用;祛痰宜輕用,解毒宜重用;調和諸葯宜輕用,緩急止痛宜重用。常用量為1~9g,最大量為60g。
周平安先生自1965年8月業醫,在臨床一線工作52個年頭。歷任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東方醫院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並先後擔任急診科主任、呼吸熱病科主任、大內科主任,一生摯愛著中醫事業,就象一位頭戴鬥笠的農夫,在中醫園地裡,安得了冷熱,經得住風雨,彎腰勞作、耕耘不已。先生出身貧寒,始終將自己定位於一位普普通通的醫生,先生總在告誡我們,要作一名真正有療效、能運用中醫藥解決實際問題的良醫!先生平素淡泊名利,生活簡樸、勤奮求實,寬仁敦厚,謙遜和善、平易近人,但在專業和學術方面卻融匯新知,衷中參西、大膽創新!尤擅於呼吸系統疾病、急性熱病以及疑難雜症的治療,在諸多領域均有開創性的貢獻!在此謹將深深的崇敬與謝意獻給周平安教授!惟願先生的學術思想傳世,不論春秋幾度,都能夠發揚光大,造福後人,這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來源 | 北京中醫藥大學岐黃研途
技術 | 朱雪瑩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