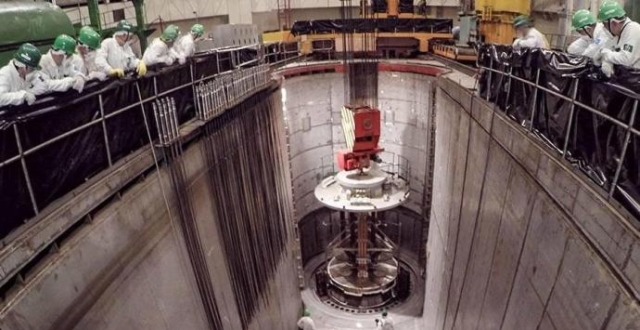納博科夫屬於“不關心全人類”的那類作家。如果不是突如其來的槍炮打碎了他平靜無事的青春歲月,他應該和他摯愛的托爾斯泰一樣,閑坐庭院中,一邊寫著俄羅斯抒情詩,一邊研究蝴蝶和棋局;或者乾脆在百無聊賴之時,動用惡毒的舌根把他知道、不知道的作家,挨個諷刺一遍。
可惜,平靜無事的青春歲月終於還是消失了。多年以後,功成名就的納博科夫回首往事,發現自己的人生早就被他的傳記作家布賴恩·博伊德輕輕鬆松地一分為二:俄羅斯時期和美國時期。這意味著他還來不及朝著事先規劃的軌跡走完一生,就被迫匆匆拿起行囊,在異國他鄉遊蕩。可是,納博科夫偏偏又是無國界的,他自稱“作家的藝術就是他真正的護照”,半個世紀獨來獨往,從不參加任何組織,更無意借助外在的標簽(比如流亡)來增加自身的份量,隻把文學當作他唯一真實的信仰。
流亡並不需要正襟危坐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樣的納博科夫的確很“佛系”。然而,比作家更“佛系”的竟然是他的小說。《納博科夫短篇小說全集》(以下簡稱《短篇集》)就是這樣一種寫作。納博科夫曾把短篇小說稱為“木桶的底”。倒不是說,這類創作不夠分量,而是他一生經歷頗豐,創作太過繁雜,以致太多熠熠發光的故事,被輕易地遺落在木桶底部,不被人關注地存在著,就像他的俄羅斯。


評論家實在不必小心翼翼、耗費精力對文本作地毯式的搜尋,因為納博科夫早就把那個最“真實”的自我袒露在字裡行間。世人皆知他曾為“理想讀者”定下不可逾越的規條。那麽作家呢?有沒有他心目中的“理想作家”?就算是讓人恨得牙癢癢的跳蚤吧,也要有自己的信條,在《嘴對嘴》一篇中,他以半戲謔半認真的口吻說出了“理想作家”的定義,“作家嘛,就得有激情,還要有同情心,敏感,公正”,“至少要讓我筆下的一個詞嵌入讀者的心”。
縱觀《短篇集》,嵌入讀者內心的詞匯成千上萬,仿佛洪流一般滾滾而來,其中最令人難忘的反倒是“流亡者”。都知道一千個讀者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納博科夫的文學也可作如是觀。比如《洛麗塔》,有人看到了殺傷力爆棚的小仙女,有人看到了猥瑣老男人亨伯特·亨伯特,納博科夫卻只看到他的俄羅斯。同樣,一千個流亡者眼裡也有一千個故鄉。有的憤懣、有的失落、有的怨懟,絕少有平靜。納博科夫終究是不同的。他本來可以名正言順地為同胞代言,以親歷者的姿態藐視同行,贏得比索爾仁尼琴更“索爾仁尼琴”的名聲。可他偏偏隻愛做自己,做超然於物外的弗拉基米爾·西林(俄羅斯時期的筆名),做沉迷於記憶的納博科夫。
上述兩種人設,都是納博科夫世界觀的生動反映。因為打從一開始,他對流亡就有了明確的態度:反對。即便反對無效,也會在心的最深處投上他否決的一票。顯然,流亡並不需要正襟危坐、嚴陣以待。它和他一生追求的“讓脊椎骨微微震顫”的極致美學觀並無差別,永遠根植於他高貴的母語和他無法返回的過去。同樣,納博科夫也不待見“現實主義”的標簽。哪怕集子裡滿滿當當地浸潤著現實的湯汁,哪怕他的人物總是急煎煎地從句子與句子之間狹小的縫隙裡冒出頭來,嘟囔著告訴讀者“我就是現實主義”。在他這裡,現實主義只能是馬戲團開場前無趣、乏味的暖場,而真正偉大的小說永遠是“了不起的神話”。

那麽,來看看《短篇集》到底寫了什麽樣的神話。《振翅一擊》裡,在相戀7年的妻子自殺後,年輕的科恩去了瑞士,被偶遇的英國女子伊莎貝爾誤認為同鄉。他以一句“你錯了,我是沒有祖國的”,輕輕打發了她溫柔的搭訕。《詞語》中,苦惱的青年祈求天使用“鴿子一般柔軟的翅膀”帶他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告訴他“如何才能救我故國”。《柏林向導》裡有一個盡職盡責的向導,他細致描繪這個城市的每一個細節:響著鈴聲駛過的有軌電車、人行道上巨大的黑色管道、海洋館裡一聲不吭的烏龜、酒吧裡悶悶不樂的客人……一切看上去自由、寧靜,充滿濃鬱的人文氣質。但終究還是異國,是太多個“沒意思的外國城市”裡的一個:換湯不換藥,難解相思苦。

想來,這就是“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必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家鄉離他越來越遠,最初的記憶日漸稀薄,剩下的只是記憶的影子,抑或“記憶中的記憶”。至於最後的歸宿,無外乎兩種:或是像普希金所說“死在決鬥中,死在流浪中,死在波濤中,死在附近的山谷裡”;或是像納博科夫自己,40年來漂泊不定,直到人生的最後17年才在日內瓦湖畔的旅館裡找到了歸宿,重返托爾斯泰、契訶夫、果戈理造訪過的地方。也算是葉落歸根了,只是有一樣,不是在他出生、長大的聖彼得堡,更不會在自家的床上。
寫給俄羅斯卻無人接收的情書
用“總體思想”來概括納博科夫小說注定是危險的,就像沒有誰膽敢為他扣上“主義”的帽子。這個不關心全人類的作家總是站在世界的邊緣,固執地寫著自我的鄉愁。無論世界如何動蕩,他只為自己而活,為他的蝴蝶,還有他的藝術。《喬爾布歸來》裡,新婚妻子死於蜜月,丈夫喬爾布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悲傷。他知道他的世界已經離他而去,就連“抱著屍體趕去最近的村子也似乎是件多此一舉的陌生事情”。那麽,鄉愁呢?或許也是“多此一舉的事”。隨後,納博科夫筆鋒一轉,告訴我們他的解決之道,“他心想,要是能把他倆一起看過的所有小東西都收集起來——這樣他就能把逝去不久的事情重塑出來——那麽她的形象就會永生不滅,她就等於永遠活著。”
循著這樣的思路,《短篇集》很快成了納博科夫的鄉愁博物館。他用盡全力去挽留往昔生活的碎片,哪怕到手的只是一點透明的影子。《O小姐》是他從前的家庭教師;《菲雅爾塔的春天》是戀人們悲喜交集的重逢;《循環》寫盡了少男對少女的隱秘情愫;《倒霉的一天》中,孩子們在舊時的莊園裡玩著捉迷藏;《聖誕節》藏著他心心念念的蝴蝶……就像是一封厚厚的信劄,他在收信人一欄明明白白地寫上了“俄羅斯”。可這注定只是一封無人接收的函件。於是他只能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用他高貴的母語反覆唱誦俄羅斯那“風月無邊的美麗”和“青春永駐的魔力”,直到調子本身也成了如假包換的安魂曲。

緊接著是他的美國時期。可惜,現實從不提供遺忘前事的“孟婆湯”。中年人納博科夫經歷千辛萬苦、滿帶儀式感地來到大洋彼岸的自由之地,卻總是找不到他想要的儀式。《似水流年》裡,半大的孩子用童稚的眼光看著車窗外的曼哈頓,漸漸生出困惑。這就是傳說中的摩天大樓?難道不是誇大其詞?“它與天空發生聯繫,特別是在溫室般晴暖的一天隱隱將盡時,遠沒有摩擦的感覺,而是難以形容的微妙、寧靜”。問題是,這片遠離歐洲的大陸真的那麽單純美好、人畜無害嗎?倒也未必。《談話片段,一九四五年》一語道破了真相。在波士頓平靜無事的“高雅生活”裡,新一代的法西斯慢慢復活。他們操著發音不純的英語,為戰敗的德國喊冤叫屈,將希特勒比作“盜火的普羅米修斯”。
於是,他轉身遁入夢境,去尋求那一劑鎮痛強心的百憂解,來安撫他那顆在漫長流放中逐漸老去的少年心。夢境真是無所不能。有時候甜美無比。仿佛一腳踏入了時空穿梭機,重新回到俄羅斯抒情詩的柔美懷抱,為拿不準少女的微妙心緒苦惱不已。有時候噩夢連連。街道上遊蕩著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人不人、鬼不鬼地站在十月冷漠寂靜的雪夜”,惶惶然不知身在何處。當然,還有審判,它的公正遠勝於世間一切,足以掃清所有暴政的余孽。在《被摧毀的暴君》裡,納博科夫輕易地終結了獨裁者,大筆一揮將他流放到遙遠的海島,“島上隻長著一棵棕櫚樹,像一個黑色的星號,指引他進入地獄的無底深淵,在那裡受盡孤獨、恥辱和絕望的折磨”。
我們隻喜歡金發小女孩
如此一來,納博科夫終於可以擺脫前事的羈絆,心無掛礙地登臨“無國界”的頂峰。他說自己是“長生不老的國際怪物”,因為沒有人能夠清楚地知道他究竟是中年美國作家,還是老年俄國作家。不過,要談論這個怪蜀黍,又怎麽繞得開人見人愛的《洛麗塔》?對小蘿莉的迷戀,就像是某種代代相襲的遺傳基因,維系著他一生的寫作。在寫於30年代初的《風流成性》裡,年輕男人康斯坦丁在勾搭已婚婦人未遂後,豪言:“這個老女人!記住,我們隻喜歡金發小女孩”。
對的,就是金發小女孩。倘若把時針撥得再快一點,將坐標對得更準一些,則會有更多路遇小仙女的機緣。《一則童話》裡,在與魔鬼達成交易之後,主人公埃爾溫急著將遇見的女子統統攬入懷中,充作他身後成群的美豔妻妾,其中不乏年紀小、腰肢軟的寧芙。這是故事,還是預言?30年後,《洛麗塔》的成功,讓世界認識了納博科夫。可早在1926年,迷戀小仙女的埃爾溫就已經呱呱墜地。毫無疑問,他就是亨伯特。彼時,他住在緊鄰俄羅斯的德國小鎮。納博科夫從倉皇的流亡大軍中一眼認出了他,“有點衰老但分明是他,正陪著他那位早熟的性感少女在我寫於近半個世紀前的故事中散步”。

如此,兩個故事在相隔半世紀後再度重逢,它們的創造者是同一個納博科夫。丹尼斯·洛契沒有說錯,納博科夫全部的藝術情感皆源於人生的頭20年,那是俄羅斯多彩的童年時期,也是輾轉歐陸的青年時代。普通讀者讀《洛麗塔》,應該會被他韻味十足的開頭所驚豔,繼而心生好奇,急著一讀為快。然而,只需稍稍改動一下,我們就可以讀出一種全新的味道:“俄羅斯,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惡,我的靈魂。俄-羅-斯:舌尖向上,分三步,從上顎往下輕輕落在牙齒上。俄。羅。斯。”可不管如何用力呼喚,納博科夫的鄉愁永遠隻屬於自己。(文/谷立立)
本文來自騰訊新聞客戶端自媒體,不代表騰訊新聞的觀點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