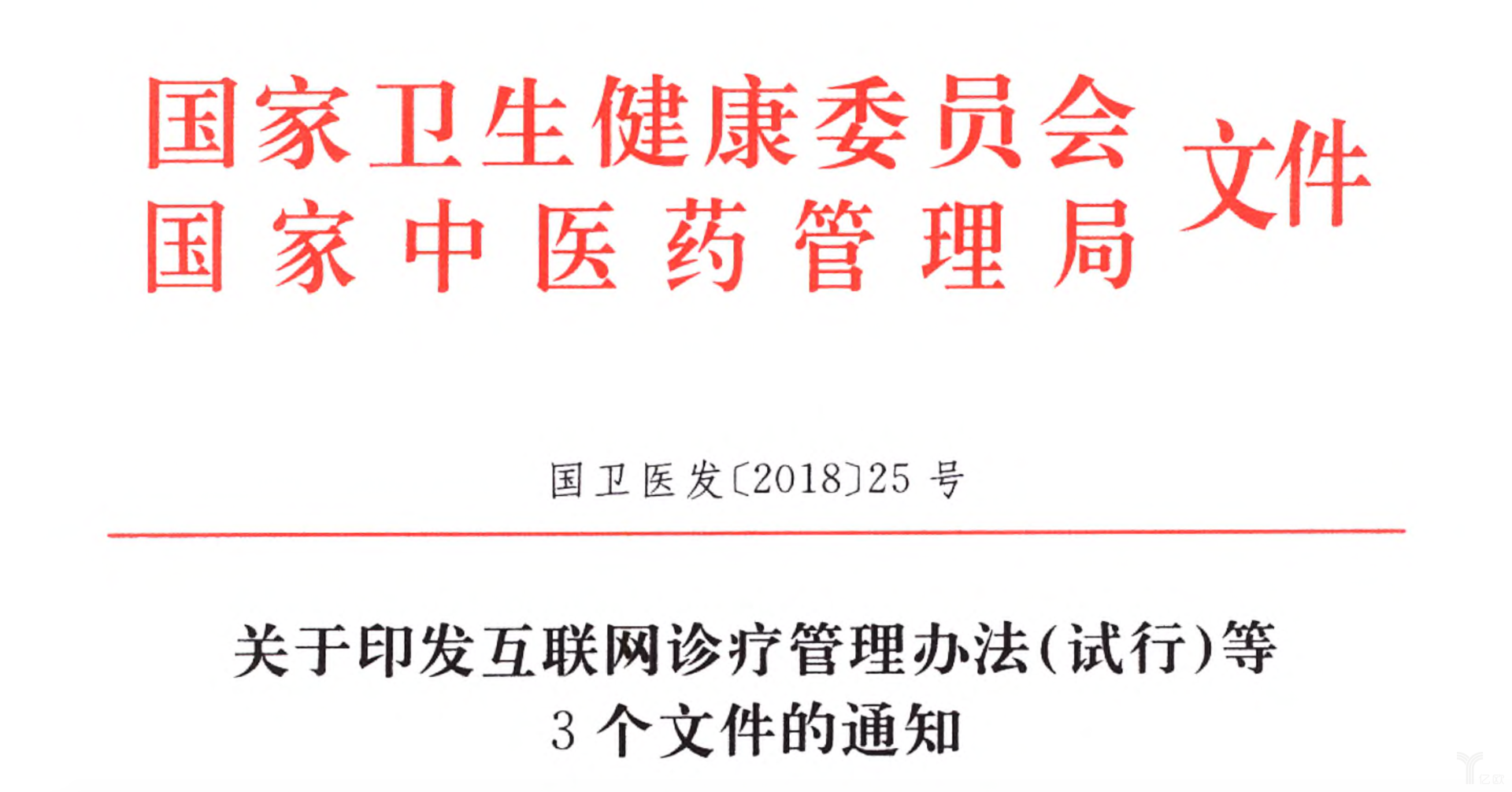來源:南方都市報
關鍵詞:
遠程醫療
調研時間:5.14-5.27
調研部門: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遠程疑難病會診中心”、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遠程會診中心”、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遠程醫療中心”、心醫國際
2017年初,肇慶市高要區人民醫院接診一位患有白內障的老年患者,當地醫生發現,他眼睛的晶體核較硬,並懷疑出現移位,情況較為複雜,常規手術難以應付。隨後,為其主治的醫生通過網絡雲端,向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發出遠程會診申請。
兩天時間,著名白內障手術專家,中山大學附屬眼科醫院副院長陳偉蓉“親自出馬”,和縣級醫院醫生通過影片“聚首一堂”。他們共同商討,為患者制定了成功的手術方案。
與此類似,在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專職遠程醫療秘書收到了來自湛江徐聞人民醫院急電,稱當地院內有位肝腫瘤病人出現緊急情況,亟須制定手術方案。隨後,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遠程醫療會診中心立即組織專家團隊召開緊急的多學科會診,包括影像、超聲、病理科、消化內科、肝膽胰外科等的專家“悉數到場”,通過影片,進行緊急會診。
以上場景,均是通過“遠程醫療”實現的。
2014年8月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印發《關於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明確支持“遠程醫療”發展。隨後“遠程醫療”平台系統在全國各大醫院“遍地開花”,廣東是其中的“先行者”。
早在2014年9月,廣東在全省範圍內開展試點,推廣遠程醫療。去年,廣東在“遠程醫療”上再次揮下“大手筆”,投入3 .22億元,以建設覆蓋全省所有醫療機構的遠程醫療體系。
根據規劃,廣東第一期將建設遠程醫療系統,聯接20家三級甲等醫院和粵東西北56家縣級醫院,開展遠程會診、遠程病理診斷、影像診斷、心電診斷、監護指導、手術指導、遠程教育等。第二期以縣級醫院為樞紐,建成延伸至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有條件的村衛生站的遠程醫療網絡,逐步實現遠程醫療在全省醫療機構的全覆蓋。
調研背景
2014年8月,原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關於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首次明確遠程醫療的定義和內容。隨後廣東提出在全省範圍內率先開展試點,推廣遠程醫療。去年,廣東在“遠程醫療”上再次揮下“大手筆”,投入3.22億元,以建設覆蓋全省所有醫療機構的遠程醫療體系。
2018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其中明確提出,醫療聯合體要積極運用互聯網技術,加快實現醫療資源上下貫通、資訊互通共享、業務高效協同,便捷開展預約診療、雙向轉診、遠程醫療等服務,推進“基層檢查、上級診斷”,推動構建有序的分級診療格局。
“患者不出縣城,也能享受省級名醫的會診”,這一理想的背後,遠程醫療發揮了多大作用?遠程醫療一直受到國家政策鼓勵和支持,而在實際操作中有哪些痛點?後續的定價、醫保政策和激勵機制如何跟上?這些問題亟待解答。
遠程醫療VS在線診療
遠程醫療是什麽?在2014年8月,原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關於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中作出解釋:遠程醫療是指一方醫療機構邀請其他醫療機構運用通訊、電腦及網絡技術,為本醫療機構診療患者提供技術支持的醫療活動。服務的項目一般包括遠程病理診斷、遠程醫學影像診斷、遠程監護、遠程會診、遠程門診和遠程病例討論———這是國家首次明確遠程醫療服務的定義和內容。
在當前的政策話語體系中,遠程醫療和在線診療已經成為互聯網醫療的兩個分支。前者指的是患者在首診醫院醫生陪同下,通過互聯網技術同上級醫院遠程會診或者遠程門診,是一種醫院之間的B2B或者B2B2C服務;而在線診療是醫院對患者個人的B2C服務。
同目前政策和監管邊界尚未清晰的在線診療不同,遠程醫療起步更早,完全依托於實體醫院運行,承擔醫療責任的法律主體明確,主管部門更為放心,也面臨更少的政策風險和掣肘。經過20多年發展,特別是“互聯網+”東風漸起,遠程醫療已經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模式,可以複製,也初具規模。
作為行業主管部門,國家衛生健康委似乎更加力挺遠程醫療。國務院辦公廳4月下發的《關於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其中提到的在線診療雖倍受外界關注,但對“遠程醫療”傾注的筆墨卻也分量不輕。
《意見》明確提出,醫療聯合體要積極運用互聯網技術,加快實現醫療資源上下貫通、資訊互通共享、業務高效協同,便捷開展預約診療、雙向轉診、遠程醫療等服務,推進“基層檢查、上級診斷”,推動構建有序的分級診療格局。
國家衛健委也表示,將推進遠程醫療服務覆蓋全國所有醫療聯合體和縣級醫院,並逐步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延伸,提升基層醫療服務能力和效率。
為患者打開生命通道
今年4月,心醫國際總裁邰從越來到海南省博鼇小鎮,參加在那裡舉辦的2018年健康界大會。在一場主題論壇上,他舉出一個數字———去年,全國總共有14400名危重病人通過心醫國際的遠程醫療網絡,為自己打開了生命通道。
心醫國際是一家以醫院院內資訊化技術為基礎,搭建並運營遠程醫療網絡的第三方平台公司。和微醫、好大夫或者春雨醫生提供的在線醫療或谘詢不同,遠程醫療是一種完全依托於醫療機構的互聯網醫療服務。第三方平台公司往往作為技術和運營服務的提供者,“隱藏”在醫院的背後。
14400名危重病人中,讓邰從越印象深刻的是,新疆自治區基層的一家婦幼保健院,一個新生兒出現嚴重的黃疸和紫癜。這雖然是新生兒常見病症,但由於當地治療條件較差,醫務人員處理應對的經驗不足,孩子情況糟糕,家屬焦急萬分。
如果是一名肺癌病人,也許可以坐飛機,甚至坐火車,去北京上海的大醫院就診治療,但這名新生兒沒有可能,他需要的是在幾個小時內,盡快聯繫上一家國家頂級兒童醫院的專家做一次遠程會診,為他確定後續治療方案。一如這名新生兒,沒有辦法長距離轉診的患者還有很多。他們往往遇到危重的情況,上天給他們打開的窗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關閉。
更多的情況是基層醫院“診斷不清”。遇到這種情況,棘手的難題就像是被扔給了患者自己。他們毫無頭緒,得了病但並不知道要去找誰,便只好開始長途跋涉的醫療漫遊,一級級地往上級醫院走,無數的精力、時間和錢財都浪費在路上。精準對接供需的遠程醫療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幫助。
“幫助患者能夠找到對的醫生、對的醫院,這在市場中是一個大問題”,邰從越說。基層醫生也擔心這樣的問題,他們還要擔心醫患關係的惡化。打開遠程醫療系統,接近專家資源,像是給他們一針“強心劑”,讓他們對自己更為放心。
對此,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副院長劉超也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建立遠程醫療系統,是實現對患者和基層醫院的“雙贏”。對患者來說,在家門口就可以享受省級醫療資源,既節省了舟車勞頓,為治病爭取了時間,又節省了醫療費用(地方醫院報銷比例高,且按二級醫院收費);對於基層醫院來說,通過遠程醫療,可以感受到有省級三甲醫院做靠山的福利,遇到疑難重症不再彷徨無助,可以及時通過遠程醫療平台進行異地面對面直接指導交流。
廣東省基層眼科能力建設工作組秘書長、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角膜病科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袁進表示,遠程醫療最大的優勢,在於醫療資源在最短時間實現最大限度的“可及性”。通過互聯網,全省甚至是全國最優秀的醫生都可以迅速匯聚一起制定最優的治療方案,“這在過去是沒法想象的”。
焦點1
“不是一個影片會議那麽簡單”
“遠程醫療”模式廣受點讚,但它的具體操作如何?記者了解到,目前各院對遠程醫療的管理不盡相同,甚至對是否採用影片實時連接,各院也有不同的選擇。
袁進介紹,在中山眼科中心,會有專職醫生對平台進行監控,接收基層醫院醫生發出的遠程會診申請,並進行初步篩查,判斷病情,尋找相對應的科室和醫生,再與合適醫生進行時間預約,等待醫生反饋進行遠程影片,再返回對接提交申請的醫院。“這是一個全人工化的過程,其實效率有待提高。”袁進說。
“遠程醫療中心通常設定在固定的場地,一次要興師動眾地讓一大幫醫生同時過去,場地受限,我覺得不現實,沒有為遠程會診提供便利性。”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院長助理、醫務處長何韻認為。
2017年9月,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牽頭,聯合16個省份的醫院,成立泛中南地區腫瘤專科聯盟。何韻說,目前該聯盟計劃在系統平台上,實現63家聯盟部門的遠程會診。為了方便醫生,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的遠程會診通常隻固定在周二下午舉行,聯盟內的醫院有需求,要提前進行預約和提交資料,然後在約定時間上線。在實行遠程會診時,醫生並不需要到固定的場地,“有個攝影頭就能實現,不受場地固定限制”。
為了提高效率,目前在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實現的很多遠程醫療會診病例,並非都以影片會診實時進行,而是由下級醫院直接將患者的影像和病歷資料通過遠程醫療系統傳輸,再由遠程秘書進行處理,尋找合適的醫生,運用碎片化時間進行遠程會診、遠程診斷,形成文字診斷報告進行回傳。
和普通人想象的不一樣,遠程會診“不是一個影片會議那麽簡單”,心醫國際的工作人員對南都記者說,遠程會診並不只是提供一套影片對話的設備,其背後既有技術,也有運營,還有學科建設。
要對接一場遠程會診,並不容易。運營人員實際工作中常會遇到各類問題。一名心醫國際的工作人員坦言,在最初摸索階段,有的時候前前後後可能要等上五六天,才能預約安排一次遠程會診。其中,遇到的問題可能包括,申請端醫院提交的檢查檢驗資料不完整,使得專家無法做二次診斷,需要補充詳盡;有時候,也會因為上級醫院專科醫生手術排期滿,導致遠程會診臨時改期。其中,少不了的是運營人員,他們在其中反覆溝通與撮合,才能讓一場遠程會診真正滿足患者的需求。他們扮演了“潤滑劑”的角色。
袁進建議,需要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融入人工智能的輔助,以減少人工的工作量。“目前技術上已經實現突破,通過網絡可以實現數據的上傳下達。借助人工智能對患者的檢查結果進行早期篩查診斷,可以降低人工成本,以提高效率。”
此外,在對接醫院時,邰從越也發現,運營中深藏中國本土特色的市場邏輯。相鄰的上下兩級醫院本來應該建立最方便的遠程通道,但實際卻並不如此。這根管道似乎在國家級醫院與市級醫院,省級醫院與縣級醫院之間才更為通暢。原因正在於,相鄰上下級醫院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競爭關係,“相鄰是冤家,相隔才是朋友”。
“如果抓不住這些本質的問題,遠程醫療的運營是做不起來的”,邰從越說。而這種運營能力也是互聯網醫療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袁進則表示,目前通過遠程醫療系統,多還是停留在對單個病種的遠程會診,但事實上,遠程醫療的功能遠不止於此,其更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暢通的“雙向轉診”。他希望,未來通過遠程醫療,可以真正把實體和網絡結合在一起,把基層醫院和中心醫院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小病在當地治療,疑難病迅速轉診,康復管理又回到基層”。
焦點2
收費、激勵和醫保政策還需跟進
相對於網絡診療,遠程醫療的定價和醫保政策走在前面。早在2013年,新疆克拉瑪依市就將遠程醫療服務納入了醫保支付。2016年9月,貴州從省級層面部署,將遠程醫療服務項目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支付範圍,開了先河。
據媒體報導,貴州的方案是,以遠程多學科會診為例,國家級公立醫院不超過每小時1200元,省級和市級分別不超過每小時320元、270元。
目前,全國已經有半數省份頒布了費用標準和報銷政策。在北京的國家衛健委直屬中日友好醫院也在相關部門的指導下,制定了11項遠程醫療項目的收費標準。其中,“非互動式遠程隨訪”的費用最低,為100元,“多學科互動式遠程會診”的費用最高,為6000元。
“現階段,北京將遠程醫療項目定義為特需醫療而制定物價政策進行收費的,是自費項目,還沒有納入基本醫療保險”,國家遠程醫療與互聯網醫學中心暨中日醫院遠程醫療中心主任盧清君說。不過,湖北、新疆、貴州等17個省份和地區已經根據實際情況將不同的遠程醫療項目納入了醫保報銷範圍,提高了患者的可及性。
在廣東,“遠程醫療”算是“先行者”。早在2014年8月,原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關於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後,廣東便提出在全省範圍內開展試點,推廣遠程醫療。去年,廣東在“遠程醫療”上再次揮下“大手筆”,投入3.22億元,以建設覆蓋全省所有醫療機構的遠程醫療體系。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遠程會診中心”,中山大學中山眼科中心的“遠程疑難病會診中心”,正是在響應這一時期遠程醫療的政策新後而建立的。根據網上公開資料顯示,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等,也先後進行遠程醫療平台建設項目的招投標,通過像心醫國際這樣的第三方技術公司,建立起自己的遠程醫療中心。
然而,建設遠程醫療平台本身就需要投入不菲的資金。《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遠程醫療中心採購項目得標結果公告》顯示得標金額為330萬元,《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開放式遠程醫療平台項目公開招標公告》顯示得標的金額為550萬元,莫論後續的運作也會持續產生人力成本。
袁進表示,目前中山眼科中心與廣東省60多家縣級人民醫院實現的遠程醫療互聯,還是屬於完全“免費”。也就是說,由下級醫院發出的遠程會診申請,中山眼科中心接診後並沒有收取任何的費用,而對於使用了遠程醫療進行診斷的病患,也不會產生任何額外的支出。而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遠程醫療項目的收費情況,何韻則說,線上遠程會診的價格,將和線下會診保持一致。
也有醫生表示,遠程醫療雖然有收費,但這個費用目前很難對會診醫生或地方醫院形成激勵。
決策參考
●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上,融入人工智能的輔助,進行對遠程醫療病例的早期篩查診斷分配,以減少協調人員工作量;
●省級醫院與縣級醫院之間連接更為通暢,遠程醫療的運營需尊重中國本土特色的市場邏輯。
●除了單純的“遠程會診”,遠程醫療所能實現更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暢通的“雙向轉診”,把基層醫院和中心醫院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真正做到小病在當地治療,疑難病迅速轉診,康復管理又回到基層。
●優化遠程醫療平台系統,適應醫生時間,可考慮不受固定場所限制,輕資產,重運行。
●各市盡快頒布或完善關於遠程醫療服務價格標準,並納入醫保報銷範疇。
●建立激勵機制,鼓勵醫生使用遠程醫療提供服務。
采寫:
南都記者 吳斌 余毅菁
陽廣霞 通訊員 林偉吟
劉文琴 邰夢雲 余廣彪
責任編輯:李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