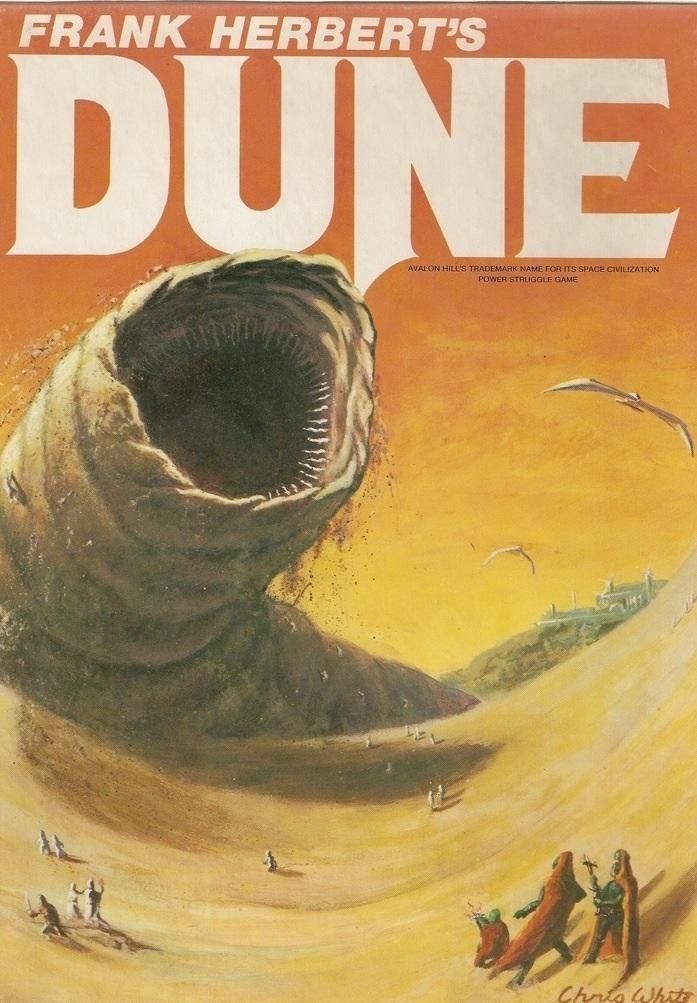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在1928年的《奇異的必要性》(“The Strange Necessity”)中像卡珊德拉那樣預言了未來者的困境:“我流離在宇宙中,無依無靠,仿佛失掉了記憶(amnesia),不清楚我是誰,我是什麽。”
在歷史的圍城中,知識分子們在言語與認知的饑饉中體嘗著流離和失憶。理查德·奧弗裡(Richard Overy)曾形容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是“卡珊德拉和耶利米的國度”,知識分子與民眾的焦慮和預言(格雷厄姆·格林稱之為“前行的恐懼”[dreading forward])夾雜在大眾消費與犧牲儀式的喧囂之中。維多利亞時代對文明和啟蒙的驕傲蕩然無存,留給韋斯特的是一堵哭牆。
沒有一個時代比這短短十年更渴求良知和言語,也沒有一個時代比這十年更缺乏決斷和確信。不同於所謂的“斜塔一代”(the Leaning Tower)的自怨自艾、緊張焦慮,韋斯特在1941年的倫敦回想起她於1936年復活節以來在巴爾乾半島看到的啟示與滅亡,犧牲與復活。這些原先隻記錄在《聖經》裡的問題,在文明崩潰的時刻,棱角分明地顯現了出來:阿蘭·巴迪歐覺得耶穌基督的復活是“超現實的景觀”——但在韋斯特的回憶裡,超現實和現實之間、被毀滅的巴爾乾半島和大英帝國的文明之間只有一道如同克羅地亞海岸線那樣碎裂的邊界。

麗貝卡·韋斯特
(Dame Rebecca West,1892–1983)
英國作家、記者、文學評論家及遊記作家。
撰文 |陳儒鵬
01
手術台上
大概沒有人會把西西裡·伊莎貝爾·費爾菲爾德(Cicily Isabel Fairfield)和巴爾乾的麗貝卡·韋斯特女爵聯繫起來:易卜生的《羅斯墨松》(Rosmersholm)讓西西裡找到了自己未來的名字,也為她鋪墊了未來那充滿了冒險與反叛的生活。在對萊昂奈爾·泰勒(Lionel Tayler)的《女性的天性》的書評裡,韋斯特不無諷刺地寫道:
“女性與男性的唯一差別在於女性不會成為天才;但這是因為她們過著一種正常而富有道德感的生活。天才則是一種非正常的自我證實的過程。男人們窺到了生活深處的不完滿、瘋癲與罪惡,甚至於靈魂上的罪愆與失敗;他們被生活的法則定罪,於是為了逃離責罰,他們通過宏大的創造成為了生活法則的一部分。”
韋斯特推翻了浪漫派以降對天才的崇拜:作為天才或是貴族的作者走下了神壇,進到出版社大樓討價還價。現代主義者們對工業革命前的秩序和幻想在韋斯特的觀念裡顯得缺少責任感:
“定義藝術標準的批評與培養對藝術品質的敏感度的文化氛圍是文明的必需品;它們就像是檢修員,告知大眾這座狹窄藝術之橋安全與否。”
在二十世紀初的文化浪潮裡,韋斯特是一根脆弱的蘆葦。她的作品並非自洽的個體,而是橫在大眾的自我麻醉與創傷的劇烈陣痛之間的一層薄膜。作為作者的韋斯特注定無法獨善其身,就像羅蘭·巴特在《如何共同生活》(“How to Live Together”)裡說“一同生活意味著同處於世的個體間一種距離(身體性的)的倫理學”;這種倫理責任需要韋斯特在自己的身體裡翩然起舞——它的遠遊、駐足、病痛和欣快——讓每一個動作,甚至於靜止或是折磨的瞬間,都反射出人的境況。
韋斯特在她的巴爾乾遊記《黑羊與灰鷹》的開篇即坦承了自己的脆弱:
“那是在倫敦的一家私人醫院。我做了一個手術,那次經歷新鮮而奇妙。一天早上,一名護士進來,給我打了一針,動作溫柔至極,還開了些玩笑。玩笑並不那麽好笑,卻適得其宜,拂去了那難熬時刻我心中的恐懼……手術留下的傷口讓我覺得,我身上似乎綁縛著重重的冰塊。”
在倫敦接受手術的韋斯特與在臥鋪車廂上聽到南斯拉夫的召喚的她無疑是天平的兩端:病痛給快樂蒙上了陰影,也讓這段遊記從開始就籠罩在暴力與無助的氛圍下。然而,韋斯特並沒有因為手術而放棄作為批評者的責任:從麻醉中醒來的她在給她注射的護士身上發現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木然——“我朝她叫道‘接通電話!我必須跟我丈夫說話。最可怕的一件事發生啦。南斯拉夫國王被刺殺啦。’‘噢,親愛的!……你認識他嗎?’”
在這一瞬間,醫生和病患的身份發生了轉移,韋斯特用藝術家的筆觸切開了這層用無關痛癢的麻木結成的痂:“她的問題讓我想起那個源自希臘語詞根的意味深長的詞‘白癡’。”她熟練地寫下了一段類似診斷書的文字:
“白癡態是女性的通病,專注於她們的私人生活,遵循命運的安排,沉迷於深淵的黑暗,她們的腦細胞有多畸形,所投射出來的黑暗就有多深。”
人們往往將發動戰爭的責任歸結於男性對暴力和犧牲儀式的崇尚:但就像伍爾夫在《空襲中對和平的沉思》對父權社會下的母性的質疑那樣——“那麽是誰滋養了希特勒,是誰養育了希特勒的奴隸呢?”——韋斯特並沒有因為性別而選擇廉價的原宥,恰恰相反,她從來不啻於用最壞的惡意來揣測這個極端年代對人性在無意識層面能造成的傷害。如果說現代主義運動將藝術從現實主義的窠臼中釋放出來,那麽在文明的黃昏,藝術又將從“每個個體陰雲密布的內心世界”裡走出來,為大腦、神經和每一寸肌膚在文化氛圍中的感受——歸屬、訓導與反抗——作見證。

《黑羊與灰鷹》
作者:(英)麗貝卡·韋斯特
譯者:向洪全 夏娟 陳丹傑
版本: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2019年4月
(點擊書封可購買)
在漢娜·阿倫特之前,韋斯特已經感知到了極權主義政體,或是在極權政體威脅下的所謂民主國家,對公民的期待——期待他們成為“巴甫洛夫的狗”,以基礎的條件反射取代思辨的力量。法西斯的陰影是手術台上的刀,而每個人在麻醉劑那樣的黃色天空下,木訥地迎接文明的終結、淪為犧牲:與她同行的德國乘客們“被擊垮、被打敗,他們選擇日常生活之輪廓的能力,他們的政治決斷能力,已不及往昔。像無頭蒼蠅的人們,他們的下一代也會變成無頭蒼蠅,必然會支持任何制度,只要能給予他們新的惟命是從的機會。”
在法西斯帶來的絕望和消弭的道德觀中,韋斯特的火車駛向了南斯拉夫:這個躺在手術台上的民族,虎視眈眈的一個又一個稱為“帝國”的醫生給它做了太多次手術,卻仍未馴服它烈馬般的反抗天性。在南斯拉夫人身上,韋斯特看到了寫作風俗史詩的可能——風俗、神話與肉體記憶共同保留了史詩的火種。“春天,復活節的時候”是最殘忍的季節,卻又增添了復活的狂歡:愛欲與哀矜兩種衝動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開出了蔚藍的奧赫裡德湖、薩拉熱窩的清真寺、科楚拉的圍城——但它們就像被奧地利洗衣工泡壞了的織錦上的花紋,在暴力面前脆弱而燦爛——韋斯特筆下的南斯拉夫就像病榻上的自己,在歷史的沉重和犧牲的痛苦中,嘗試獲得現代文明、奴性意識之外的真實——這樣的現實拒絕了“挺立的大軍”的腳步,無可救藥的南斯拉夫人讓所謂的文明與秩序顯得野蠻而無趣。
02
犧牲:神話還是日常生活
韋斯特在《黑羊與灰鷹》的尾聲撥開了這道由全南斯拉夫民族的犧牲織成的帷幔:
“他們不能忘掉戰場上降臨到他們頭上的痛苦……他們沒有被岩石的神化統治;他們沒有將失敗作為錢幣,從白癡的神靈那裡購買救贖;他們沒有把自己作為黑羊,供奉並不虔誠的牧師。”
如果歷史是一個白癡的夢囈,那麽在犧牲的儀式背後掩藏著的精神焦慮、死亡衝動和景觀狂歡就是這場噩夢的頂點——在聖喬治節前夕,她在馬其頓見到了那塊神化了的紅褐色的石頭,表面上“噴濺的血已看不出顏色,只是一團汙穢,整個就是在展示腐爛……這景象讓人想立馬轉身跑回車上把車開走,離它遠遠的。但是這個地方有著攝人心魄的威嚴。它是死亡的形體,是我們身上惡的種子,是鍛鐵爐,鍛造的劍可以將我們殺死。”
這塊石頭在書的尾聲似乎嵌入了被征服的南斯拉夫的肌體之中“從此之後,南斯拉夫地圖好像是被汙黑、惡臭的油滴滾滿了一樣”;死亡在抽象的概念與具象的形式之間如同鍾擺一般搖曳,而犧牲也被置於拉扎爾大公的神話與購買和平的贖罪券之間。犧牲的重大讓獻上祭品的人與國度顯得渺小而膽怯;祭品的苦難讓背叛它的人市儈的面目顯得尤為可笑。韋斯特對犧牲的刻畫撕碎了犧牲的理性外表和期望;慕尼黑陰謀以來、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的政治背叛不過是粉飾太平的政治遊戲。

麗貝卡·韋斯特
威爾弗雷德·歐文在《老人與青年的寓言》裡寫道:“但是這個老人不願意獻出公羊,卻殺戮了他的兒子/ 一個接著一個,殺死了歐洲一半的種子。”被改寫的亞伯拉罕的神話讓在戰爭中幸存的父輩——比如說吉卜林——的雙手上染上了鮮血,他們因為一場徒勞無益的戰爭將自己的子嗣獻給貪婪與暴力的欲念:這種罪惡讓幸存者迫切地希望為死者們染上神聖的光輝。
戰後對犧牲者的刻畫與集體紀念為死者們套上了一襲華美的袍——他們是為了文明死難的年輕人,善良、正直、虔誠而無所畏懼。犧牲的浪漫引發了更多的暴行,也將犧牲從戰場引入了日常生活甚至於資本市場——戰時的配給制度以及大後方的轟炸讓幸存的公民產生了自我犧牲的幻想與安慰——而介於死者與生者之間的傷者、失業的人、難民和彈震症患者成為了阿甘本筆下的“神聖的人”(homo sacer):他們“無法被清晰地定義為物種或是物質;比起這些,他們更類似於一種用來定義人和物種的機器或者工具。”
犧牲者的脆弱讓他們同時成為了神聖的祭品又成為了無法觸碰的怪物:他們棲息在文明與社會之外,而獻祭的過程是人自我證明的儀式。祭司們也因此為自己罩上了和平與理性的道袍,啟蒙與儀式在死亡的定奪中似乎第一次實現了“完美的和諧”。

《黑羊與灰鷹》英文書封。
這種儀式在慕尼黑陰謀達到了頂峰,犧牲既是和平的籌碼,也是背叛的見證。麗貝卡·韋斯特不禁在為南斯拉夫人立傳之時寫道:
“如果我們沒有這般虛弱、瘋癲,莫名其妙而愚蠢地向劊子手屈服,捷克人和波蘭人本不必忍受這一切的。這汙點我們窮盡一生也無法洗淨……於是,當我們走向窗前,看著倫敦燃燒時,甚至都沒有無辜感的慰藉……我們可以說燃燒的街道已經破舊,能用更好的來替代;卻不能徒勞地向一個為母親掉淚的兒子指出,她已經年老色衰。”
祭祀的儀式和被玷汙的無辜在韋斯特的筆下僅僅是投降的怯懦,世俗化的犧牲帶來的只有平庸化的背叛、崩潰的文明和信心:那塊石頭從南斯拉夫的地圖延伸到了一個又一個“不真實的城市”:“一個沒有堅實大地的世界,只有血和泥混合成軟爛一灘,猶大永不停歇地在上面反覆踐踏,引誘彼此在背叛的圈裡循環不止,劊子手說著‘趕快趕快’,還沒來得及清洗斧頭,自己的耳朵裡也聽到了同樣的聲音。”
韋斯特對理性化,甚至於市場化的犧牲的痛斥讓她站在了自殺悲劇的反面:她並不相信成為黑羊能夠帶來任何的善報,這種鬱悶而痛苦的升華除了能滿足自戀的安慰,不能為和平與復活帶來任何的籌碼。帝國的冤罪殺機與憂鬱讓麗貝卡·韋斯特在流浪之時走向了黑羊的那邊,讀者們也透過她的眼光看到了在這個充滿了密謀和殘忍的時代下,罹難和流放成為了唯一的凝聚力量:
“我看見塞爾維亞人踏上陰鬱的路途……他們去弗魯什卡·格拉朝聖,在拉扎爾大公身上見證失敗本身。”但韋斯特的同情並不是無條件的,她所希望記錄的風俗史詩並不是偽裝的復活、虛假的藝術。犧牲後的屍體並非神聖的象徵,惡臭和腐爛提醒著死亡與暴行的恐怖與惡心,在塞爾維亞的密特拉教儀式之後:“葡萄和小麥起源於這頭死去公牛的血液和骨髓,動物起源於它的精種,這並不是事實。死去公牛的血液,骨髓以及精種凝結腐爛,散發出陣陣惡臭。”
通過祭祀儀式形成的“想象共同體”缺少生者的真實,只有死亡的象徵意義:這與其說是詩意的想象不如說是殘忍的具象。未來主義者們與先鋒派希望在死亡與盛大的犧牲之中尋找到的崇高,在麗貝卡·韋斯特的回眸下變成了腐爛的過程——如果說法西斯象徵的是一種重生的文化,那麽韋斯特從“厄科的骸骨”(Echo’s bones)裡聽到了這種重生背後的浪費。與同時代人如湯因比等人對“衰退與墮落”的沉迷不同,韋斯特希望為文明開出藥方,在沉默和混亂之中找到可能的現實出路。而這劑藥方只能是渴望正義的藝術。
03
通往正義?
德裡達在《不是啟示,至少不是現在》(“No Apocalypse, Not Now”)裡提到,“文學是屬於熱核時代的——一個充滿了危機與批判的時代——無論與歷史有無關聯,這個時代的全景意味著完全的自我毀滅,沒有啟示、沒有真理、也沒有絕對的認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文明的希望消弭在虛假、背叛與人類對自我毀滅的沉迷:對虛無的恐懼取代對幸福的追求成為了維系人群的紐帶。二戰中,貝爾格萊德、布魯塞爾甚至是巴黎成為了“開放的城市”(Open city),投降讓毀滅成為了懲罰怯懦和抵抗的合法行徑,而文學和藝術也因此變得無比脆弱:這不僅僅是因為圖書館的毀滅,也應當歸結於在巨大的暴行和正義的嚴酷訴求面前,藝術的救贖光環幾近不複存在。
但韋斯特並沒有因此陷入悲觀或者是向玄想的國度逃避。與1928年的她一樣,韋斯特依舊相信藝術擁有著“奇異的必要性”,只是在毀滅的陰影下她需要尋找新的形式,為離散與消失的物件與經歷提供新的言語:哪怕韋斯特對藝術品和日常物件的執著將她的文字帶向了人類歷史的虛無,但這些承載著冤罪殺機和不安的嘗試至少能為戰時的英美讀者帶來一點希望,那就是他們的抵抗,甚至於一顰一蹙,都能在文字找到棲居的所在。
藝術已經從一種“奇異的必要”轉為“不可能的必要”,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史傳作者無疑持守著大廈將傾之際的正義。韋斯特記下了她在通往黑山路上見到的一個老婦人:“她把毛線團放到額頭來回蹭動,眼睛裡透出思考的痛苦……我看見過藝術淪為裝飾……可是她的欲望不在於寧靜,不在於金錢,而僅僅只在於知曉,到底自己的生命意味著什麽。”儘管知識和啟示並沒有因為毀滅而呈現出來,文字也只能訴諸隱喻、否定和一些客觀關聯的物件來尋求表達苦難中深邃的真實,但是“假如意識能夠拉開星辰後的黑幕,可能會被超越星光的輝煌照得眼花繚亂。那也許是另一個戰場,為未曾知曉的衝突而設。這位婦女指向的是這一片輝煌。”
“再見,母親!”與韋斯特同行的德拉古廷這樣喊道。

麗貝卡·韋斯特
這種母性的生命意志在這團毛線球與深邃的眼光裡流淌出來,而這個老婦人,就像伍爾夫在《達洛維夫人》裡描寫的那個唱著萬靈節的靈歌的老嫗那樣,在人類的至暗時刻,卻指向了簾幕後的星辰和無盡的甦生。生命的感染力超越了勝利的需求,成為了文字需要傳遞的唯一標度;韋斯特回憶起馬其頓人在混亂之中依舊自然地編織著織錦、記錄自己生活的故事,她不無浪漫地慨歎道:
“因為藝術給我們以希望……什麽是藝術?它不是裝飾。它是經歷的重生……事件不能被複製,它必須被記憶,被再次經歷,從意識的某些部分再次通過,這些部分積極地參與生活。”
歷史、記憶、希望和正義在韋斯特眼裡是讓藝術再度高貴起來的唯一方法,它們讓人在奧斯維辛的冤罪殺機之後重新學會理解生活。藝術與律法擁有著一樣的局限,它們只能徒勞地向經歷與正義的彼岸狂奔。
於是戰後對背叛者的處決(參見麗貝卡·韋斯特《背叛的新意義》 [The New Meaning of Treason])甚至是紐倫堡審判在韋斯特的眼裡都顯得如同一場戰勝者與戰爭犯共同演繹的鬧劇:“這是一個無法稱為‘經歷’的‘事件’罷了”(“An event that did not become an experience”)。在同一個法庭,韋斯特與漢娜·阿倫特一道感到在絕對的無辜與罪惡之間,所有的舉證、控訴和判決都缺失了最重要的維度——在這場帝國之間共同的靜謐的同謀之中,正義已經超出了法律與國家的框架,它沉沉地落在文人與歷史學人的肩膀之上:他們是廢墟的凝視者,是在那個老婦人之後望向星辰時刻的雙眼。
但正義依舊在星辰的背後,籠罩在黑暗之中,韋斯特開啟的旅途遠遠未到終點。巴爾乾半島在戰後依舊戰火不斷,但至少在災禍之中,人們學會了將事件轉述為經歷、在死亡與犧牲之中看到真實與生命的力量。當代波斯尼亞詩人法魯克·西西奇(Faruk Šehić)筆下的薩拉熱窩,似乎和麗貝卡·韋斯特在八十多年前見到的別無二致:“我在被圍困的薩拉熱窩住過好幾個月,這是我的榮耀……從城外看去,一切都被毀棄了,空空如也,荒草叢生,但城內還是歌舞喧囂,咖啡館裡富有生趣和歡樂……這種經歷也許和空襲時的倫敦居民很相近吧——那忤逆死亡的精神,這是我的薩拉熱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