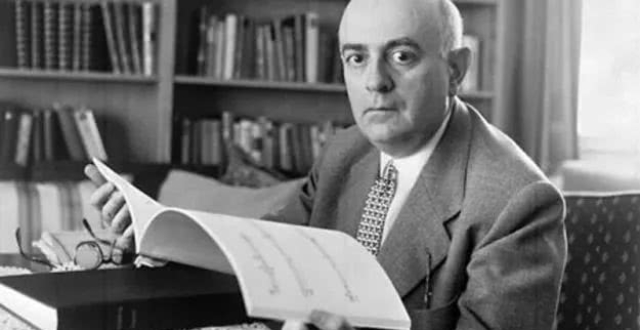去歲迄今,陳東東連續三冊詩文出版:詩論《我們時代的詩人》、長詩《流水》和這冊短詩集《海神的一夜》,加上手裡他自編的詩作編年稿本,含《詩篇一》(1981-1989)、《夏至書》(1987-1988)、《解禁書》(1990-1999)、《詩篇二》(1990-1999)、《詩篇三》(2000-2015),應該說是大備了。

《海神的一夜》是他1997年所出詩集用過的名,由箱篋翻檢出來,嚇我一跳,舊版詩集竟是我作的序,題謂《擴散的經驗》,20余年自己反給忘了,底稿湮滅無影,重讀下來,以為不少觀點應該說仍然有效,畢竟社會的進化,曲折是非繁複和語言一樣,並非直線,更何況,西人所言現代文學特徵,經福樓拜從1850年迄今,再東漸影響我們,仍見其端倪、余波,即波德萊爾描述的“過渡的、短暫易逝的、偶然的”。余完整記得東東的第一首詩即《偶然說起》,與《海神的一夜》定下了他後來的基調:逼近神話原型的,用事及物的,當然,也是現代主義免不了“感傷的”。除了波德萊爾製下的各種定義,若再加上齊美爾、克拉考爾、本雅明等人的描述,碎片化和現代性的整體關係,也被提攜至更深刻的意識,非具體辨析不可。

事隔這麽多年,東東重複使用“海神的一夜”,以詩題統書名,想他很看重這首詩,細想也頗有道理,儘管修辭有“含混”、“綜攝”和“歧義”各種手法,但這“海神”源自希臘波塞冬(Poseidon)是很明顯的,“一隻三叉戟不慎遺失”便已交底。吾民的海龍王不玩這器械,直接吐水火即是。較希臘、華夏神話起源,希臘不似希伯來人或吾民,好男女陰陽混淆之說,而更願接受人由樹木石頭、河流海洋本身孳乳的觀念,所以諸神眉目清秀,辨析語境,言河必言海,荷馬史詩敘之river ocean,伊狄帕斯濡染弗洛伊德,俄爾甫斯象徵失敗之拯救,左右裡爾克,都不含混,不似吾民,迄今甲骨文“江”“河”未明,以為識“河”,悲乎?泰西政治之三權分立,怕與天神地祗孳乳的獨眼三巨人(分別代表三種恐怖)、海洋百首怪物三者、復仇、農事各三女神都有淵源,此種天、地、海洋孳乳的創世氣質,自與漢語境的內陸氣質迥異,吾民今日想回頭再玩史詩時代之海洋玩具或氣質,怕已晚矣,現實強烈的反彈便是旁注,幾乎可用“驚恐萬狀”形容不為過。
政治歸政治,這裡,我倒另外想的是詩學問題,我之所以說此作定下了他今後的某種基調,是因為,弗萊所謂“想象的語境”和“意圖性語境”,在這首詩的生成的過程中忒具象徵意義,描述的希臘海神與亞裔人種合一,生出失落感來,並暗責“生活無度”,敘述忒逼真,卻囿於想象,畢竟是詩,而“遺失”和“洩露”,雖近史蒂芬·平克稱作的“敘實動詞”(factive verb),即“說話者相信它所敘述的事實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但,在詩的上下文中,的確很明顯地表達了作者的意圖,單一也好,含混也罷,作者顯然偏向後者。當我們跳出詩外,搗騰腦子,也的確發現與歷史敘述和今日的現實吻合。我說的“歷史敘述”,指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特別強調的複數“諸般文明”(不知讀家窺破沒,東東巧妙運用重疊敘述的也是複數),而且,恰好把希臘和中國兩種文明形態相提並論:最為古老,卻是覆滅型的。遺憾的是,湯因比在伊斯坦布爾構思這本書時,尚未意識到,文明滅亡之緩死,也是一種形態,此為題外話。我感興趣的是,我並非說東東非要讀了《歷史研究》才寫了這首詩,但,對於平行的批評閱讀,辨識有意識或無意識具同等價值,這點很重要,就像張棗先生未必讀契訶夫的《櫻桃園》,才孳乳了“櫻桃邏輯”,我說了,詩的瞬息神,超過任何思維張牙舞爪的神祇,否者,波德萊爾便不必敘“感應”了。

正因為這感應,作為海神統禦的反環境,內陸便顯示其價值:內陸氣質在地大,想吾民今日口吻恍若財大即知,梁啟超所謂“天然大一統之國”,面積十五倍於日本,合歐陸瑞典、挪威、丹麥、匈牙利、德意志、瑞士、意大利、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諸國幅員之大。梁任公言“中國遜於泰西優於泰西均在此”頗為深切,不客氣地說,即最大的富庶最大的貧賤,故近世求變,又遭遇二分法衝突,無大洋之緩解,一切外來,要麽妖魔,要麽神聖,反常化下來,骨子不求變,襲舊法,地不愛寶故又消耗殆盡,集體記憶,遂墮愚蠢的傲慢,此社會演繹豈是神話!
我這般敘來,並非說東東一把借來的“三叉戟”便異塵餘生了這內陸民族歷史的全部,而是想通過其詩作(何止一首)或隱喻,把蘊育其中的價值思想——或統稱“思想的語言”,置於很特殊的一種輿地氛圍,舊時好言“風物”,其實也就是瑞恰慈以來新批評所謂的“語境”,來觀察“現代詩”的積澱層,而非一家語言形式的長短——其實,在現代批評眼裡,這些也都是修正變化的結果,或歸“風格”、“語義”層面的研究。詩學語言涉及每個詩人的實際經驗表現在許多層面上,可綜合觀察,但不能混淆。我不大同意“創造新語言”一類的說法,這有違常識,沒有誰一個人能創造共生的語言,無此前提,便不存在交流,這本無需提醒,稍具人文素養即知,但由於B.B.(Big Brother縮寫)系統一向習慣的強辭,橫蠻起來,是不管什麽邏輯不邏輯的,“新話”(Newspeak)結構中之個人有時會忘記這點,以為是個什麽新記錄,或新神話,文藝比比皆是,怵目,其實是“新瓶舊酒”,巧舌如簧而已。
所以,我更讚同弗萊的看法,“不存在個人的象徵主義”,那種個人如何“創造了新語言”,“一個人的抗戰”之類,沒有什麽意義,所以,詩人和學人一樣,“不能只為他自己思考或不著邊際地思考;他只能擴展一種思想的有機整體,合符邏輯地為他或他人已經思考的東西增加一些相關的東西。”詩既然憑借“社團語言”而加入交流,那他只能在個人的“意象結構”方面,生成某些變化,增添點新把戲,或重複某些東西,即便如此,也還得看條件如何,按人口比例,中國詩人如此之多,主要建立在認知和信息的不對稱上,還遠遠談不上交流的有效性,或內在價值。所以,弗萊認為,相似性和同一性,是批評理論中最難的問題之一,反說明,怕也是寫作選擇個人框架之最難,絕非個人憑空掉下來個什麽“標準”,虛誕便說興滅有無高低。語義學中,標準無非是同一語境中的不同框架而已,所以,也只有同一性才能使個性成為可能。

所以,東東的作品之詩意性,或風雅,清淡,避臧否,不在“駭俗”一類,其體魄心髒怕也不支撐,若用名家比附,即“柏樺式的”,而在釋皎然《詩式》所言“淡俗”:“此道如夏姖當壚,似蕩而貞;采吳楚之風,然俗而正。”百年白話文篩洗過後,忒有一番“漢才西魂”的營造——但,其間的比例是變化著的,因歷史的原委,泰西現代性的衝淡,與粵埠有別,首先偏移融入東南內陸氣質,塑造民風、語言,絕非舊時單純“吳語噥噥”能概括——古九州“右岸”(江之南謂右岸,非巴黎之“右岸”)的底蘊,梁任公敘之甚詳,揚子江流域,政治的創業未就,敗亡有余,故蘊苟安旦夕的外表,熏染人文,易生成綺麗的規模、清隱的局勢,雖氣魄文弱,卻可觀明月畫舫緩歌慢舞,故梁任公謂:“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這是影響東東風格最重要的文化語境。記得有年,東東有詩入蜀,最早讀到“軍艦鳥”和“費勁的鳥兒在物質上空”,想他的個頭和孱弱,便會意一笑,覺得新鮮很開心,西邊的人,是道不出這“軍艦鳥”的,就像江南詩家,猝讀蜀人“廢話詩”怕覺得很無聊。
原來文學好訾議“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卻少言一地有一地的取捨,雖都是文明強力轟開國門、西學東漸白話文的語境,但自1842年中英條約簽署後,上海開埠,洋涇浜教化最深,軍艦帶了槍炮和萬國旗來,也自然帶了依附的風俗、人和鳥來,希臘人滬上購房也是有的,美神、海神、古甕、薩福如何不來!這些都入過東東的詩篇。余恰好偶涉宋氏家族秘案,即知,宋氏三姊妹,青年時代見希臘船長的滬上別墅,煞是羨慕,國共決戰,蔣公奔台,美齡購下此屋遺慶齡。革命激蕩,朝雲暮雨,摧枯拉朽,奇形怪狀的人與建築,不說逛街來著,就回憶一下,人也未必吃得消。至關緊要的是物質改變了生活方式,既帶來便利,也附加了成本,更複雜的心智。對傳統,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代價。社稷開放倘若要列什麽第一,分市政、租界、外交、軍用、財務、金融、工業、交通、教育、出版各類,怕都在滬上。這些,東東的詩,隔世都有零碎的感受,所以,混合的經驗,在他作詩最最緊要。

觀堂所言甚好:“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這是針對古雅詩詞而言,現代作詩,不啻造句,更在思想語言整體的推演,究意象結構,故作詩,亦如造景,既造景,便需語言的材料,而材料,則出自經驗的選擇,而現代的經驗,較胡適那陣,複雜了不知多少倍,異塵餘生甚廣,僅靠漢語敷衍,捉襟見肘,遂若觀堂言:“至翻譯西籍時而又苦其不足”,語不足,百年來漢語都只好西用,符合全球化語言交流的通則,“海神”即是,而且,因有反環境之下的思想推演和具體的語境,庶可謂本土意義的現代詩用事之先驅。固然,漢語境沒直接的海神,《山海經》言海,後來搞清楚了是說內陸的海子,神話起源,與希臘不同,吾民一向言天體、星宿、大地、洪水,附會八部、五星、五嶽、五行之神,四瀆江祠河神,東王公西王母,鎮海有“海龍王”,後轉“媽祖”信仰……故東東遠取波塞冬,其實,就像“整肅”、“流亡”語境中的詩人,若布羅茨基、茨維塔耶娃、張棗,性命難保,生存難捱,語言和希望,便必不能廢,故好取俄狄甫斯,或赫克托。所以,讓-皮埃爾·韋爾南在《神話政治之間》裡說:“神話總是真實話語。”
東東《海神的一夜》這首,就其代表集子中所有的詩,他本也想讓我們清楚地看到這點,現在回過頭看,也的確重要,而那些隻盯著自己偉大措辭鳥不拉屎的同行,何曾在它上面停留過一秒鐘,究竟裡面海嘯有多深呢?余發此言,乃在於它帶有作者後來哪怕更為成熟的作品也必不可少的某些特徵,雖不說全部,開篇已有交代。
一個詩人,寫了幾十年,從頭至尾,要經歷頗多階段,由此詩集大致看出有三:整個80年代至90年代初,為第一階段,若以現代詩技術分,故《諷刺的性質》(1992年)可為轉捩點,反諷的自覺運用,肯定是個標準;後來,再由單純敘述轉為結構複雜的雙重敘述,短詩集2000年後的不少,或別集的《流水》(1997-1998)是為開始,或更晚些,這與文體多寡沒關係,我指的是一種多元的思維方式,包括思想推演過程。其實,《海神的一夜》就蘊了思想推演的苗頭。當然,詩人之思,和哲學邏輯性思考不同。總之,詩人風格的演變與這些推演是分不開的,思想歸思想,語言歸語言(史蒂芬·平克語),我們的詩家和批評怕還沒習慣此共識,但演繹的過程,卻依然在看得見看不見,為人所知和不為人所知之間,甚或最後,變得來更不像我們自己,這頗具反諷意味,這在他的詩,也並非沒有征兆。後面,我會稍事作結。但,首先要了解,任一詩家階段性的意圖、風韻的變化,都在經驗的變化,由經驗看,是應變現代都市精神交流綜合的經驗,而這經驗的建構,和閱讀、於日常生活的身歷其境分不開。廣義的閱讀,帶來廣義的神話,集子中《買回一本有關六朝文人的書》,裡面出現了嵇康,這可不是文禍時代超逸的神話,而是超驗性的轉世,我一直注意50年代和我同代的詩家,無論語言玩得多麽高明,包括已故的張棗先生,最後都無可奈何地為強大的宿命論所吞噬,儘管方式不同,夠傳統的了,在現實政治裡,我們也看到同樣的血統,“精英”若此,蒼生不亦悲乎!

而在東東那裡,最致命的不是宿命,而是寂寞,寂寞帶來的無聊感——用愛倫·狄波頓的話說,即“乏味地點的魅力”,人一旦進入這些地點——《海神的一夜》集合了幾乎所有這類地點——便會墮入“擺脫心智的習慣”,或可用憂傷的快樂來形容。東東集子中就有《寂寞也一樣》,也是由那看不見的海神界分,難道,他也想通過“敘實動詞”告訴我們,寂寞和進化論是一種共生現象?我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說,“寂寞”是東東主要攝入的語境,尤其在他的《解禁書》中的《喜劇》一詩中,描敘甚細。在余看來,多少帶了一點巴爾扎克的味道,都市主義的著魔,在他和波德萊爾、T. S. 艾略特、龐德一路,都可敘之“人間喜劇”,《流水》所謂“戲仿的嚴肅性”也很接近。本雅明就曾看出“波西米亞人”的喜劇性,或滑稽性,再配以建築、地點、迷宮,世俗神話的雙重建構,這些都是東東詩學敘述最擅長的,並形成特徵,其語言表現糾結本身,就含此特徵,此特徵力道,太過強烈時,甚至導致了瘀滯、無力感,寂寞感深沉的人不可能活蹦亂跳,即使在他最優美的那首傑作《奈良》中,寂寞也倏然而至。奈良,其實也不過為其深感威脅的寂寞提供了一個最適合花開花落的場所。夫子言“我乃殷人”,殷邑在蜀(毫無懸念),乃右岸之宗,東瀛多越人血統,百越庶可為證,世代感受吳越之地的東東,卻臆想那是最理想的葬身之地,這是一種怎樣循環的血統啊!
除了遊離、閱讀,參加各種景觀社會的“詩活動”,日常生活,則帶來最直接的現實觀照。神話,現實,兩相融合,在有我無我的寫景之中,就像他在《蟾蜍》中寫的,“金色的自由,而自由是不自由”——至多是“自由的幻想性”,所以,詩結尾才得出一個出其不意的近似神話的結論:“嫦娥子宮的癩蛤蟆詩人/虛空裡——不僅蹲坐著一個嚮往”,大概在他寫《偶然說起》時,我就注意到,他一直“枯坐”在那裡,遂有了我那篇早期的隨筆《走廊》,都市主義消費的主要特徵,就是用物質圍堵個體,軟性的傳統意識形態遠遠無法比擬,這個轉移,最深刻地體現在東東的“滬地詩”中,媒介的改變,帶有極大的欺騙和麻醉性,讀《海神的一夜》(包括裡面其它詩),你最能看出,東東如何采取了浪漫主義的一種手法“自然之中和”,不是排斥,而是妥協,加以接受,響應神話,就像波德萊爾用“感應”(Correspondances)接受“自然的神殿”一樣,靠了綜合的經驗。所以,人神糾纏在一塊的結果,最後,以不眠者的醒來混合而泯滅無痕,表示權力的三叉戟被話語溶解,算得到了呼應,但不是解決問題,“生活無度”可以產生無數的歧義,不管這種方式,是否早期受過埃利蒂斯的影響,都讓我很容易就聯想到波德萊爾的航海神話,他曾在一份自傳裡敘及印度洋的旅行,去過錫蘭、印度斯丹等地,連戈蒂葉也引用過,但,後來的材料證明,儘管說法誘人,但卻含了青年人真誠的虛飾,其實,那次目標為印度的著名遠航,他隻乘船走到毛裡求斯便自行中斷,而且立即打道回府,但,卻在《惡之花》中留下諸多海上冒險帶異國情調的詩篇,其中《信天翁》頗為有名,在我看來,《人與海》也不錯,人和大海在他筆下是種對偶關係,不是誰對誰更眷念,更無情,彼此吸引的是深奧、富饒,各守秘密,也“互相鬥狠爭強”,遂陷悖論。和史蒂芬·斯彭德的一種看法吻合:“現代是時期和歷史階段問題;現代主義則是藝術和技巧問題,是想象的一種奇怪的扭曲。”波德萊爾之所以被稱作“第一個現代人”,就在於他開始疏離自己所屬的都市和文化,而且,開始用傳統的語言來表現新的異化現象。

因語境和敘述經緯不同,在我看,《海神的一夜》(新版隻改動了一句)這首,雖不具那樣的強度,但就語言層面而言,“海神藍色的裸體”顯然也是自然的一種象徵,和《惡之花》中諸如《信天翁》《感應》和《人與海》諸多詩篇所表現的主題一樣——“自然是一座神殿”,而這神殿,卻是用來和都市化相抗,或協調的,也就是說,詩人身歷其境,有意無意地就意識到了,現代主義最明顯的標誌即傾向於濃縮城市經驗,手法顯然也是象徵隱喻的,《海神的一夜》表達了這種疏遠,勿論隱喻借用了西方的還是東方的,其主旨,正是哲學家指出的:“這些神話邀請我們詢問自己”。這冊詩集,許多作品的陳述,都符合這種條件。不過,與波德萊爾那首相反的是,人和海或海神不是那種哲學的“小對體”,也非什麽“主體間性”,而更像原始思維的習慣,通過一種“互滲”的方法,找到神話功能和現實用事的結合,最後,至於海神偃旗息鼓,和剛從床上掀開毛毯睡眼惺忪爬起來的作者重合,無意間還泄漏了點什麽,那麽明顯的“文化詩”(湯因比視文化為分子社會內外表現),出於性格,作者則採用了保守療法,或含混修辭,因我們也不排除淡俗“似蕩而貞”的內容,飲食男女,在漢語境,一向是通過觸覺感覺味覺的轉換而生成的,詩人運用通感,什麽都有可能。但,作者的技巧,或方法,在這裡已呈雛形。

東東所在的城市,一向是以“都市主義”著稱,就生活區域看,他雖現已逃逸出來,我認識的他同代的諸多詩人,恐怕最後,都難免為其擁擠的“銀行魔鬼”(龐德在一篇《銀行》的短文中是這樣稱呼的)邊緣化,所謂“新上海人”現在看來,幾乎就是權力遊戲中金錢和洗錢的代表,“建設”這個詞,在這本詩集,怕你是尋不到的,而且,還更加排斥“閑逛者”,上海可不是巴黎,除非你放棄詩歌日課,都市對個體就是虛榮和囚籠的代名詞和集合體。所以,在讀集子中那首沒有標明滬上——若《外灘》一類——而大致是滬上詩的《魔鬼的詩歌已經來臨》時,情欲化的都市攜了懶庸、寂寞、頹廢躍然紙上。“魔鬼的詩”不是詩,而是詩意性的本能粉墨登場,遂致我們內心的分裂,誰都不可避免這一課,因為,現代主義的場景,對於超驗的詩或憑借語言的思索來說,就是語境,是不大可能抱了自然主義的態度退出其記憶的。《海神的一夜》縈繞於此,何止一夜,最後那首《略多於悲哀》,裡面所隱藏的“蝴蝶效應”,和他後期許多詩作中的“宇航”母題,構成了兩個角度,現代詩人就是“監視者”,要在萬花筒般的滾動的碎片中,組織各種無聊的閑話,幻景,這恰好就是Spectator之本義。東東所有詩篇,幾乎貫穿了這個特徵,甚至可以說,他的幾乎所有詩篇,是“看”出來的,看讀,所以,在一首關於長篇小說的詩中,除了閃現我們熟悉的“癩蛤蟆詩人”(至多變了個身形)然後,就是一句頗有嚼頭的白話文先驅者們的文言文:“梁啟超倡言詩界革命,意思也無非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注意了,小說當然是都市主義消費的首要條件,人物用事,即小說的特徵,東東的詩,在用事上,恰好具備此特徵,我們已沒有必要再說詩的散文化的問題,那已陳腐不堪,他的詩中,神話名物,直接切用,隱喻目標或替代性敘述,在構想時就已完成了,他的敘述方法,是歷時性神話和現實事物同時攜手,一邊彼此消解一邊建構,以求無縫對接和雙重性,包括換喻,正像他寫道的:“被象徵的意願先於象徵”。這既是他個人詩歌技術表現本身所需,也是他深藏意圖語境的一種方法。南朝詩人的影響於他,何止他,怕整個精英話語系統都植入了潛意識,現實的權力話語系統也一直擺在那裡。我估計讀者讀他的詩,時而會陷入迷津,評論者說著說著便有失語之嫌,都和這特徵相關。詩人各有一套,誰能說什麽呢。

我曾說過,現代主義是一條不斷匯入的河流,有的乍到即入,有的要並行甚至繞道許久,然後才融入,T·S·艾略特和龐德就分屬不同的兩者。而且,對今日全球化的資本解構,後者更富預見,並命中要害。由此也可以看出,有時,現代詩的敘述,這一切引誘和魅惑,非惟詩歌的樣式決定,而恰恰取決於我們每個人對詩和現代意識的看法。觀陳東東迄今的寫作,我個人認為,他屬於後面的迂回者。而我比這更感高興的卻是,通讀其詩篇,你會發現,他在盡可能地排除那些強人時代日益彌漫而討厭之至的B.B.系統的“精英意識”,緊緊地梳耙著現實,唯一能保護自己的,除了我們頑強、淳厚的內心,沒有別的。
2018年10月11日於蜀

《揚子江評論》 2019年第1期目錄
名家三棱鏡·李洱
程德培| 眾聲喧嘩戲中戲——從《花腔》到《應物兄》
李宏偉| 應物兄,你是李洱嗎?
李 洱| 《應物兄》後記
大家讀大家
邱華棟| 小說的創新性:異態小說(上)
張 棗著亞思明譯| 魯迅:《野草》以及語言和生命的困境的言說(下)
文學史新視野(主持人 王彬彬)
史建國| 區域文化與現當代文學研究再思考——以齊文化與張煒、莫言等作家的研究為例
陳 林| 1980年代文學與知識分子的自我塑造
新作快評(主持人 王 堯)
鍾 鳴| 變化的經驗——讀陳東東《海神的一夜》
方 岩| 歷史的技藝與技藝的歷史——讀王安憶《考工記》
青年批評家論壇·青年寫作的現狀與前景(三)
馬 兵| 頹廢的日常生活與曹寇的意義
楊立青| 雙雪濤小說中的“東北”及其他
作家作品論
吳義勤| 作為民族精神與美學的現實主義——論陳彥長篇小說《主角》
賀仲明| 讓鄉土文學回歸鄉村——以賀享雍《鄉村志》為中心
韓春燕 薛 冰| 徐則臣小說創作論
顧奕俊| 王蘇辛中短篇小說片論
思潮與現象
周安華 盧 葦| 當代新文藝電影:思想和實驗的邊界與空間
王士強| 新世紀詩歌民刊的困境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