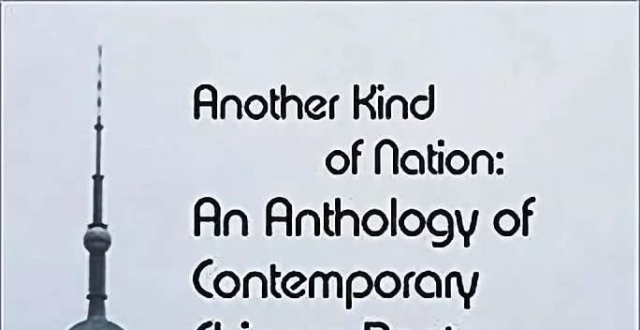撰文 新京報記者 吳鑫
實習記者 聶麗平
“詩歌是非常神奇的東西,說了一個詞語,這個詞語會在空中旅行然後擊中另外一個人的心靈,穿透那個人的感性。” 斯洛文尼亞著名詩人阿萊士·施蒂格認為,每一首詩歌本質上都是實驗,它是溝通人與人之間的實驗,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的實驗。
詩歌如何完成溝通人與人的實驗?物和物之間,人和物之間能不能進行有效真正的交流?詩歌語言具有什麽獨特魅力,翻譯又是否會減損詩歌的魅力?5月11日,斯洛文尼亞著名詩人阿萊士·施蒂格、古巴詩人維克托·羅德裡格斯·努涅斯與華東師范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金雯在上海作家書店進行對談,就以上問題進行了交流。

活動現場,從左至右依次為阿萊士、維克托、金雯。
詩歌開辟人類對於人與世界定位的新視角
2005年,阿萊士用斯洛文尼亞語創作了《事物之書》,這本詩集在2011年被翻譯為英文。金雯介紹,這些詩歌很多是以物為中心的,譬如從牙簽聯繫到平定帝國的暴力征戰,從敲碎蛋的舉動聯想到對於弱者的碾壓。這涉及對詩歌與物的關係的理解。
阿萊士講道,在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的時候,人類認為對於物的關係是佔有的關係,我們是對物控制、佔有、掌握的主動者。但寫詩還有其他的藝術創作是一門工藝,而工藝講究的是完美,任何創作出來的詩,實際上都是寫詩的技藝進展過程中很小的階段,不是最終的目的地。在追求技藝進展的最終目標時,詩人必須不斷丟棄過去的呈現,過去的思維方式要向新的經驗、新的思路不斷地敞開自己。當我們開始進行一種反常規的思維,與常規的思維進行搏擊的時候,會發現一張紙開始書寫我們,一杯水開始對我們說話。這不只是一種冒著傻氣的語言遊戲,這實際上是對於人在世界中的重新定位,把人和物的關係進行重新的想象和書寫。

《麵包與玫瑰:柏林故事》,[斯洛文尼亞] 阿萊士·施蒂格 著,梁麗真 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人的自然形象不斷地掌控,不斷地組織我們身邊的世界。但是走到一定深度的時候,會發現一個虛空。當人不斷掌控和操控外界事物的時候,發現外界事物如果只是人臆想的產物的話,最終一切皆為虛空,虛空會讓人停頓、反思。所以此時,對於物的重新考察,用詩歌的方式重新想象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重新讓這個世界中所有的事情都來改變我們作為人類的視角。雖然是寫物,但是阿萊士寫物的邏輯,也可以拓展延伸到政治和生態的領域,就是人與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一種交往的新模式。
每一首詩歌本質上都是實驗
維克托認為,所有的抒情詩總有一個所謂的言說的主體,就是詩歌裡面出現的虛構的人物形象,那就是“我”。這個人物的聲音是虛構的聲音,不是代表著詩人本身的聲音,這個虛構性往往被很多讀者所忽略。因此他認為,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詩歌得以成立,得以成為詩歌的語言,這個語言比詩歌背後可能隱藏的“我”更為重要。
2000年左右,維克托開始了詩歌實驗,他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寫作方法,即在日常用筆電記錄很多詩歌的思緒和日常的觀察。最後當筆電填滿了之後,他會把裡面的內容用電腦謄寫出來,再改造成詩歌,最後加以不斷的修整。把原來的筆記變成詩歌,這是實驗性寫作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並不是20世紀初葉芝等詩人進行的“自動寫作”實驗,將無意識的思緒記錄下來,變成詩歌。相反,這是很有方法、條理、主動意識的作詩方法,且更加忠於所謂的現實、真實。
維克托介紹,他之所以會從2000年左右開始進行詩歌實驗,是因為在這之前,他更多用比較理性的方法寫詩,對詩先有一個預期和構思,再進行寫作。但從2000年開始,他盡量讓自己的思緒鬆綁,讓注意力不受自己的控制,讓這種方式能夠異塵餘生到不同的事物當中去,用記筆記的方式,把這些發散的思維、思緒記錄下來,再回過頭去,用一種比較審慎的態度,用形式對內容進行規範約束,把這些原始的素材重新組合在一起。目前,他的詩歌實驗的主要方向是時間,更加關注詩歌如何構建空間,空間又如何成為語言的主體。
阿萊士則認為,每一首詩歌本質上都是實驗。語言本身就是實驗,溝通人與人之間的實驗,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的實驗。所以任何的詩歌,雖然有一個很長的傳統的脈絡,但是也必須不斷地更新自己。對於詩歌,阿萊士都有一種幻覺的性質,這種幻覺就是你看到了平時看不到的東西。而真正有抱負的詩人,會把自己先放在深淵裡面,把自己推向懸崖,置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再從中寫出對於語言有更新作用的詩歌。所以詩歌總是危險的,總是可以跨時間傳達一種不可能的能量和信息,我們今天可以讀400年、500年之前的詩歌,就好像是發生在當下一樣。
詩歌要抵禦所有的固定思維
金雯講道,維克托和阿萊士分別來自古巴和從前南斯拉夫獨立出來的斯洛文尼亞共和國,他們都經歷了冷戰及冷戰之後的重要歷史時刻,對於當代全球有很深刻的思考。但是在他們的詩歌裡面,看不到非常明顯的對於政治或者歷史的指涉,只有很多的隱喻和已經被記憶所改造過的對於歷史的反思。他們是如何讓自己的詩歌變得有政治影響和文化意義,同時又具有很低的身份感呢?
維克托認為,詩歌要抵禦所有的固定思維。固定思維把人為構建的規範自然化,把它們變成好像是自古就有而且合情合理的東西,而詩歌的寫作與這個過程恰好相反,會重新審視世界上所有的語言和事物。
把人們人為區分開來,再建構一個不存在的身份,這個身份又會加重很多刻板印象和人們固有的對於不同人群的理解。因此,作為出生在古巴,並且在古巴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詩人,維克托就是要打破人們對古巴的成見。他認為,身份不是自然就存在的,是從人們之間的認同過程生發的,認同的過程比身份重要得多,他覺得他和阿萊士之間的認同超過其他古巴人的認同。

《無限灰》,[古巴]維克托·羅德裡格斯·努涅斯 著,袁婧 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阿萊士認為,詩人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個共和國,本身就是一片大陸,他們是自成一格的語言天地。所有的詩歌創作者都認為,詩歌有政治性,他們可以讓語言有復甦的狀態,會對自己語言包含的那些日積月累沉澱下來的人類的慣性進行重新的審視和挑戰,所以語言在詩歌裡是處於甦醒的狀態。任何的寫作注重復甦語言的人物,那一定是有政治內涵的。所以,他們寫日常生活中的片斷,似乎沒有政治的指涉,但是同樣是很重要的創作。
他還認為,詩歌對於世界的反思,往往有時間滯後的效應。比如波斯尼亞戰爭發生了20年之後,前南斯拉夫共和國的詩人才會寫出最震撼人心的詩歌。詩人必須要在內心對歷史事件進行拒絕之後,才可以做出對歷史的有效反饋。詩歌有一種跨時間性,往往把過去和當下邊界模糊在任何一個政治危機中。往往,我們發現,一個詩人突然找到可能來自於很多年前的主題,但是與當下的某一個可能突然契合。而詩人永遠不可能知道,讀者會不會發現這種契合,所以他只能把詩歌拋擲到空中和空無一人的空間去,希望有人可以把他們撿起來。
翻譯是一切文明的基石
現場有讀者問道,母語書寫是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寫作方式,堅持母語寫作是一種反叛還是對某種規範的固守。
對此,阿萊士認為,任何語言都有一些很獨特的概念和表達方式,譬如在斯洛文尼亞語裡面,有一個詞表達靜止的水自我的旋轉,這樣的詞和概念在其他的語言裡很難找到,所以每一種語言都是文化基奠和獨特的文化構成,也是人類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堅持自己的母語,也是堅持世界文化的豐富性和多元性。同時,從實踐的層面來講,任何一個詩人都不可能在其他的語言裡面,做到在自己的母語裡面可以達到的創造性,即使他要反叛,他對這個傳統有一種類似觸覺親密關係的時候,才可以做出創新和變革。

《被解釋的美》,金雯 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維克托則認為,詩人雖然是用一種母語寫作,但是他們沒有在用那種語言寫作。譬如,他非常敬仰且視為偶像的秘魯詩人巴列霍所使用的語言並不是西班牙語,而是巴列霍語,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語言,沒有人可以模仿的語言。維克托講道,他本人在美國肯亞學院教授文學和創意寫作,生活分割在美國和古巴兩地,他雖然仍用西班牙語寫作,但這種西班牙語已經受到英語句式的影響,所以很難界定他的母語是西班牙語還是其他語言。
阿萊士和維克托還和現場讀者交流了對翻譯的看法。維克托認為,翻譯是一切文明的基石,翻譯所需要的能力、技能可能要超過寫詩本身的技能。他講道,他的妻子是他見過的最好的譯者,能把西班牙語翻譯成英語,妻子雖然沒有發表自己原創的詩作,但是他認為她也是詩人,因為她的詩作就是她翻譯的作品。
他認為,有人常常說詩歌在翻譯過程中會失去很多的東西,包括靈魂。但這類說法是片面的。實際上不可翻譯的元素,可能在翻譯過程中打開了更多創造空間的元素,所以,不可翻譯的東西,也是譯者重新對詩歌加以創作的契機。此外,翻譯實際上也是對自己母語的背叛。通過翻譯,對於自己原來的母語也是一種解構,一種拆解。
維克托還提道,杜甫是他最喜歡的中國詩人。在西班牙語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語境裡,中國詩歌的地位非常重要。西班牙語世界從19世紀起就有大量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杜甫有至少25個版本。
作者
新京報記者 吳鑫實習記者聶麗平
編輯
安也校對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