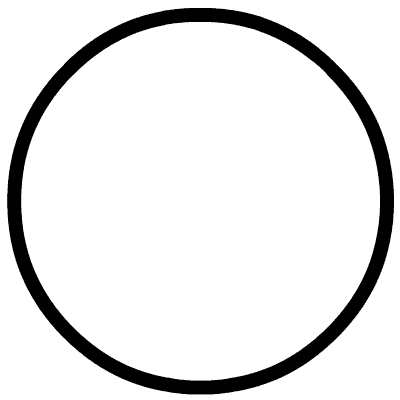年輕的妃子當著乾隆皇帝的面,吐槽他詩才並不出眾,審美俗氣逼人。她提到一幅《鵲華秋色圖》,乾隆蓋了足足四十餘個章,“高興了敲一個,不高興也敲一個,和以前在天橋底下看到的狗皮膏藥一樣,揭都揭不開。”
這當然不是史實,而是電視劇《延禧攻略》的橋段。編劇寫這段戲,顯然受到了民間對乾隆藝術修養的評價影響。網絡上,人們吐槽愛在名畫上題字的乾隆是“彈幕鼻祖”,又笑他把自己變裝入畫,稱他為“Cosplay大帝”,而在他指導下創作的藝術品,更是被調侃為“農家樂審美”。

《鵲華秋色圖》,上面布滿了乾隆的印章
這些吐槽雖有其道理,卻也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乾隆的身份。
“作為一個文人,這些‘高雅藝術’不僅是他的精神食糧,也是其博學的標誌,而這正是乾隆想要塑造的形象。”哈佛大學亞洲歷史教授歐立德在《乾隆帝》中這樣寫道。
他塑造這種形象,自有其目的。作為大清帝國的皇帝,統禦群臣治理天下的最高長官人,他的藝術創作實則和江山穩固有關。
盛世皇帝的憂思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二十三日上午,驛馬從萬裡之外傳來定邊右副將軍的捷報,新疆天山南北所有叛亂徹底平定,清朝最大的一塊心病根除。三代皇帝七十年努力終於在這一天收獲成果,大清版圖得以擴張,領土面積達到1453多萬平方公里,環顧四周,都是屬國,大清內外,全無對手。
大清盛世在乾隆這一代走向頂峰。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財力雄厚,一直到乾隆辭世,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GDP佔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庫銀在1790年甚至達到8000萬兩,將近康熙朝最高庫銀年(1719年)的兩倍。
據歷史學家張巨集傑介紹,從1759年開始,清朝檔案中就頻繁出現“盛世”二字。可乾隆帝並不滿足,在經濟、軍事、政治的力量達到巔峰時,文化也不能落下。北京畫院研究員趙琰哲在其書中寫道,清朝入關,統治中國,“如何讓漢族子民承認自己作為儒家文化正統皇權的延續,一直是乾隆帝的心頭所思”。
趙琰哲認為,在乾隆帝看來,對待漢族傳統文化與儒家古訓,消極抵製絕非良策,積極了解,重新塑造才是王道。乾隆對漢文化的推崇和尊重是其維護統治的一部分。漢文化講究琴棋書畫、品鑒古玩、作詩填詞,乾隆帝一生也在努力把這些做到極致——哪怕只是數量上的極致。
“通過把自己訓練成一個藝術鑒賞家和實踐者,乾隆想要展現給眾人的是一個理想的君子形象。”歐立德在《乾隆帝》一書中寫道,精通射術並不足以讓他贏得文官的尊敬,他必須在文章和武德之間取得完美的平衡。
文化征服
2014年,故宮工作人員清理文物時,在庫房發現兩個寫著“乾隆詩稿”的紅色髹漆箱子,打開竟是乾隆寫的2.8萬首詩,既有用朱筆寫的禦筆稿,也有大臣謄寫稿。
這還只是乾隆詩作的一部分。他一生寫了四萬多首詩,數量可媲美全唐詩,從10歲開始,到89歲去世,平均每天兩首,有時靈感一來,一天可以寫十幾首。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有一天乾隆遊覽昆明湖,不到一小時就寫了8首詩,平均7分鐘一首。他專門寫了一首詩記載這個小小紀錄的出現:“舟行十裡詩八首,卻未曾消四刻時。”(《禦製詩二集》)如此積累,乾隆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多產的詩人。
對乾隆來說,什麽都可以成詩,就像現代人發微博發朋友圈。據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邱士華介紹,乾隆一吟詩,隨臣立刻寫在長方形小紙片上,然後再謄寫一次,讓他確認,若要修改,乾隆就用朱筆在上面改,形成詩稿。這些詩稿每十二年整理一次,讓人多抄幾份,留存下來。
雖然在影視劇中,常常被認為是風流天子,但乾隆詩中兒女情長並不多見,甚至也從不見“酒”字。乾隆說,自己吟詩,不為了風雲月露,而是希望以小見大。
乾隆以詩為文,後世也可以從中了解他當時的思想、境遇。“平心而論,乾隆的詩,歷史價值大大超過藝術價值。”清史學家戴逸在其書中這樣寫道。
北京畫院研究員趙琰哲認為,乾隆帝詩作如此高產,一方面是他真的喜歡詩詞,另一方面,也是有意通過這種方法,把自己塑造成文士形象,希望漢族官員或子民認同他。
“漢族文士,包括在朝為官的人,有點像現在的知識分子,有傲氣的地方。靠錢財或靠武力,沒辦法打動我。”趙琰哲分析道,對這些人,需要靠文化征服,讓他們產生認同感,“咱倆都喜歡一個東西,都喜歡玩古董,都喜歡看畫,都喜歡寫字,那我就不覺得你是一個滿族人。”
當然,乾隆作為九五至尊,並不是想以此討好大臣、士紳,他需要在武力之外,讓被統治階層在文化上也臣服於自己。
至少表面看來,當時也有其效果。雖然乾隆大部分詩寫得像流水账,錢鍾書在《談藝錄》中直言不諱地談到:“清高宗亦以文為詩,語助拖遝,令人作嘔。”可當時有名的文人趙翼則讚美他的詩歌,“神龍行空,瞬息萬變”。
乾隆不但寫詩,還常作畫。1788年,荊州大水,乾隆恰好看到南宋李迪所繪的《雞雛待伺圖》,感慨道,“雙雛如仰望,其母竟何之”,由此聯想到荊州子民,覺得渴望賑濟的饑民就像畫中小雞,於是,他親筆仿了一幅《雞雛待伺圖》,命人刻在石頭上,將拓畫賜給各省督撫觀賞留存,並將禦製仿畫製作成緙絲掛屏,在上面題詩,警示官員做好父母官。
歐立德發現,乾隆常把自己的書法作品賜予賞識的人。比如除夕之夜,乾隆會賜予朝中重臣“福”字,並在眾人面前署上自己名字。歐立德認為,乾隆之所以如此,是“把自己在書法上的天資轉變成一種政治資本”。
農家樂審美
乾隆六年(1741年),景德鎮督陶官唐英的日子特別不好過。遠在京城的乾隆帝嚴厲申飭他督陶不用心。
雍正時期,他造的精美陶瓷多次得到雍正帝的誇獎,可到了乾隆朝,皇帝最多就批複一個“知道了”,也不說自己到底喜歡還是不喜歡。唐英只能戰戰兢兢地工作著。有一年,他按照舊樣燒製陶器,乾隆大發脾氣,甚至讓唐英自己承擔造瓷費。後來,皇帝又特意派內務府催總老格到禦窯廠協助他。
遠道而來的老格透露了乾隆帝的喜好——喜歡成對的,新奇的,巧勁的東西。一下子,唐英就像打開了任督二脈,使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不斷研發新品,挑戰難度大的。
乾隆八年的四月,他督造了夾層玲瓏交泰等瓶九種,送京呈進。乾隆帝雖然隻回復了一句:自行創作。這已是莫大的認可。
乾隆時代最知名的一件瓷器作品,是央視《國家寶藏》上展現的“瓷母”各種釉彩大瓶。網上嘲笑乾隆農家樂審美也由此而起,瓶身花紋繁複、色彩豔麗。

“乾隆所處的時代是天朝盛世,歌舞升平,所以他就去追求熱鬧的東西,”陶瓷收藏家韓傑說,禦製瓷器的特點反映的是帝王的心態。康熙的瓷器看上去從器形到畫工都非常挺拔,釉子和胎結合非常緊密。雍正的特點是比較柔美,比較雋秀。而到了乾隆時期,文飾非常繁縟,技術複雜。
韓傑的工作室裡藏了兩件陶瓷,一件是乾隆朝的外銷碟,呈粉紅色,牡丹爭奇鬥豔,線條呆板擁擠,色彩濃豔,另一件是雍正朝鬥彩碗,處處留白,清新雋雅。
“從藝術審美來說,確實沒有雍正的造詣高”,韓傑說,但是乾隆時代的瓷器勝在技術好,“那時歐洲工藝逐漸進入中國,融合了這些,從工藝和科技上都進步了。”
飽受吐槽的“瓷母”各種釉彩大瓶就是如此,燒製難度極大,各種釉彩在燒製過程中熔點不同,製造這個瓶子,最起碼得要燒20多次,每一次入窯的溫度都比上一次要低,才能完成。“不得不說乾隆的瓷器在工藝上到達了極致”。韓傑說。
“這代表了當時所能夠掌控的最高超的陶瓷技術,這種集錦、集大成的品位也是他喜歡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余佩瑾也持相同說法。在余佩瑾看來,瓷器也是乾隆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大使來訪,乾隆做了很詳細的準備,送給他轉心瓶還以及禦製詩,希望那些人回國後看見瓶子就像看到他一樣。
微縮世界
每天到下午五時,乾隆常會步入養心殿西暖閣臨窗最西頭的“三希堂”。這裡是他的書房,也是他一己打造的微型文物館。
乾隆帝不僅自己創作,還好收藏名家作品。藏品的來源首先是進貢物品。乾隆帝七十大壽慶典上,一位朝鮮使臣被贈送禮物的場景驚訝得目瞪口呆,光是車載的禮物就有三萬多車,為了搶運貢品,各地車輛“篝火相照,玲鐸動地,鞭聲震野”,而人力挑送或由馬匹、駱駝馱載的禮物尚未包括其中。
有時,乾隆帝也會出錢購買,但並不多。若是大臣有名家藏品被乾隆看到,他還會以借的名義取入宮中。大學士傅恆曾經收藏一幅米芾的書法《蜀素帖》,並傳給長子福隆安,有次家中不小心失火,幸好書法裱在外面,幸免於難。乾隆帝對此垂涎三尺,後來借口說哪裡都不如宮內安全,把書法收入宮中。
乾隆對這些藏品也很花心思。乾隆初年,由於內府收藏了大量歷代書畫,乾隆帝命大臣張照、梁詩正等對所存書畫一一鑒別,挑選其中的精品編成《石渠寶笈》一書。從此,不管是乾清宮、養心殿,還是三希堂、禦書房的藏品,每件都擁有了編號,清楚記載了它們的收藏地址、款識印記、前人題跋,以及有沒有禦題和寶璽。
這本書一共有四十五卷,到了乾隆五十八年時,因為書畫實在太多,他又命人編纂了《石渠寶笈續編》,嘉慶朝又續三編,據統計約有一萬二千五百多件精品。
“這些詳盡細致的目錄反映出乾隆一種近乎偏執的想法,他想擁有整個世界,至少是世界上的一些樣品。就像是乾隆要在紫禁城內創建一個微縮的世界。”歐立德如此分析道。
末代皇帝溥儀曾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據說乾隆皇帝曾經這樣規定過:宮中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準丟失。為了讓這句話變成事實,他拿了幾根草放在宮中的案幾上,叫人每天檢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這叫做‘寸草際’。”
據邱士華介紹,乾隆每次出巡,都會帶著他的至愛——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子明卷”。有感而發時,直接在畫作上題跋,累計下來,一共題跋了五十五處,畫卷上密密麻麻,各種印章異常顯眼,這裡一塊那裡一坨。
乾隆帝蓋印章,五個成套:“乾隆禦覽之寶”、“乾隆鑒賞”、“三希堂精鑒璽”、“石渠寶笈”和“宜子孫”。過年過節過生日,他還會再蓋兩章,七十歲生日時蓋個“古稀天子之寶”,八十歲蓋個“八征耄念之寶”。也因此,有了文章開頭,電視劇中“狗皮膏藥”的吐槽。
在趙琰哲看來,人們這種吐槽,源自對這些畫作的不同心態。“現在是一個公共系統,認為藏品是公家的東西,沒人有權對畫作動手動腳。但對乾隆帝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畫,自然全都是我的,我隨便對它做什麽都可以。第二,我就是喜歡,為了表達喜歡之情,我就題字,這是對你的一種看重。”
慶幸的是,乾隆帝瘋狂題字的《富春山居圖》“子明卷”是一個仿作,1746年的冬天,乾隆帝意外得到黃公望的真跡《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卻認為是仿品,束之高閣,所以“無用師卷”得以免於“慘遭毒手”。歷史就是如此陰差陽錯。只是其他類似書畫就沒那麽“幸運”了,像極其珍貴的王羲之的書法原作《快雪時晴帖》,每年冬天,乾隆帝都題字,到他去世時,已在書軸上題字賦詩73處。
不變的內核
雖然乾隆帝愛詩、愛畫、愛藝術,但本質上,他有一個最重要的內核身份——皇帝,而且是一位滿族皇帝。
乾隆帝經常在畫中把自己Cosplay成文人、菩薩的形象,試圖拉近與其他民族臣子、子民的距離。比如他收藏了一幅宋代佚名《人物》畫。畫中有一位盤腿坐在床榻上的國字臉文士,穿著飄逸的漢服,一手執筆,一首持紙卷,身旁一童子往杯中倒水,床榻兩旁擺放著書籍、畫軸、古琴、茶爐、盆景。乾隆帝很喜歡這幅畫,命人臨摹,把畫中人改做自己。那位國字臉文士變成了乾隆清瘦的長臉。
乾隆讓人把自己Cosplay進畫裡不止這一次。乾隆十五年,皇帝讓畫家對明末丁雲鵬所繪的宗教畫《掃象圖》進行仿繪,並將自己形象加入其中。完成的《弘歷掃象圖》中,乾隆帝身著右衽漢裝,臂戴寶釧,頭戴金箍,模仿菩薩裝扮,坐在寶座上。不僅如此,乾隆帝把自己模仿菩薩的畫像發到各個寺中,供信徒朝拜。
據趙琰哲介紹,自元代始,藏傳佛教把中國皇帝看作文殊菩薩在世間的轉輪君王,稱為“文殊菩薩大皇帝”,到清代,西藏黃教首領也用“文殊菩薩大皇帝”尊稱乾隆帝。“由此,乾隆帝自認為是文殊菩薩在世間的轉輪君王,具有文殊菩薩的智慧與威力,以此獲得西藏信徒的支持。”
現實中,乾隆既沒穿過漢裝,也沒扮過菩薩。甚至在編纂《禦製詩三集》時,他還曾特別加上小注說明,在《宮中行樂圖》中,之所以穿著漢裝,是因為原畫如此,因而未改“圖中衫履即依松年式,此不過丹青遊戲,非慕漢人衣冠”。
現實中,乾隆對服裝規製,要求極為嚴格。據歐立德介紹,到乾隆登基時,滿洲人正日益面臨著腐化的危險,當年驍勇善戰的軍事精英變成一個寄生的階層。乾隆帝一直在警惕金朝的歷史重演,他認為,一個少數族群如果想要確保統治,就需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所以要保存滿族傳統,有三點不能變,滿族語言文字、衣冠制度以及尚武精神。他甚至將之視為關係清朝存亡的事情,“且北魏、遼、金以及有元,凡改漢衣冠者無不一再世而亡”。
雖然在民間,人們常把乾隆想象成一個浪漫的、多情的風流帝王,但實際上,乾隆對自己的身份,對自己的職責有著比常人更清晰的認知。“他最主要的一個身份還是皇帝,”北京畫院研究員趙琰哲說,“不管是書畫還是瓷器收藏,一切東西都是圍繞他的統治。”
●參考資料:
《清乾隆朝仿古繪畫研究》,趙琰哲著,中央美術學院2013年
《乾隆帝》,歐立德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乾隆一日》,吳十洲著作,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
《乾隆帝及其時代》,戴逸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清代官窯瓷器的裝飾特色及文化傳承研究》,劉慶著;
實習生教欣銘對本文有貢獻。
看天下430期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