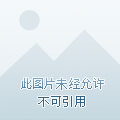內容提要:在古代文論語境中,「以意逆志」以正確詮釋作者創作意圖為目標。為有效落實該法,古人在詮釋對象、詮釋者兩方面預設了諸多條件。但無論哪種都難以保證其普遍有效,也常令詮釋者在思維方式上陷入獨斷,從而低估多元詮釋的可行性與合理性。「以意逆志」與「見仁見智」存在實質差別。該說的實際意義主要是,在客觀上為文本詮釋提供有價值的角度與觀點,推動古人對文學詮釋倫理、詮釋法則的探索,激活詮釋者之生命體驗與價值訴求。
關 鍵 詞:以意逆志/條件/限度/意義
基金項目:2013年度中國人民大學「明德青年學者計劃」項目《中國古代文論基本觀念研究——以其內在問題及當代意義為中心》(13XNJ038)。
作者簡介:徐楠,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徐楠(1978- ),男,黑龍江哈爾濱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論、中國古代詩歌研究。
在當代文學研究視域中,孟子解讀《詩經》時提出的「以意逆志」,屬於「創作意圖詮釋」,被視為古人最基本的文學批評方法之一。除研究此法的內涵、思想基礎、流變過程、當代意義外,學術界亦對其限度存在關注。從董洪利《孟子研究》、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及尚永亮、王蕾《論以意逆志的內涵、價值及其對接受主體的遮蔽》等代表性成果可見,時賢已能從詮釋學及文學批評常識出發,就「以意逆志」是否可能、「以意逆志」對文本意義及接受者的遮蔽等話題,展開予人啟發的探討。而在筆者看來,相關考察似還有推進的必要。若想對此類問題產生更為細緻的認識,仍需進一步深入歷史語境,直面古人自身理路,逐一檢驗「以意逆志」信奉者為落實該法而預設的諸種條件,思考它們何以產生、有效程度如何。這既有益於我們通過剖析古人的運思方式、價值訴求,來理解「以意逆志」限度之具體表現、產生根源等問題,亦有助於我們判斷該法之於古人的實際意義。
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中,「以意逆志」的意涵是經歷代申說而日益豐富的。不過,該方法的提出者孟子,畢竟為後世的發揮奠定了基礎。而後人有關該方法成立條件的預設方式,也多可溯源至孟子。因此,相關分析仍須從孟子開始。
我們知道,「以意逆志」說產生的原始語境,是孟子通過與鹹丘蒙辨析舜的事跡,揭示君臣、父子關係應遵守之準則。在結束了「舜之不臣堯」的話題後,鹹丘蒙繼續提問:「《詩》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曰: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1](P638)。
解釋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這段名言時,研究者的興趣大多在於辨析「意」到底指說《詩》者之意還是文本之意,以及「文」、「辭」二概念的具體所指。不過,如果避開這類思路的干擾,便可發現,這段話其實還潛藏著三方面重要資訊。其一,孟子將「志具有真實性、唯一性」當成了無須分辨的常識。在這個申說倫理原則的語境裡,《詩》之「志」,亦即詩人的創作意圖,乃是證明孟子觀點的關鍵論據。既然如此,它必然被孟子視作可準確指明的真相,而不會只是一種見仁見智、「無達詁」的推測。其二,孟子同樣信賴「志必由文顯」。具體而言,他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只是反對迂執地將文本的字面含義等同於志而已。這種觀點與《孟子·盡心》中的「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1](P1010)具有相似內蘊:它們都承認文辭表象與真實意圖可以存在差別,但絕不是要否定文本傳達真實意圖的有效性。其三,孟子認為,詮釋者能夠通過對文、辭的合理解讀,穿透字面含義,揭示詩中之志。也就是說,他覺得詮釋者完全可以具備正確解讀文本的能力。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即便志確在《詩》中,也是斷無被揭示之機會的。
接下來的兩個問題是:對這《詩》中的志,孟子是否有性質上的規定?既然詮釋者必能逆志,那麼,孟子是否對其實現逆志的條件有所反省?先看前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古代文論中的「志」概念,在廣義上可泛指人心中所有之思想、情感、意念,在狹義上則專指思想、情感、意念中理性的(尤其是政教層面的)內容。在《盡心》中,孟子曾將「志」明確界定為「仁義而已矣」[1](P926)。而通觀《孟子》涉及《詩》的三十餘例可知,無論解說還是引用,孟子都無一例外地將《詩》當作仁義之辭看待。而且除了對《齊風·南山》中「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句是否具備普遍法則意義略存異議外,他一直將《詩》視為修身、立言的根本依據。顯而易見,在《孟子》的語境中,《詩》中之「志」,不可能泛指人間各類情感意念,而是被預設了純正無邪、足為讀者楷式的特徵。這一情況,周光慶、張伯偉等均曾涉及,故筆者僅補充證據,不作過多展開。
再看後一個問題。從論說的原始語境可知,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直接動因,是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理解為詩人緣事而發的怨憤之辭,反對將其判為真理性陳述。為了增加這一論斷的說服力,他還進而指出:「《雲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從這兩例來看,孟子似乎懂得,對於「逆志」來說,能否理解文學表現手法的特點應是前提之一。可耐人尋味的是,他並未沿此路徑自覺提出「關注文本藝術特性」一類要求,在其解《詩》的其他案例中,也鮮有從該角度分析文本的自覺傾向。除開這一點,今人亦已發現,孟子在與公孫醜論《小弁》、《凱風》的創作意圖時,曾應用過論「尚友」時提出的「知人論世」法。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結合《詩》之歷史語境來「逆志」的手段,在《孟子》中也屬吉光片羽,它同樣很難說是得到了孟子自覺反省的。
那麼,為了逆志的有效實現,孟子是否在詮釋者這一方面規定了更具普遍意義的條件呢?其實只要回到上述諸例的原始語境,就不難發現,無論是關注表現手法還是運用知人論世,它們都存在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服務於孟子自身的政教、倫理觀念。孟子之所以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視為怨憤之詞,更深層的原因恐怕在於,如果不這樣詮釋,他堅持的「父父子子」倫理原則,便很難得到來自經典的支持。這樣的話,他也就無法有效解答鹹丘蒙提出的「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這個疑問。與此相似,孟子用知人論世法解讀《小弁》、《凱風》,不僅是要逆志,更是為了以此論證他「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1](P820)這一觀念。而通觀孟子用《詩》的各種實踐,這種以言說自身政教倫理觀念為準則的詮釋特徵,確乎是他一以貫之奉行的正道。正如羅根澤所說:「孟子雖然能提出以意逆志的好方法,但以自己是講道德、說仁義的哲學家,而不是文學家,由是其意是道德仁義之意。」[2](P39)明乎此便可知曉,孟子說《詩》引《詩》,為何時而能正確指出文本表現手法之奧妙,時而卻脫離文本語境,或將《大雅·既醉》中的「既飽以德」誤讀為「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1](P797),或決絕地以「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1](P926)揭示《魏風·伐檀》中「不素餐兮」的含義,甚至在引用《大雅·公劉》、《大雅·綿》時產生諸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1](P139)這類匪夷所思的「亂斷」。原因無他,恰恰在於:這位大儒根本沒有從語言藝術角度獨立分析文本的自覺。也就是說,在他的邏輯中,說《詩》者應該具備的普遍有效之「逆志」條件,並不是有關語言藝術特徵、規律的理解力,也不是搜求史料證據、以史證詩,而是正確的政教、倫理觀念及由此產生的判斷力。關於此點,他那著名的「知言養氣」說,為我們提供了重要旁證。眾所周知,孟子「浩然之氣」的產生根源,乃是達到至高水準的道德理性修養、覺悟。而是否具備這種修養、覺悟,正被他看作能否「知言」的關鍵條件。不難推知,對於孟子而言,具備這一條件,不僅能洞悉「詖辭」、「淫辭」、「邪辭」、「遁辭」,也必然能正確地理解經典背後的意義。對此,張九成在《孟子傳》中曾有所揭示:
父不得而子,蒙乃引《詩》普天率土之意以問,亦可謂難答矣。然天下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幽明一理也,豈有作《詩》者使父不得以盛德之士為子乎?孟子乃解此詩為嘆獨勞而言,非為父子而雲也。因又使學者先當明天下之理,然後以理探詩人之意……故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說[3](卷22)。
張九成認為,一則《詩經》作者不可能寫出違背倫理原則的內容;二則孟子解《詩》的根本前提是「明天下之理」,亦即具備領會倫理原則的能力。這種分析與文學創作基本規律水米無乾,也帶有濃重的理學家味道;但觀其大旨,正可謂深得孟子之心。這種思路下的讀《詩》,其實便是將詮釋視作說《詩》者、作《詩》者兩顆仁義之心的相迎相會。而這種相會之成為可能,自然也完全可以從孟子宣揚心心相通、推己及人的「心之所同然」、「強恕而行」等基本觀念那裡得到支持。跳出孟子這一邏輯看其解《詩》,則其結論確乎時而合理,時而純屬主觀臆測。然而就這一邏輯的自身理路觀之,則它們之於孟子,哪一個不是符合「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要求的正確解讀呢?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對《詩》及說《詩》者能力的一系列預設,構成了孟子「以意逆志」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不過也正是從這些預設中,我們看到,孟子的「以意逆志」,主要成就的是對《詩》在經學意義上的價值揭示。至於《詩》之創作與詮釋在實然層面存在的複雜情況、《詩》文本無可迴避的文學品格,則只是因與特定話題機緣湊泊,才偶爾得到其合理闡發。整體上看,它們並未被孟子作為核心問題自覺納入論證視野。就此而言,他的「以意逆志」之成立,其實是依託於獨斷論語境的。這樣的「逆志」,既容易誇大道德理性修養之於解讀文學文本的有效性,亦註定會窄化文學文本的詮釋空間。志是否具有真實性、唯一性,是否必在文本中?仁義之心是否能成為洞察文辭奧秘的關鍵因素?這些疑問也許對於孟子而言,都是不成其為問題的。但,它們又都是真實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