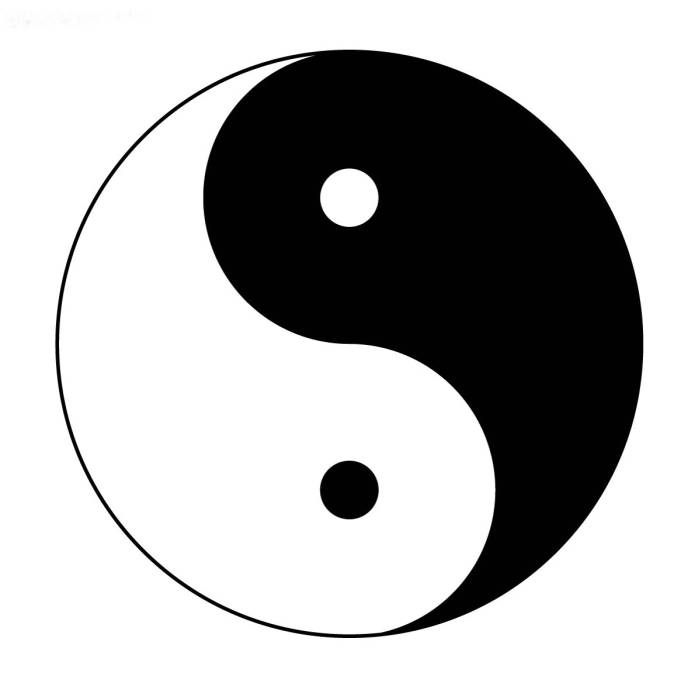作者簡介丨劉成紀,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學研究所所長。
原文載丨《哲學研究》,2018年03期。
摘要
在《“闡”“詮”辨》一文中,張江提出建設當代中國闡釋學的構想,這使中國傳統有無自身闡釋體系成為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本文認為,中國古典闡釋學雖然涉及古代經典的方方面面,但以儒家經學為主導。自西漢以降,《易經》被推為群經之首,相應也使河圖洛書成為闡釋原型。從中國文明史看,河圖洛書作為一種詮釋模式,既解釋歷史也被歷史解釋,具有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雙重意義。中國文明進程則表現為向這一述史模式不斷回溯又不斷放大其解釋邊界的過程。據此,抓住了河圖洛書,也就抓住了中國古典闡釋學體系的關鍵,同時也可以借此為中國人文科學的整體進展理出一條縱貫的軸線。
近20年來,中國學術界對西方闡釋學的關注,已逐漸擺脫了早期的譯介狀態,轉向對自身闡釋理論的重建。2017年,張江發表《“闡”“詮”辨》一文。該文以字義辨析為切入點,從本體論的高度為中國闡釋學的體系建設規劃了方向。如其所言:“中國闡釋學何以構建,起點與路徑在哪裡,方向與目標是什麽,功能與價值如何實現,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迫切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堅持以中國話語為主乾,以古典闡釋學為資源,以當代西方闡釋學為借鑒,假以對照、選擇、確義,由概念起,而範疇、而命題、而圖式,以至體系,最終實現傳統闡釋學觀點、學說之現代轉義,建立彰顯中國概念、中國思維、中國理論的當代中國闡釋學”。這一論斷對中國闡釋學建設需要解決的問題和研究路徑給予了清晰昭示,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建設當代形態的中國闡釋學,必須建基於對民族自身傳統的理解,即張江所講的“中國話語”問題。那麽,中國傳統的經典闡釋有無自己的話語?如果有,它又是以什麽為核心構建了自己的話語體系?筆者認為,對於這一問題的探尋,必須重新返回到中國傳統思維的獨特性上。按照王樹人的講法,與西方概念思維不同,“中國傳統思維,表現為以‘象’為核心,從而圍繞‘象’來展開。這在《周易》中的表現最為典型。”據此看中國古典闡釋學,它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影像優先原則,而河圖洛書則被視為一切影像的本源。這也提示人們,由張江提出的“由概念起,而範疇、而命題、而圖式”的中國當代闡釋學建設路徑,與中國傳統有著重大不同,即它不是“由概念起”,而是“由圖式(影像)起”。下面,筆者將以此為背景,探討“河圖洛書”以及由此衍生的卦象理論對中國古典解釋學的影響,並借此為當代形態的中國闡釋學建設提供一個可資反思的歷史案例。
一、“河圖洛書”闡釋模式的建構
在傳世文獻中,中國先秦時期留存下來的關於河圖洛書的史料均是片斷性的。如《尚書·顧命》提到周成王葬禮上的宮殿布置:“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提到孔子的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易傳·系辭上》也講:“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些文獻雖然支離破碎,但連綴在一起卻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釋義鏈條,即《尚書·顧命》中提到的河圖,極可能是黃河灘塗地帶撿拾的玉石,但它在當時人的想象中卻被賦予了神性,成為天命或神啟的暗示物。正是在此意義上,孔子將“河不出圖”視為被神靈拋棄的預兆,所以陷入深深的絕望。以此為背景,“河出圖,洛出書”,即河中玉石的紋理和龜背的裂紋被賦予了人文肇始的意義,人間聖哲正是通過對其紋樣的摹擬,將天文接引為人文,河圖洛書由此也就成了中國文明的神性和自然起源。它作為神賜的聖典,具有為後世一切經典立法的意義。或者說,它以它的本源性而獲得本體價值,成為張江所講的中國詮釋史上的“前置模式”。
河圖洛書真正被確立為中國文明的歷史本源和前置模式,始於西漢。此前,對這一本源的追溯一般停滯在伏羲時代。如《易傳·系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換言之,在先秦時期,中國文明的人(聖王)創觀念要遠比神賜觀念更具主導性。但自西漢始,《易傳·系辭上》中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句的神意被發揮出來。如孔安國講:“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史記集解·孔子世家》)此後,揚雄《覈靈賦》講:“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全漢賦評注》)又按《漢書·五行志》所記:“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范》是也。”到東漢時期,這種神賜觀念則成為縱貫朝野的共識性判斷。如《白虎通德論·封禪》:“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王充《論衡·雷虛》:“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為,人讀知之。”鄭玄《六藝論》:“河圖洛書,皆天地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均是將作為神賜或自然生成的河圖洛書置於伏羲作卦之前。由此形成的解釋序列是:河圖洛書是本源性的,然後是“繼天而王”的伏羲仿照河圖作卦,再然後是夏禹比照洛書創作《洪范》。在這一序列中,河圖洛書無疑被視為中國文明的最原初範本,伏羲、夏禹則是後起的領受者、摹仿者或闡釋者,至於孔子編訂六經以及後世層出不窮的傳、注、疏,則不過是對摹仿的再摹仿、詮釋的再詮釋罷了。
在今天科學昌明的時代,沒有人會相信文明的神賜論,所謂河圖洛書也只能被斥為妄言。但是現代學者介入歷史研究必須區分兩種真實:一種是歷史的真實,一種是觀念的真實。換言之,河圖洛書雖然缺乏歷史的真實性,但它如果被一個時代的人信以為真,那麽它就在觀念層面擁有了真實性。由此形成的對經典起源的認識和解釋實踐,則在效果層面形成了中國解釋學的真歷史。從歷史看,中國文明早期散碎的神賜觀念之所以會在西漢時期被發揚出來,應與當時陰陽五行觀念的廣泛流行密不可分。董仲舒“推陰陽為儒者宗”(《漢書·五行志》),進而以“陰陽消息”作為神啟的預兆,則是其直接的理論動因。也就是說,這種天命觀念盛行的時代氛圍和理論響應,使漢代儒家敏銳抓住了先秦儒學中的支言片語,重建了中國文明的原始意象。從闡釋學的角度看,這種新解釋起點的建立明顯是對先秦文獻過度詮釋的結果,但也證明了任何解釋總是通過植入創造實現歷史重建的特性。
1922年,顧頡剛在與錢玄同的通信中,曾提到中國上古史建構中的“層累”特性。在他看來,中國上古史是後人不斷疊床架屋的想象性構建物,即“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根據這一規律,商周時期,上古聖王只有夏禹,至春秋時期累加上了堯、舜,戰國至西漢陸續累加了黃帝、神農、伏羲,直至東漢又累加上盤古,於是一個完整的上古聖王譜系得以形成。以此為背景看,漢代學者在伏羲畫卦之前疊加上河圖洛書,明顯具有同樣的性質。它說明了中國早期歷史總是一方面給後人留下誘發想象的蛛絲馬跡,另一方面則借助過度闡釋顯現出新的模態。於此,闡釋學成為一種歷史的建築學。從漢代學術史看,這種歷史重釋雖然缺乏信史依據,但它卻對漢代學術架構的調整形成重大影響。比如,自戰國至西漢中期,儒家六經的排序,一直以《詩》為首,即《詩》《書》《禮》《樂》《易》《春秋》。但至西漢後期,劉歆《七略》卻將其調整為《易》《書》《詩》《禮》《樂》《春秋》的新秩序,自此《易》代替《詩》成為“六經之首”。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顯然來自於“河圖洛書”對當時知識格局的重塑。如上所言,劉歆將河圖視為八卦的原初形式,將洛書視為《尚書·洪范》的範本,這意味著河圖洛書與六經中的《周易》《尚書》具有最直接的匹配關係。所謂次序調整則無非是因為史源重置導致了對現有知識秩序的乾預,使歷史在與現實的相互參證中形成了新格局。同時,在傳統的六經排序中,以《詩》為首具有心理發生學意味。孔子講“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講“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都是在強調詩對人內在心志的興發作用,具有先導性。到西漢時期變為以《易》為首,則預示著自孔子時代為順應人性成長設計出的知識秩序,開始讓位於哲學對一個完型化的知識體系的反向重構。這種從知識生成向知識建構的轉化,明顯是漢代經學從傳統計程車人修身之學向國家哲學轉進中必須作出的調整。
在河圖洛書的解釋框架內,漢代學術中,不僅經學的學術架構被重組,而且直接促成了當時讖緯之學的興盛和泛濫。關於河圖洛書與讖緯的關係,東漢王逸《楚辭章句》釋王褒《九懷》雲:“河圖、洛書,緯讖文也。”這是將河圖洛書直接視為讖緯。但漢代及後世學者的主流意見仍是在兩者之間作出區隔。如桓譚《新論·見徵》:“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複加增依讬,稱是孔丘,誤之甚也。”王充《論衡·實知》:“讖記,所表皆效圖、書。”《晉書·天文誌》:“末世之儒,增減河、洛,竊作讖、緯。”均認為河圖洛書在先,讖緯之文則是漢代儒家以河圖洛書為母本形成的想象性拓展和意義附衍。至此可以看到,河圖洛書不僅重塑了漢代經學的知識格局,而且是當時讖緯之學的根源。當然,後人也進而認為讖和緯並不是一回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附錄》案語講:“案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也就是說,讖與緯雖然在綜述河圖洛書、將人的世界觀念神學化方面具有一致性,但緯專注於對六經的神性闡釋,更趨於學術,讖則是對世間吉凶之兆的具體勘驗,更傾向於實踐。據此,河圖洛書對漢代闡釋學的影響又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對六經體系的價值重塑;二是對緯書所涉知識疆域的整體神化;三是通過符讖與神仙方術的融合,將河圖洛書神學化的詮釋取向在現實中尋求兌現。至此,中國古典闡釋學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前置模式”。
二、“河圖洛書”模式的解釋視域
關於漢代學者對經典的過度闡釋,桓譚曾以當時一位秦姓學者為例講:“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新論·正經》)其他文獻也提到,當時經學家“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漢書·藝文誌》),“一經說至百萬言”(《漢書·儒林傳》),可見過度闡釋是當時普遍性的問題。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固然和漢儒解經過於繁瑣有關,但更重要的則是想象式解讀導致的經典釋義的無界性。尤其是當時的今文經學,它依托的經典本身就是漢儒的口傳,口傳過程中滲入個人見解具有必然性。以此為背景,流行於漢代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論,極大拓展了儒家的知識邊界。漢代儒學之所以能從經到緯、再到符讖無限蔓延,離不開這種知識視野被過分放大的背景。對於當時這種非理性的經典闡釋法,後世正統儒家一般缺乏好感,認為這一時代,“偽學迭出,讖緯風行,儒道之言,皆喪失本來面目”。但是,就漢代儒學由這種解釋視域的融合所獲得的知識廣博性而言,可能在中國經學史上是無出其右的,它使漢代政治、文化乃至人神關係的“大一統”格局,以儒學的方式進行了創造性回應。同時,這種解釋視域的放大並沒有破壞知識的一體性,其原因有二:一是漢儒以河圖洛書為本體,有效提升了六經詮釋的哲學高度,使其能夠形成對經學和讖緯的總體籠罩和覆蓋;二是河圖洛書作為一種解釋原則,基本縱貫了從經、到緯、再到讖諸層面,使其獲得了內在的飽滿和秩序感。套用張江的話說,漢代學術“是用其恆定的思維模式作了過度闡釋”。這恆定的思維模式就是象思維,被過度闡釋的對象就是河圖洛書。
當然,也正是河圖洛書在漢代思想體系裡獲得的解釋廣度、哲學高度和歷史深度難以超越,後世學者解經和對藝文的解析,基本沒有越出這一框架。他們要麽直接追溯到河圖洛書,要麽降以伏羲畫卦為始點。也就是說,從河圖洛書到伏羲畫卦,這一具有恆定性的文明創始模式,基本規劃了漢代以降中國人對人文學科的認識和解釋視野。現分述如下:
首先看經學。在中國儒家經學史上,有所謂的漢學與宋學之別,但在尊奉河圖洛書作為釋經原則這一點上,雙方卻保持了一致,並由此形成了關於經學史源的主流性看法。如清人趙翼所講:“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大禹因洛書而演疇……自此說行,而劉歆宗之,亦以為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范》是也。於是馬融、王肅、姚信輩群奉其說,至今牢不可破矣。”到宋代,道士陳摶再創河洛圖式,其《龍圖序》雲:“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這基本延續了漢儒設定的河圖洛書生成模式。關於它的傳承和影響,清人張惠言講:“宋道士陳摶以意造為龍圖,其徒劉牧以為《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為‘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同為清人的趙翼和張惠言分別用“牢不可破”、“牢不可拔”形容河圖洛書模式對中國解《易》傳統的影響,而《易》又被奉為眾經之首,由此可以看出,它對於中國經學史而言,是一條縱貫始終的軸線。這中間,如果我們認同儒家經學在中國文化史中的主乾地位,認同經學史就是儒家經典不斷被解釋的歷史,那麽,河圖洛書在中國闡釋學史上的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
其次看文學。按照現代的學科分類,文學有其自身的源頭(如勞動、遊戲、情欲)和獨立價值(如審美、象徵),但在中國述史傳統中,“文”作為一個廣義的概念,它和其他人文學科具有同源性和一體性。這個共同的“源”就是河圖洛書或者作為其順延形式的伏羲畫卦。如南北朝時期,劉勰《文心雕龍》開篇即講自然之文向人文之文的轉渡問題,而河圖洛書則被視為這一轉渡的始點。如其所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屍之?亦神理而已。”(《文心雕龍·原道》)也就是說,作為“言之文”的文學,其核心價值在於領悟“天地之心”,而從人工製作的八卦、九疇到河圖洛書,再到不可言喻的“神理”,則是接近“天地之心”的路徑。其中,如果“天地之心”和“神理”都是不可感知的,那麽“河圖洛書”就是與之最相切近的形象化隱喻,並因此具有了中國文學解釋原型的意義。當然,在中國文學設定的天人交感或人神感通模式中,學者們也未必單純以神秘化的河洛意象窮極解釋的極限,而是僅將其追溯到人可以理解的範圍之內,即以伏羲“畫八卦,造書契”為始點。如《文選·昭明太子序》雲:“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但即便如此,依然證明中國人對文學的理解從來沒有被現代意義上的“文學”一詞限定,而是將之視為朝更廣義的人文、哲學乃至超驗世界不斷探進的方式。換言之,中國古典闡釋學的“河圖洛書”模式之所以對中國文學是有效的,並不是因為它直接充當了這一解釋模式的摹本,而是昭示了文學闡釋必須在文學之上尋求更高目標的意向。至於這個目標是哲學還是神學的,並不是那麽重要。
第三看書畫。在諸種藝術形式中,中國文字的象形性和繪畫的影像性,意味著兩者具有一體同源關係,也意味著它們與河圖洛書及伏羲畫卦的承續關係更為直接。從中國藝術史看,書畫被統一納入《易傳》的述史系統有一個漸進過程。如西漢孔安國《尚書序》講:“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此後,許慎的《說文解字序》接續了這種看法,認為伏羲畫卦為文字的創造提供了基本原則。南北朝時期,顏延之則進而將繪畫納入這一述史模式,認為“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並認為書法和繪畫分別以“圖識”和“圖形”分有了卦象的“圖理”。到唐代,張彥遠則進一步將這種述史模式系統化。比如在《歷代名畫記》中,他首先借助傳統的書畫同體、同源觀念,將這兩種藝術歸並為一個整體,然後綜合前人的片斷言論,將河圖洛書、伏羲畫卦與書畫的關係理出了一個完整順序。如其所言:“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跡暎乎瑤牒,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張彥遠,第1-2頁)這裡的“龜字”即洛書,“龍圖”即河圖。在他看來,這兩種帶有天啟色彩的自然之象在更久遠的有巢氏、燧人氏時代即有顯現,但直到聖王包犧(伏羲)氏出現,才形成真正的領受,於是有了“典籍圖畫”的發端。在這裡,張彥遠隻提及“典籍圖畫”,似乎沒有提及書法,但典籍本身就是由文字書寫的,書法則是文字書寫的藝術化。也就是說,典籍天然地包含了書法,並成為書法的指代者。同時,在這段話中,洛書被視為文字的起源,河圖被視為圖畫的起源,這也有效厘清了文字性典籍與觀賞性繪畫之間的歷史分野問題,使河圖主要訴諸觀看、洛書主要訴諸識讀的特點得到彰顯。
第四看音樂。與書畫等造型藝術不同,音樂是一種時間藝術。但在中國古代哲學觀念中,它依然可以被有效納入到伏羲作畫和河圖洛書的解釋模式之中。這是因為,八卦雖然是關於自然世界的抽象圖式,但這一圖式並不是靜態的,而是充滿變量。從《易傳》看,為八卦帶來變量的是自然之氣。氣的流動生成風,風與萬物相激相蕩發出聲音,聲音秩序化則形成音樂。基於這種氣與音樂的關係,氣的強弱變化就成為音調和音律的測量標準,由此可分出五音十二律。以此為基礎,通過音律與卦象的配位就可以將其納入到太空性的八卦體系之內。而八卦與河圖洛書的源流關係,則使後者有了被設定為音樂本源的可能性。從中國音樂史看,自春秋時代,這門藝術開始被組入到一種太空性的世界體系,如《左傳·昭公二十年》錄晏子語雲:“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戰國之後則借助納音法和卦氣說使之成為八卦象數體系的組成部分。比如在漢代,京房根據《周易》卦象,將傳統的十二律推演為六十律。在他看來,“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見《後漢書·律歷志》),這就確立了樂律與《易》卦的關係,並將音樂的本源上溯到了伏羲時代。
但從現存史料看,在音樂與河圖洛書之間建立直接關聯應起於宋元時期。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記,元余載著《韶舞九成樂補》,“所定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樂類》),到明代,則成為權威性的音樂本源解釋法。如朱載堉講:“夫河圖洛書者,律歷之本源,數學之鼻祖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則之者,非止畫卦敘疇二事,至於律歷之類,無不皆然。蓋一切萬事不離陰陽圖書二物,則陰陽之道盡矣。”(見《律學新說·律呂本源第一》)這是講河圖洛書對樂律的肇始意義。對於這一問題,清人童能靈在其《樂律古義》中講的更直接,即:“《洛書》為五音之本,《河圖》為《洛書》之源。《河圖》圓而為氣,《洛書》方而為體。五音者氣也,氣凝為體,體以聚氣,然後聲音出焉。”(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樂類存目》)至此,河圖洛書作為中國音樂本源的地位得到最終確立。
從以上情況看,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河圖洛書作為恆定的解釋模式,是一個既具本源性又具廣延性的概念。在中國文明的起點,它首先以神啟的方式向人昭示出這一基本知識模態。然後,河圖對應於伏羲八卦,洛書對應於夏禹九疇(《洪范》)。其中,《易》因為與八卦的直接關聯而被排於六經之首,《尚書》則因與《洪范》的關聯而居於次席,但在總體上,《易》和《尚書》又對群經有總體統攝意義。以此為背景,河圖洛書的解釋視野進一步放大,文學藝術等一切文明成果都被納入到了它的解釋視域之內。這中間,雖然各種人文形式進入這一體系的時間有早晚,但它總體上體現的擴張態勢是不言而喻的。同時,河圖與洛書就知識分類而言,前者是影像性的,後者是文字性的;前者是圖譜的肇始,後者是典籍的起源;前者訴諸描畫,後者訴諸書寫;前者供人觀看,後者供人識讀。兩相配置,則顯現出了其包容人類知識的整全性。關於這一點,宋鄭樵曾講:“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這裡的“左圖右書”,既可以指本源意義上的河圖洛書,又可以泛指一般意義的圖書。據此可以看到,中國古典形態的闡釋學史,就是指對河圖洛書不斷回溯、理解並在闡釋中不斷被放大的歷史。這一中國文明的原發意象,作為歷史事實是虛假的,但它卻在闡釋學所注重的“效果史”層面表現出非凡的綱領性價值。

三、“河圖洛書”模式對中國古典闡釋學建構的意義及問題
從以上分析可知,中國傳統闡釋學,就其主體而言,是一種既從影像出發、又以釋圖為本位的闡釋學。在這一模式中,河圖與洛書的關係,最本源地被設定為影像與文字的關係,即圖先文後。作為解釋手段,則認為“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強調“以象釋象”的優先性和解釋效能。由此可見,中國古典闡釋學圍繞河圖洛書形成的闡釋體系,可能遵循的是一個與現代闡釋學背反的邏輯,即這一體系的建構,不是張江所講的“由概念起,而範疇、而命題、而圖式,以至體系”,而是相反,即以“圖式(影像)”為其肇端,然後命題、範疇、概念,以至體系。所謂闡釋學領域裡的中國聲音或中國話語問題,也正是以這種體系生成秩序的倒置得到了凸顯。那麽,這種從河圖洛書或者從影像本體出發的闡釋傳統,對中國古典闡釋學的建構到底有什麽價值和意義?它與建設當代形態的中國闡釋學存在什麽關係?現簡述如下:
首先,從河圖洛書出發,可以形成對中國文明的整體闡釋。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原型角度介入中國哲學、文學乃至泛文化闡釋的學術成果不在少數,如傳統龍鳳圖騰、昆侖神話系統、荊楚神話原型等均被涉及。但是,這類成果要麽缺乏歷史本身的觀念支持,要麽關注的問題被區域性和民間性限制,無法形成對中國文明的整體含攝。與此比較,河圖洛書則既因其原型特性而自然與現代哲學或文化人類學對接,同時自秦漢以來,中國人對這一原型又具有高度的理論自覺。換言之,該原型不是現代人的新造,而是以自覺形式存在於歷史之中。以此為背景,自秦漢以來,河圖洛書一方面因與經學的關聯而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正統性,另一方面,它的影響力則同時指向緯書、符讖和民間佔驗實踐,具有從中心逐步外向蔓延的性質。而這種蔓延之所以是可能的,一是因為八卦圖式以“象天法地”的巨集闊性囊括了人的一切世界經驗,二是因為這一圖式在起源上被賦予了神性,從而將人神兩界打通。也就是說,河圖洛書模式具有縱貫天地人神的整體特徵,顯現出表意的無限廣度和開放性。後世,它又逐步從一個原型概念泛化為一般圖書的指代者,這也是它可以形成對中國文明整體詮釋的證明。
其次,河圖洛書作為闡釋原型,有助於厘清中國古典闡釋學為闡釋對象設定的主從次序。在中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始,儒家經學一直代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相關經典的詮釋則成為歷代經生的神聖事業。河圖洛書作為眾經之源,當然也成為經學闡釋學的源頭。同時,按照中國文化向來重史的傳統,經典的歷史性與其真理性是一對互證的概念,即歷史愈久遠,闡釋對象愈切近真理。這樣,在儒家的價值譜系中,河圖洛書與眾經的關係,也就成為真理的一源分流關係,經典闡釋的過程則成為對這一真理的分有過程。在這一解釋序列中,河圖洛書的主乾地位顯然得到了強化。另外,河圖洛書作為真理之源地位的獲得,也和它出現的地理區域有關。自上古始,地處今河南西部的河洛之地,一直被視為聖王所居的天下中心,也是距離神界最近的地方。此處出現的圖籍,當然也會因為河洛在傳統國家地理觀念中佔據的中心位置,價值得到彰顯。據此可以看到,河圖洛書作為解釋原型,它的價值不僅在於儒家經學體系之內,而且也顯現於傳統國家政治和文化地理諸層面。換言之,歷史維度的原發性、認知層面的真理性、價值層面的神聖性和地理層面的中心性,共同使其在中國傳統闡釋學中佔據主位。與此比較,一些區域性或民間性的原始意象,則是次生性的,僅具亞文化的意義。
第三,河圖洛書的解釋史,凸顯了中國傳統闡釋學總是在多元中尋求一體的價值取向。有漢一代,是中國闡釋學河圖洛書模式的奠定期,也是中國歷史上“大一統”觀念獲得理論自覺的時期。這種一統不僅表現為國家的政治統一,同時也表現為文化、學術一體性論述的形成。如前文所言,先秦時期,河圖洛書只不過留下了有限的史料片斷,它在漢代之所以能獲得一統眾經的神聖價值,首先是因為儒家六經被帝王賦予了“獨尊”地位,而六經的“六”要獲得一體性,就有必要找到眾經之首和共同本源,河圖洛書據此充當了六經背後的“一”的角色。所謂文化、學術一統,在此則被見證為河圖洛書對六經統攝地位的確立。以此為背景,漢代經學為擴展這種一體觀念的含攝範圍,運用納甲法,將天乾地支、陰陽五行、五音十二律等傳統非儒家的知識元素,均納入到它的框架之內。這樣,河圖洛書就不僅是眾經之源,而且被放大成了一切文明成果的本源。後世,這一模式又將文學、書法、繪畫、音樂等不斷納入其中,似乎一切人文學科只有進入這一模式才能獲得合法性。據此可以看到,中國傳統闡釋學始終懷抱著一種在多元中尋求一體的價值衝動,它的目標不是在解釋中使對象出現價值多元,而是通過不斷納入和填充的方式,促成一個既成解釋框架的內在飽滿。
第四,河圖洛書以其循環性解釋,維系了中國文明的歷史連續性。從河圖洛書的闡釋史看,這一問題主要表現為對中國文明起源的不斷回溯,但每次回溯又都包含著強烈的現實關切,即通過歷史追憶使中國文明的道統(乃至神統)得到有效維系。比如,西漢作為河圖洛書闡釋模式的確立期,它通過建構這一模式,有效地將自身與中國文明的源頭關聯起來。但是此後,魏晉玄學的辨名析理,使這一傳統弱化;晉唐之間佛教勢力坐大,更使這一述史模式的正當性受到威脅。在這種背景下,中唐至北宋學術界出現複興儒家道統的運動,也就變得可以理解了。從歷史看,北宋對於儒學的複興,佔據源頭及核心位置的依然是《易傳》中的河圖洛書問題。而這一原型圖式之所以被宋儒反覆討論,則無非是因為它充當了儒家道統薪傳的象徵物。至明清之際,關於河圖洛書的討論再起,原因也大體一樣。據此來看,河圖洛書作為中國文明的原始意象,無論是漢儒對這一闡釋模式的奠定,還是後世對它的重新規劃和發掘,均使相關闡釋形成對中國歷史的縱貫。所謂中國文明的歷史連續性,在此則表現為同一個闡釋原型被代代遞交的過程。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河圖洛書作為原型影像,對重新認識中國古典闡釋學的解釋原則和體系架構具有重要價值。但同時必須指出的是,這種追求整體、主從、一元、連續的闡釋方式,明顯具有本質主義傾向,並不符合現代闡釋學追求價值多元的解釋旨趣。同時,在中國歷史上,儒家通過持之以恆的教化活動使人圍繞這一模式形成了廣泛共識,但由此形成的公共闡釋,明顯帶有強烈的強製色彩,說它是一種強製闡釋也不為過。這預示著,本質主義和強製闡釋不僅是西方闡釋學存在的問題,而且中國自身的傳統也不例外。由此來看,建立在公共闡釋基礎上的新型闡釋體系的誕生,其前提不但要批判西方式的話語霸權,而且也要反思民族自身的傳統。換言之,建立當代形態的中國闡釋學體系,雖然要立足於中國傳統,但同時也需要超越這一傳統,它應該屬於在中西之上昭示出的第三條路徑。筆者在本文中通過對“河圖洛書”模式的討論將這一民族傳統揭示出來,目的也並不是強化它的理論正當性,而是要為建立一種更趨公正、合理的中國當代闡釋學,提供一個可資反省的歷史方案。至於它是資源還是負擔,是需要全盤接受、創造性轉換還是另起爐灶,則需要有識者作出明斷。
轉自:上海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