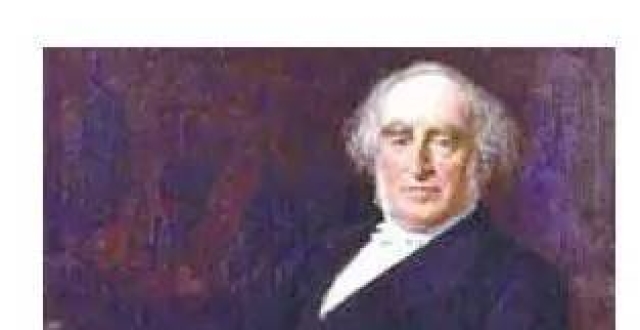作者=仙朵拉
“博物學”一詞本是舶來品,是對英文“Natural History”( 拉丁文Naturalis Historia)的傳統漢譯。從“History”最初的含義“調查、研究、探尋”來看,“Natural History”是指“對所有自然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它是西方近代科學的起源,西方的博物學又可以稱為博物科學。西方學者對博物學的分類研究可以追溯到理性科學的代表人物亞裡士多德,他的相關著作有《動物志》、《動物的器官》、《動物的運動》等。亞裡士多德從事的這種知識分類研究強調收集和鑒別“事實”,然後是對之描述和命名,最後是分類編目。後來,經院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不僅大力推崇新的科學試驗方法,更是把博物學納入了科學認知過程之中,認為博物學是新形式自然哲學的必經之路。培根著名的歸納法分為三個階段,收集足夠多的資料、分類列表、謹慎歸納。其中收集資料是博物學家的工作。之後的皇家學會遵循了培根的思想,保持了博物學的研究傳統。
而在中國,從上古一直到晚清時期,單從知識分類的角度講,沒有和西方一樣的博物學傳統和研究體系,但是中國的“博物”觀念卻是很早就有了。如果翻開現在的漢語詞典,我們會發現“博物”的意思主要有四個:1.通曉眾物。2.指通曉各種事物的人。3.指萬物。4.舊時對動物、植物、礦物、生理等學科的統稱。在中國傳統的認識中,“博物”這一概念主要包含一、三兩項,即“物”與“博”兩個層面。
“物”不僅指自然界的事務,還包括了萬事萬物,甚至包括了人文社科知識,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在中國傳統的博物著作,比如《山海經》、《博物志》中會出現各種神話傳說和歷史事件。而從“博”這個層面來看,中國古代博物學著作撰寫的宗旨就是為了拓展人的視野、增加見識,而並不是像西方博物學一樣純粹為了了解自然事物而對其進行觀察研究。這樣的特質,可以在諸如《詩經》、《爾雅》等著作中略見一斑。因此,中國古代的博物學傳統重點指人而不是物,目的是為人服務。這就決定了中國傳統博物學具有非常明顯的人文性和實用性。
事實上,不僅東西方了解、認知世界的方法論有著天壤之別,對待“博物學”態度也不可同日而語。
17-18世紀,隨著西方啟蒙運動的興起,博物學在當時的歐洲強國英國得到了繁榮和發展。18世紀中葉,瑞典的植物學家林奈的命名和分類體系傳入英國,很快博得了一大批英國博物學家的親睞。與之前備受詬病的博物學研究方法相比,林奈的分類法簡單明確且便於交流和傳播。這既迎合了大航海時代新物種層出不窮對簡單分類法的需求,也迎合了沒有植物學專業背景的大眾獲得一種“高貴文化”的需要,從此他們也可以像貴族和中產階級一樣從事博物學活動了。於是,林奈體系的引入成為了英國全民“博物熱”的催化劑。收集、辨別、賞玩奇花異草一時成為從貴族到平民的一種時尚休活動。而在中國,搞博物研究被當成不務正業,雖然自然資源豐厚,但從來沒有產生過全民博物熱潮。
18-19世紀,東西方“博物學”涇渭分明的時段結束了,隨著英國的殖民擴張,博物學的發展在遠東的殖民國家也得到了強勁的推進。領事、商人、官員和傳教士或因自身興趣,或因利益驅使,紛紛成為大英帝國在華的博物學“特使”,熱衷於探索東方古國的珍花異草。西方博物學家在華期間的科學實作,不僅為中國當時沉悶的博物界帶來了勃勃生機,也引發了不少有意思的文化遭遇事件。《知識帝國》這本書便給我們描述了這樣一段有趣的歷史。
流產的“中國大英博物館”
18世紀中葉之前,英國人少有機會對中國自然界進行調查。18世紀中葉以後,英國逐漸取得歐洲對華貿易的主導地位。隨著貿易量的增加,越來越多的英國人來到了中國。因為英國博物學盛行的緣故,這些人中有不少博物學愛好者,這也正好為科學研究提供了人力與資源。1757年,清政府改變了對洋人的政策,將對外貿易活動限制在廣州一個港口(後被在華洋人稱為“舊廣州時期”),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葉。
18世紀晚期,來華的博物學研究者大部分都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成員。他們收集動植物標本和相關科學資料時非常依賴於與中國人之間的貿易往來。那時,東印度公司廣州分行和其他分支機構一樣,內部風行的是一種吃喝玩樂的氣氛,而非認真追求學術的風氣,但是也不乏像斯當東這樣既年輕又受過良好教育的英國紳士。
19世紀20年代末,廣州分行成員開始醞釀成立一個博物館,並取名“中國大英博物館”。

《知識帝國》
(美)范發迪/著
袁劍/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年1月
英國人興建這座博物館的初衷有二:
首先,作為在華博物學研究的輔助機構和進行自認為的“文化教化使命”。
19世紀,園藝和博物學在英國本土蔚然成風,而中國富饒的自然資源自然稱為英國博物學工作者們收集標本和進行科學研究的後花園。廣州分行的成員們認識到,必須得成立一個當地的科學機構來輔助自己的博物學研究。同時,如果能在中國成立一個博物館,讓中國人親眼見識到歐洲人研究博物學的動機和成果,說不定能激起中國人對西方博物學的興趣。
其次,作為中英商貿的展示視窗,促進貿易。
這些英國人認為,商貿與科學密不可分,提出“商貿活動是現代科學發現的先驅。”所以這座博物館就不能隻展示一排排的動植物標本和礦石,還有陳列中國哪些有 “競爭力”的手工藝品和其它製造品的樣本。這樣一來,“中國大英博物館”就具備了既可以滿足科研需求,又能對貿易有所助益的雙重性質,何樂而不為呢?
不過遺憾的是,廣州分行因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終止而解散,因此這項巨集偉的“中國大英帝國博物館”計劃最終流產了。
即便項目最終還是失敗了,但最初的倡導者們一直堅持建館計劃的基礎是英國博物學者對文明進步的理解,這代表了當時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英國精英、貴族們的觀點。商業、貿易、有用的知識和公平競爭正是成熟文明的基石。
廣州畫師筆下的“西洋博物畫”
如果說“中國大英博物館”計劃並未在當時的中國留下什麽痕跡的話,那麽“西洋博物畫”技法的傳入則著實為中西文化的碰撞抹上了絢麗的一筆。
由於當時的英國博物學家們只被允許在一定區域內活動,所以進入中國內地采集標本的事就不得不靠中國人來完成。用這種方法得到的標本少而又少,也很難在遠洋航行中存活,博物學家們只得另辟蹊徑解決這個難題。
18世紀末時,歐洲已經發展了一套成熟的標準化詞語體系來描述標本可以觀察到的特徵。這套體系的優勢是詞語精確到可以讓受過訓練的科學工作者通過這些術語對標本進行描述,彼此間進行有效地溝通。然而由於缺乏教育、訓練和實踐,對於那些受雇於英國人的中國采集者來說,想掌握它卻是十分困難的。於是在華的英國博物學家們想到了使用圖畫來替代語言體系描繪標本。這些在華博物學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約翰.裡夫斯。他主張利用廣州的洋畫行業,雇傭當地畫師來繪製標本,即博物畫。
其實,類似的合作在18-19世紀的印度也很已頗為常見。當時許多印度畫師已經根據英國雇主的要求調整了繪畫的方法和風格,繪製博物畫。在廣州,這種合作因為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經過了十分有趣的碰撞,最終使中國畫師的博物畫形成了集科學和藝術價值於一身,既精確又具觀賞性的獨特風格。
中國傳統典籍中的植物和動物畫,注重寫意,往往比例不對,風格上抽象大於具象。《本草綱目》式的植物畫強調突出有用的、局部和重點的部分,比例嚴重失真,完全滿足不了這些博物學家提出的將植物加以完整、客觀描繪的要求。對英國博物學家們而言,除了少數能夠剝製並長期保存的標本,還有很多無法長期保存、原樣帶走的動植物標本,需要畫下來才有後續價值。這就要求博物畫和繪製必須符合這種西方博物學實作的特點,於是中國的西洋畫師作坊隨之產生。
西方人對博物畫的要求和中國畫師原來受過的訓練截然不同,致使英國博物學家的要求對中國畫師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即使在具體的要求之下,畫師在繪製過程中仍會有一些無法改掉的習慣。比如中國畫師在畫鶴這樣帶有典型中國文化意涵的影像時,總是情不自禁地將鶴的一隻腳藏起來,讓鶴的眼睛平靜地看著前方;在畫梅花的時候,總是著力表現出梅花的風骨,而不是按照實物完全照搬。而西方博物畫要求精確的反應動植物的生物特性,看重的是忠實地再現不能被帶到英國本土的那些奇花異草、飛禽走獸的原貌。
最終,兩種文明在博物學繪畫這樣具體的實作中經過不斷地混合、調和與雜交,使得中國畫師筆下的博物圖鑒日臻完善,成為了19世紀早期英國人獲取中國博物知識的重要來源,為遠在英國的博物學家們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自然科學數據。
傳教士漢學家與博物學
由於英國人人在華活動區域的受限以及政治現實和制度的束縛,許多英國博物學家遙望著中國地大物博的內地卻求入無門,只得從漢學著作中打開一扇窗,窺視廣袤的自然博物資源。19世紀後半期,英國人在華的學研究逐漸從日益專業化的漢學中汲取力量。
漢學與博物學的聯繫在19世紀前就以開始了。耶穌會士們自16世紀起進入中國傳教,在近代早期向歐洲傳播有關中國的資訊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其中就包括博物學研究。當時,極少有歐洲人懂中文,幾乎所有的歐洲學者們都不得不從耶穌會士的著作和記錄中尋求幫助。
耶穌會,作為羅馬教廷的“精兵”,是一個全球性的集權製修會。耶穌會自16世紀創立時起,就開始向遠東國家派遣傳教士。耶穌會士們通常經過15年左右的學習和培訓,在進入他國傳教時要先學習該國語言、文化、風俗,為迅速適應當地社會和進行傳教做準備。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很多傳教士都成為了著名的漢學家。無獨有偶,這些教會等非科學機構也造就了博物學方面的研究者,並為搜集和傳遞科學資訊提供了交流網絡。
法國耶穌會士韓國英是傳教士中醉心研究博物學的代表人物。他18世紀中期後來華,曾擔任清朝宮廷機械師、園藝師等職。他與當時的法國國務大臣的貝爾坦私交甚篤,曾寄給貝爾坦很多有關中國國情的論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貝爾坦的中國觀。韓國英博學而謙遜,論著頗豐,對中國語文和歷史有濃厚興趣,研究過中國天文學、地質學、化學與動物學,尤其關注植物學,算得上是傳教士漢學家中“雜家”的代表。
韓國英,和另兩位耶穌會士巴多明、湯執中,一直持續地向歐洲寄送有關中國植物的書簡及資訊。他在傳教地進行田野調查和標本采樣,撰寫植物圖譜類書籍,襄助法國了解中國物種情況。此外,他和另一位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共同編纂了18世紀歐洲漢學巨著《中國雜纂》。由他本人撰寫或翻譯的文章多達63篇,題材涉及博物、社會、歷史、政治、語言、文學、醫學等,其中博物類文章佔了三分之二多。
韓國英為代表的17、18世紀的耶穌會士為中國植物知識的西傳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兼具漢學家與博物學家的雙重身份,擁有介於中西治學之間的獨特視野,將注意力從傳統的中國歷史文化轉向博物研究,對中國的自然科學進行觀察、記錄與分析。他們對中國動植物的調查常常會借助中西語文學、地理學和歷史學方面的研究,同時運用漢學家的學識加以分析、比較和詮釋文獻,因此開創出了傳教士漢學研究的一個獨特論述領域:漢學博物學。通過這種跨學科和跨文化的知識傳譯,進一步打開了歐洲人的眼界,成為當時和後來歐洲本土科學家探索遠東自然科學知識的豐富源泉。
雖然本書的重點並不在研究中國博物學演變的歷史,不過我們從種種史料中不難看出,其實“近現代中國博物學”是在近現代“西學東漸”背景中產生的,是融合了西方博物學與中國傳統博物學的一門學問。而回顧18-19世紀晚清歷史,西方國家在當時之所以擁有霸權,靠的並不止是武力技術優勢,更源於一個強大的“知識帝國”在那裡,知識被充分整合起來,形成了人人愛知識、求知識的局面,知識聚累已成為了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現代科技崛起,如今博物學已衰落,但歐洲各國的博物文化依然保存。一有閑暇,人們便回到大自然中,在觀察、發現、采集中獲取樂趣,這也成為歐洲科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樣一段很容易被忽略的歷史實在發人深思。我們不禁要思考,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該如何構建我們自己的知識帝國?
經濟觀察報書評
eeo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