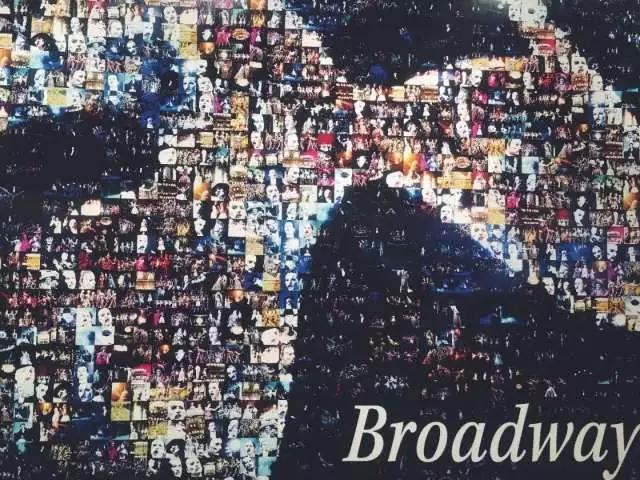《飛越瘋人院》劇照。攝影/ 郝晨光
精神病人比利在舞台上跳了樓,“死”在觀眾面前。精神病院的秩序崩塌,故事抵達高潮。這是中國版話劇《飛越瘋人院》第二輪演出時的一幕,死亡被直接地呈現。
其實,中國觀眾對於《飛越瘋人院》並不陌生,更多的人已通過電影知道了這個故事:麥克墨菲為了逃避監獄裡的強製勞動,裝作精神異常被送進了精神病院,他的到來,給死氣沉沉的精神病院帶來了劇烈的衝擊。他挑戰嚴格的管理制度,開始計劃著帶領一眾病人逃離瘋人院。最終,這個帶領大家奔赴自由的人卻被切除了大腦額葉,最終被戲劇性地殺死。
1975年,米洛斯·福爾曼導演的電影《飛越瘋人院》拿下了5項奧斯卡金像獎。它的原作則是作家肯·克西於1962年創作的長篇小說《飛越布谷鳥巢》。1963年,小說被搬上了百老匯的舞台,此後連演千場。2018年,80後話劇導演佟欣雨第一次把它帶到中國的劇場裡。如今,它又一次和觀眾見面。
“酋長”視角
2015年,佟欣雨翻譯製作了澳大利亞戲劇《燃燒的瘋人院》之後,獲得當年小劇場票房冠軍,製作人洛奇豆子建議他,可以把精神疾病題材做成一個系列。他們很自然地想到了電影《飛越瘋人院》,中國還沒有人把它做成過話劇。
在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動蕩混亂,年輕人迷茫、反叛,毒品和搖滾樂成為了他們的精神出口,嬉皮士運動為那個時代做了最重要的注腳。原著長篇小說《飛越布谷鳥巢》就基於那個時代,被視為嬉皮時代反文化運動的經典,故事來自於作者自己在醫院參與藥品試驗項目的經歷。
1963年,音樂劇《我,堂·吉訶德》的詞作者Dale Wasserman把小說改編成話劇。那一年,它在百老匯的演出紀錄是82場。到了1971年,它開始百老匯之外的巡演,三年半內演了1025場。2001年,再次回到百老匯複排,獲得托尼獎最佳複排話劇獎。
2017年,佟欣雨找到Dale Wasserman的版權代理團隊,想購買版權,對方團隊提出需要先看佟欣雨翻譯的劇本。佟欣雨的改編基本遵照原著進行,把製作的劇本交給對方之後,對方找人再次翻譯成英文來看,最終得到認可。
佟欣雨喜歡這個戲的原因在於,作品讓人看到跟自己對抗的勇氣。如今,中國人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裡遭遇迷茫,某種程度上,中國觀眾可以從這個故事中感受到某些特殊的感受。
對於中國觀眾而言,他們更熟悉的是電影版的《飛越瘋人院》。電影中,精神病人“酋長”成為一個讓麥克墨菲走向死亡,而又通過麥克墨菲的死亡重新意識到和獲得自由的襯托者。佟欣雨還原小說的呈現方式,酋長是主要的視角,以他的獨白串聯整場故事。
舞台上,精神病院是簡單的北歐風格布景,區別於電影中破敗的教堂改造而來的病院場景。白天黑夜在舞台上通過燈光營造和轉換,一切都被壓縮在一個空間裡。
31歲沒有性經驗的口吃病人比利的死亡,是這次這個新版本著重加強的改編點。這個活在母親強大控制欲之下的男子,被生活窒息而無力反抗。麥克墨菲給他找來姑娘,讓他約會。但當護士知道後,威脅比利要告訴他的媽媽,導致他最終選擇了自盡。
相比於去年的首演,比利的死亡方式被更加直接地呈現。這個轉折之後,全劇走向尾聲。麥克墨菲被強製做了手術之後,躺在病床上,失去了所有反抗能力。高大的“酋長”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用被子捂死了麥克墨菲,而後用魁梧的身軀撞開了精神病院的“屋頂”,掙脫有形的束縛和無形的權威。
普世版本
去年的首輪演出之後,觀眾的反饋是,話劇神還原了電影,但是問題在於中國演員卻操著一口翻譯腔。這是佟欣雨故意為之,他並不想把這個故事變成一個中國故事,他想做的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版本,能夠被各種文化背景下的觀眾所接受。
在翻譯的過程中,佟欣雨覺得語言是最大的難點。作品寫於60年代的美國,其中很多台詞中混雜著美國南部的俚語。而這些遣詞上的雙關使用,是文本最大的特色,保留到中國舞台上非常考驗技術。
佟欣雨並非科班出身,他2012年畢業於浙大竺可楨學院統計學專業,話劇算是愛好,而後通過自學成為從業者。這讓他在導演作品時,有更加切近真實生活的本能。在物色演員時,佟欣雨除了對形象氣質有要求之外,還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寫角色小傳分析。電影版本中的酋長扮演者威爾·山姆普遜,本是電影拍攝地附近的一名公園護林員,身高和形象驚人地符合酋長的角色。而佟欣雨在首輪挑中的“酋長”演員特尼格日是蒙古人,一米九的大個兒,玩兒搖滾,留著長頭髮,也是完美地契合了角色。
主角麥克墨菲的扮演者馬仁傑是出生於1992年的演員。來面試的時候剃了光頭,蓄著鬍子,但生活中並不狂野,佟欣雨知道他喜歡打拳和玩摩托,覺得他內心的某些狀態是符合角色需求的。馬仁傑和佟欣雨在分析角色時達成共識,麥克墨菲是美國垮掉一代的典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從小就混跡在各大酒吧,但又絕不是一個壞人,也不是一個勇敢的人,但必須把自己包裝成那種形象,才能在魚龍混雜的社會生存下來。
去年首演之後,他們對於這個主角的展現不太滿意,覺得有點將他塑造成了英雄,而這顯然是不準確的,今年的複排中,他們做出了更細致的改變。
其他角色也都如此,並不是非黑即白,並不是絕對的正義與邪惡的對照,而是某種更深層的、更複雜的原因讓一個個角色成為了他們最後的樣子,這一切都在新版本中被謹慎地矯正。
在佟欣雨看來,“瘋子”是少數融入不進大集體而被壓製的異類的隱喻。他對於這樣的主題著迷。對於《飛越瘋人院》而言,佟欣雨最終選擇的落點還是在於每個人物對自我的一種認知,“討論的並不是某個政體下的壓迫,我們討論的是個人問題,個人對自己的對抗,能不能戰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