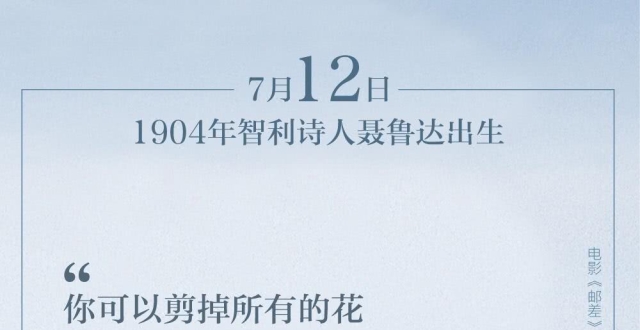講起聶魯達,不能不提《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這本1924年夏天出版的少作(當時聶魯達還不到20歲)立刻為聶魯達贏得最初的聲譽,此後在很多年裡,這本詩集的每一個外文譯本都複製了它在智利的成功,到1961年,這本薄薄的詩集已經在全球銷售了一百萬冊,到今天,這本詩集的全球銷量早已過億。其中的幾首詩,似乎已成為“愛情”這個詞固有屬性的一部分,它銘刻在全世界讀者的頭腦裡,嘴唇上。比如第十五首的開頭:“我喜歡你沉默,仿佛你已不在”,以及第二十首的首句:“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句”。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吟唱對象主要是聶魯達深愛著的兩位少女——阿貝提娜和特蕾莎,前者是聶魯達一位詩友的妹妹,後者是聶魯達老家特木科的一位選美冠軍,儘管兩位少女最初也都給予聶魯達熱情的回饋,但是由於兩位少女父母的反對(嫌棄聶魯達卑微的家庭出身),兩段戀情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終結。《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聚焦於受挫的愛情絕望、難熬的一面,替深陷情網的男女道出心聲。

聶魯達是一位早慧的天才,他十四歲即發表詩作,他最初的幾部詩集——如《黃昏》《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熱情的投石手》《大地上的居所》——和許多傑出詩人的早期階段一樣,主要是對個人情緒和感受的發掘,是一種偏於內向的詩作,當然,在這些詩作中聶魯達已經顯露了卓越的才華,沿著這條道路,他也會成為一名優秀詩人,但是可能不會像最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位複雜廣博的聶魯達那麽重要。
上世紀30年代中期,聶魯達的詩歌有一次重要的蛻變,那時他三十歲左右,寫作生涯已持續了十幾年,積攢了足夠的經驗。另一方面,1934年聶魯達就任智利駐巴塞隆納領事,兩年之後的夏天,西班牙內戰爆發,1936年8月中旬,聶魯達摯友、西班牙詩人洛爾迦在家鄉格納拉達被右翼的長槍黨徒虐殺,這件事決定性地將聶魯達從痛苦的個人苦悶推向左翼,推向一種基於社會使命的寫作。在一種激憤情緒中,聶魯達開始寫作西班牙內戰犧牲者的讚美詩——《我心中的西班牙》,這本充滿熱情的詩集的第一首詩是《犧牲民兵之母的歌謠》,這是聶魯達清晰表明他忠於社會和政治正義的第一首詩。這首詩作於1936年9月,僅僅在洛爾迦死後幾個星期。
今天我們看《我心中的西班牙》這本詩集,當然可以感受到作者真誠、激憤的情緒,但是對於聶魯達初次使用的高亢音調,我們也能感受到某種刺耳。是啊,一位習慣了低語和情話的詩人,突然讓他扭頭向著大眾放聲歌唱,其中的困難可想而知。但是被社會正義和政治熱情點燃的篝火持續燃燒,聶魯達此前十幾年個人化的寫作經驗,也逐漸順利對接到社會、人群和原野,他逐漸適應了用高亢的音調發聲,它們不再刺耳,反而變得像優秀的男高音歌唱家那般美妙。1950年,聶魯達傾向於社會使命的抗鼎之作《詩歌總集》正式完成,這部史詩般的作品,毫無爭議地成為了聶魯達最優秀的詩作,它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一場出色的恢弘的交響樂,總要勝過一曲小提琴手的低語。
從最早寫於1938年的《獻給馬波喬河的冬日頌歌》,到1950年最後一章完稿,聶魯達用生命中精力最旺盛、閱歷最豐富、觀念最成熟的12年來寫作這本厚達六百多頁的詩集。和許多傑作一樣,《詩歌總集》是一部生長中的開放的作品,起初聶魯達只是想寫一部《智利的詩歌總集》,但隨著聶魯達對墨西哥、危地馬拉、秘魯等拉丁美洲國家的廣泛遊歷,《詩歌總集》最終變成一部有關整個拉丁美洲的史詩。
1943年10月,聶魯達遊覽了高居安第斯山上的著名的印加帝國堡壘城市馬丘比丘,這是一次至關重要的遊歷,許多人認為這次與古代文明的接觸永久性地改變了聶魯達的視野,正如評論家羅伯特·普林·彌爾所指出的:“當聶魯達真真切切到達了馬丘比丘,它的高度表明了它是一個使得一切其他事物變得富有意義的地方,包括他自己的大陸。”幾年後,聶魯達寫道:
看了馬丘比丘的廢墟之後,古代的傳奇文化似乎是由紙板做成。……我理解,如果我們踩在同一片承前啟後的土地上,我們與那些美洲社會的崇高努力有著某種關聯,我們就不能忽略它們,我們的無知或者沉默就不僅僅是一種犯罪,而且是一種失敗的延續。我們貴族式的世界大同思想不斷把我們引向最遙遠的人們的過去,卻讓我們對自己的珍寶視而不見……我回想著古代的美洲人。我看到他的古代鬥爭和當今的鬥爭交織在一起。正是在那裡,我要創作一個美洲《詩歌總集》的想法的種子開始萌芽,某種編年史……如今我從馬丘比丘的高峰上看到了整個美洲。那就是我新構思的第一首詩的題目。
一種罕見的豪邁之感由此貫穿整部《詩歌總集》,通過這部詩集的寫作,聶魯達終於拋棄早期作品內向的痛苦感,那種強烈的孤絕,在這本書中,通過對他者之愛,他首次獲得了一種樂觀主義熱望,渴望革新,渴望秩序,普林·彌爾正確地把這稱作聶魯達的“個人宇宙學”。當我們讀到《馬丘比丘之巔》短促的結句,我們可以清晰體會到激情完全融化於語言的那種歡樂:
給我沉默,給我水,給我希望。
給我鬥爭,給我鐵,給我火山。
支持我的血脈,支持我的嘴。
為我的語言,為我的血,說話。
聶魯達在自傳中坦言,遊歷馬丘比丘高地給整部《詩歌總集》帶來了明確又恢弘的主題,在自傳中他沒有明說的,是一種新風格的準備。顯然,過去那種低語、敏感的詩風已經無力駕馭如此宏大的主題。聶魯達從來不是遮遮掩掩的詩人,關於《詩歌總集》的新風格,在長詩《伐木者醒來》中,他明確給出了答案:
沃爾特·惠特曼,把你的聲音給我,
把你埋在土裡的胸懷的重量,
把你面容的莊嚴的銀須給我,
讓我歌唱這些重新開始的建設!
整部《詩歌總集》大概也就此處提到了惠特曼,卻至關重要,聶魯達正是用惠特曼的語言方式——“你的聲音”——歌頌新的事物。當聶魯達在馬丘比丘之巔俯瞰整個美洲時,惠特曼早在一百年前就寫過《向世界致敬》《轉動著的大地之歌》《向印度航行》《哥倫布的祈禱》等詩作。《草葉集》裡某種放眼世界的宇宙眼光,某種豪邁、英勇的氣質,某種粗糲不事雕琢的語言風格,都被聶魯達繼承下來,並在歌頌自己的美洲時獲得了一種更圓融高亢的音調。1945年,聶魯達在位於海邊的黑島居所開始寫作《馬丘比丘之巔》,居所書房的牆上懸掛了一張惠特曼的照片,一次,聶魯達請來乾活的木匠指著惠特曼的照片問:“那是您爺爺嗎?”聶魯達回答:“是的。”1972年,聶魯達去世前一年,他訪問美國,在紀念筆會美國中心成立十五周年的晚宴上,聶魯達終於有機會在美國向惠特曼表達敬意:
至於我自己,如今我是一個幾乎七十歲的人。在我發現沃爾特·惠特曼——我的第一個債主的時候,我才十五歲。今天,我站在這裡,在你們中間,仍然虧欠著那幫我生活下去的巨額債務。偉大有很多層面,但我,一個用西班牙語寫作的詩人,從惠特曼那裡學到的比從塞萬提斯那裡學到的更多。在惠特曼的詩中,無知的人並不卑微,而人類的狀況也從未遭到嘲笑。

在此,我們不免要比較一下惠特曼和聶魯達的高下了,儘管《草葉集》和《詩歌總集》都堪稱史詩般的傑作。在《詩歌總集》中,我們可以看到聶魯達對於科爾特斯、阿爾瓦拉多、巴爾博亞、克薩達、巴爾迪維亞等美洲早期征服者的憎惡,也可以看到聶魯達對當時智利當權者維德拉的鞭笞和譏諷。與此相應,《詩歌總集》第八章《名叫胡安的土地》,以戲劇獨白的方式歌頌了美洲普通民眾,包括托克比利亞的鐵鏟工克里斯托巴爾·米蘭達、種地的農民赫蘇斯·古蒂埃雷斯、塔爾卡瓦諾的鞋匠奧萊加裡奧·塞布爾維達、伊基克的水手阿爾圖羅·卡裡昂、哥倫比亞的漁夫安托尼諾·貝爾納萊斯、玻利維亞的礦工何塞·克魯斯·阿卻卻利亞等十餘名美洲普通勞動者,顯露出聶魯達愛憎分明真性情的一面。但在《草葉集》中你很難找到憎恨的情緒,頂多只能找到被愛的洪流融化之後的憎恨的遺跡。也就是說,整部《草葉集》沒有給諷刺留下立錐之地,這大概是後者更為傑出的一個證明。
平心而論,《詩歌總集》某些章節,如《馬丘比丘之巔》《智利的詩歌總集》,在抽象的崇高方面達到了《草葉集》的高度,但是在《征服者》《解放者》《名叫胡安的土地》等章節中,形式和內容並沒有取得完全的均衡,我們可以感到聶魯達在自己選定的主題上奮力開掘前進——一種節奏“咯吱”作響的奮力前行,不過話說回來,這種不完美的感覺大概也是偉大作品的一個標誌吧。
當然,《草葉集》對於《詩歌總集》只是一種風格上的影響和啟發,後者作為拉美史詩自有其獨立的地位和重要性。《詩歌總集》沒有《草葉集》那種更深遠的世界性眼光,沒有那種包容一切的悲憫胸懷,但是,《詩歌總集》裡有更具體的人的命運,在具體而微的欣喜、悲傷和憤怒中,聶魯達將普通人的命運和宏大的背景結合得更自然、緊密。第一章《大地上的燈》開宗明義:
我來到這裡,是為了歌唱歷史。
從野牛的寧靜,直到
大地盡頭被衝擊的沙灘。
在這章中,聶魯達以粗獷的筆觸概括性地歌唱了拉丁美洲的植物、獸類、礦藏、河流以及生活在這塊大陸上的人類。從一開始,聶魯達就展示了自己卓越的語言能力,為整部詩集的斑斕色彩奠定了基礎:
在怒潮奔騰的大海盡頭,
在海洋的雨中,
升起了信天翁的翅膀,
好似兩堆白鹽,
在陣陣的浪潮之間,
以它寬闊的等級,
建立起孤寂的秩序。
明確以人類歷史作為主題的長詩,除了《詩歌總集》,還有聶魯達瞧不上的納粹支持者龐德的《詩章》,但《詩章》關注的主要是歐洲乃至整個人類的文明史,在龐德雄心勃勃的筆下充斥著維吉爾、但丁、維庸、孔子這樣的文化人物,龐德從這些文化人物的視角,探討人類歷史上諸多他關心的問題。而《詩歌總集》關注的拉丁美洲歷史基本上是一種蠻荒狀態中的歷史,從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主要是科爾特斯、巴爾博亞這樣的西班牙殖民者以及更多籍籍無名的普通民眾。聶魯達不可能像龐德那樣便利地借助歷史文化名人獲得文化積澱的支撐,他只能用自己的筆觸賦予這片土地初次述說的能力,簡言之,就是賦予這片沉寂的土地以文化生命。這是一次艱難的文化拓荒行動。
《詩歌總集》第二章即是備受讚譽的名作《馬丘比丘之巔》,聶魯達從第一章《大地上的燈》的概述過渡到對古印加帝國著名城堡的具體描寫。親身遊歷此地,安第斯山巔曾經繁榮的都城,曾經熙攘然而永遠消失的人群,人類曾有過的抗爭、奮鬥似乎被莊嚴的死亡瞬間弭平……所有這些,都為聶魯達在接下來的詩篇中反覆歌唱的現實抗爭設置了強有力的背景。《馬丘比丘之巔》自身也憑借其超拔的視野成為聶魯達最優秀的單篇詩作,而且在《詩歌總集》開端部分即為整部詩集樹立了詩藝的高標。
第三章《征服者》、第四章《解放者》引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拉丁美洲土著人民,以及後者抗擊殖民者,努力擺脫被殖民命運的主題。第五章《背叛的沙子》則以詩的形式譴責了近兩百年來奴役各拉美國家人民的獨裁者,因為是對自己人民的奴役,因而題目中出現了“背叛”的字樣。和這三章所起作用相似的還有第八章《名叫胡安的土地》,十幾個被奴役被壓迫的拉丁美洲普通民眾的群像。在這四章中,聶魯達描寫了數十個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人物,敘述的口吻逐漸替代了聶魯達擅長的抒情詩風,敘述中不自覺地對於自然意象的倚重(一種可以理解的寫作慣性),也削弱了優秀的敘事詩可能擁有的緊湊節奏和力度。這些都使得這四章成為《詩歌總集》中相對較弱的部分,但是從全局看,這四章也不可或缺,它們為《詩歌總集》提供了堅實肥沃的土壤,使得聶魯達所擅長的抒情之樹得以在其中瘋狂生長。換句話說,它們是一首複雜的交響樂中必須具備的低音段落,襯托出其他章節高亢的美妙樂音,誰又能在600頁的篇幅中始終保持高八度音調呢?
在第六章《亞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呼喚你的名字》、第七章《智利的詩歌總集》、第九章《伐木者醒來》中,聶魯達恢復使用抒情詩風,他盡情讚頌拉丁美洲的氣候、一朵玫瑰、一隻蝴蝶的生與死、海上的工人、鞍匠、陶工、阿塔卡馬的礦藏、佩烏莫樹、契爾更鳥、植物園以及雨中的騎士和智利的海。回到自然意象就像魚兒回到水中,聶魯達又恢復了嫻熟的身手,《智利的詩歌總集》最後三首詩《雨中的騎士》《智利的海》《獻給馬波喬河的冬日頌歌》都堪稱《詩歌總集》中的精品。
在寫作《詩歌總集》過程中,1948年年初聶魯達終於和日益右傾的維德拉政府決裂,1月13日在智利議會上聶魯達公開譴責維德拉政府:“我是一個受迫害的人,並且正遭受迫害。一個剛剛開始的暴政必須迫害那些捍衛自由的人們。”從那一天起的一年多時間裡,聶魯達在自己國家成為東躲西藏的逃亡者,經常在午夜,聶魯達在共產黨小組的幫助下從一個秘密藏身之所轉移到另一個,在有跡象表明警察正獲得他的蛛絲馬跡之後。《詩歌總集》第十章《逃亡者》正是對這段生涯的描述,並為整部詩集增添了極為戲劇性的一幕。《逃亡者》的十幾個片段顯然是聶魯達在十幾個不同的藏身之所寫下的急就章,聶魯達無法在那樣的情境下仔細斟酌用詞,結果反倒保留了一種珍貴的倉促印跡:
向大家,向一切,
向所有我不認識的人,向從來
沒有聽過我名字的人,
向生活在我們漫長的河邊的人,
在火山腳下的人,在銅的硫磺
陰影中的人,向漁夫,向農民,
向玻璃似的閃光的大湖
岸邊的藍色印第安人,
向這時刻正在詢問
正在用古老的手釘皮子的鞋匠,
向你,你並不知道而等待我的人,我要說:
我屬於你們,認識你們,歌唱你們。
另一方面,逃亡生涯也使聶魯達被迫杜絕他熱衷的社交生活,得以專注地推進這部已經寫了十年之久的拉丁美洲史詩,而逃亡本身也刺激了聶魯達的靈感。據幫助聶魯達逃亡的共產黨小組負責人記載,詩人在和他們聊天時,突然會站起來慌忙溜走,不做任何解釋,“就好像詩句正在逃亡或者從他身上掉下來,他待在隔壁房間。很快我們聽到他那台便攜式打字機鍵盤的敲擊聲,那是他在極速且無情地擊鍵”。這真是老天的完美安排,使聶魯達有一年時間專注於《詩歌總集》的殺青工作,而逃亡的緊張孤寂也賦予《詩歌總集》的鬥爭主題一種耀眼的光亮。1949年2月下旬,聶魯達取道智利南方安第斯山的秘密小徑離開智利,而此時卷帙浩繁的《詩歌總集》也已接近完成。
第十二章《歌的河流》是聶魯達獻給友人——西爾瓦、阿爾維蒂、卡巴略、雷布埃爾塔斯、埃爾南德斯——的頌歌,這組詩使聶魯達在之前各章中反覆歌頌的兄弟之情有了具體的落腳點,而其個人化的傾訴則顯得尤為真摯感人。第十三章《新年大合唱:獻給我黑暗中的祖國》則是對維德拉政府暴政下受迫害人民的祝福,也是在道義上對他們的聲援。其中《皮薩瓜的人們》尤為引人注目,那是一首獻給被囚禁在皮薩瓜集中營的六百多名左翼人士的頌歌,在1948年初的智利議會上,聶魯達曾經逐個念出他們的名字。
整部《詩歌總集》以自傳性的章節《我是》作結,在這一章中,聶魯達回顧了自己的前半生,回顧了自己的故鄉、父親、最初的愛情、在聖地亞哥窮困潦倒的遊學生涯、在遙遠歐洲的領事生涯、在西班牙所經歷的殘酷內戰,甚至寫到了想象中的死亡和遺囑:
這本書就在這裡結束;在這裡
我留下我的《詩歌總集》;它是在
迫害中寫成,在我的祖國
地下的羽翼保護下唱出。
《詩歌總集》600頁的篇幅超過不少詩人一生的創作總量,十年多的創作時間也使聶魯達得以從容寫作和修剪自己這部雄心勃勃的巨著,而整部詩集15個章節又保證每行詩可以圍繞較小的主題展開,這使《詩歌總集》避免了許多長詩通常會有的松垮和拖拉。總體而言,這是一部張弛有度的詩集:史詩的雄心和細如發絲的細節保持了一種平衡,詩集主體的作者角度抒情和眾多人物的獨白構成另一種平衡,而詩集的抗爭主題和詩人內在的敏感亦構成一種隱蔽的平衡。儘管單獨看,詩集中某些詩歌更為完整和有力,但從全局看,每一部分都不可或缺,都是壘砌整部詩集的“馬丘比丘之巔”的重要磚石。

也許正是因為想著《詩歌總集》,聶魯達在自傳中驕傲地總結自己的寫作:“我的詩和我的生活宛如一條美洲大河,又如發源於南方隱秘山巒深處的一條智利湍流,浩浩蕩蕩的河水持續不斷地流向海口。我的詩絕不排斥其豐沛水流所攜帶的任何東西:它接受激情,展現神秘,衝開進入人民心靈的通道。”
聶魯達後來還寫過諸如《葡萄與風》《打倒尼克松,讚頌智利革命》這樣的政治抒情詩,但都遠遠難以達到《詩歌總集》的水準。那兩本詩集和政治過於貼近,犧牲了語言和詩本身的獨立性,那種從政治現實中躍身而起的抽象能力,聶魯達也只是在《詩歌總集》中幸運地擁有過。後來聶魯達還寫過火熱的愛情詩集《船長的詩》和《愛情詩一百首》,它們都保持了相當高的水準,因為愛情本身就是永恆的主題,它和現實保持著天然的距離。但最好的詩總是從現實中生長出來,又得以從現實遮天蔽日的籠罩中逃離的詩篇,因此《詩歌總集》當然是聶魯達最好的詩,也無可爭議是二十世紀詩人獻給世界的最佳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