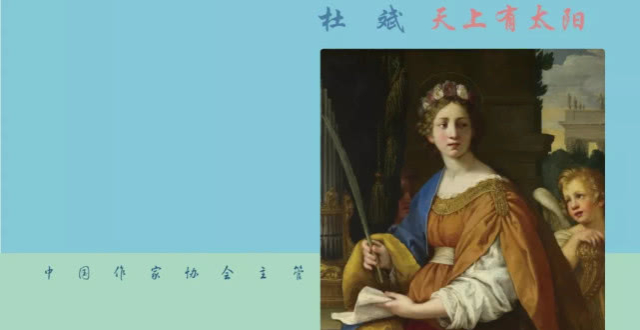★
···創刊於1949年6月···
··新中國文藝第一刊··
★
主持人語|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高校人事改革和教學創新的不斷深化,部分大學也陸續開展了一系列的人才引進工作。在這當中,知名作家進校園最是引人矚目。從複旦大學引進王安憶,到南京大學成立畢飛宇工作室,再到北京師范大學以莫言為核心,逐步建立作家駐校的常規制度等等,當代作家轉型為大學教師,繼而以授課的形式去推動文學批評的大眾化運動,業已成為了近二十年來發生於中國文壇的一個重要事件。毫無疑問,這一現象對於改變當下文學批評的話語格局顯然是意義非凡。
與學院派批評相比,很多駐校作家的文學批評個性十足、靈動多變,充滿了創造的活力:像王安憶溫婉細膩的心靈解讀,馬原天馬行空的藝術想象,以及畢飛宇綿密有序的邏輯推理等等,都讓這些曾以小說名世的批評家,成為了青年人眼中的文藝明星。那麽,對於這樣一場批評的變革,我們究竟該怎樣看待?
本期邀請的三位作者中,於可訓先生既是著名的文學史家,也是近年來聲名鵲起的小說家,因此他對作家進校園問題的思考,就有了一種天然的說服力。而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裴亮博士,則秉承文史兼治的學術理念,周密梳理了作家駐校製的前世今生。至於年輕的呂興博士,更是以一位青年學子的身份,詳述了作家批評給當下文學教育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六年前,我在《長江文藝》上說過一回作家進大學的事,這回再說,就是再作馮婦,雖然也可能“為士者笑之”,但關於作家進大學,又確有一些值得再說之事,既然如此,也就顧不得那麽多了。
六年前,我說這事兒的時候,作家進大學雖然早已有之,但尚屬少數個案,似乎還不那麽普遍。這幾年,卻大有與時俱增之勢。究其原因,從大學一方面說,不聘請一些作家駐校,似乎跟不上潮流,顯不出等級,也讓人覺得不重視人文教育,理工科大學尤甚。就作家一方面說,既然有許多人已成為駐校作家,自己沒有這個名頭,也覺得有失身份,沒有面子。這當然都是一些很世俗的想法,甚至難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學校和作家也許有更崇高的念頭,但在這念頭尚未說出之前,我倒想說說我個人的一些很卑微的想法。
首先我想說的是,現當代文學史上,作家的種種“進”和“下”。中國人說話講究,就拿這作家的空間位移來說吧,但凡此一空間與彼一空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則以“進”言之,低者,自然就得說“下”,所以到大學去當駐校作家,可以說“進”,倘若像半個世紀以前那樣,到工廠、農村、連隊去“深入生活”,那就只能說“下車間”“下農村”“下連隊”了。或者說,也有說“上”的吧,有倒是有,但那是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是說作家。作家永遠是自認或被認居人之上的,只會“下”無須“上”,現在總算是平移了,說來也是個歷史的進步。
接下來我想說的是,作家進大學,幹什麽去。上課?帶研究生?誠然。現在進了大學的許多作家,都是這麽做的。說來也是,既然頂著個教師的名頭,自然就得好好教書。而且這書還要比別人教得好些,否則就顯不出作家牌教授的水準和特色。話雖是這麽說,但問題是,現在的大學,光教書還不夠,還得騰出手來搞科研,甚至要比搞教學花去更多的時間精力。大學的評價體系,說是教學科研並重,實際上這天平總是往科研傾斜,有時還斜得很厲害。這就要進了大學的作家作好思想準備。或者說,這準備我早就做好了,搞創作也要研究社會人生問題,都是個研究,應該沒有問題。這話說起來輕鬆,可做起來並不那麽容易。我不是在故弄玄虛嚇唬作家,但我要提醒這些樂觀派作家的是,此一研究非彼一研究。大學裡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雖然也不外乎社會人生問題,但活動方式和遊戲規則,卻不同於作家的研究。作家的研究多半是為己的,大學教師的研究則大半是為人的。你不能覺得你對什麽有興趣,或覺得什麽有意思就去研究什麽,你得接受一種規範和要求,按照這種規範和要求去做研究。或者說,這個我也能接受,誰還能在真空世界裡自由翻飛,都會有規範和要求的約束,都會有的。但如果說這規範和要求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具體體現在開會、填表、申報、論證、檢查、評估、考核、驗收等等繁瑣的程式上面,你也能接受?如果這也能接受,你的創作心境還能保持得住?如果沒有這份耐心,你又到哪兒去找科研必須的課題和經費。在如今的大學,沒有課題和經費的教師,輕則被人瞧不起,重則影響部門績效,日子都不好過。作家自尊心重,好勝心強,實在不是一件輕易就能適應的事。除非大學網開一面,不要求作家搞科研,那就另當別論。但這樣一來,這教授的名分也就要大打折扣,倘若還想晉升,那就更加尷尬。好在有的作家還有作協的一份待遇保本,不至於太過在意,倘若沒有這份本錢,那可就慘啦。
以上說的,都是現行的大學體制與作家駐校制度的不能兼容,或作家難以適應的一面。這當然都是一些很消極的想法,像我們這些在大學呆久了的人,或許覺得這是一個死結,很難求解。但是,如果換一個思路呢,“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其實要解決起來,也不困難。既然上述清規戒律或曰遊戲規則,都是學校訂下的,解鈴還得系鈴人,學校真的就對駐校作家網開一面,廢了這些清規戒律,改了這些遊戲規則,又能如何,連科舉這種實行了千百年的制度都被人廢了,區區一個大學的規定就廢不得麽。我這不是在過嘴巴癮,最近,南京大學聘請畢飛宇當駐校作家,就做了這樣的解鈴人,解開了這個多少人都認為難以解開的死結。據畢飛宇說:南大對他非常寬容,既沒有給他硬性的科研任務,也沒有給他硬性的教學任務,“南京大學明確告訴我,不會用我的所短,也就是教學科研,而是要發揚我的所長,也就是寫作,所以我還是可以將百分百的精力放到寫作上。”我孤陋寡聞,也許在南京大學之前,就已經有學校做了這樣的開明君主,但我能看到的,卻是在南大結出的一點碩果。畢飛宇最近把他在南大講的小說課結集為一本同名書《小說課》,正火爆萬丈。相信在南大校園,這火爆的天氣會更有質感。我在讀這書的時候,同時也在想象那質感的場面。這書寫得真棒,這課自然也講得出奇的好。到底怎麽好,我不想在這裡做具體的評價,我一評價,難免又要用上許多理論概念,這理論概念一用,就不是在講畢飛宇,而是在證明這些理論概念。捨棄這些理論概念,我想說的是,根據我的感覺印象,畢飛宇的這個講法,是把他人的作品、他人的創作,當作自己的作品、當作自己的創作來講。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把他自己代入他所要講授的對象,用他自己的感覺和經驗去體貼作品的每一個細部,去解析創作過程的諸多環節。就像他筆下的推拿師按摩穴位,先在自己身上試過了,然後再施之於人。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推己及人的過程,所以他就能說出人所經驗的種種酸麻脹痛的感覺,讓圍觀的聽眾也能在想象中經驗同樣的感受。結果就像托爾斯泰定義文學所說的那樣,把自己體驗到的東西傳達給別人,讓別人也得到這種體驗。今天的評論家喜歡說回到文學的本位,什麽是文學的本位,文學不是廟裡的菩薩,有固定的座位,在我看來,像畢飛宇這樣,把創作講回了創作,把小說講回了小說,這就是回到了文學的本位。其實,這也是大學的文學教師很久以來的理想,但要達到這理想的境界,對學院出身的教師來說,很難。筆者近年常常引用我的老師說的一句話,說我們這些教文學的人,是不知道雞蛋怎麽炒,還要教人家怎麽炒雞蛋。為了弄清這雞蛋的炒法,筆者近年來也試著自己炒雞蛋,在上課之餘,做了一點小說創作的嘗試,結果,所得雖淺,卻大有益於教學,再讓我來講小說,我就得琢磨寫作時的情形,回味寫作過程的甘苦,對作品的精妙,也會有更多的領悟。我自然比不了駐校作家,但從我這個粗淺的體驗看過去,駐校作家的文學課,將要改變大學文學教學的歷史。
我最早想到這個問題,是“聽”了王安憶在複旦大學講的“小說課”。在畢飛宇之前,王安憶已出版過一本名為《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的書。這書給了我很大的震動。我在大學講了幾十年文學課,從文學理論講到文學史,雖說不上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但對這些“矛錘弓弩銃,鞭鐧劍鏈撾,斧鉞並戈戟,牌棒與槍叉”的耍法,自認也能得其要領,用來教授學生,雖比不了八十萬禁軍教頭,也不至於誤人子弟。等到讀過了王安憶的這本書,卻禁不住心生疑竇,就像《狂人日記》中的狂人疑心自己也參與過吃人一樣,我也疑心我的弟子已然被我誤過。王安憶的講法與畢飛宇的講法雖略有不同,但重視細節和感性經驗,卻是共同的。這恰恰是大學課堂上的文學課由來已久的一個缺項。就拿小說來說吧,在大學裡,文學理論課要講,文學史課也要講,文學理論課講它的創作過程和構成要素,文學史課講它的起源發展和作家作品。但因為講的方法都是“概而論之”,或“總而言之”,居高臨下,縱覽古今,就像坐在飛機上巡天掠地,放眼望去,身子底下都是些抽象的線條和版塊,上帝花了六天時間創造的那些作品,竟不見纖毫,就算是從自家屋頂飛過,也看不清紅牆黑瓦。我不是自己在砸自己的飯碗,而是覺得用這樣粗放的模式教出來的學生,充其量也只能當一個同樣粗放的理論家和歷史家,是斷斷乎寫不出文學作品,也當不了作家的。這就又要說到大學能不能培養作家的老話題上了。這樣的話題本來與駐校作家無關,但據有關資料顯示,美國一些專門培養詩人、作家的創造性寫作專業,似乎大都是由駐校作家在主持。而且,美國當代一些創作活躍的詩人、作家,有許多就是由這些駐校作家的創造性寫作專業培養出來的。這樣,駐校作家也便有了一項新的功能,即為當代中國文學訓練新軍。最近,坊間有人發出一個“提案”,建議有關部門積極推行駐校作家、藝術家制度,並期望逐步取代專業的作家協會和畫院制度。我對聘請駐校作家這件事沒有這麽高的期待,我只希望已聘有駐校作家的大學和將要聘請駐校作家的大學,能像南京大學那樣,在管理上,給駐校作家留一塊飛地,劃一個特區,讓他們在成為大學教師之後,仍然是一個作家,仍然在以作家的身份發揮作用,而不要被現行的大學體制所異化。
—END—
《長江文藝》2019年第2期
責任編輯 | 何子英 丁佳雯

於可訓 | 作者
於可訓,1947年3月生,湖北黃梅人。現任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長江文藝評論》主編,曾任中國寫作學會會長,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於可訓文集》10卷,近年來發表小說《地老天荒》《特務吳雄》《才女夏媧》《幻鄉筆記》《鄉野異聞》《金鯉》和散文《淡水的詩意》等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