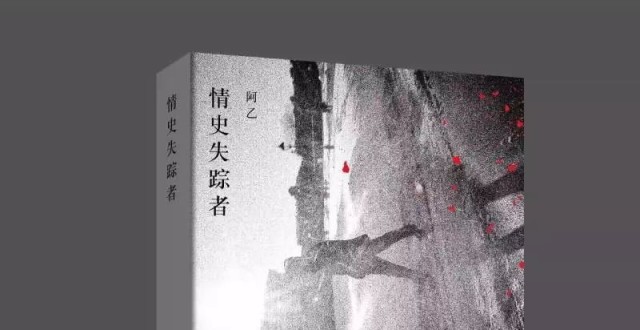原載於《上海文學》2018年第10期
理解一個短篇小說
李偉長
一
在英語文學中,小說就分兩種,長的和短的。
長的叫novel,短的叫short story。後者譯作中短篇小說。中篇小說在西方文學中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它是我們從中單獨拉出來的一頭牛,並慢慢形成一些約定俗成的文學認知。如果不計較中篇和短篇的差別,統一叫做短篇小說的話,會便於我們用長久以來在閱讀中感受和習得的觀念,來理解一個短篇小說創作的秘密。是的,一個短篇小說,不是一部,或者一篇短篇小說。“一個”作為量詞,讓人感覺到它可以是一個物件,經由造物之手打磨過的,有著別樣的精氣神。理解一個短篇小說,就是理解一個物件,是觀者與製作者在審美層面上的見面、較量和共同上升。理想的狀態並不是高山流水,不只是相互懂得,而是不只懂得,還有相互的責問和辯論,在你來我往的刺激中得以往更高處走。所謂懂得也分深淺的,淺的很多,深的難見。理解變得困難和奢侈,不能怪罪於讀者的懶惰和小說家的敷衍,而是生活越發顯得靜水深流。
小說家被形容為一個手藝人。這個比喻有其高妙,也有其局限。高妙在於手藝人的匠心和對技藝的崇尚,在反覆的練習中得以提升技藝,也慢慢探知自身的不足。能根據材料的不同,看到不同且尊重這份不同,做出好的作品來。局限在於手藝人不免重複,有相對固定的作品樣式,有個人擅長的作品種類,譬如木工手下的一把椅子,一般不會只有一把,可能有兩把、三把甚至更多。最接近小說家的手藝人是篆刻家,根據要刻的字樣,取一方石材,視料下刀,刀飛字現,觸印泥而成,一枚印就是一枚印。合適的石頭,合適的字樣,合適的刀法,還有與之相配的印泥,缺一不可,都在篆刻家的法眼裡。挑字樣,選石材,定刀法,配印泥,講究的無一不是手藝人的修為。技術到了一定的水準,與藝也就相融為體了。
短篇小說家呢?技藝高明的一樣自如從容,從某些現實中獲得啟迪,調動自身的經驗,將這份啟迪和靈感,用文學的合理置換進行照亮,化某一個事件為既普遍又獨特的敘述。據馬爾克斯自己說,構思《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花了他三十年,他不想直接取材於現實案件,而是從中獲得啟迪,審視這個案件,並置換為文學的表達。一個短篇小說也許用不了這麽久,無論是直接取材還是從中獲得啟迪,都需要時間醞釀提升,繼而完成新的更為真實的創作。不用擔心靈感的稍縱即逝,馬爾克斯說,如果一個想法經不起多年的丟棄,我是絕不會有興趣的。在張新穎的《斜行線:王安憶的“大故事”》一書中,有一篇兩人關於《匿名》的對話。王安憶提到,上世紀80年代在婦聯的信訪站,聽到一個大學老師退休後去雁蕩山玩後失蹤的故事,久久找不到。這個老師會去哪兒呢?會不會是自己出逃了,重新活一次?這個故事和想法在王安憶的腦海中盤桓了很多年,直到寫出《匿名》。寫長篇還是短篇,從生活中獲得啟迪的機制都是相似的。相對長篇,短篇需要更多的小念頭。小說家在創作之前,對故事所能達到的長度往往是有意識的。某個題材能寫成多大、多深乃至多廣闊都有著基本差不離的判斷。寫一個短篇小說所耗費的心血與世俗的收成,的確難成比例。
從生活中得到的啟迪,在要求編寫複雜故事的今天,常常被故事遮蔽了。短篇小說變得並不受人歡迎,它有限的篇幅來不及展開一個豐滿的故事。中篇小說的興起,正是取了短篇和長篇的中間值,說到底寫一個故事還是小說家所習慣的。不講故事,有些小說家就不知道小說還能幹什麽,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寫小說。編織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編碼)成為他們孜孜以求的事情,也是被訓導許久的事情,甚至夢想著趕緊被那些沒什麽眼力勁兒卻又手握鈔票的影視人們相中,趕緊買走,迅速變現。短篇小說的創作從未像今天這樣艱難。現代短篇小說所要求的又恰恰是走出洞穴,告別曾經傳遞和分享經驗的傳統模式。對一些雄心勃勃的作家而言,短篇小說的創作更多是一種練習,對語言的練習,對靈感變為文字的練習,對塑造敘述者的練習。而對有些小說家來說,練習本身就是創作,習作也可能是傑作。在一次次的練習中,一個小說家同樣可以建構同樣駁雜磅礴的文學世界,其深度和廣度並不輸於長篇小說。就像蘇童,即使沒有創作長篇小說《黃雀記》,他筆下的香椿街也早已在短篇小說中完成建制。作為蘇童的寫作地圖,香椿街上流動的正是普通人群的日常生活。
愛爾蘭小說家威廉·特雷弗寫了一輩子短篇小說,他認同弗蘭克·奧康納的話,即短篇小說講的是小人物,短篇小說不屬於英雄,更適合講述平常人的平常際遇。通過大量短篇小說的切面,他構建了關於愛爾蘭鄉村的人情和人心的世界,如一顆鑽石,經由高超的切工技藝,收獲了更多的切割面,最終光彩奪目。相比之下,奧康納比特雷弗冷酷多了,淹沒的人群的人性幽暗和邪惡在她筆下更為普遍。同時寫小說和評論的喬伊斯·卡羅爾·奧茨在評論契訶夫的《牽小狗的女人》時,認為契訶夫寫出了“平常人陷入了不平常的境遇”。所謂不平常的表述,多少還是有人為戲劇性的潛在暗示。在特雷弗這裡,便連不平常這樣的限定詞都隱去了,意味著人們所習慣已久的戲劇性也退去了,直接轉為平常人的平常境遇,以及平常生活中的暗影和角落。這是現代小說觀念的變遷,也是生活本身發生的變化,特雷弗迷戀普通生活中的皺褶、氣味和方向。他想探索一下未經修飾的生活本來的樣子。結果是特雷弗發現了和照亮了生活中的許多個瞬間。與特雷弗同樣鍾情於普通生活的,還有愛麗絲·門羅,一生都在寫短篇小說,有的篇幅更接近我們概念中的中篇小說。
說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當然需要提到福樓拜和他創作於1877年的短篇小說《純樸的心》,在批判現實主義盛行的19世紀,這篇小說像是一個異數,堪稱超越時間的經典,寫盡了時代中普通人的生活。福樓拜寫了一個普通女仆人的一生,她曾經歷戀愛,也有過親戚來往,最後她養了一隻鸚鵡。老仆人忠心耿耿,一生都聽主人的話。女主人說什麽,她做什麽,就像鸚鵡一樣,學說主人的話。鸚鵡真的沒有自己的想法?老仆人沒有自我?顯然不是。鸚鵡由此成為談論福樓拜其人其作無法忽略的經典細節。為什麽是鸚鵡?有何象徵意義?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注意到了這隻鸚鵡,並專門寫了一本書,就叫《福樓拜的鸚鵡》,從鸚鵡開始以小說的方式為福樓拜立傳,也探索福樓拜的心靈世界和小說技術。
關於福樓拜筆下的普通女仆,奧康納有一個詞道盡其曲妙。奧康納在《小說的本質和目的》(錢佳楠譯,《上海文化》2017年3月)一文中說:“小說就是關於任何人生於塵土歸於塵土的事情,如果你不想搞得自己滿身塵埃,那你不應該奢望著寫小說。”所謂塵土的表述,不過就是綿密的日常生活細節,令人尷尬、落寞的灰塵,就像福樓拜的女仆人,一生都在經歷灰塵,滿身塵埃,卻又不是淒慘的血淋淋的災難。發軔於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傳統,依舊是今天寫作者難以回避並習慣接受的方式。畢竟,在卡夫卡和博爾赫斯的那條路上,擁擠著的都是往山上走的哲人們,那裡的路越來越窄。契訶夫的信徒們則走向平原,分散而行,至少開闊得多。即使我們感受到了塵土,也被搞得滿身塵埃,甚至灰頭土臉,我們依舊難以將塵土的感受告訴別人,於是需要一個故事幫助我們傳達,這幾乎是一個悖論。
二
從本雅明的《講故事的人》後,很多作家都說自己是個講故事的人。
小說家和講故事的人顯然有別,現代小說家不是講故事的人,而是創造敘述者的人,由敘述者去講故事。只要敘述者成立,其他也就成立了。創造敘述者就是一個技術活兒,就是小說家的關鍵工作。問題在於,如何編一個故事現在變得過於迫切和急功近利,以至於編劇出身的羅伯特·麥基撰寫的《故事》成為小說家寫小說的案頭指南,就多少顯得本末倒置乃至有些滑稽了。儘管麥基說過一些深刻的話,如“故事是生活的比喻”、“你的才華會被無知餓死”,但這並不意味著將小說與故事等同起來,那些被編織出來的欲望、困難和突圍,以及花團錦簇、跌宕起伏的情節,和小說所要求的內容並不等同,甚至背道而馳。因為生活的複雜無序,讀者需要一個比喻來準確地理解生活。只是影視劇需要的比喻和小說需要的比喻,天然地有著大象般的差別。為了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麥基會要求編劇考慮人物的欲望,設定人物遭遇的困境,安排人物結局困難的嘗試,最後排除險阻完成由欲望引發的任務。這種“遊戲性”的故事設定,將文學的頭顱高高地懸掛了起來。至少就短篇小說而言,如此完整的過程就不是必須的,一個念頭的升起也可以是一個短篇。
故事依舊盛行,故事術廣受歡迎。緊張的、匪夷所思的、複雜的故事依舊源源不斷地被編造出來,有的故事還被認為是想像力的一種飛躍。特別是看似基於現實的某類故事變得越發魔幻。詹姆士·伍德在《不負責任的自我》一書中,有一篇《歇斯底裡的現實主義》,對這類故事提出了激烈的批評,甚至不惜冒犯拉什迪、扎迪·史密斯、品欽和福斯特·華萊士等一群大佬。伍德認為他們不停地講故事,故事中套故事,不惜一切代價追求活力,永不停歇地講故事,炫耀故事穿行的繁忙和擁堵。一出生就在嬰兒床上彈空氣吉他的搖滾巨星(拉什迪);一只會說話的狗,兩盞會說話的鍾(品欽);一個名叫輪椅刺客、致力於解放魁北克的恐怖組織和一部很感人、看了它的人都會死的電影(華萊士)。這些情節在伍德看來,根本不是魔幻現實主義,而是歇斯底裡現實主義,算不上是偉大想像力的證據。這些非人的故事,在借用現實主義的同時似乎在逃避現實,成了想像的道具,意義的玩具。在這些被謬讚為釋放想像力的作品中,我們得以感知寫作者的才華,但也可能在故事中迷失。
過度講故事的表現還在於,苦心孤詣地給小說人物牽線搭橋,讓他們產生聯繫。離群索居的現代生活似乎在他們身上不構成影響,即便深宅也會被小說家精心炮製的線索拉出房間,與現實生活中八竿子也打不著的人進行接頭。越複雜繁瑣的線團,纏繞得越緊,將生活變得越是戲劇化,就越會深得電視導演們的認可:多麽有想像力,多麽有故事,多麽有戲劇性。即便是電影本身,過於強調故事的完成度,也引發了人們的憂慮。導演蔡明亮在《一念》一書中,就拿那些過於強調劇情的電影進行開刀。蔡明亮認為,過於追求劇情,使得電影沒有時間讓觀眾思考。觀眾根本來不及思考,也沒有思考進入的太空。觀眾容易從長鏡頭中,捕捉到自我思索的線索,從而獲得電影和自我相溝通的契機,猶如一道門,步入這道門後,方能感知到被懸置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擁擠迅速的故事,同樣無法營造一道足以讓讀者進入的門,而止於故事本身的消遣和刺激。
詹姆士·伍德的話不無偏激,這位以學識和敏銳出名的評論家,並不在乎他所批評的小說家們的反應,事實上他不過是借助他們的作品,抒發自己的思想,扎迪·史密斯不幸地被他用作了論據。關於扎迪·史密斯的創作,比如《白牙》當然可以另外看待,但這不影響我們作出一個基本判斷,當故事變得越來越荒唐,越來越強調難以置信的可能,催生的未必是荒誕的批判,也可能降低了小說的衝擊力。就故事而言,相比難以置信的可能,令人信服的不可能,更令人期盼。《追風箏的人》作者胡賽尼有一個觀點:“我感興趣的是那些完全不可能發生的愛。”不可能比可能更有現實意義。小說家迫不及待地通過情節和偶然的遇見,讓小說人物產生聯繫,遭遇可能的相撞,繼而推動故事。當故事只是故事,當故事越來越像故事時,我們可以肯定,它們離現實很遠,離生活很遠。或許一開始,當故事被設想時,就不是為了抵達現實並試圖超越現實生活的,而是製造一個個逃離生活的溫柔陷阱。如果說啟迪得之於偶然,那由啟迪之後的第二步則是考驗小說家的手藝,即安放這個啟迪和靈感的太空或者事件。選擇一個故事安放啟迪和靈感,而不是讓啟迪湮沒於故事當中。
在講故事的縱隊中,異質性被敷衍地理解為稀奇古怪的事件。看看文學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說就可以感覺到了。底層作為一個故事太空,近年來被討論很多,也有一些爭議。撇開藝術不談,僅就故事來說,底層寫作的確存在諸多問題。鄉村生活、小鎮生活、底層經歷依舊是大多數小說的主題,衰敗、破壞、停滯、失范和迷失是常見的基調。關於城市生活的中短篇小說,基本上寫的是遊離於城市邊緣,被城市拒斥的失敗者們(有的小說家不願意這樣被描述,更願意稱之為普通人),即當下版的農民進城記。真正與城市生活發生密切關聯的城市小說少之又少,我們的小說家絕大多數生活在城市中,卻對早已離開許久的鄉村生活念念不忘,對身邊的城市生活漠不關心,也無興趣去深入了解自我日常生活之外的經驗。
如果底層不再被消費,那小說家鬼金的出現就不是個意外,這位“吊車司機”以近乎凶猛的姿勢闖了進來,然後坐定。以他的文字水準來看,出場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小說集《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以敗落無用的軋鋼廠為背景,收納了那些遊蕩於金屬中間的無力的人群,眼看著破敗而來,個人卻無能為力,只能跳躍其中,這就是裹挾。鬼金的作品會被認為是真的底層文學,拒絕被消費,沒有哀嚎,扎根身邊,說到底,底層就是大多數人的生活,暗湧著熱流和力量。鬼金說儘管我把軋鋼廠寫得像煉獄,但我依舊感謝它,沒有軋鋼廠就沒有我的寫作。沒有否定與割裂,而是站在一起,深入其中,成為衰敗的同類。鬼金的清晰自我就建立在軋鋼廠與社會的關係中,衰敗總是整體性的,不然人的困境從何而來。有趣的事情在於,如果說鬼金的自我經驗經過了價值的衡量,那他所書寫的是時間生活,還是價值生活呢?用福斯特的觀點來說,故事敘述的是時間生活(life in time),然後……然後……再然後,而小說應該寫的是經過價值衡量過的生活。沒有被衡量過和反省過的生活,接近於“未經被審查的生活”。時間生活裡的經驗可以是可靠的,也可以是自我的,那價值生活如何體現呢?價值生活(life by value)與普裡切特、卡佛的現實觀念是一致的。這不僅是鬼金的難處,也是沉浸於自我經驗和身邊生活的寫作者的難處,貼地氣這樣的修飾語,並不是體現文學價值的修辭,而是指向價值的反面。越是大量地掌握一手生活經驗和熟練地使用自我經驗的寫作者,越要謹慎地對待“價值生活”的可能,越要用更為普遍的諸如愛、欲望、人性、正義等,去審視筆下的人物和生活。
如何拿捏故事和觀念的分寸,劉汀在小說集《中國奇譚》有一番試探。十二則短篇小說,如《煉魂記》《換靈記》《歸唐記》《製服記》《牧羊記》等,有筆記體小說的影子,安置著十二個看似不可能的故事。這些故事遊弋在真實與虛構的邊界:有靈魂更換的詩人和商人;有從穿警服墜落到穿城管服最後再穿囚服的人;有因拆遷成為植物人卻還能聽見周遭聲音的人;有收割世人臨死前恐懼的死神,卻總是收割到悲憤、沉悶和仇恨;有把公車急速奔跑數百公里從北京開去了秦皇島的夜班司機。不可能的事件,經由劉汀的虛構,變成了可能的真實。劉汀對現實的發言,借由這些看似荒誕的故事,獲得了超乎傳統現實主義的力量,荒謬和反諷相依相生。劉汀一再強調,虛構之本在構,而不是虛,這像是某種自我辯護。虛構的根本在於賦形,賦一種觀念以可靠的形,呈現出可以接觸和理解的內容。對於有清晰自我的小說家而言,虛構就是賦形之術,關鍵是那被賦形的觀念足夠堅硬。作為小說家的劉汀對現實生活的某些幽暗是不滿意的,他對我們聽不見、看不見、做不出的生活背面充滿了好奇。劉汀所呈現出來的文體意識,不全是來自寫作本身的刺激和有意而為,而是源於所寫對象,即他期望通過文字照亮的“一瞥”的驅使所然。
三
關於什麽是短篇小說,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在一篇文章《論寫作》(OnWriting)中,借用過英國小說家、評論家V.S.普裡切特對短篇小說的一個定義:“Something glimpsed from the corner of the eye,in passing.”可譯為眼角順帶一瞥。卡佛不斷提醒我們,短篇小說首先是這“一瞥”,其次是順帶的一瞥。如果足夠幸運,這一瞥能夠照亮瞬間、賦予鮮活生命和更寬廣的意義。卡佛強調,短篇小說寫作者的任務,就是盡其所能投入這一瞥中,充分調動他的智識和文學技巧,去施展他的才華,把握認識事物本質的分寸感和妥帖感,說出他對那些事物與眾不同的看法。這神乎其神的“順帶一瞥”,就是普裡切特的短篇小說觀。卡佛完全接受了普裡切特的“一瞥”,並就如何完成這一瞥,進行了技術提升。
《巴黎評論》專訪了V.S.普裡切特,問他為什麽偏愛短篇小說,而不是長篇小說?普裡切特先是自嘲一番,說長篇小說需要足夠的耐性,而他缺少足夠耐性,不適合寫長篇小說。接著他就正面回應了這個問題:短篇小說顯示出一個由很多孤立的事件組成的確定的現實觀念。並繼而分析,短篇小說最重要的事是細節,不是情節。情節是有用的,僅僅在於它提供了那種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推動行動發展的細節。卡佛的“與眾不同的看法”,與普裡切特的“確定的現實觀念”,異曲同工。可以確認,對普裡切特來說,短篇小說就是細節,他是個徹底的細節主義者,那些孤立的事件們是他所鍾愛和依靠的表達方式。
從普裡切特的回答中,我們可以得到兩方面的資訊,一是關於細節的解釋。何謂細節?孤立的事件,真是巧妙的答案。將孤立的事件串聯出所謂的意義來,就是小說家要乾的活兒,最體現一個寫作者的技術。其二,這個確定的現實觀念,就是一個作家在文本中構建的清晰的自我,它由分散在情節中的細節投射而成。關於這個確實的現實觀念,雷蒙德·卡佛進一步做了明確,就是必須表達出與眾不同的見解和觀念。對大多數寫作者來說,每次出手都要與眾不同,都要獨一無二,有些苛求了,至少卡佛自己就沒有做到這一點,普裡切特先生也沒有全部做到,普裡切特創作小說的水準就遜於他的評論。話又說回來,即便這樣,也絲毫不影響我對普裡切特和卡佛的歡喜,他們關於短篇小說的觀念,以及對理想的短篇小說的盼望,的確給我們提供了一些識別卓越短篇小說的路徑和方法。
如何面對這“一瞥”,喬伊斯·卡洛爾·奧茨的建議是“忠於”。她在《短篇小說的性質》一文說,“我們寫作,是要忠實於某些事實,忠實於某些情感,是為了‘解釋’那些表面上古裡古怪的行為……一個聰明的年輕人為什麽會變得暴戾恣睢,會去殺人;一個無憂無慮的女人為什麽會跟人私奔,結果毀了自己的一生;一個頭腦清楚的人為什麽會去自殺?”奧茨的寫作就出於一個很簡單的願望:我想知道人類各種情感後面的“為什麽”。關於她所列出的問題清單,我們都想知道,不是麽?我們也想知道契訶夫為什麽要寫《牽小狗的女人》這樣的小說,我們也想知道福樓拜的鸚鵡為什麽那麽吸人眼球,我們更想知道世界上那麽多的古裡古怪是因為什麽。對小說家來說,唯有忠於某類價值,才可能發出神聖的光澤,才可能照亮普裡切特所說的一瞥,才可能做到卡佛說的表達與眾不同的看法。
忠於某類意義,是不是就非得寫大事件、大場面呢?這似乎也是糾結在中國寫作者心中的大問題,當然不是,普裡切特和卡佛的一瞥觀說得清楚,是眼角的一瞥。奧茨更是不以為然,她認為只有還沒入門的作者才會挖空心思,想什麽“大”事件。業餘作者往往想寫大事情,表現嚴肅的主題。但世上沒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筆。所有的主題都是嚴肅的,或者愚蠢的。沒什麽規則。我們無所羈絆。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潛伏著俯拾皆是的素材和經驗,但要變成小說需要足夠的耐心,足夠的等待。
假如我們有幸捕捉了“一瞥”,並照亮了它,那理想的“一瞥”會是怎樣的?優雅,王安憶的答案是這兩個字。在短經典叢書的序言《短篇小說的物理》中,王安憶認為短篇小說的一個定義就是優雅,像愛因斯坦談論的物理定律那樣,盡可能地簡單,但不能再行簡化。“短篇小說多是寫的偶然性,倘是中長篇,偶爾的邂逅就還要發展下去,而短篇小說,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於,這樣交臂而過的瞬間裡,我們能做什麽?塞林格就回答了這問題,只能做有限的事,但這有限的事裡卻蘊藏這無限的意味。也許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寫得不多,簡直不像職業作家,而是玩票的。而他千真萬確就是職業作家,唯有職業性寫作,才可將活計做得如此美妙。”要在有限的事裡藏進無限的意味,顯然需要不一般的技藝。塞林格值得起人們的服膺,《九故事》就是現代短篇小說的典範之作。
王安憶有一篇小說《眾聲喧嘩》,寫一個老爺子歐伯伯,在老伴過世後,為安頓好自己的晚年生活,也為排遣晚年寂寞,開了一爿小小的紐扣店。歐伯伯是個有想法的老爺子,常常感覺兒女們並不認真聽他說話,也不懂他的所思所想,就有了煩惱。反倒是不相關的小保安,能夠認真聽他講,還能及時呼應。裡頭有兩句尋常的對白,真是奪人眼目的細節,是老爺子與小保安聊天時說出來的。老爺子說完看法後,愛習慣性地來上一句:不可能的呀。小保安總會及時呼應一句:就是講呀。這兩句話有意思,一呼一應,看似簡單,但用上海話一讀,就能意會其中妙處,裡頭有著別致的對話,二人呼應極為到位。作為上海人聊天的常用句子,這兩句上海話,有著天衣無縫般地銜接和呼應,潛藏著明白、理解和讚同的意思。與其說這是方言的魅力,不若說是這兩句話中的對話關係引人注意。句子與句子之間的內在呼應,生成了獨特的語境。這份語境與人有關,與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有關。合乎分寸的關係應該就像這兩句對白一樣,具有呼吸感覺。一個人即使不停地說,到底有多少話,能到達聽者的耳中?有多少能真正被聽懂?王安憶發現了這一瞥,並說出了她獨特的看法,有時候人的交流得於語言自身的呼應,而不是人與人的交心。
這種語言的自發呼應交流,在趙松的《積木書》中也有。《積木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短篇小說合集,更像是一部散裝的長篇小說,由很多閃爍著各種小說元素的獨立短章構成。這些斷章和碎片並不刻意構成完整的故事,但它是開放的,隨時可以進入,又可以出來。趙松的小說意識,表現在他對小說如何繼續發展充滿興趣。趙松製造了一批小說零組件,也就是小說細節,提供給讀者。細節就是一個個場景,閱讀就此變成了一場難以意料的剪輯旅行,或者說是一次積木遊戲。趙松這樣做,其實很冒險,但這種冒險又是基於對閱讀者的充分信任,甚至是一種邀請,共同來完成這個遊戲。有這樣一個細節:
……在路口那裡等著的,是個幽靈般的人。他坐在計程車裡,手搭著方向盤,眼神迷離,半夢半醒,倒是跟這午夜時分非常的契合……他的車裡有兩個小寵物,一個是蛐蛐,一個是蟈蟈……它們都在叫著,各佔一個聲部。這樣不會困麽?不會。他說“不會”的時候,臉部輕微抽動了一下。應該在擋風玻璃下面種上一片草,這樣開著車窗時,風吹進來,聞著草的味道,再聽著它們的叫聲,就會覺得自己是一直在郊外行駛呢。聽了這話,他忍不住笑了笑,沒有答話。
午夜時分,一個計程車司機等在路口,也就幾十秒的故事時間。這個瞬間被趙松的語言照亮了,被他賦予了生命,就像一個精心捕捉的電影鏡頭。幽靈般的司機眼神迷離,困意隨時來襲,光影婆娑,意味深長,它的敘事時間似乎變得漫長起來。這個瞬間不止是靜止的,還有人的對話,以及其他的聲音,蛐蛐的,蟈蟈的聲音。趙松無一字寫司機的孤獨,隻問,這樣不困麽?司機回復是不困,但是臉部透露一點言不由衷的資訊。閱讀者可以感受到那一刻被平靜裹挾的巨大的孤單和昏沉的睡意。
接著就是神來之筆,“應該在擋風玻璃下面種上一片草,這樣開著車窗時,風吹進來,聞著草的味道,再聽著它們的叫聲,就會覺得自己是一直在郊外行駛呢。”這段話將這個瞬間放大了,乃至拋了出去。如果真有一片草,還有風和味道,被想像的可能生活,是誰的呢?這個句子如此殘酷,前半句讓人生出希望,聞著這草的味道,迎著吹進來的風,後半句再次鎖定,再如何還是在郊外行駛。一個計程車司機,真的需要一片草麽?“聽了這話,他忍不住笑了笑,沒有答話。”沒有答話,就很好,安靜無言,但司機還是笑了笑,忍不住地笑了笑。作為一個玩笑,司機回應了笑。但作為一個建議,他沒有答話。你所認為的“應該”,在對方未必就是“應該”,這算是有效還是無效的交談呢?趙松的小說零件本身已然足夠迷人,即一種可以被期望的現代漢語,已經生長為值得省察的案例。
四
雙雪濤有一個短篇《白鳥》,用連續幾個看似孤立的事件和人物,構建了一個寫作者的精神世界,即關於寫作者莫名的來處和被打斷的狀態。其中有一個細節,印象深刻。雙雪濤寫了一個女教師,從學校離職了,不知道去了哪裡。據說後來有人在長安(西安)見過她,當時她斜背長劍,像一個女俠,越過人群。這個斜背長劍的形象和她越過人群的場景,至今還盤桓在我的腦海中,她的消失就像一次被虛構的出走,難辨真假。
薛舒的短篇《越野》從她以往的題材中生長了出去。一輛車所寓意的現代城市生活,發生了一些偏離,繼而恢復如初。一輛本該越野的牧馬人,失去其最初的使命而融於日常生活,蝸牛般地爬行在城市的街道,但即便緩慢,開車的人也會擁有一種被隔絕的短暫的自由和不被打擾。小說人物從汽車裡出來,加入人潮如織的地鐵,很快又渴望回到不再有人打擾的私家車裡。這層反覆,折射出的是女性日益習慣的生活常態狀,以及渴望不被打擾的獨立太空。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愛麗絲·門羅的《逃離》,一個期望逃離既有生活秩序的女人,隻逃出了三站路就感到了害怕,打電話給老公,來接她回家。薛舒的小說事件看上去都是孤立的,地鐵、搭訕、汽車、先生、懷孕、回歸,在組合中相互生成了聯繫,構成了隱約的現實觀念。
在文珍短篇小說《夜車》中,夫妻鬧離婚,分居半年後,丈夫被查出肝癌晚期,余日不多。為了“過好”剩下的日子,夫妻倆一起“去遠方”。冰天雪地,兩人落腳在一家小旅館:“現在萬事皆休,終於只剩下我和他兩個人,在一個沒人知道的飛地,一個無人入住的小賓館,沒有小孩,沒有第三者,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剩下一隻孤零零的蛾子盤旋往複。我很少想到永恆,但這一刻,我的確希望時間可以停止。”這兩個人,正在表演著獨特而又普遍的人性,與那孤零零的蛾子一樣,盤旋往複,欲言又止,終趨於停止。兩個人,愛到極致,也厭倦到極致。“希望時間可以停止”,在這一刻,蛾子盤旋著,時間已經停止了,語言從中獲得了活力,所有的死寂沉沉全壓在蛾子的盤旋上。試想,曾經愛過的兩個人,如今男的將死,女的早已心死,躺在一個遙遠的小旅館裡,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麽,一起回首往事?不合適,也沒有必要。一起暢想未來?不,沒有未來。只有現在,只有沉默的此時此刻,只有萬事皆休的此時此刻,也只有尚未結束的此時此刻。這是文珍的文學法術,將某個場景,某個時刻,從現實中,乃至從虛構中,自然地抽離出來,並懸空而置,變成一只在盤旋的蛾子。即使是短暫的片刻,懸空起來也會釋放出擾亂人心的力量。
擾亂人心的力量在張怡微的《櫻桃青衣》小說中也能感受到。九個短篇呈現出一種自然的生長性和靜穆的氣質,張怡微獲得了從容不迫的自由。有一篇《度橋》,張怡微寫了一個患癲癇病的女人,每天站在路口,面無表情,吹著淒厲的口哨指揮來往交通,二十年如一日,人們都以為她是真的交通協管員。其實不是,她就是一個瘋女人,有自己的世界,並沉浸其中,誰又知道她不是在自己的世界中真的遠征和燃燒?張怡微沒有在她身上安放廉價的同情,然而,這個“我的青春計時器,也是世事變遷的度量尺”的瘋女人,也無可挽回地衰老了。瘋女人指揮交通的細節,在小說中顯得如此突出,賦予小說一種難得的悲憫感。張怡微建立了一個有內在法度的敘述者,形成一種有自我辨識度的敘述聲音,然後從生活中取來一盤沙,砌成一個沙堡,潮水一來,又衝刷而去,一複如初的靜穆,就像什麽也沒發生過一樣,然而那些孤立的彼此摩挲的沙子,並未真的就消失了。唐傳奇中“始迷終悟,夢而覺也”的一種母題,可視為一種文學影響在張怡微身上得以接續。
董夏青青在小說集《特恰裡特山下》,寫過一個死亡場景。邊疆軍人戍邊,一隊戰友騎馬過冰河,突然冰面破裂,出現一個窟窿,一個戰士掉進了冰洞,瞬間被湍急的河水帶走。冰面透亮,戰友眼看著冰下的腦袋,隨著水流往前衝。戰友一路去追,根本來不及再去敲破冰面,也不敢敲。一個戰友就這樣在面前消失。這個細節的震撼有來自生活的真實,也有小說家捕捉那瞬間的能力。董夏青青的小說意識不在於寫這些極端的意外事件,而是著重考量在極端情況下這些軍人正在經歷的日常生活。好的小說家有能力帶著我們,穿過生活的迷霧,去看清常人看不見的東西。因為在閱讀中,我們得以過了一遍與我們形式不同,但本質上趨於普遍的生活。就像羅曼·羅蘭所言,看清楚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它。除了熱愛,你別無選擇。有能力看清生活真相的人,還得有能力不讓自己墜落。
抵達真實是一種莫大的誘惑,但如果這種真實被誤讀乃至被縮小了呢?評論家李雲雷這些年對“底層文學”這一文學理念的闡釋可謂用心良苦。必須承認的一種現實,“底層文學”一定程度上,被人理解為粗糙的、主題先行的和缺少文學審美的創作,甚至曲解成對抗城市文明的反面形態,這顯然並不符合李雲雷對“底層文學”的想像。李雲雷試圖通過《再見,牛魔王》呈現理想的底層文學應該有的樣子,同樣注重敘事創新,同樣講究建構敘述聲音,同樣關注人的命運。李雲雷將小說和散文筆法進行融合,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敘述聲音,在關於故鄉、童年和鄉村的記憶裡穿行。李雲雷虛構了一個敘述者“我”,在《電影放映員》裡,我將一個男子送給小姨的信,揣在褲袋裡,忘了給小姨,後來小姨嫁給了別人,“我”才想起是不是誤了事。小說陡然轉到當下,前幾天“我”還和姨夫一起喝了酒,小姨和姨夫看上去過得很幸福。在時間軸上瞬間移動人物的寫作方式,讓小說具有一張突然而至的張力。李雲雷寫的是那些正在被遺忘的人。被遺忘的人,並不意味著一定就是被傷害的,他筆下的鄉村生活才沒有那股急切的“鄉土味”和廉價的同情氛圍。
五
在馬爾克斯的《番石榴飄香》一書,有一章“談寫作”,談到靈感,馬爾克斯說:“‘靈感’這個詞已經給浪漫主義作家搞得聲名狼藉。我認為,靈感既不是一種才能,也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作家堅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為他們所努力要表達的主題作出的一種和解。”這和福樓拜的觀點不謀而合:才華就是緩慢的耐心。發現“一瞥”的才華,從現實生活中得到啟迪的能力,以及不斷雕琢的技藝,都需要時間和耐心的加持。
指摘一篇小說是容易的,這種容易會讓批評者放鬆警惕,變得隨意和專製起來,置小說可能的“發現”而不顧,相比於標榜偉大小說該有的面目,感受寫作者的艱難與嘗試,理解一個小說家的技藝和觀念,則顯得更加重要。努力讓自我變得更加清晰的小說家才會不斷嘗試。那些找到了自己的故事和還在努力尋找的小說家,都是幸運的人。如果說寫作者多焦慮於尋找“一瞥”,那作為讀者,我們終生都在尋找被點亮的“一瞥”,那或許是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能夠告訴我們為何出生,為何而活。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停止閱讀小說,因為正是在那些虛構的故事中,我們試圖找到賦予生命意義的普遍法則,試圖識別被小說家們寫下來的“一瞥”,因為我們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