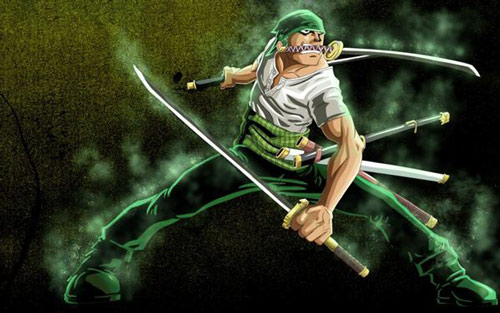20歲時,田耳就在社會上乾活了。他做過很多奇怪的活計,養過鬥雞、修過冷氣機,在小報上寫過兒童文學,還在派出所編過內刊。2000年前後,他常去酒店要冷氣機拖欠款,那時他還不善言說,跟對方吵不起來,就自己買包煙、買便當,安安靜靜一坐一整天。用他的話說,就是“用無聊來打壓對方”。可是,光坐著實在太無聊了,他就在腦袋裡構思小說。當時電器店主營的是科隆冷氣機,要不是科隆冷氣機後來出事斷貨了(指2005年科隆冷氣機顧雛軍案),田耳說,他說不定還在做冷氣機生意。

田耳與新作《被猜死的人》
《被猜死的人》是田耳今年出版的一本中短篇小說集,其中收錄的一篇同名小說,就寫於他在上海讀書期間。那時他們住在青浦的一個養老院裡,養老院裡沒有老人,倒住上了作家,這讓他覺得奇怪。晚上睡不著,他就琢磨在自己此刻躺著的床上,是不是也曾死過老人。《被猜死的人》寫出來,講述的就是養老院裡的老人一個接一個死去,剩下的老人們聚在一起,用猜誰死作為遊戲來打發時間。其中一位極不起眼的老人每次都能“猜”對,剩下的老人漸漸對他畏懼不已,甚至要給他送禮,以延遲自己的“死期”。依仗這一點,這個養老院成了歸順於他的一方領土。
2007年,田耳獲得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他將這次獲獎稱為“改變命運的時刻”。那一年,他一共有兩篇小說入圍,一篇是短篇小說《衣缽》,另一個是中篇《一個人的張燈結彩》,後者最終獲獎。有朋友跟他說,“一個人的張燈結彩”雖然名字好,但是寓意不好,可能會一語成讖。但田耳似乎不忌諱題材不吉利。新書拿到手那天,他左看右看覺得有點問題,在書封上,題目“被猜死的人”和作者名“田耳”的字體字號完全一致,仿佛是連起來的一句話。他對出版社的行銷編輯說,“你看你們排的這個書名,排成了‘被猜死的人 田耳’,就差一個逗號了。”接著又尋思,“沒事,該猜死就猜死。不是說封建迷信,我這人很信命的。”

《一個人的張燈結彩》
田耳 著
作家出版社 2007年
縣城讓人天生膽小,
出來投稿被當成小商小販
田耳出生於湘西鳳凰,小時候家裡就有一套《沈從文選集》,父親告訴他,這是本地的作家,他翻了翻,覺得沒什麽意思。他很早就想當作家,但讀書時沒上過學校的油印校刊,給文學期刊的投稿也大多石沉大海了。“自由投稿別人不看的;我先投地市級的,像是《廈門文學》《青島文學》;後來再投省級。”田耳說,他在湖南吉首大學跟文學社的學生混過一陣子,那時常借了同學的圖書卡去閱覽室找期刊一頁頁地抄投稿地址,結果卻屢屢失望,“人家根本不搭理你,連退稿信都是一種美好的傳說,發表這件事對我們小縣城的人來說,太困難了。”
他還記得,之前白天做生意,晚上就在店裡一個人寫小說。1999年寫完《衣缽》,自己覺得好,可再沒有別人覺得好,他就找了熟人發在內刊上,算是給自己寫作生涯留有一線希望。另一方面, 他對寫作的“愈挫愈勇”已經引發了父親的憤怒。在一篇題為《被溺愛打開的世界》的自述文章中,田耳寫道,“2002年春節,在大姨家,喝了些酒,我就放狂話,說我寫的小說在整個地區都是頂好。父親就潑涼水,說他一個教語文的同事,看了我小說,還是學生作文。我說那個同事看不出好壞。父親斥我狂妄。我說五年後我會成為全國出名的作家。”其實,他那時候心裡依然很怕父親,看到父親的背影都哆嗦,借了酒勁才敢頂撞,後面酒醒了,嚇得不敢回家。“我們70後這代人都是恨爸爸。”田耳在採訪中說。
多年受挫之後,他決定越過市級、省級期刊,直接向《人民文學》和《收獲》投稿。投出去的那篇叫做《你癢嗎》,寫的是1983年嚴打被抓到監獄裡的強奸犯怎麽解決青春期的苦悶,“寫得挺狠”。出乎田耳意料的是,這兩家雜誌幾乎同時給他回信,以差不多的口氣告知田耳,他的作品不適合本刊,但希望他可以把其他小說寄過來看看。
其中一封是《收獲》編輯王繼軍寫給他的。田耳收到信的時候,正好要到上海採購,就直接帶了稿子去找王繼軍,倆人一塊兒吃幾十塊一份的快餐。王繼軍問他現在在做什麽,田耳就“固執”地把做生意的事兒原原本本講給他聽。“我估計,老王心說,原來他是個小商小販,所以飯都沒吃提前走了。”田耳後來才知道,王繼軍當天晚上就看完了《衣缽》,覺得自己還是應該把那頓飯吃完。 在內刊發表了6年之後,《衣缽》終於登上了《收獲》。
縣城的氛圍讓人天生膽小,田耳說,他是在2007年到上海念作家研究生班才把膽子練大的。膽子練大後,他還負責在同學中間調節氣氛,誰喝酒要邀請人都叫他出頭。他當時的同學裡,就有徐則臣、姚鄂梅等人。

田耳
寫作要有邂逅,
憋在家裡瞎想沒用
2007年田耳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之後,縣裡幫助他解決了工作,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跑社會”。 講起這一段他顯得有些興奮,“我乾得活多了。”他學過維修冷氣機,在養殖場養過鬥雞,曾去廣西憑祥友誼關買越南西貢雞。“那種鬥雞腦袋長著大冠子,這容易成為它的弱點,後面就淘汰了。”他喜歡乾這個活,想了很多辦法讓鬥雞變得更強壯。他說自己曾買了一個大篾罩,把一隻母雞罩在中間,同時給公雞喂激素類藥和壯陽藥,公雞這就一圈圈繞著籠子跑。“它腦子不開竅,老覺得前面有個窟窿能鑽進去,雞一跑一兩個小時,肌肉就鍛煉出來了。還要注射鬥雞人血蛋白,那時候50毫升四百多塊,在打架前一周,每天注射1毫升,所以鬥雞到最後比的是藥力。”田耳笑道,“那些雞吃的比一般部門員工都要好,我還不能偷吃。” 養到最後,同樣大小的鬥雞,體重是三黃雞的兩倍,老闆買幾隻本地雞跟鬥雞鬥,有時幾下子就被乾掉了。因為鬥雞戰鬥成績卓絕,他的老闆當年被稱為“湘西雞王”。
田耳還去過兩家報社。一家是市裡教育局主辦的報社,專門賣給鄉鎮學校的,最後垮掉了。那時候他換各種筆名,一版一版地寫稿子,其中不少是兒童文學。還有一個是小派出所的內刊,每一期印幾百份,是那種“給長官表功的”報刊。
“我跟同代作家最大的不同是,我進入社會很早,他們一直在讀大學。讀大學也許乾別的行當有用,寫作的話派不上什麽用場。”田耳說,“跟高爾基一樣,我讀的大學就是社會,做生意知人面世、揣摩人心,這都是寫小說最起碼的訓練。”他的故事都是從現實中碰到的,“我這人不會瞎編。”
除了前面提到的小說《被猜死的人》,他的其他許多故事也都是“邂逅”來的。例如《衣缽》講的是來自山村的年輕人在城裡讀了大專、又子承父業做起道士的故事。早在1999年讀大專租房子的時候,田耳就寫成了這篇小說,題材取自合租時遇到的道士之子。另有一篇題為《牛人》的故事是這樣的:2000年左右,一位鄉村婚慶歌手“牛人”的固定演出是下跪唱歌,邀請他前來演出的人們因為他的下跪而倍感光彩。“牛人”的原型是當年田耳開電器店時遇到的酒吧歌手,他與此人熟識已久,也常揣度他的心態——為什麽好好的人,非要下跪唱歌。“你要寫窩囊,你能寫透窩囊嗎?我們原來是喜歡這種表演的,現在覺得很惡俗。”他說,“就像長途大巴過去會放二人轉,原來我們是喜歡的,現在受不了了。”
隻不過,在他成為專業作家之後,邂逅故事就不那麽容易了——人們會因為他是作家,而改變對他說話的方式,並過濾掉一些資訊。“我特別怕有的老同志找到我家,要跟我講他的故事,開口就是‘我的一生那真是本很厚的書’。只要他說這話,後面就一個字也不要聽了。”現如今他更喜歡自駕,跟人喝酒聽人瞎扯,還找了一些固定的地方“蹲點”。有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個火車站,那裡還有很久以前生活的況味——“活到現在,真的跟我們童年時代沒什麽關係了,像是穿越一樣,人們越來越沉默,同學聚會還要拿個盒子把手機先收起來。”
雖然人們越來越沉默,田耳仍然相信,講故事的傳統並未消失,而是在以更豐富的形式滲透進入生活,“比如廣告,比如宣傳,比如評比,比如電視選秀(歌手嗓音都不錯,就比誰能將自己的經歷講得催人淚下),比如傳銷,比如騙子行騙,都在講故事,而且對故事品質要求很高。”田耳現在大學裡教寫作,發現有一個情況普遍存在——即便是中文系畢業的學生,寫了十多年作文,仍然不會講故事,無法讓材料形成故事,他認為這是無法應對將來的工作的,“以後即使是寫宣傳材料,也得用故事宣傳‘本行當的先進事跡和人物’。”
《夏天糖》
當年我做生意,中午在樓下食堂吃飯,隔壁有個發藝學校,中午這些學美發的學生也過來吃食堂,大家就一塊兒聊天。有個女孩講,她從沒上過幼稚園,童年唯一的遊戲就是躺在家門口的馬路中間。那個馬路是一個上坡,窄到只能過一部車,這個小女孩就喜歡讓司機一次次把車停下來,把她抱起來放到草地裡。當時我一聽,覺得這個畫面太好了,表面不露聲色,實則內心狂喜。邂逅一個好的小說故事或題材,就像是偷偷拿了別人的好東西。只要這一句話、這一個場景,一篇好小說該有的全都有了,就等著我構思了。

《夏天糖》
田耳 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1年
在《夏天糖》裡,我就寫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司機,輟學開車,生活非常枯燥。一天經過一個上山的山坡,看到有一個小女孩穿一件綠衣服睡在坡頂,他就下車把女孩抱起來,放到路邊。這樣偶遇數次,司機將女孩抱開數次,他就期待繼續遇上睡在馬路中間的女孩,這甚至成為了他的生活裡唯一的一抹亮色。後來呢,女孩就成了路邊店的小姐,司機要拯救她,因為她當年睡在馬路中間的形象,幾乎是他一種理想的寄托,是他腦袋裡最深的圖景,容不得玷汙。可是女孩覺得這個工作適合她,別的還嫌累,嫌賺錢不夠。
為什麽當初一聽到發藝學校的小女孩講到這個場景,我就覺得該有的全有了?你想,她小時候為什麽喜歡司機一次次把她抱起來?我想,其實潛意識裡她對於男性是不拒絕的,這都是從那一句話裡得出來的。所以,他倆最後又回到這個點上,找了一段路,想要體驗當年的感覺,司機要當了發廊女的妹子躺到前面馬路中間,讓自己再將她抱開。最後的結尾你肯定能想到:車軋過去了,因為他們回不去了。
《被猜死的人》
《被猜死的人》是我在2007-2008年間寫的,當時在讀一個作家研究生班,學習的地方選在一個敬老院裡。幾十畝地,兩人一間房,文學環境特別好。我就想,這麽好條件的養老院,為什麽老人家不來,讓給作家?後來知道這地方雖然環境好,風水不行,進去老死人,老人家就跑光了,換我們去住,所以說當作家也不容易。兩人一間房,我老打呼嚕,室友晚上總失眠。有天晚上我突然睡不著,就開始想,我睡這個床死沒死過老人家?沒聽見室友打呼嚕,我還去探了一下他的鼻息……這就構思出了《被猜死的人》,想老人院裡一群老人坐在一塊兒沒什麽事兒,就猜誰先死吧,拿死開玩笑。

《被猜死的人》
田耳 著
大方·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8月
《衣缽》
《衣缽》是我讀大專時跟同學租房子,發現這麽個題材。和我一起租房的是一個道士的兒子,這個人對爸爸充滿敬意,老說行道士行的種種特異的本事。我們70後一代都是怕爸爸恨爸爸,很少提到父親,就他一個人老提,還引以為榮。他的道士父親其實特別窮,有時進城,還和我們住到一塊。我當然就奇怪,為什麽他這麽愛自己父親?我覺得,當道士確乎和一般人不太一樣。能寫成《衣缽》是因為我接觸到了一個道士和他的兒子,這麽好的題材和人物關係,瞎想也想不出來。
《牛人》
寫《牛人》時,我還在做冷氣機的店裡,那時候店二樓是個酒吧,晚上有客戶,我就請他們上去。酒吧裡有很垃圾的表演,比如給小費,讓歌手跪在你面前唱。很多人就衝著這個請朋友來,因為當時還認為這很有面子,你去敬酒,他就跪著跟著你走,人們很享受這個。那個歌手跟我也熟,也時常到我店裡坐一坐。我覺得他也算當地名人呢,就揣摩他的心理,想來想去就想出了這個故事。這個歌手人物早就有了,最後就等一個極端的故事環境,一個能讓他的下跪行為有極為充分的發揮的環境。很多人都是為寫而寫,現在人多難溝通難交流、難被人打動,你自己都不興奮,別人怎麽會看呢?現在,遇到好的故事、與小說題材邂逅的幾率越來越低,因為大家在一塊不聊天了,都在看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