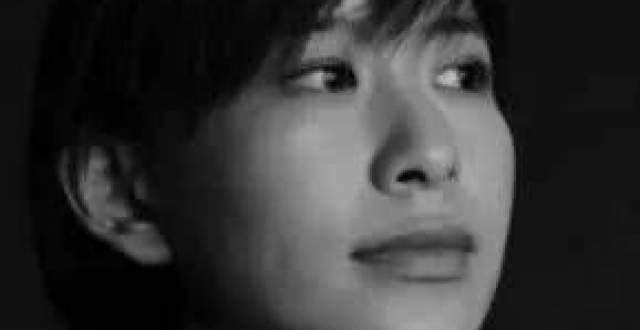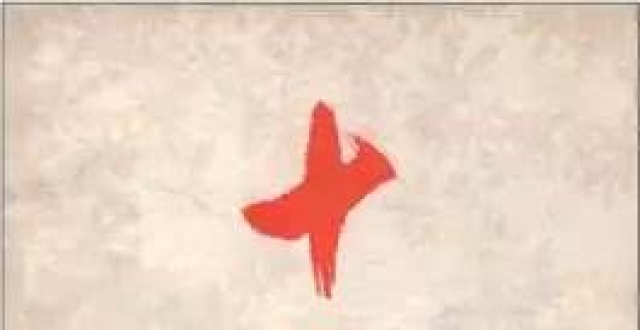林賢治/文
雜文的寫作,對中國現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魯迅來說,可以說是一個身份性標誌。
在新文學運動初期,魯迅同時進行小說、新詩和隨感錄等多方面的寫作,但是很快地就告別了新詩,隨後也告別了小說,惟是集中地寫他的雜文。鬥爭的緊迫,心情的蕪雜,已經不容他耽留在記憶和寂寞裡了,因此,放棄創作而抓住一種便利於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雜文樣式,對於一個啟蒙戰士來說,實在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然而,反對他的人據此譏評他為“雜感家”,喜歡他的人也無不以他的中斷創作為憾。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一樣忽略乃至抹殺了魯迅雜文的真實價值。
的確,雜文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正如魯迅指出的,是“古已有之”的一種文體。所謂“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文論家劉勰便把十六種文體劃歸雜文範疇,並且把它們都看作是“文章之支派”,“暇豫之末造”。
在魯迅那裡,雜文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用法。廣義相當於“雜著”,魯迅說他編書時,“隻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於是就成了‘雜’”。狹義是文體的用法,準確一點說,是應當叫作“雜感”或“短評”的。魯迅說:“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這裡包括了三個要素:一是批評性,二是輕便性,三是隨意性。作為一種文體,雜文因魯迅的實驗性的運用而變得更純熟、更完整、更豐富,既富含思想又饒具藝術的意味,從而帶上範式的意義。
中國現代雜文史是同魯迅的名字連在一起的。許許多多用於批評的、駁難的、諷刺的文字,常常被稱為“魯迅風”。事實上,魯迅的雜文是無法仿製的,他明顯地帶有個人天才創造的特徵。不問而知,魯迅雜文的首要特點是它的批判性、思想主動性、直接性。他對雜文的要求是“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這種對社會上日常事變的敏感,來自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這一根本立場不可能屬於單一組織或團體的,而是人類的、社會的、民間的,但又是全然立足於個人的。惟其是個人的批判立場,才能始終保持一種獨立性,並藉此與強權者相對抗。
瞿秋白說魯迅的雜感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但是必須看到,魯迅的戰鬥是個人性的,他的雜文不僅僅表現為觀念和理論上的鬥爭,而且有著靈魂的搏戰,因此獲得一種自覺的“荒涼和粗糙”,那為他所不懼憚也不想遮蓋的“風沙中的瘢痕”。
其次是互文性。魯迅雜文的材料來源十分豐富,從神話傳說、文史知識、社會新聞、個人瑣事,直至身體語言,由“面子”、頭髮、胡須、牙齒而腰臀、膝蓋、小腳,簡直無所不包。我們說魯迅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作家,卻並非是那類羅列知識的博學家;所有這些知識材料,在他那裡都因戰鬥的調遣而作著十分機敏的處理。文本性、副文本性、超文本性,材料的互動作用,在魯迅雜文中蔚為奇觀,形成一個龐大而幻變的互動系統。
我們注意到,魯迅視“正史”為偽史而常常使用野史、筆記的材料;還應當看到,他充分利用了現代傳媒相對發達的條件,即利用新聞和雜聞的材料進行寫作。尤其雜聞,那種無法分類、不合規則、沒有條理、荒誕離奇竟或平淡無奇的事件,是魯迅所重視的。當他一旦從某個邊緣地帶和反常狀態中發現了它們,便迅即發掘那裡的觸及人類深層狀態的隱匿的潛力,揭示控制人類生存的公開或神秘的法則,總之力求突出其否定的本質。同野史、筆記的“反歷史”(Contre-histoire)的使用一樣,魯迅對於新聞和雜聞的使用,將駁雜的材料在秩序的顛覆與重建中交織到一起,目的則在於反現實。
瞿秋白說魯迅雜文是“文藝性的論文”,所謂“文藝性”,最大的特點是形象化的概括。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評述,魯迅常常使用兩個手法:一是形象化,一是類型化。譬如說中國社會是“鐵屋子”,漆黑的“大染缸”,說中國文明是“人肉的筵宴”,說權力者的精神毒害為細腰蜂式的“毒螫”,武力討伐為“血的遊戲”,專製統治的原則是“動物主義”;又稱“吃英雄飯”的老英雄為“吃教”,稱創造社的革命文學家有“創造臉”,是“才子加流氓”,他們對革命和文學的態度是“腳踏兩隻船”;稱周揚等“拉大旗作為虎皮”,“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雜文中的許多概括性的說明,都運用了比喻,由此及彼,以使意義豁顯;但也慣常地把本質性的特徵直接抽取出來,劃分類型或製造典型,單刀直入,十分精警。對於中國歷史,他只須拿兩句話來概括,便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這樣的例子很不少。
魯迅說“砭錮弊常取類型”,又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其中有一種特殊的類型化手段,就是瞿秋白發現的,他在“私人論戰”中使重要的論敵的名字變做了代表性符號,如章士釗、陳西瀅、“四條漢子”等等,都有著特定的文化內涵。
所謂“知人論世”,魯迅的雜文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度的概括力,顯然同他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環境的深入認識有關,尤其在中國人的精神方面。所以,他可以很自信地說:“中國的大眾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裡了。”偏激性,也是魯迅雜文的一大特點。他自白說:“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還特意提出“偏激”與“中庸主義”相對論列。著名的例子是《青年必讀書》的答卷:“我以為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典型的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為此,同“痛打落水狗”一類結論一樣,招來不少謗議。
其實,偏頗不僅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方法,因為我們所面臨的世界,並非出於公平和公正的初始狀態,因此他必須向弱勢者、反叛者或改革者傾斜。當群眾因愚庸或卑怯而固守弱者的地位,甚至漠視乃至反對為他們的利益而犧牲的人時,是特別為他所嫉恨的。他在《即小見大》中說:“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後,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像《戰士和蒼蠅》《別一個竊火者》《拿破侖與隋那》等前後許多文字,都表達了這樣一種戰士的孤憤。
魯迅雜文中備受注目的特點,恐怕莫如諷刺了。論戰的文字自不必說,就算文化隨筆,也不同於蒙田,論說人生也不同於培根,他缺少西哲的那份從容淡定,那份形而上,在自由言說中仍然迫不及待,隨處閃耀諷刺的機鋒。
魯迅的諷刺不乏直接的攻擊,可以寸鐵殺人,但是也有許多諷刺在隱蔽處閃現,尤其當他身處嚴密的書報審查制度之下,如他所說,“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這類諷刺,在魯迅那裡常用於三種情況:一是好用反語,私人論戰中應用尤廣,或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反話正說,正話反說,完全的“推背圖”式。二是隱喻,這是“鑽網”的最好的法子。三是與此相關的影射。小說中的形象如《奔月》的逢蒙、《理水》的文化山上的眾學者,都能讓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他們的原型;雜文也如此,《阿金》之所以被禁止發表,魯迅聽說過,這同當局猜想影射第一夫人宋美齡有關。還有一種放大的影射,即是借古諷今,利用千百年專製歷史的前後時段的相似性,順利進入現實禁區。如說秦史、魏晉史和明清史,在魯迅雜文中是比較突出的。
諷刺這一手法,使魯迅的雜文特別地富於生氣,大大驅除了小說般的幽黯,而處處充溢著短促而明亮的笑聲。托馬斯·曼說,諷刺的笑聲,正是“人文主義鐵匠店裡鑄造出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馮雪峰說魯迅的雜文是詩和政論的結合,指出了詩意作為一個基本元素的存在,構成為其他雜文家的作品所稀缺的品質。事實上,魯迅雜文中的詩意表現不只限於政論,還有史論,以至對哲學文化內容的滲透。在雜文中出現的詩有兩種:一種是語言形式上的,如《聖武》《夏三蟲》《小雜感》《無花的薔薇之二》《火》《夜頌》《半夏小集》等,凝練、睿智,直接的啟示或充滿暗示。尼采的影響隨處可見,直至最後說的“最高的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仍然是尼采式的。還有一種表現是環繞湧流於字行中間的,那是作者的天生仁愛的外化,以非戰鬥的內涵契合於戰鬥,是一種人性化氛圍,一種溫和的氣息,一種柔情,對整體的文字結構而言,造就一種內在的剛柔兼濟的節奏。
以上種種特徵,是通過富於個人筆調的語言組織起來的。自然,無論何種文體,都需要某種特殊的敘述語調,但對雜文來說,似乎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它沒有像小說的情節,詩的分行,或戲劇的對白一般可以作為文體的顯著的外部標誌,惟靠筆調把自身同其他言論性文字區別開來。魯迅把自己的雜文同創作分開,可能是從藝術想象的角度出發;實際上,小說是虛構性的寫作,雜文則是非虛構性寫作,應當一樣劃歸文學創作的。筆調是文學性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個人化、風格化的表現。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魯迅的筆調是獨異的,文白夾雜,莊諧並用,這在雜文中尤其突出。由於進攻性的需要,又因為心性孤傲,視群敵為無物,所以鋒利,明快,洗練,激越而又從容,有清峻通脫的一面;但是,由於文化環境的險惡,執拗地反抗屈從而不得不作深沉的韌性的戰鬥,所以文風也有很平實沉著的方面。加以天性多疑善怒,行文不免常常流露質疑和抗議的語氣,頻頻使用諸如“然而”“卻”“究竟”一類連接詞,形成魯迅時常自稱的“吞吞吐吐”“彎彎曲曲”的風格。
魯迅的雜文,不但具有巨大的思想價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審美價值。對於後者,鬱達夫有一段話說得很精彩:
“至於他的隨筆雜感,更提供了前不見古人,而後人又絕不能追隨的風格,首先其特色為觀察之深刻,談鋒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筆之簡潔,又因其飄溢幾分幽默的氣氛,就難怪讀者會感到一種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淒厲的風味。”
顯然,對於魯迅的雜文的評價,是並不在小說之下的。
至於同樣為鬱達夫所說的,雜文中“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的史的意義,就更不消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