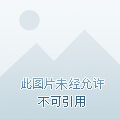儋州故城,渡海夜螢火
黎荔

前兩天,與書法家麻天闊主席、資深媒體人李朵,一起飛到海南島參加“海南省紀念蘇東坡北歸中原920周年”系列活動。北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農歷六月二十日,蘇東坡在海南寫下最後一首詩《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流淚登船,渡過瓊州海峽,永遠地告別了海南。彈指一揮間,920年悠悠歲月已悄然而過。8月9日(農歷六月二十日),正是東坡先生渡海北歸的日子,在海口參加完“海南省紀念蘇東坡北歸中原920周年專題學術報告會”後,我們一行驅車兩個小時前往當年蘇東坡寓瓊三年的所在地——儋州。

公元1097年,蘇東坡以瓊州別駕的虛銜貶昌化軍(今儋州市中和鎮)安置,生活之苦難,更超過黃、惠二州。初到時,暫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時一夜三遷,當地官吏張中景仰東坡,派人稍加修葺,第二年,即宋紹聖五年四月,朝廷派出湖南提舉董必武赴廣西察訪途中,在雷州得知東坡居儋州官舍,將東坡逐出,並追究了張中的責任。東坡父子無室可居,處境十分淒涼,東坡先生在城南買了一塊自己的地準備建房。當地百姓見狀,十分同情,得知蘇東坡在桄榔林中建房時,大家一起動手搭茅屋,僅一個月時間,即紹聖五年五月間,三間茅屋落成,儘管周圍荒蕪,蚊蟻滋生,環境惡劣,但詩人總算有了自己的家。由於茅屋處在“竹身青葉海棠枝”的熱帶喬木桄榔林中,東坡自命為“桄榔庵”。父子二人在庵中“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蘇東坡與當地人結下深厚感情,同年十一月,儋州州守張中和當地黎族逸士黎子雲兄弟共同集資,在黎子雲舊宅澗上建屋,既可作蘇東坡及其少子蘇過的棲身之處,也可作為以文會友的地方,蘇東坡根據《漢書·揚雄傳》中“載酒問字”的典故為房屋取名“載酒堂”。以後,蘇東坡便在載酒堂裡會見親朋好友,並給漢黎各族學子講學授業,傳播中原文化。當時海南被認為是“蠻荒之地”,因為交通不便,居民還過著原始的生活方式,很少接觸中原農耕文化,蘇軾描述當時情景為“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每無炭,夏無寒泉”。蘇軾在儋州居住三年多,以文會友和講學,傳播中原文化,培養人才,此後儋州就開始“書聲琅琅,弦歌四起”,海內外名士接踵而來,成為了全島文化的中心。當年東坡先生的幾大功績,一是教化當地人民,不以耕牛祭祀,二是種糧種瓜種菜,三是培養出了海南第一位舉人薑唐佐。蘇軾獲赦北歸後,他的弟子連續不斷的考上了功名,有宋一代,海南歷史共出十二位進士,使“蠻荒之地”放射出文化人才的曙光。至明代,桄榔庵舊址依然。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有人在此掌教,載酒堂便改稱“東坡書院”。1996年,東坡書院被國務院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部門。

8月9日當天下午,我們一行在東坡書院做完題為“海南詩心,茲遊奇絕——《長安說》紀念蘇東坡北歸920周年”的直播活動後,已經是七點半了,東坡書院的青年書法家裕明請我們在桄榔庵舊址對面的二爺大排檔吃飯。飯桌間,裕明說到儋州故城年久失修,目前正在整修期間,要不要去探訪一下。我們三人一聽,二話不說就出發了。
儋州故城,又稱中和古城,位於儋州中和鎮的西邊村附近。始建於唐,初為夯土城牆,明代增砌石包牆,清代多次重修。1927年、1951年、1952年部分城牆及東、南門被拆除。至今古城內外保留東坡井、魁星塔、桃榔庵遺址、州衙遺址等。雖然已有心理準備,這是一座破敗的古城垣,但最後所見到的荒蕪不堪,還是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在彌漫牛糞味的小路,走過稻田菜地、幽深林木,我們一路向前走,蟲鳴蛙噪漸次響起,晚間的天空高遠清澈,八月星光璀璨。不知在哪裡一拐彎,我們就站到了一個黑魆魆的城洞前面。儋州故城到了!

因為伸手不見五指,沒有辦法拍出照片,我只有借用了一張儋州故城白天的照片,在網上搜到的,現實狀況中比照片中要破敗得多。當時,在深濃的夜色中,一步步彎腰弓身,走進這神秘的城洞盡頭,我們去到了另外一個奇異世界——一座千年前的南荒古城。覺得闖入其中的我們,如同搬山卸嶺尋龍訣、勘輿倒鬥覓星峰的摸金校尉,前方等待我們的將是無盡的黑暗與幽魅。
2018年儋州發大水,已經把原有的古城牆衝塌,我們走近的城牆,是當地文物部門正在進行的補救性搶修,斷壁殘垣,搖搖欲墜在腳手架的支撐下,四周荒煙蔓草、藤樹牽纏。彎腰低頭,在一個個交錯的腳手架下穿行,進入這座北宋故城的幽暗深處,讓我想起宮崎駿動畫片《千與千尋》中,千尋和爸爸媽媽一同驅車前往新家,卻不慎誤入一條荒蕪小徑,穿過漆黑的隧道口,來到了一個中世紀的小鎮,遠處飄來食物的香味,滿條街都是飯店,卻沒有一個人,暮色四合,幽暗處漸漸浮現出一個個樣子古怪、半透明的人。千尋的故事中,隧道代表的是一個空間上的傳送點或月台,在現實世界偶有這樣的傳送點或月台,可以連接到神隱世界。眼前這座南荒故城隱藏在黑夜中,像一位年邁長者留下滄又桑歲月的傷痕。以其境過於淒清,讓人不敢久留。在如果穿過這黑暗中的城洞,可以溯遊千年的話,在那裡,我會遇上津津有味大啖生蠔和芋頭、搖頭晃腦吟詩作詞的東坡先生嗎?記得當時,我一馬當先,走在前面,因為是尋訪東坡先生而來,所以沒有絲毫恐懼不安,我甚至覺得城門深處,如果真有幽靈出沒的話,那個異世界一定是一個神秘又好玩的所在。

長夜裡一片清涼,挨近黑魆魆的灌木林,在露珠晶瑩的野草間,我們突然看到了許多明明滅滅、影影幢幢的幽靈,靜靜的、微微的,飄忽不定,如一朵小小的靈魂漫天飛舞。“是螢火蟲!”我們齊呼。多少年沒在野外見到螢火蟲了!螢很單薄,水汙染、光汙染、農藥化肥,都會致命,美麗的東西都脆弱。而且,現在即使還有流螢於公園水濱出沒,明亮的城市路燈下根本很難觀察到。只有真正的暗黑,才能看到螢火蟲微弱的小燈吧?在這個夜訪儋州故城的夜晚,草叢中的螢火蟲成群飛舞,猶如晴朗夜空中閃爍的星星,密集成一片,連在東坡書院工作長達十年的裕明,也奇怪地說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多的螢火蟲。
螢火亮了,隨風微蕩,點點流光掠過我的臉頰。那抹淡淡的光彷佛無處可歸的遊魂似的,在濃暗中不停地徘徊。在這座千年故城中,堪稱“宋朝第一人”的大文豪蘇東坡,在此居儋三年,開啟瓊州人文之盛。這裡曾閃耀南越首領冼夫人“親披甲,乘介馬”的英姿,這裡曾響徹蘇東坡敷揚文教的聲音,這裡曾駐守過海南前所、儋萬所等軍事組織,如今。只有流螢照亮瘋長的雜亂草叢,野花藤蔓淹沒以腳手架支撐的、隨時可能坍塌的古舊城牆。

在螢火的飛舞中,吟誦著蘇東坡920年前離島渡海、北歸中原的詩篇《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
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此時此際,一盞盞忽明忽暗的螢火,像極了精靈惺忪的睡眼。今夕何夕,真讓人生出時空穿梭、古今連通之感。東坡萬裡投荒,來到儋州州城,他創建的載酒堂、居住的桄榔庵、開挖的東坡井,依然保存至今。距離東坡渡海北歸的1100年農歷六月二十日,站在2020年8月9日這個時間節點,已經過去了整整920年,古今變遷早已天翻地覆。往事一去不複返,斯人風華卻長留人間。

清澈甘甜的東坡井。東坡謫居桄榔庵,有感於“百井皆鹹”,而當地百姓又習慣飲河塘水,常生病,便親自挖了這口井。東坡常汲井水釀酒,與王霄等友人“夜攜壺汲水於此”。東坡井是東坡居儋唯一保存完好的遺物。
記得看過科普文章,螢火蟲和一些深海生物使用的閃光信號中有玄機,是另一種語言,可惜我不能解讀這種語言。螢雖蟲,但民間很少以蟲稱之,其綽號數不過來:蚈、照、夜光、景天、挾火、宵燭、宵行、丹鳥、耀夜、熠耀……我最喜歡的還是“流螢”。一個“流”字,將其隱隱約約、稍縱即逝、亦真亦幻的飄曳感、夢遊感,全勾畫了出來。那光,或說青色,或說黃綠,還有說冰藍,我覺得皆似,又皆非。想去捕捉那道光,幾次伸出手去,但卻什麽也碰不到。撲不滅,追不著,那抹小小的光線,總在我指尖就快碰著的地方。我們千年奔赴而來,都想用手機拍下儋州故城的渡海夜螢火,但李朵兄以手機連拍,卻隻拍出一幀幀的黑暗,我用手機拍了一張,草叢中最亮的那點螢火,明明是一動不動被攝入鏡頭的,結果回到酒店一看,手機拍到的,卻是一道幽綠的光的軌跡。
這是值得記錄下來的事情。六月二十日蘇子渡海夜,隨緣與夜之精靈在草木間邂逅,在千年前的宋代儋州故城。我走入了東坡先生當年曾經歷過的南海夜暗,那黑暗裡,會發光。流螢如靈魂,靈魂如流螢,幽幽消失之後,那道光依舊在我心中滯留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