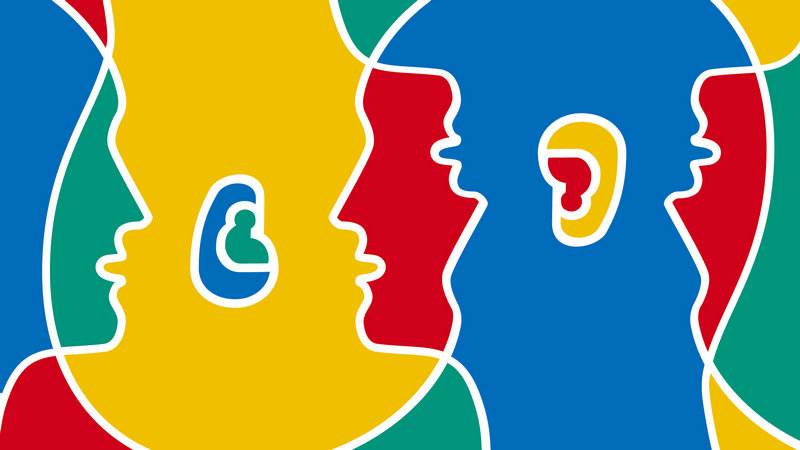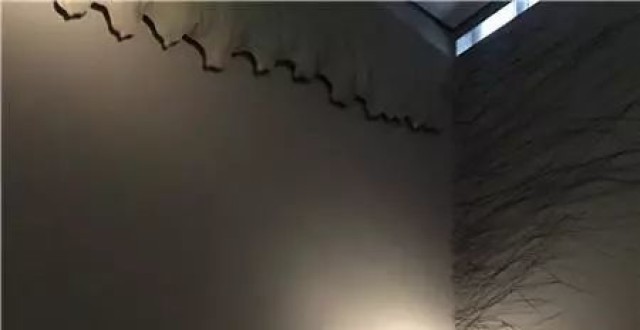反諷是一個古老而迷人的話題。古老,是因“反諷”一詞來源於希臘文的“eiro年”,意為“裝傻者”,指的是蘇格拉底的談話方式——在智者面前裝作一無所知地請教問題,結果反而推演出相反的命題,即一種最初的表象與事實不符的言語結構範式就會出現。迷人,是因在反諷的歷史上,從古希臘蘇格拉底式反諷開始,以施萊格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以布魯克斯為代表的英美新批評派以及存在主義鼻祖克爾凱郭爾等都癡迷於從各自的哲學、修辭學等領域對其進行闡發。於是,關於反諷的理論從各個不同角度得到了詮釋。可見,反諷的概念是一個不斷發展著的概念,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反諷理論的譜系。
原文 :《後現代反諷——一種文化政治的實踐》
作者 |浙江師范大學教授 王洪嶽 溫州市職業中等專業學校 周丹丹
圖片 |網絡
反諷作為一種政見
反諷的理論也吸引了加拿大後現代理論家琳達·哈琴。她研究內容涉及到後現代主義文化和藝術的多種表現形式,包括歌劇、繪畫、小說等,從中尋繹出反諷作為這些文化和藝術形式的主要特徵,這是由於哈琴立足於她的後現代主義立場,把反諷視為一種後現代文化政治的廣泛的話語實踐。

“文化政治”是一個後現代概念,它指的是一種微觀政治,與社會政治強調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政黨、國際關係等問題不同的是,文化政治關注的是文化領域中的權力關係的問題,包括性別、種族、生態等話題,我們的文學、繪畫、音樂、戲劇、攝影甚至日常生活,都可以成為各種權力相互較量的空間。而哈琴認為這種後現代的“文化政治”可以通過反諷來實現,所以在她那裡,反諷並非浪漫主義者眼中的通向真理和自由的生存態度,也並非新批評派眼中為達成審美訴求的文學結構的基本原則,而是作為後現代文化政治的話語實踐或策略。這樣,後現代反諷打通了文化與政治的封閉空間,在反諷文本的呈現中折射出政治主張的演繹過程,因而反諷作為一種政見,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文化進入甚至乾預社會政治的窗口。
後現代反諷:重新審視世界
後現代反諷拋卻了那種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抨擊某個政治現象或觀點的做法,采取一種“同謀性批判”的立場,即反諷肯定的與破壞的政治功用是不可分割的。反諷能夠實現這種“同謀性批判”的首要條件是語境的切換,即把對象話題從現實的社會政治語境中抽離開,書寫到文化文本的語境當中,然後又通過文化文本的藝術表現形式使人們得以重新觀照社會政治中存在的問題。

語境是反諷意義構建與傳達的關鍵一環,後現代反諷依然強調了語境的重要性。早在哈琴之前,新批評派的布魯克斯就已經把反諷定義為“承受語境壓力的語言”,是“語境對於一個陳述語的明顯歪曲”。但布魯克斯僅僅將反諷限定在單一的文本結構當中,考察日常語言如何生成為文學語言,因此他所說的“語境”指的是具體文本上下文的語境。哈琴則進一步地擴大了語境的範圍,涵蓋了社會、歷史、政治等因素,考察的是政治語言如何生成為文化語言及藝術語言,或者說文化語言及藝術語言如何駕馭政治語言。
美國系列電視動畫片《辛普森一家》則非常典型地詮釋了文化語言及藝術語言對政治語言的消化與重構。自1989年首演以來,這部由美國福克斯公司精心製作的動畫片成為老少皆宜的熒屏常青樹,活躍在人們的娛樂視野中。它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在一個以虛構的斯普林菲爾德小鎮為地理坐標的動畫故事中加入了許多成人化的思考,不僅對婚姻、道德、個體意識等價值觀念做出了獨到的理解,還對美國社會生活中同性戀群體、勞工問題、政府制度、醫療體系等亞文化層面的問題一一予以揭露,從而極大地提升了自身的內涵與格局。在由社會政治語言向文化語言的生成過程中,“反諷”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辛普森一家》所講述的故事雖然對美國的當下現實甚至政客明星進行了調侃、揶揄,但它並非真刀實槍地對抗這種主流意識形態,而是在現實的社會語境向虛構的動畫語境的轉換中,以藝術表現的方式重新審視社會政治內容,並采取一種幽默滑稽的輕鬆格調做出別具一格的後現代意味的解讀。後現代的意味指的就是一種對權威、秩序、統一表示深切質疑的後現代精神。該劇的編劇喬治·邁耶曾談到,這部動畫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們重新審視這個世界,尤其是他們世界中的權威形象。主創馬特·格勒寧也曾表示,他希望能夠在輕鬆娛樂的背後提醒人們,讓他們注意到可能正受到哪些方式的操控與剝削。《辛普森一家》以反諷的方式完成了一種後現代的實驗。比如,在第一季中通過巴特與尼爾森模仿希特勒式的軍事訓練打群架的滑稽場面,質疑了戰爭的意義,以此來呼籲和平。再比如霍默坐在牧師講道的教堂裡,耳機裡播放著球賽報導,球賽講解員的激情解說與牧師的誇張動作配合得天衣無縫,這諷刺了作為神聖機構的宗教所存在的弊端。這樣,反諷在現實語境向動畫語境的轉換中,使原來的現實問題在動畫文本中得到了重新的定位與詮釋。

在後現代社會的大背景下,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讓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加地緊密,話語呈現多元噴發的局面,語境也變得更加複雜多樣,任何語境都可以成為反諷的出發點。哈琴所關注的反諷的語境包括了許多領域,比如文學、音樂、繪畫、歌劇等等。反諷既發生在高雅的審美形式當中,也發生在流行文化當中,這些使用了反諷的文化文本成為政治權力的格鬥場,雖然在藝術的表現形式當中總是反向地否定和嘲諷了文本所呈現的對象,但它更多地不是要以自己取代某種政見,而是要“通過加強或削弱各種各樣不同的利益,巧妙地效力於範圍廣大的種種政治立場”,哈琴將後現代反諷的這種特性稱之為反諷的“跨觀念的”特性。

於是,這種反諷常常被認為是以不羈的遊戲態度解構或戲弄各種政見而飽受責難,但哈琴認為:“‘反諷的遊戲’是極其錯綜複雜地包含在目的和主題的嚴肅性當中的。事實上,後現代主義的反諷也許是當代的人們走向嚴肅的唯一途徑。必須思考‘過去的陳詞濫調’,而且只能以反諷的方式重新思考。”因此,反諷是以遊戲的方式表達嚴肅的思考。如果說哲學反諷是要通過對現實的質疑來達到真理,那麽哈琴的後現代反諷則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它要通過在對現實社會政治的再描述和嚴肅思考中拷問和消解既有的所謂真理,從而想象一種新的真實的存在景象或境界。儘管二者的最終目的不同,但它們似乎都繼承了施萊格爾浪漫主義反諷中把反諷當作一種“永恆的靈活性的清晰意識”的精神氣質,具備一種共同的超越自我的精神訴求和否定的勇氣。反諷自身具備的這種理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從蘇格拉底開始一直延續到了哈琴的後現代反諷,在反諷從最初的修辭學領域不斷向哲學、美學、社會文化和藝術領域的滲透過程中,表明了反諷到了後現代反諷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9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