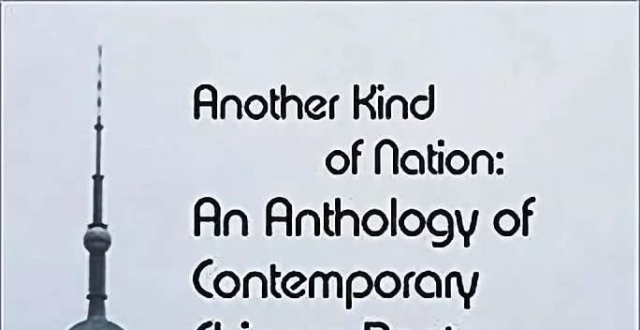物
致
於
此
小
得
盈
滿
明代詩話中的《詩經》文學品評
胡祥雲
“詩話”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詩歌批評形式,一般地說,是“評論詩歌、詩人、詩派以及記錄詩人議論、行事的著述”。因此,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的《詩經》,不可避免地會被後世學人在詩話中反覆論及。迨至明代,人們對詩話的寫作已很普遍,而此時人們對《詩經》文學性的認知也漸臻一致,故而在明代詩話中,對《詩經》文學品評的內容是極為豐富的。
明代詩話對《詩經》的文學品評,主要圍繞以下四個話題來展開:
一、對《詩經》的產生歷史進行文學性的探源;
二、對《詩經》的審美意蘊進行多視角的揭示;
三、對《詩經》的表現手法進行悉心細致的體味;
四、闡述《詩經》對後世詩風詩情的智慧啟迪。
下面,我們將對明代詩話中的這四個話題分別作一梳理。

一、對《詩經》產生歷史的文學性探源
對《詩經》產生的歷史,可以從多個視角進行考察,人們常見的視角為考察《詩經》中的作品是如何獲得的,現在一般認為《詩經》三百零五篇源自三處:一是貴族統治者為配合禮樂而專門製作的詩歌;二是公卿列士為補察時政所獻的詩;三是民間采集的歌謠;這一表述是就《詩經》具體作品的獲得來考察的。另有一個視角是考察《詩經》所收作品的表意文體形式源自何處,它包括對《詩經》中的詩歌形式、情感狀態和語言材料的起源問題進行考察,這是對《詩經》產生歷史的文學性探源;對此,明代詩話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徐禛卿在《談藝錄》中提出:
詩理巨集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卿雲》江水,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跡,興廢如存,佔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元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征,被之於簧弦,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此古詩之大約也。
在這裡,徐禎卿明確指出,《卿雲》、《烝民》、《麥秀》等古代歌謠,開啟了《雅》《頌》和《國風》,因此,《詩經》中的詩歌形式是汲取古代歌謠的營養而茁壯成長的。對於這一觀點,謝榛表達了相同的看法:
四言體始於《康衢歌》,暨《三百篇》則盛矣。滄浪謂起自韋孟,非也。
而王世貞在《藝苑巵言》中說:
古逸詩箴銘謳謠之類,其語可入《三百篇》者:“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薑,無棄蕉萃。”“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棠棣之華,翩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魚在在藻,厥志在餌。”“九變複貫,知言之選。”“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在這裡,王世貞雖然沒有直接說古代歌謠開啟了《詩經》的詩歌形式,但他在“古逸詩箴銘謳謠”中,找到了一些與《詩經》表情達意相類似的語句,並認為它們“可入《三百篇》”,這就使《詩經》的詩歌形式之源,由古代歌謠擴展至“古逸詩箴銘”等古代文獻,這為後人探討《詩經》詩歌形式之源開拓了更廣闊的視野。
除了以上各家對《詩經》的詩歌形式進行沿波討源之外,還有人從詩歌創作的情感產生機制上對《詩經》的情感狀態進行了探索,揭示出《詩經》更有緣情生成的內在機制。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說: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蕩血脈,流通精神,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
我們知道,關注於詩歌的情感產生與表達,是一種文學性的關注,也是對詩歌進行文學品評的最得力的抓手。李東陽以上這段文字,不但論述了詩與樂之間的關係,還指出了《詩經》具有“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蕩血脈,流通精神”的情感特徵,這是對《詩經》最好的文學闡釋。
除了李東陽之外,謝榛在《四溟詩話》中也指出:“《三百篇》直寫性情,靡不高古,雖其逸詩,漢人尚不可及。”在這裡,謝榛明確地告訴人們,《詩經》之所以“靡不高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直寫性情”,這是直奔《詩經》文學本質而去的一句的評。
在對《詩經》進行文學探源的論述中,還有人對《詩經》語言材料的出處問題進行了探討,楊慎在《升庵詩話》中就作了這樣的考察:
宋人論詩雲:“今人論詩,往往要出處,‘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此語似高而實卑也。何以言之?聖人之心如化工,然後矢口成文,吐辭為經,自聖人以下,必須則古昔,稱先王矣。若以無出處之語皆可為詩,則凡道聽塗說,街談巷語,酗徒之罵坐,裡媼之詈雞,皆詩也,亦何必讀書哉?此論既立,而村學究從而演之曰:“尋常言語口頭話,便是詩家絕妙辭。”噫!《三百篇》中,如《國風》之微婉,二《雅》之委蛇,三《頌》之簡奧,豈尋常語口頭話哉?或舉宋人語問予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予答曰:“‘在河之洲’,便是出處。”此言雖戲,亦自有理。蓋詩之為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關關,狀鳥之聲;雎鳩,舉鳥之名。河洲指鳥之地,即是出處也。豈必祖述前言,而後為出處乎?然古詩祖述前言者,亦多矣。如雲“先民有言”,又雲“人亦有言”,或稱“先民有作”,或稱“我思古人”。《五子之歌》述皇祖有訓,《禮》引逸詩稱:“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小旻》刺厲王而錯舉《洪范》之五事,《大東》傷賦斂,而歷陳保章之諸星,此即古詩述前言援引典故之實也,豈可謂無出處哉?必以無出處之言為詩,是杜子美所謂“偽體”也。
在楊慎看來,“聖人之心如化工,然後矢口成文,吐辭為經”,但“自聖人以下,必須則古昔,稱先王矣”;此言怎一聽似乎是在鼓吹聖人先知先覺,但其實不然,因為楊慎接著說道,“蓋詩之為教,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關關,狀鳥之聲;雎鳩,舉鳥之名。河洲指鳥之地,即是出處也。豈必祖述前言,而後為出處乎?”這就明確告訴我們,《詩經》是對現實世界的反映,它的語言材料首先來自於活生生的現實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才使“聖人之心如化工,然後矢口成文,吐辭為經”,因此《詩經》“豈必祖述前言,而後為出處乎”?也就是說,在楊慎看來,《詩經》不必完全都要“祖述前言”;實際上,楊慎也並沒有否定“祖述前言”的重要性,而且,他也曾指出“古詩祖述前言者,亦多矣。”因此,從楊慎的這段論述中,我們看到了《詩經》語言材料的兩個來源:一個是鮮活的現實生活,另一個是“祖述前言”。
從上面的梳理中,我們看到了明代詩話對《詩經》產生歷史所作的文學性探源的結果:《詩經》的詩歌形式源自於“古逸詩箴銘謳謠”,《詩經》的情感內容源自於人自身的“感發志意”,《詩經》的語言材料源自於鮮活的生活與“祖述前言”。

二、對《詩經》審美意蘊的深刻揭示
明代詩話在對《詩經》的文學品評中,十分重視對《詩經》審美意蘊的揭示。所謂《詩經》的審美意蘊,是指在《詩經》中所展現的對事物的審美感知和源於心靈深處的審美體驗,以及這種審美感知和體驗在日積月累中形成的審美範式,從而成為後人論詩的一種準的。
在論及《詩經》對事物的審美感知中,明代詩話特別注重《詩經》所蘊含的“真”與“誠”的審美取向。如柯潛在《歸田詩話序》中說:“古詩《三百篇》,孔子取‘思無邪’一言有蓋之。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誦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要,豈有外於誠乎?”審美取向除“誠”之外,與之相應的還有對“真”的追求,然而《詩經》所追求的“真”,乃是藝術的“真實”,對此,陸時雍作了很好的揭示:“詩貴真,詩之真趣,又在意似之間。認真則又死矣。柳子厚過於真,所以多直而寡委也。《三百篇》賦物陳情,皆其然而不然之間,所以意廣象圓,機靈而感捷也。”因此,《詩經》所追求的“真”,是“在意似之間”的“真”,是在“然而不然之間”的藝術的“真實”,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意廣象圓”的審美效果。
《詩經》在感知事物時強調“真”與“誠”,這種審美感知的結果潛入心靈,便釀出氣韻生動的審美體驗,對此,陸時雍也作了很好的闡述:
《三百篇》每章無多言。每有一章而三四疊用者,詩人之妙在一歎三詠。其意已傳,不必言之繁而緒之紛也。故曰:“《詩》可以興。”詩之可以興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韻也。夫獻笑而悅,獻涕而悲者,情也;聞金鼓而壯,聞絲竹而幽者,聲之韻也。是故情欲其真,而韻欲其長也。二言足以盡詩道矣。乃韻生於聲,聲出於格,故標格欲其高也;韻出為風,風感為事,故風味欲其美也。有韻必有色,故色欲其韻也;韻動而氣行,故氣欲其清也。此四者,詩之至要也。
有了這種審美體驗,一旦訴諸文字,形成詩文,必然是曲盡情思,韻味雋永,這正如徐禛卿所揭示的:
“《鹿鳴》《頍弁》之宴好,《黍離》《有蓷》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歎,《蟀蟋》《山樞》之感慨……,皆曲盡情思,婉孌氣辭。哲匠縱橫,畢由斯閾也。”
《詩經》中真切的審美感知和深刻的審美體驗,使得《詩經》的審美意蘊極為豐厚,當這一審美意蘊被人發掘而冠為“風雅”,並被推為典範的時候,於是“風雅”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後人論詩的準的。
“風雅”是《詩經》審美意蘊的最簡要的概括。在明代詩話裡,有時也用“《國風》之意”、“《三百篇》之意”等類似的話語來表達《詩經》的審美意蘊,於是,“《國風》之意”、“《三百篇》之意”等類似的話語也就成了衡量後世詩歌的審美標準。如楊慎在《升庵詩話》中說:
“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躭歌舞,猶恨春陰咽管弦。”與聶夷中“二絲五穀”之詩並觀,有《三百篇》意。
“南樓西下時,月裡聞來棹。桂水舳臚回,荊州津濟鬧。移帷向星漢,引帶思容貌。今夜一江人,惟應妾身覺。”有《國風》之意,怨而不怒,豔而不淫。
除了“風雅”之外,《詩經》中“頌”的審美意蘊也是極為豐富的,所以明代詩話自然不會放過對“頌”的探討,並且把“頌”也推為論詩的審美準的。如王世貞《藝苑巵言》說:
屈氏之《騷》,《騷》之聖也。長卿之賦,賦之聖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故自作者,毋輕優劣。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有六義,《頌》簡而奧,瓊哉尚矣。《大雅》巨集遠,非周人莫為。《小雅》婉孌,能或庶幾。《風》體優柔,近人可仿。然體裁各別,欲以漢魏之詞,複興古道,難以冀矣。西京崛起,別立詞壇,方之於古,覺意象蒙茸,規模逼窄,望湘累之不可得,況《三百》乎?
這樣,明代詩話通過對《詩經》中的審美感知、審美取向和審美體驗的考察,揭示出沉潛在《詩經》作品中的審美意蘊;對這一審美意蘊最簡潔的概括,就是後人津津樂道的“風雅”二字。

三、對《詩經》表現手法的悉心體味
對《詩經》表現手法的研究,是《詩經》文學品評的重要內容,對此,明代詩話作了具體而又深入的探索。
首先,明代詩話對《詩經》的詩法作了充分的揭示。所謂詩法,是指創作詩歌的常用方法,就《詩經》而言,這常用的方法就是人們常說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自從《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提出“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後,人們對《詩經》的表現手法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最後把“賦比興”確定為《詩經》的常用手法。在明代詩話中,對這一在歷史中形成的結論是完全接受的;但是,他們不僅僅只是接受現成的結論,而是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辨析。如楊慎在《升庵詩話》中說: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鍾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並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楊慎不喜宋人詩論,時時對之發難,於此段文字可見一斑。在楊慎看來,《詩》與《易》《書》《春秋》等書的區別在於“《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楊慎認為,因為《詩經》采取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的“比興”手法進行表情達意,而不是採用“類於訕訐”似的“直陳時事”的手法,所以《詩經》的“比興”手法為高;並且,他通過一系列的例句進行對比,讓讀者領略到“比興”手法的藝術魅力。應該說,楊慎強調《詩經》“比興”手法的重要性,理應無可厚非,可若乾年後,王世貞卻對之進行了發難,他說:
楊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雲:“詩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其言甚辯而覈,然不知向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
王世貞的此番反駁,是不給楊慎一點面子的。王世貞之所以義正辭嚴地駁斥楊慎,是因為他抓住了楊慎隻講“比興”不講“賦”這一破綻;由此可見,“賦”的表現手法與“比興”一樣,是同等重要的。楊慎、王世貞的批駁與再批駁的過程,實際上是對《詩經》表現手法更深入地辨析的過程,從中讓讀者對《詩經》的詩法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楊慎雖不喜宋人論詩,但對杜甫並不像王世貞所說的有譏諷之意;相反,楊慎在其他地方論及《詩經》詩法時,對杜甫是褒揚有加的,如:
杜少陵詩曰:“不及前人更勿疑,遞相祖述竟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此少陵示後人以學詩之法。前二句,戒後人之愈趨愈下。後二句,勉後人之學乎其上也。蓋謂後人不及前人者,以遞相祖述,日趨日下也。必也區別裁正浮偽之體,而上親《風》《雅》,則諸公之上,轉益多師,而汝師端在是矣。此說精妙。杜公複生,必蒙印可,然非予之說也。須溪語羅履泰之說,而予衍之耳。
此處雖是楊慎轉述他人之論,但從中我們既看到了楊慎不掠人之美的誠實學風,也看到了他讚同杜甫“別裁偽體親《風》《雅》”的學詩之法,從中我們能領略到楊慎對杜甫是十分尊重的。
其次,明代詩話在對《詩經》的細讀中讓人深切地感知《詩經》的表現手法。
“細讀”是對《詩經》具體篇章的逐句逐字的解讀,從中發掘《詩經》在謀篇布局和遣詞造句過程中的文學表現力。在明代詩話中,既有對《詩經》謀篇布局的深刻分析,也有對《詩經》遣詞造句的細心體味;在這方面,楊慎做的尤為突出,如在對《詩經》謀篇布局的分析中,這段文字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雲:“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似戾於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後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攜仆望岨,雖托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後妃思文王之行役而雲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仆痡”者,文王之仆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
對於《卷耳》一詩的章法結構,今天的讀者已了然於胸了,但在楊慎這段文字之前,人們的理解還是懵懵懂懂的。毛傳、鄭箋的解說迂曲難通,不足為訓;至宋代,朱熹在《詩集傳》中對毛傳、鄭箋提出了質疑,以為首章是“後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下面三章是“托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相比毛傳、鄭箋,朱熹之說與《卷耳》的章法結構更為接近。而楊慎結合原詩,審視朱說,認為“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攜仆望岨,雖托言之,亦傷於大義矣”,於是他提出此乃“後妃思文王之行役而雲也”,即《卷耳》後三章寫的都是後妃想象中的文王在外跋山涉水、酌酒解憂的情景,如同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的意思;至此,《卷耳》的章法結構才大白於天下。後來,方玉潤、錢鍾書等人在楊慎闡釋的基礎上洞徹幽微,《卷耳》一詩才得到神滿意足的解讀。
楊慎對《詩經》的遣詞造句體味得也很真切,如: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薑,洵美且都。”孟薑,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蓋冶容豔態,多出於膏腴甲族熏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會穿衣吃飲,苟非習慣,則舉止羞澀,烏有閑雅乎?
又如:
劉勰雲:“‘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喈喈’逐黃鳥之聲,‘嗷嗷’學鴻雁之響,雖複思經千載,將何易奪?”信哉其言。試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楊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
對於《詩經》的遣詞造句之法,王世貞也有深切的體會,他說:
《風》《雅》三百,《古詩》十九,人謂無句法,非也。極自有法,無階級可尋耳。
儘管王世貞認為《詩經》之句法“無階級可尋”,但他在《藝苑巵言》中還是不厭其煩地大量摘抄出《詩經》中一些精美的詩句,讓人真切地體味《詩經》遣詞造句的魅力;最後,他總結說: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吾故摘其章語,以見法之所自。其《鹿鳴》《甫田》《七月》……《執競》《思文》,無一字不可法,當全讀之,不複載。
第三,在明代詩話裡,著述者還對《詩經》的修辭和聲韻情況進行了考察。如對《詩經》修辭情況的考察:
江淹《貽袁常侍》詩曰:“昔我別秋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阪,春日媚春泉。”子美《哭蘇少監》詩曰:“得罪台州去,時違棄碩儒。移官蓬閣後,谷貴歿潛夫。”此皆隔句對,亦謂之“扇對格”。然祖於《采薇》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在這裡,謝榛在對“扇對格”的溯源中,析辨出《采薇》乃“扇對格”之祖。
“別觀蒲桃帶實垂,江南豆蔻生連枝。無情無意尚如此,有心有恨徒自知。”《詩》雲:“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此詩祖其意。
這是楊慎在梁簡文帝蕭綱的《和蕭侍中子顯春別》詩作中,看到了它對《詩經·隰有萇楚》之“反襯”修辭格的繼承;同時,這也是對“反襯格”的溯源。
對於《詩經》的聲韻情況,謝榛似乎比別人更加的關注。在《四溟詩話》中,他多次談及《詩經》的聲律與葉韻之事,如:
《三百篇》已有聲律,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暨《離騷》(應為《九章·湘夫人》——引者注)“洞庭波兮木葉下”之類漸多。六朝以來,黃鍾瓦缶,審音者自能辨之。
古詩自有所葉,如:“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對《詩經》的修辭和聲韻情況進行考察,表明明代詩話對《詩經》的文學品評,已經進入到“有意識為之”的自覺學術行為的層面。
第四,當歷史行進到明代的中後期,思想解放的浪潮衝刷掉了人們心頭塵封的積垢,面對《詩經》,人們已不像過去那樣戰戰兢兢的了。尤其當他們把《詩經》視為一部文學作品時,更是毫無顧忌地進行品評,故而一些“指瑕”的言論在一段時間裡絡繹不絕,如謝榛在《四溟詩話》中說:
《詩》曰:“遊環脅驅,陰靷鋈績。”又曰:“鉤膺鏤錫,鞹鞃淺幭。”此語艱深奇澀,殆不可讀。韓柳五言,有法此者,後學當以為誡。
此處不但批評《詩經》之語“艱深奇澀,殆不可讀”,甚至連效此之法的韓愈、柳宗元也一並黜落,謝榛的勇氣實在不小。
相比於謝榛的率猛,王世貞似乎顯得委婉些,但指出的疵點之多,卻又讓人怵目驚心:
詩不能無疵,雖《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載獫歇驕”;有太直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有太促者,“抑罄控忌”,“既亟隻且”;有太累者,“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有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類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無義,不死何為”之類也。《三百篇》經聖刪,然而吾斷不敢以為法而擬之者,所摘前句是也。
對於謝榛、王世貞的“指瑕”之言,我們不一定能夠接受,因為《詩經》的語言是在一定語境下生成的,不管它是“太拙”、“太直”、“太促”、“太累”,等等之類,只要切合當時的語境,就是恰切的,鮮活的,富有表現力的;如“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廛”,這是“太累者”對“不累者”的控訴,故而越“累”越有控訴的力量,因此,此處“太累”非但不是疵點,而是詩中的閃光點。當然,我們雖然並不讚同他們的“指瑕”,但他們在“指瑕”時所展現的勇氣,讓我們著實感受到了明代詩話文學品評的開放情懷與濃鬱生意。

四、《詩經》對後世詩風詩情的智慧啟迪
在明代詩話對《詩經》的文學品評中,著述者們幾乎都關注《詩經》對後世詩風、詩情的智慧啟迪這一問題,故而對這一問題的闡述也較為充分。
針對《詩經》對後世詩風、詩情的智慧啟迪這一問題,明代詩話一般是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論述的:一是《詩經》對後來某些時代詩歌風格(詩風)的形成所發揮的啟迪作用,另一個是《詩經》對後世某些詩人或作品詩性情韻(詩情)的形成所發揮的啟迪作用。
首先,我們來考察明代詩話就《詩經》對後代某些詩風的形成所發揮啟迪作用的論述。
陸時雍說:“前不啟轍,後將何涉?前不示圖,後將何摹?詩家慣開門面,前有門面,則後有途轍矣。不見《雅》《頌》《風》《騷》,何人擬得?此真人所以無跡,無言所以無聲也。”當《詩經》作為中國詩歌史上的第一座豐碑而高高矗立在先秦之時,其對後世詩風產生影響將是必然的事情;緊承先秦緒風的兩漢魏晉,將首受《詩經》甘露的沾溉:
文章固開氣運,亦系於習尚。周召二南、王豳曹衛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
此處李東陽雖然是從地域之屬來論詩,但揭示的卻是漢魏西晉詩風的渾厚之質,是直承《詩經》北系之氣韻的。
實際上,漢魏詩風所受的影響,並不僅限於《詩經》“周召二南、王豳曹衛諸風,商周魯三頌”等北系氣韻;應該說,整部《詩經》都是漢魏詩歌的受益源泉。對此,王世貞比李東陽更為通達,他說: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泛布濩之。”……此二雅、《周頌》和平之流韻也。“犖犖紫芝,可以療饑。”……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此秦齊變風奇峭之遺烈也。
王世貞一邊連篇累牘地摘抄漢魏詩歌,一邊與《詩經》各部分的風格相比照,從而揭示出《詩經》對漢魏詩風的浸潤與影響。
關於《詩經》對後代詩歌的影響,徐禎卿的兩段論述很有見地,他說:
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壯麗巨集奇。縉紳先生,鹹從附作。雖規跡古風,各懷剞劂。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為《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裡,棄妻思婦,歌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
又說:
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我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繢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裡》為工;不詠《關雎》之辭,則《桑中》為雋。故匪師曠,難為語也。
由此可見,《詩經》,乃至一切優秀的詩歌,是後世健康、純正詩風的精神之源。
接下,我們來考察明代詩話就《詩經》對後世詩人詩性情韻的形成所發揮啟迪作用的論述。
詩人的詩性情韻是比詩人風格更為具體的認知對象。一個詩人風格的形成,所受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包括“詩內”、“詩外”等諸多因素;但一個詩人詩性情韻的形成,則主要來自以往詩歌經典作品養液的饋贈,是以往的經典作品授予了後世詩人的軌度與情韻。關於這層意思,徐禎卿作了較為恰切的論述: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驅者,托之軌度也。
於是,針對《詩經》對後世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的影響力,或者說後世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對《詩經》的領悟與繼承,明代詩話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如:
韋孟詩,雅之變也,昭君歌,風之變也,《三百篇》後,二作得體。
《詩》“行道遲遲,心中有違”,思致微婉。《紫玉歌》所謂“身遠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其意。
子桓王粲,時激《風》《雅》余波,子桓逸而近《風》,王粲莊而近《雅》。
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仿。命意托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為多。觀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
不但《詩經》正文對後世詩人有影響力,即便是《詩疏》,也能啟迪後世詩人的創作靈感,如《升庵詩話》所述:
唐劉采春詩:“那年離別日,隻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本《詩疏》“何斯違斯” 一句,其疏雲:“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此一處,今複乃去此,更轉遠於余方。”韋蘇州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此本於《詩》“泛彼柏舟”一句,其疏雲:“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眾物泛泛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其余尚多類是。《三百篇》為後世詩人之祖,信矣。
由此可見,《詩經》對後世詩人的影響力該有多麽巨大。正是在《詩經》的啟迪下,後世詩人取資化用,推陳出新,從而創造出輝煌壯麗的中國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