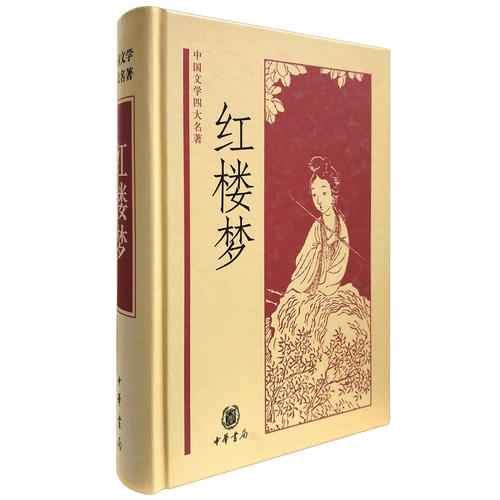看!世界真遼闊
現在的電腦是會窺探人的,一次無意的點擊,一次失誤的主題搜索,或者只是一次偶爾來串門的好奇,等等…..這些有意或是無意的動作我們以為發生了就會消失的無影無蹤,可是電腦不會,直到有一天出現在眼前的內容讓你聯想起自己曾經的不經意。在“算法的世界”裡,電腦比人更關心人。不過,有時這些關心也能給人帶來一些出乎意料的結果來。”陳年喜”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到我的眼前的。再具體一點,他是2020年的春天時我才知曉的人。他寫詩,也出了詩集。詩集的名字有些重金屬的份量-----《炸裂志》。
他在《炸裂志》這首詩裡寫了被炸得千瘡百孔的生活:
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
我把岩層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組合
我微小的親人 遠在商山腳下
他們有病 身體落滿灰塵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
我身體裡有炸藥三噸
他們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在他們床前
我岩石一樣 炸裂一地
這樣的詩適合一口氣讀完,就像著急的引信奔著炸藥而去一樣,讀完,人的心裡面也會崩塌一角,在升騰起的滾滾煙塵中看到電影中的某個鏡頭。如果將生活與電影做對比的話,電影是多麽仁慈啊!總能讓錯過的人再相遇。生活就是生是生,死是死,沒那麽多的神奇,硬邦邦的就衝著人來了。

陳年喜是1970年生人,現在也已到知天命的年紀了。陝西商洛市丹鳳縣人。早年出來打工為生,做了十六年的礦山爆破工作,除了收獲賺錢養家之外,他的收獲還有右耳的失聰和後頸上植入的三塊金屬,以及他自己閑暇時寫的詩。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稀稀拉拉寫了三十年”。對於是否有人讀到的詩,他這樣寫:
《有誰讀過我的詩歌》
有誰讀過我的詩歌
有誰聽見我的餓
人間是一片雪地
我們是其中的落雀
它的白 使我們黑
它的浩盛 使我們落寞
有誰讀過我的詩歌
有誰看見一個黃昏 領著一群
奔命的人
在蘭州
候車
一首詩始終不會只是寫給自己看的,給別人看時,心裡還是有忐忑。不過在讀這首《有誰讀過我的詩歌》時,忐忑的是我自己。也許很多出門在外的人大多都會記得自己在火車站第一次出門遠行時的焦灼和忐忑,在擁擠的人群中覓得一席之地,在南來北往的火車上憧憬著在異鄉可以找到的種種可能。只是那時我們可能並不覺得自己都是奔命的人。不過在進站出站的匆匆疾步中,我們的確是用“奔”來找到生活的。
按照有關陳年喜不多的文字介紹,他第一次走進公眾視野,是在2017年的工人詩歌紀錄片《我的詩篇》中出現。紀錄片公映後,陳年喜的詩集《炸裂志》出版,隨之他的生活也離開了需要不斷爆破才能向地底延伸的巷道。在2020年3月,他確診了塵肺病,十六年的巷道爆破工作帶給他命運遠比他想的複雜。塵肺病雖不是嚴重,但不會根治。生活對他來講,依然是幽深的礦洞。他在《牛二記》這首詩裡有自己獨特的回憶:
《牛二記》
牛二是我的副手 三十六歲 山東人
而鬢角已經過了五旬 雜草叢生
他說 這雜草 源於半生的革命
革命 是與生俱來的本能
目的不一 方式也各不相同
牛二選擇了向內的暴力
以汗為先鋒 以血為後盾
要殺開命運的另一條華容道
牛二十五歲進煤窯
從山東到山西 從四川到廣東
他要抓住黑暗裡一盞照路的馬燈
他一路窮追 血肉縱橫
最終 以兩根手指一條肋骨的代價
換得母親八年的殘喘
弟弟十年的舉人夢
牛二的另一面生活
一直是一個謎
黑暗的身體裡是否亮起過另一盞燈
或許 那道門從未開啟
或許 根本就沒有門
二十一年過去 不是一揮間
仿佛陳勝吳廣抗秦
李自成請命
以高亢開始 以灰喪結束
如今 我看見牛二已經疲憊不堪
像戰國末年
這首《牛二記》不但把人困在時間裡,也困在歷史裡。就像歷史在原地紋絲未動一般。這位牛二在地面的生活是走進了新時代裡,不過一旦回到地下,在黑暗的礦道裡,就一下子活在春秋戰國的《左傳》裡。“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鑒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眾,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戰國的境況要比春秋更糟糕一些。春秋戰國的歷史記錄中只有君王、貴族和士大夫,沒有民。直到秦之後,民才獲得了一個特定的稱謂:黔首。或許把詩中涉及到的名詞如此解讀是我想多了。總之,誤解的責任全在我,不是牛二,也不是陳年喜。不過如果將這首《牛二記》譜上曲,唱出來,我會覺得它的鼓點一定會很密集,貝斯的低音就像每一次爆破後安全生還後的急促呼吸聲。
一本詩集中並非所有的詩都出彩,陳年喜的詩歌是和岩石較量的,有的詩用力深,有些詩用巧勁。這一點就像他寫給兒子的詩:我想讓你繞過書本看看人間/又怕你真的看清。
陳年喜的詩寫礦工,巷道,和幽深的黑暗。讓我想起了另外一首詩《黃麻嶺》,黃麻嶺村位於廣東省東莞市東坑鎮,那裡曾經工廠林立,鄭小瓊就曾是在那裡上下班的人潮中的一員。她這樣說黃麻嶺這個地方。
《黃麻嶺》
我把自己的肉體與靈魂安頓在這個小鎮上
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線一個小小的卡座
它的雨水淋濕的思念頭,一趟趟,一次次
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愛情,美夢,青春
我的情人,聲音,氣味,生命
在異鄉,在它的黯淡的街燈下
我奔波,我淋著雨水和汗水,喘著氣
——我把生活擺在塑料產品,螺絲,釘子
在一張小小的工卡上……我的生活全部
啊,我把自己交給它,一個小小的村莊
風吹走我的一切
我剩下的蒼老,回家
鄭小瓊的《黃麻嶺》與陳年喜的《炸裂志》這兩首詩,落腳點有些相似。生活給人剩下,都是不得不拿起的東西。畢竟,每一個人的生活不管是光鮮亮麗還是一堆爛攤子,還是得自己來收拾。這些詩,可以喚醒我們的時間,我們的記憶,也還會成為我們記錄生活的一部分。
讀陳年喜的詩,還會想起喬治·奧威爾的一本著作《通往威根碼頭之路》,不誇張的講,如果沒有寫作這本書的經歷,那麽《一九八四》或許就不是現在這番模樣了。文字之間總是有相通之處。陳年喜的詩如果可以拆解開來的話,應該都是長長的故事,而且會帶著在巷道爆炸之後的余音回響。從人的角度來看,在無名無姓的年代裡要活得有名有姓,似乎是天生的衝動。陳年喜將這些衝動揉捏在一起,變成字,寫成詩,而不是其他什麽?這或許就是那些不斷響起的炸裂聲遺留下的副產品。
從陳年喜的詩開始談起,那就還是用詩來告一段落。不同的詩人和詩歌,就像三棱鏡一樣,讓白光的底細一覽無余。
《那些把肉從桌上拿走的人》
作者:貝爾托·布萊希特 翻譯:黃燦然
那些把肉從桌上拿走的人
教導人們滿足
那些獲進貢的人
要求人們犧牲
那些吃飽喝夠的人向饑餓者
描繪將來的美好時代
那些把國家帶到深淵裡的人
說統治太難,普通人
不能勝任。
=====================================================
每一次閱讀都會邁向遼闊!《短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