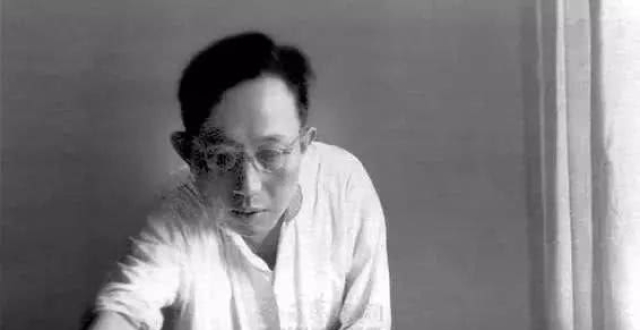當今藝術學院林立,每年成千上萬的學子報考,坊間更有無數的藝術培訓。經濟繁榮而藝術勃興,學子需要前輩金針度人,台灣知名藝術評論家何懷碩的《給未來的藝術家》便是一本適宜的著作。何懷碩自序說:“任何世代總有許多熱愛藝術的朋友,懷著對藝術的渴慕與追求的熱忱,希望得其門而入。然而不少人踟躕、彷徨,無所適從,甚至焦慮、失望。這本書試圖幫助這些朋友解開困惑。”

藝海茫茫,而時代巨變。何懷碩說:“今天做一個藝術家,與過去大不相同。比如過去的文人,寒窗苦讀十年書,便算飽學之士。今天資訊、知識之廣之多之快速,沒有古今中外的視野,沒有追逐時代文化變遷的勤奮,很容易孤陋寡聞,抱殘守闕,不能與時代脈息相應。如果對過去的傳統認識不足,自己的定見不堅,面對五花八門的時代浪潮,便很容易迷失自我。所以當代的藝術家比古代艱難,因為時代社會的變遷腳步太快了。不過,當代的優點也不是沒有。資訊發達,參考數據易得,藝術品與有關出版品或資訊很容易接觸到,中外交通便利使我們見聞豐富,這都是過去所不具備的良好條件。如何有效地利用這些時代的優勢,正考驗我們的智慧。”然而,技藝易學,智慧的形成倒是需要更深的基礎。
藝術界愛講“天才”,到底何為天才?何懷碩便有例證:拜倫與李賀英年早夭,屬於早熟的天才;畫家莫迪裡阿尼與清末的任伯年都在短促的人生中才華畢露。但歌德的偉大作品《浮士德》寫了六十年才告完成。近代中國大畫家齊白石與黃賓虹,不到八九十歲(他們都活到九十多歲),其天才的峰頂尚未出現,可能便只是一個不重要的中小畫家而已。“天才既有早熟,也有晚成,我們更無從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天才。我們不應相信生而知之、不學而能的神話,隻管以熱誠、毅力與不求功利之心去追求。”

中國畫壇特別講究師承與門派。何懷碩卻有清醒的認識:“我們須知每個人不一定有幸能遇得到一位名家為師。誰能得到吳昌碩、齊白石、傅抱石,或者塞尚、梵高、克裡木特等大畫家為師呢?況且若有幸遇到,問題仍多著:第一,大畫家不一定肯當老師教你學藝;第二,他們是大畫家不一定就又是最好的教師;第三,跟他們學,能學到手的只是一套形式技巧,所謂‘傳衣缽’,都只是技藝。但你不是他,即使得其衣缽,在藝術創造的價值上也毫無意義,因為完全喪失了自我。所以大師的學生或後人,若不能另起爐灶,走出自己的路,藝術成功的可能性還不如一般人。大師的後人與學生,很難有獨立的風格,往往成為‘副本’。這種例子多得很。”誠哉斯言,放眼中國畫壇,“小齊白石”、“小小傅抱石”、“小小小徐悲鴻”何其多!一時間似乎“大師滿街走”,可是又有多少“小師”夢醒呢?

何懷碩在台灣師范大學美術研究所教授多年,對於“老師”自有看法:“出名的畫家不一定必然是最好的老師;反過來,藝術修養深廣的、造詣超過他個人藝術創作成就的人,也可能是很好的老師。……好老師要有中外藝術的修養與品味,要有知識與表達能力,要能因材施教。他自己藝術創造成就很高當然更好,但更重要的是他堪為良師,他會輔導有希望的學生完成自我。”
早年何懷碩在西班牙畢加索的故鄉巴塞隆那參觀畢加索美術館,看到畢氏青年時代的許多畫,簡直是印象派早期畫家的翻版。“畢氏以革新、反叛傲然獨立於西方現代畫壇,但他年輕的時候居然有那樣模仿前輩的作品。梵高也曾臨摹日本浮世繪,那更是跨文化的模仿。吳昌碩、齊白石也有不少模仿(有的根本是臨摹)八大山人的畫。傅抱石早期學石濤。都是對前代大師的模仿。林風眠的花鳥人物,明顯的從民間瓷器大寫意的書法學習、轉化而來。同時他也受馬蒂斯、莫迪裡阿尼的影響。”模仿可以是創造的起步或基礎,卻不等於創造。何懷碩說:“模仿與創造似乎是矛盾,但是正確的運用、發揮模仿的功用,模仿便成為創造的媒介與創造的起因。”

中國畫面對前人的作品臨摹,西洋畫則面對自然物象臨摹,這都是入門學習的方法之一。何懷碩以潘天壽“背臨八大”畫作進行分析:“八大原畫圓潤、渾穆,用筆如行草。潘天壽這一幅凝練、矯健,用筆如篆書,多金石美感的趣味。而兩幅在簡練、生動,不重細節重神韻上則相似。古人說‘師其心,不師其跡’,在這裡可以領悟是怎麽回事。而中國藝術學習中的所謂‘臨摹’的意義與多種方法,也可以得到啟發。臨摹與寫生一樣,也可以有‘創造’的可能。”但是對中國畫的一些“積習”,何懷碩有非常理性的思考:“中國畫因為把臨摹當目的,陳陳相因,大批大批近乎複製的作品充斥人間,使中國繪畫相對西方繪畫不但在藝術價值上,而且在市場價格上完全不能相提並論,都與此有關。我們應好好認識臨摹的真義,正確把握其正面意義,消除其流弊,中國水墨畫才可能有擺脫陳腔濫調的泥淖,提高藝術品質的可能。”

何懷碩對中國大藝術家的風格了然於胸:傅抱石喜畫雨景,他的雨景以膠礬水甩於宣紙上成條狀排列的許多“點”,再以水墨渲染而顯出白色的雨。這是前人所未有的表現方法。黃賓虹則慣用層層重疊的“積墨法”以及“破墨法”(以墨破水,以水破墨)。他用墨之變化多端,深沉厚重,在中國畫史上,比古代用墨最富變化的畫家(如石溪、程邃、龔賢、石濤等)超越許多。“我常說中國水墨畫中,墨法複雜豐富以黃賓虹為最。張大千潑墨畫喜歡以石綠、石青、朱砂等礦物顏料傾瀉於重墨之上,形成流動狀態,色彩豔麗,甚為醒目,變成他媚俗的‘招牌菜’。吳昌碩以篆書筆法寫竹木,以金石之古樸蒼勁營造氣韻,以篆刻布局作構圖,形成他‘金石派’獨樹一幟的風格。齊白石則喜歡以日常生活平凡的物象作畫,比如魚蝦青蛙、鋤頭畚箕、算盤、不倒翁、山花、小雞、酒罈等。”由藝術家與眾不同的風格,何懷碩告訴同仁:“從大的方面到極微小的地方,都是個人顯示風格該留心的範圍。各有慧心,大小兼顧;各有巧妙,並無公式可循。你若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你便知道如何發揮自我的種種可能,千方百計,不甘為既有模式所束縛,也不願為前人之奴,為的是顯現一個鮮明的‘我’。”

藝術界都有一些習以為常的方式,比如寫生,中外皆然。何懷碩則有獨到的見解:有些畫家一輩子在寫生。世界名勝古跡,名人美女,奇花異卉,珍禽猛獸,盡收筆底。這種畫家永遠只有寫生的習作,可就是永遠沒有創作。“在寫生中創作,要達到像塞尚、梵高、莫奈,像石濤、龔賢、黃賓虹、李可染等名畫家那樣,他們的‘寫生’才達到藝術的境界。那種作品,其實已不能稱為單純的寫生,因為所寫的物象只是表現他們的思想感情的‘材料’而已。他們從客觀世界采集了材料,在主觀的加工之後才誕生了創造。”
在《給未來的藝術家》中,何懷碩特別強調創作記錄的重要意義,並現身說法:“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有幸認識一位華裔美國學生,名叫宋漢西(James H. Soong),他是斯坦福大學中國美術史研究生,後來得到博士學位。他六十年代來台灣學中文並收集有關中文資料。他是最早賞識我、鼓舞我的同道友人。他建議我要為每一件創作做記錄。自那時起,至今三十多年,我每一件創作都有完整的記錄,應該感謝他的提示與建議。”而回顧千年畫壇,中國畫家都忽略了自我創作記錄的工作,以致後代美術史的研究與畫家研究十分困難。中國畫家尤其沒有興趣自己建立作品記錄。因為許多不嚴謹的應酬之作、賣錢之作草草完工,固然不願意也不值得自留記錄。比較用心的作品,也多為雷同或重複製作,專畫馬、牛、老虎、老鷹、麻雀等畫家,或者“秋山論道”“松下高士”“柳蔭美人”等畫舉目皆是,所以也不想記錄。這一點上,何懷碩的“創作記錄”對未來藝術家具有重要的啟示。

何懷碩在美國藝術界沉浸多年,對西方藝術有深入的了解,卻格外重視“中國風格”。他認為:“常玉是二十世紀旅外中國畫家中最具中國風格的一位,他的畫從被忽略到近二十年逐漸受到重視與肯定。我在三十多年前看到他的油畫,便認為他是有意開創中國風格油畫的畫家,對他有特殊的敬意。可惜常玉的畫風隻開了個頭,還未達到成熟的高峰便去世。他在巴黎的生活潦倒散漫,畫畫的材料極低劣,影響了他的畫的品質,是一大遺憾。”而許多“國畫”了無新意,既無時代精神,又缺乏個人獨特性,因之本土藝術也漸漸僵化而失去創造的生命力。這也恰好是“全盤西化”的最佳土壤。在何懷碩看來,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尤其是美國“超寫實主義”有如飛來一片烏雲,“我們曉得這一片烏雲遲早要消逝,正如二十多年來抽象主義、硬邊藝術、龐圖美術運動,超現實主義、波普、歐普藝術等浮雲一樣,終歸是一時的風雲過境而已。”何懷碩更以“傳統藝術要現代化,外來藝術要本土化”來期勉朋友。

針對當代“藝術的異化”,何懷碩顯得憂心忡忡,更勇於抒發己見:“商業化與大眾化成為時代主流的結果,在當代就是川普取代傑弗遜;哈利波特取代莎士比亞;沃霍爾取代了倫勃朗;村上春樹取代夏目漱石;女神卡卡之取代卓別林;九把刀、韓寒取代了梁實秋……當代因為一切產品都商業化,文學藝術電影等成為娛樂的商品。商品的目的在謀利,便不能高唱‘陽春白雪’,而要取悅‘下裡巴人’,所以大眾化是文藝低鄙化、粗俗化的關鍵。”而他對未來藝術家的忠告是:“繼承中外古今的藝術資產,從傳統出發,但不抄襲,不人雲亦雲;忠於你所生活的時代與文化,真誠地去表現你自己所見、所聞、所感、所思,表現你自己的獨特性與創造性。不受蠱惑,表現你自己,這是任何時代的藝術家永遠不變的信條。”
世間多少畫師教給徒弟的是繪畫的技藝,而往往忽視藝術背後還有潛移默化的溫情與敬意。何懷碩則重視人文的情懷:“藝術家根本上是一個熱愛世界,關懷人與宇宙,對與人有關的一切都有高度熱情的人。有這種胸懷,專門的技巧才能發揮作用;如果缺欠這種胸懷,那只是工匠。許多人追求藝術而藝術離他甚遠,就是這個緣故。”這種胸襟和見識,誠為未來藝術家的忠言良藥。(文/李懷宇)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