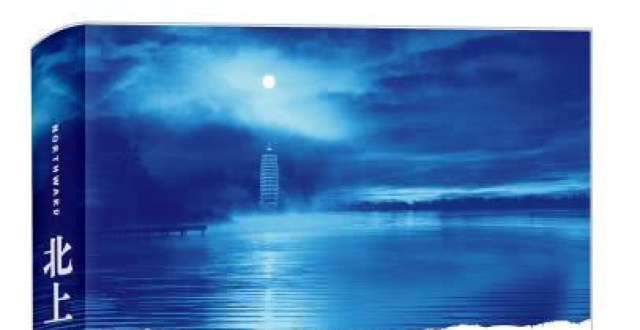《北上》是著名作家徐則臣潛心四年創作完成的長篇新作。本書闊大開展,氣韻沉雄,以歷史與當下兩條線索,講述了發生在京杭大運河之上幾個家族之間的百年“秘史”。
大水湯湯,溯流北上,本書力圖跨越運河的歷史時空,探究普通國人與中國的關係、知識分子與中國的關係、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探討大運河對於中國政治、經濟、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變遷的重要影響,書寫出一百年來大運河的精神圖譜。
在這個意義上,大運河是中國的一面鏡子。作為中國地理南北貫通的大動脈,大運河千百年來如何營養著一個古老的國度,又是如何培育了一代代獨特的中國人,在作品中亦有深刻的文化思索與藝術表達。
本書的天氣、格局,“北上”兩字適足以當之。譬諸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地隔中原勞北望,每依北斗望京華,“北”是地理之北,也是文脈、精神之北。小說一個重要主題恰是借一條大河寫舊邦新命。兩層意義,兩字見之。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想象一條河流的三種方法
文 | 徐則臣
最重要的是等。
你永遠不會知道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什麽時候會在你的頭腦裡真正長成,所以只能等。我在《北上》裡把京杭大運河當作主人公來寫。在此之前,寫了近20年的運河,水與船都只是小說的背景,主人公是河邊和水上的人家,是穿行在千里大運河上的一個個人。這一次,背景走到前台,這條河流要成為主人公。對我來說這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寫作就這樣,某個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長的意志,暗地裡緩慢地豐滿、立體,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個新主角誕生了。
那些作為小說背景的元素也一樣,當它們羽翼漸豐,也會悄無聲息地從後方突圍到前台,你不得不正視。《王城如海》如此:主人公其實不是話劇導演余松坡,而是我所生活的這座城市;北京城被我寫了十幾年後,已經不甘隻做背景,挺身衝到了前台。《北上》亦如此:小波羅、馬福德、謝平遙、邵常來、謝望和、孫宴臨、邵秉義、胡念之、周海闊他們固然也重要,需要濃墨重彩歌之蹈之,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生活中最大的背景,浩浩蕩蕩的一條長河,這一次,它進階到小說的最前沿。
遲早有這麽一天,你必須面對它。所以,當我說《北上》寫了4年,其實我說的是,《北上》我寫了快20年。在20年前寫下第一篇關於運河的小說時,我就已經在寫《北上》了。它在20年來我所有的運河小說裡暗自成長,直到2014年的某一天,它跳到我面前,說:我來了。我只是稍稍愣一下神,就明白該乾活兒了。瓜熟蒂落指的就是這感覺。我等到了《北上》。
要寫不意味著就能寫。的確也如此,一個人站在你面前,囫圇圇你肯定能看個差不離,一旦深入細節,需要描述放大鏡和顯微鏡下才能呈現的細部景致時,你會發現,你離真相還遠。2014年,我決定寫《北上》,那條我以為熟悉得如同親人的河流,突然變得陌生和似是而非了。我沒法如想象中那樣,伸手就來。電腦打開,手指頭總落不到鍵盤上。問題來了。儘管我從小生活在水邊;儘管我初中時校門口就是寬闊的運河,大冬天宿捨的自來水管被凍住,我每天早上都要抱著臉盆牙缸一路狂奔出校門,就著水汽氤氳的溫暖運河水刷牙洗臉;儘管後來我曾短暫寓居的淮安,京杭大運河穿城而過,我在河邊散步、遊玩,一天要跨過運河上的水門橋、北門橋、若飛橋若乾次;儘管我斷斷續續寫了近20年的運河、運河邊的花街和石碼頭,自以為裝了一肚子水邊的掌故和人生——它們還是沒法把我的手指頭摁到電腦鍵盤上。我要做第二件事:
走讀。走和讀,邊走邊讀,邊讀邊走。
2014年開始,我決定重走運河;首先要建立一個對運河的整體感。很多年裡從南到北,走過京杭運河的不少河段,但多屬無心之舉,看了就看了,留下來的不比到此一遊的觀光客更多。但這一次,我帶著眼睛、智商、想象力和紙筆走。我看,還要看見,更要看清楚,看清楚河流的走向、水文,看清楚每一個河段的歷史和現在,看清楚兩岸人家的當下生活。這是個大工程。京杭運河從南到北1797公里,跨越浙江、江蘇、山東、河北4省及天津、北京兩市,平常工作忙,雜事也多,沒有可能一次性沿運河貫通南北,只能利用出差、還鄉等機會,一次次“南下”,隔三差五便走上一段,看多少算多少,4年裡竟也把運河丈量了一遍。部分有疑難的河段反覆去了多次,沒辦法,大運河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加上中國南北地勢起伏、地形複雜,河水流向也反覆多變,不親自到現場做詳盡的田野調查,各種史志資料中描述船隻“上行”“下行”根本弄不明白。尤其是幾處重要的水利工程,比如山東南旺分水樞紐,僅憑紙上談兵是理解不了的。儘管現在荒草萋萋,河道漫漶,當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遺跡所存甚少,但在現場一站,隻10分鐘,比之前苦讀10天的資料都管用,豁然開朗。

明清兩代,漕運總督一直駐於淮安,這裡的清江浦擁有“九省通衢”“天下糧倉”等美名,也是小說《北上》重點提到的地方。
“南下”對《北上》的意義,如何高估都不為過。在寫作上我越來越像個實證派,我希望每一個細節都經得起推敲。屢屢南下為我建立了對京杭運河的整體感,閉上眼我能看見大水經行之處的地形地貌,看見水流的方向和洪波湧起的高度,由此也能推算出1901年春夏之交,意大利人小波羅乘船穿行某段河道可能需要的時間。我的中國地理知識一向貧乏,因為寫《北上》,4年裡每天面對運河地形圖,在告別中學地理課20多年後,終於補上了這一課。
走是真走,讀也真讀。
運河1000多公里的征程中,歷史上單改道一項,可以寫幾十卷大書,我必須知道小說行經的年份和河段,船究竟從哪裡走;小說自1900年起,至2014年止,100余年,數不清的人和事,虛構必須建立在基本的史實基礎上,我得弄清楚一個雞蛋在1901年的無錫和濟寧可能賣一個什麽價;我也得知道意大利人小波羅點燃他的馬尼拉方頭雪茄用的布萊恩特與梅公司生產的大火柴,一盒能裝多少根。我還得知道,運河到了2014年,一個跑船的人如何展開他一天的生活,而這個跑船的人,在他的一生中,駕駛過哪些船,每一艘船在他的生命中佔據了怎樣的位置。我像患了強迫症一樣,希望每個細節都能在小說裡扎下根來,它們扎下根,我的虛構才能有一個牢靠的基座,小說最後才可能自由放曠地飛起來。我要寫出一條文化意義上的運河,首先要有一條日常生活中的真實的運河。
唯有閱讀方可獲取這些歷史和現實中的知識與見解。對我來說,閱讀相關資料本身就是寫作的一部分,是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我辟出書櫥兩層專門放置相關書籍,4年下來,認真通讀的不下60本,隨手翻閱的書籍和瀏覽的影像資料更多。必須承認,百分之九十的閱讀在小說中都找不到半點蛛絲馬跡,但倘若沒有這浪費掉的百分之九十,斷不會有這部《北上》。

比較視野下的歷史與河流
文 | 李徽昭
無論中西或古今,河流都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不同文明文化形態的出現及其發展轉換無不與大小河流產生種種關係,但將河流作為小說寫作的主要題材,尚不多見。徐則臣長篇小說《北上》以30多萬字的寬闊篇幅來寫流貫南北、穿越歷史的京杭大運河。
小波羅(意大利名為保羅·迪馬克)和弟弟(費德爾·迪馬克)懷著對馬可·波羅書寫的美好中國的期待,先後來到中國,他們與同船的謝平遙、邵常來、孫過程,與中國女子如玉,由北往南,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到濟寧、天津,從搖晃的運河行船到運河兩岸,經歷與見識煙花柳巷、船閘人家、兵馬劫匪、纖夫官員,遭遇了人生所能遭遇的一切,將一個想象的馬可·波羅的中國,轉化為身體力行、耳聞目見、鮮活生動的中國。沿著時間和歷史的流淌,意大利兄弟倆100多年前的同船者、遭遇者,也繁衍出各自後代,即邵秉義、邵星池、謝望和、孫宴臨、馬思藝、胡念之、周海闊等眾多後輩。在各自命運中,演化出新世紀運河邊上與河流結緣、行走生活並關注河流的現代故事。《北上》中,河流不僅是故事發生的空間,也是與人物性格、命運發生密切相關的文化焦點。意大利人小波羅懷著對中國的美好想象,雇船沿運河北上;弟弟費德爾坐船參加聯軍攻打北京;邵秉義、邵星池父子倆是運河船夫;謝望和做運河電視節目《大河譚》;周海闊收集運河文物、在運河邊開旅館;胡念之對運河進行考古。這一切均與運河息息相關,河流是能指也是所指,成為小說故事推進的重要力量。
不僅如此,徐則臣以30多萬字的篇幅書寫一條大河,拉開了100多年歷史的巨集大視野,使河流與中國命運、現代中國歷史產生一種密切的扭結關係,在人物命運、河流和歷史的互動關聯中,故事性得到相當的彰顯,現代中國歷史也與運河彼此互動共生,散發出長篇小說的深遠思想內涵。小說首先呈現的是運河漕運衰落史,落點在1901年,古代中國向現代中國巨變的前夜。暗流湧動中,戊戌變法、八國聯軍、義和團起事、抗日戰爭、“文革”、改革開放??所有現代中國人繞不開的大事件、並應與之產生命運呼應轉折的重大事件幾乎盡皆在小說中出現,歷史及其核心事件由此呈現出與我們脈搏跳動的聲息。歷史事件不再是抽象虛空的概念,而是小說人物性格與命運發展的背景,是人物行動及其命運的驅動力量。小說中,歷史已由黯淡的聲音和文字內化為人物的直接感應。到謝望和、孫宴臨、周海闊、胡念之等當代故事中,前輩遭遇的歷史面影和氣質繼續得到感應和承接,這一切故事轉換與推動的歷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與故事,而是個人的敘述,每一個個體都生活在歷史中,歷史也生活在故事裡。《北上》也由此穿越歷史,成為當下史、個人史。

“70後”這一代作家,大多沒有歷史的包袱,歷史也因此甚少成為他們敘事的關注焦點。歷史的闕如使得這一代作家既可輕裝上陣,也因此缺少文學史的深度與厚度。由運河入手的《北上》卻獨辟一條彎彎的小路,不但直面20世紀早期重大歷史,而且將這一歷史的重錘延宕敲擊到之後人物命運身上,串聯起京杭大運河與20世紀中國與中國人的命運,使歷史呈現出別一向度,以獨特的歷史書寫重塑了“70後”一代作家的新形象。
這種歷史的直面書寫首先以保羅·迪馬克、費德爾·迪馬克兩位意大利人為主線鋪成延展開來。這一對兄弟何以來到中國?在中國這樣一個異域文化空間,兄弟倆觀察視角有何不同?這種不同對於認識20世紀早期中國有何意義?這是徐則臣必須要解決的問題。進入兩個成長經驗、生活環境迥然隔離於中國的意大利人身上,首先就確定了一種難度。這一難度的完成就在於小說寫作手法的新意,也即小說主角的異域生活經驗形成了一種間隔作用,使敘述者以文化比較的方式進入20世紀中國歷史,這種小說寫作手法可以說是一種類似於比較文學式的小說寫作方式。當下的比較文學,在“平行研究” 、“影響研究”之外,開始倡導一種“跨文化研究”,並形成了一種比較視野的形象學。比較形象學強調他者的意義,《北上》正是在比較的小說寫作方式中建構起兩個意大利人的他者形象,以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的比較視域,在20世紀中國歷史巨集大背景中,呈現了一種文化性的、日常生活化的京杭大運河。
《北上》中,作為一種比較視野的保羅·迪馬克、費德爾·迪馬克兩位意大利兄弟,與謝平遙、邵常來、孫過程、秦如玉等中國大地上出生成長的中國人,互為比較形象。對於謝平遙來說,以清末翻譯工作為業,經常接觸外國人,在小波羅(保羅·迪馬克)這個外國人身上發現了人的多重性,這個意大利人既對中國好奇,又有著“歐洲人的傲慢和優越感”。而在小波羅帶著馬可·波羅式的浪漫中國想象中,他對運河、對中國筆墨方式、對中國大地上的一切都充滿好奇,他給中國人拍照、與船夫聊天、和中國官員接觸,在和中國人的朝夕相處中,深切地感受著一個“老煙袋味”一般的古老中國。不僅如此,他絲毫不掩飾自己人種的異質性,願意被中國人觀看。互為他者的小說形象形成了小說內在的文化間離效果。在小波羅雇傭謝平遙、邵常來北上的一船同行中,他們走過船閘、訪問教堂、走進官府、落入妓院、經歷劫持、偶遇平民,這一系列坐船北上的運河之旅,互為他者的比較的小說寫作方式充溢著一種跳出中國(以兩位意大利人敘事視角)看中國(變革發展的多元性)的文化間隔效果,營造出豐富多元的文化意蘊。
《北上》的小說敘事也營造出不同的比較方式。小波羅的北上故事以第三人稱敘述起筆,謝平遙視角為主。到第二部對小波羅弟弟費德爾·迪馬克的故事敘述時,轉而使用第一人稱。兩種敘述人稱前後迥然。第三人稱敘述中的小波羅病死於運河上,第一人稱敘述的費德爾·迪馬克最後變成了中國人馬福德,繁衍出後代馬思藝、胡念之。此外還有謝望和視角的第一人稱敘事,第三人稱的胡念之、馬思藝、周海闊。不同的敘事者與故事推進發展的聚焦者,使得小說不同人物重疊對照,也使意大利人視角的中國與中國本土視角的中國,衍生出戲劇性的敘述張力,並由此演化出對中國歷史追問的多層意義空間。
《北上》的比較式的小說寫作抑製了寫作中的散漫與情緒衝動,即,他不得不借助於兩位意大利人視角來審視中國,不得不接受一個遠離了中國這個本真寫作身份的挑戰。他需要處理好作為故事敘事者的創作主體與兩位意大利人帶來的異文化的關係,這就需要作者必須能夠跳出中國來講述中國,將兩種觀念經驗不斷比較,進行恰當運用,需要作者能跳出中國歷史來審視京杭大運河,不斷以兩位意大利人的世界運河經驗來重新觀照京杭大運河。無疑,《北上》的處理是成功的,小波羅經常以意大利的運河感受穿梭審視著眼裡所看、耳中所聞的一切,由此審視著中國,使這條大河蔓延著無限的文化與歷史意蘊,無論其興盛還是頹敗,都是生動的20世紀中國故事。

圖上的橋為拱宸橋。
應該注意的還有,《北上》比較的小說寫作方式還體現在對攝影這一現代工具性藝術與運河歷史故事之間的對照式處理。小波羅、孫宴臨的攝影行動,孫宴臨的攝影課程,攝影家郎靜山的作品介入,不僅映照著京杭大運河的文化與歷史,也同樣映照著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變化發展。攝影是一門依賴技術的藝術行動,照片所攝取的人物、風景安慰了時間流逝所形成的悲傷,也在後來者的生活中承擔著復活記憶的紀念功能。對於攝影者而言,可通過即時瞬間的獲取,滿足自我的見證與歷史記錄的實現。然而,對前現代中國而言,攝影的這些功能與意義是完全意外的事物。當小波羅在運河邊美麗的油菜花田地,準備給一些下層民眾拍照時,卻遭遇了不願被拍的中國語境。攝影機器對人像的攝取與前現代手繪成像形成了反差,現代機器對於前現代社會的中國下層民眾是一種恐懼的靈魂攝取者,而非紀念與自我形象認知功能的相片,最後一位受刑的民眾以誓死的姿態接受了拍照。對於小波羅而言,攝影卻具有另一種旅遊休閑的意義,他在船閘上下左右地拍照,與前現代中國的民眾對攝影的拒斥,構成了相當大的文化反差。攝影在中國的前期遭遇及其文化反差有著中西不同的工具語境和裂隙,直到孫宴臨這個新世紀攝影家這裡才日益消弭。當孫宴臨對邵秉義父子的漁民日常生活進行記錄時,攝影行動的雙方達成了內在的和諧,也由此記錄了運河的日常生活,並因此引起謝望和關注。作為日常生活記錄並藝術化的攝影行動,孫宴臨滿足了攝影的現代意義。在孫宴臨和小波羅之間,則有孫宴臨小祖父因攝影獲罪、郎靜山藝術攝影獲得經典化的另一種遭遇。從孫宴臨追溯到小波羅,攝影構成了小說中另一條比較式的敘事線索,以一種跨學科介入小說敘事的寫作方式推動了《北上》多重意蘊的生成。
徐則臣以一種比較的視角介入長篇小說《北上》的寫作,將兩個意大利人放置到中國運河人文歷史書寫中,由跨越100多年的巨集闊視野講述運河故事,形成了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故事與攝影多重的比較視野,同時以20世紀諸多重大事件介入到人物行動與命運中,使這部小說具有了時間與歷史的長度、題材與問題的難度、思想與藝術的厚度,可以說,在題材、思想、寫法上均是徐則臣乃至“70後”作家長篇小說寫作有意義的突破。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12月24日3版


徐則臣
著名作家。1978年生於江蘇東海,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人民文學》副主編。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過中關村》《青雲谷童話》等。曾獲莊重文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馮牧文學獎,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2015年度中國青年領袖”。《如果大雪封門》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同名短篇小說集獲“2016中國好書”獎。長篇小說《耶路撒冷》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說”,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第六屆香港“紅樓夢獎”決審團獎。長篇小說《王城如海》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17年度十大中文小說”、被台灣《鏡周刊》評為“2017年度華文十大好書”。部分作品被翻譯成德、英、日、韓、意、蒙、荷、俄、阿、西等十餘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