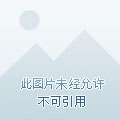孩子的童真無疑值得每一個人關心並守護,但怎樣體貼的關心才是最合適的?有人說是以兒童文學作品陪伴孩子成長。
近年來,有一些成人文學作家進入到兒童文學圈裡為孩子創作,這對兒童文學來說是一種良性的互動。他們以創造力與愛心回應孩子的天真與純粹,以美好的文字陪伴著孩子成長。
但也出現了一種聲音,說現在的兒童文學缺乏現實主義的作品。這不禁令人思考,什麽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它對題材的要求需要聚焦於家庭與校園等生活場景中麽?而這有沒有可能是一種局限呢?
即使是幻想作品,如果其中有現實主義的精神作支撐,內容不一定寫實、嚴肅、深刻,也因其中有對現實的關懷及反思,從而具有令人震撼的力量。4月25日,在作家虹影少兒奇幻新作《彩虹之心》的新書沙龍上,嘉賓止庵、楊葵、解璽璋、王紅旗、陳香分享了他們是如何理解兒童文學與現實主義的關係。

現場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張舒婷
現實主義
是現實世界與想象世界的結合

虹影,著名作家、詩人、美食家。代表作有長篇《好兒女花》《饑餓的女兒》《K英國情人》《上海王》等。六部長篇被譯成30多種文字在歐美、以色列、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出版。
虹影:其實我寫的就是現實世界跟想象世界的結合,非常現實。像桑桑(“神奇少年桑桑系列”主人公)這樣一個孩子,父親去世,母親在紗廠做女工,上夜班可以有加班費,所以他們只有早上的時間才可以在一起,十年都是這樣一種狀態。
在現代的世界裡,當今的很多孩子其實比桑桑還要可憐,第一是留守兒童,第二就是家中把孩子都交給了保姆或者長輩,孩子跟父母的接觸非常少。我們要怎麽跟孩子相處,怎麽讓孩子在一個有父母引領或有健康情感交流的氛圍裡成長?
現實是有缺失的,我們的孩子比較早熟,但這種早熟其實是種心靈創傷。這種狀態並不是好事,人的成長應該按照每一步驟來,他不應該缺失某一部分,也不應該有創傷。
我們不能夠把一個人的成長過程部分扭曲或者拔苗助長,這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說都是損害。我們跟孩子在一起時,應該能夠讓孩子自然成長。因為我是一個沒有父愛的孩子,所以我要寫桑桑跟父親的關係,桑桑可以到另外一個世界與心中的父親交流,而獲得父愛的力量,這使我們的孩子變得更強大。

《神奇少年桑桑系列》
作者: 虹影 著; 切麗登曼 繪
英譯: 尼克·史密斯
版本:蒲公英童書館·貴州人民出版社 2018年04月
我每天有給我女兒讀書的習慣,在我讀書的時候,沒有選擇說這本書兒童可不可以讀或適不適應讀。我覺得需要從小讓孩子認識到這個世界有死亡且生死無常,生死就是我們人的生命。
我經常講到媽媽有一天可能不在了。第一次我跟她講這個事時,她會哇得一聲大哭,等她哭夠了,我跟她說:“但是我會永遠在這裡,你相信嗎?”她說相信,於是我們度過的每一分鐘都會成為記憶,這個記憶是不能被拿走的。
我在處理這些題材的時候,想這是一個顛覆,我打破了中國兒童的習慣性的思維:一個是寫到死亡生命的殘酷,第二是兩情相悅,幾部故事中都有講到戀愛。孩子們可不可以喜歡一個男孩子,或者喜歡一個女孩子?愛情是廣泛的。
有強烈的現實觀
便是有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

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從事報刊編輯、圖書編輯二十餘年,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解璽璋:為兒童創作要比給成人寫作更困難,因為兒童的心理,甚至比成人的更難把握。特別是一個成人的心理已經成熟後,他再返回去了解兒童的心理,其實不是很容易的。像虹影這樣,回過來給兒童寫作,是跟她自己當了母親有關。我覺得每個父母可能都有這樣的心思,在這時對孩子產生深深的愛。
這並非說她要顛覆自己以往的書寫,而是說她對母親的認識更深刻了,有了很多新的發現。因為她自己當了母親,不養兒不知父母恩,只有到這個時候才能感覺到母親多麽偉大,她才能重新書寫自己和母親的關係。

虹影與女兒,圖片來自虹影微博。
她還在重新處理自己記憶當中的一種文化積澱。她是重慶人,重慶這地方有很多歷史遺存,這些都沉澱在她的記憶中,她要重新處理這些東西。這是她成長的一方面,比如書裡對巴國這一傳統和女媧補天故事的處理,她用了“彩虹之心”的解釋,跟傳統文化當中提供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這是她視野上的一種廣闊。

陳香,中華讀書報總編助理
陳香:兒童文學是一種淺語的藝術,作家要舉重若輕的言說;同時,兒童文學始終是以“美和善”為旨歸的,無論展示了多麽斑駁的圖景,最後還是要給孩子答案和希望。
我覺得應該多層次來理解現實主義,它更多是一種精神,現實主義和現實主義題材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像虹影老師的作品,她雖然寫的是一個幻想和現實交織的世界,但有強烈的現實觀,它也是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如果現實主義的題材,只能夠寫家庭、校園、生活,我覺得也是自我限制了現實主義的概念和範圍。
原來兒童文學的寫作更多局限在校園、家庭,最多也就是幻想,這是三大重點題材。兒童文學這個概念其實本來也是文學的一種,寫的是成長,不管是心理的成長,還是生理的成長,還是寓意著一個人在對接廣闊的社會是應如何實現成長,都值得去關注、都值得去書寫。
想象力,是對現實生活的彌補
亦能直接創造一個現實

止庵,傳記隨筆作家,周作人、張愛玲研究者,自由撰稿人,著有《惜別》、《周作人傳》、《神拳考》等。
止庵:“神奇少年桑桑系列”涉及的主要地點是重慶,這個地方有好多東西外地人不太能理解,開玩笑說就是有點“裝神弄鬼”,背後有種近乎神秘的文化,虹影將這些東西用在了自己的書裡。
而且虹影富有想象力,想象力其實是一種能力。在我看來,想象力大概有兩種,一種是對於我們了解有關古往今來的現實生活的一種彌補,比如拍攝古代的電影或電視劇,人們怎麽吃飯、怎麽穿衣,史料不足,就得依靠想象。
還有一種想象力則是無中生有,創造的是另外一個世界。我個人覺得後者是更可貴的一種想象力,它直接創造了一個現實。虹影的“神奇少年桑桑系列”和《米米朵拉》實際上交替使用了兩種想象力,後一種想象力更多體現在作品的結構和人物塑造上。

楊葵,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從事報刊編輯、圖書編輯二十餘年,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楊葵:胡適曾經說過,看誰白話文做得好,有一個檢驗標準,就是到幼稚園去給孩子講一堂課,孩子要是聽懂了,你的白話文就做得好。其實他說出了兒童文學的要領所在——怎麽在形式上把故事結構、語言文字寫到最簡化,但是最簡化的東西裡又有最豐富的內涵。
為一個孩子寫東西,如果你的想象力不夠,他會把你淘汰掉。因為小孩的想象力在你這裡得不到任何回應,對於孩子來說,他是天然的。對於一看死板的、沒有想象力的東西,他就沒有興趣。所以,這也是所謂的寫兒童文學更難。從成人文學到兒童文學,我覺得虹影把自己的內心圖象撐大了,比如她對母女、母子關係的處理,她的故事有了更大的背景,我覺得這是一種成熟,不光是生命的成熟,更是整個心界的成熟。

王紅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編審。現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女性文化》《中國女性文學》主編。
王紅旗:虹影做母親後,筆鋒變得不那麽尖銳,而且很柔美、溫暖。這並不代表不深刻,“神奇少年桑桑系列”仍然深刻地在思考人類發展與教育問題,而且完全打破了傳統觀念與方式。
當代教育真的問題很多,親子應該在教育當中相伴成長,成就真善美的完整人格,才是童話的本質意義。尤其在當代,人們在被物質、金錢的繁榮和富有遮蔽下,從孩子到成人,因精神追求的缺失,心裡寂寞、焦慮、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意義,虹影用童話的方式給大人和小孩提供了一種愛和希望的可能,給生命注入了一種愛的精神力量。
她寫男孩女孩的成長穿越多重時空隧道,歷經挫折和災難對生命的淬煉,讓我們重新思考自己的人性和審美,以及精神追求的定位。《彩虹之心》就是講人性的初心,愛與希望會給孩子和家人在閱讀過程中帶來更豐富的親情體驗,也會讓這個社會和生活充滿愛的燦爛和希望。
本文內容整理自《彩虹之心》新書沙龍現場的嘉賓發言。現場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舒婷;編輯:走走、張得得。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2018年“兒童文學的諾貝爾獎”揭曉啦,孩子們永遠熱愛魔法和想象力


長久的生命力是鑒定優秀童書的第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