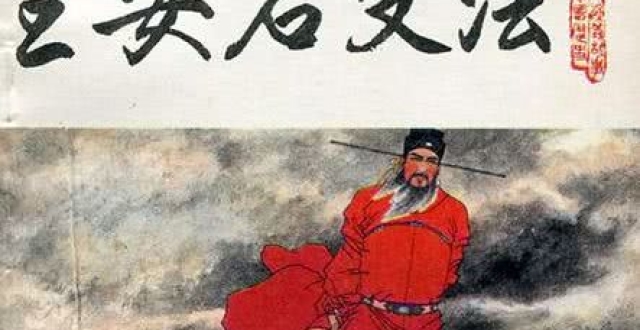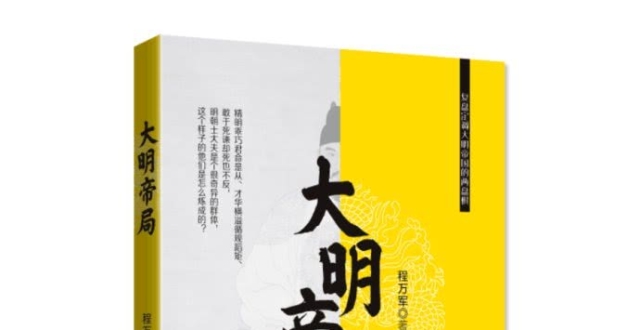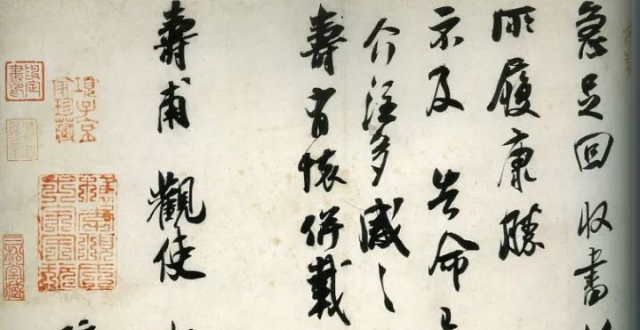然而此時,朝中並無用能臣、革舊製的共識。仁宗晚年無子,一直為立嗣之事糾結,吳奎是少數幾個上疏力諫仁宗立宗子為皇子的大臣之一,神宗因此認為他“輔立先帝,其功尤大”,即位後便重用其為參知政事。
吳奎的進言是:應對民困財乏問題,要順其自然,帝王的職責是辨忠奸,用君子,讓各級官員發揮作用,國家自然會大治。若在太平盛世,吳奎的看法並無問題,但神宗面臨的絕非這樣的局面。
所謂君子小人之辨,完全是傳統儒家的政治理念,對於實際的用人問題於事無補。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說得清嗎?滿朝大臣中,唯一能理解神宗的,恐怕只有韓維。
早在仁宗朝後期,韓維便做了神宗的老師。1063 年五月,十五歲的神宗初封淮陽郡王,次年,英宗即位,神宗繼封為潁王,韓維均侍奉左右。韓維對神宗的管教嚴格,神宗對於這位老師也極為尊重。
《邵氏聞見錄》載:“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日:‘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韓維不僅管神宗的學習,還管他的品行。為解新君之憂,韓維舉薦了賦閑於江寧的王安石。
1063 年八月,王安石母親吳氏在京去世,王安石去官,奉母靈柩歸江寧,與其父合葬。服母喪三年後,王安石繼續留在江寧講學,收陸佃、龔原、李定、蔡卞等人為弟子。英宗屢召他赴京,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懇辭。
王安石放棄朝廷征召的原因,寫在他在江寧時所作的《古松》詩中。詩曰:“森森直乾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萬壑風生成夜響,千山月照掛秋陰。豈因糞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廊廟乏材應見取,世無良匠勿相侵。”詩表達的意思是,高大的古松乃自然之造化,假如廟堂之上缺乏這樣的棟梁,就儘管來伐取吧。但如果不是良匠,就不要糟蹋這珍貴的材料!

神宗問:王安石現在哪裡?
韓維說:在江寧。
神宗問:朕召他,他肯來嗎?
韓維說:王安石志在經世,非甘心老於山林,若陛下以禮致之,安能不來?
神宗說:卿可先給王安石寫信,說明朕意,隨後便召他。
韓維說:這樣啊,王安石必不來。
神宗問何故。
韓維說:“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彼必能達。”
神宗與韓維的以上對話說明,韓維對王安石的個性、志向、心態了如指掌,並且通過王安石之子王雱,與王安石保持著熱絡。韓維不僅推薦了王安石,而且斷定王安石能應召,前提是,這個人有點傲氣,“以道進退”,皇帝你要“以禮致之”。
神宗對王安石並不陌生,韓維講課,每次得到神宗嘉許,都要露出神往的口氣說:這不是我的想法,是我朋友王安石說的。神宗答應了韓維的要求,召王安石入京。但王安石仍舊婉拒,理由是,生病了。
神宗忙召問執政大臣說:王安石是先帝的大臣,先帝請不動,我原以為是他態度不恭。現在又請不來,是真的病了,還是要提什麽條件?
宰相曾公亮說:王安石文才、學識、品德俱佳,應該大用,屢召不起,肯定是身體有病,他不會欺罔陛下。
吳奎卻說:臣曾與王安石共事,此人有錯不認,剛愎自用,主張迂闊,一旦受重用,必定紊亂朝綱。
神宗還是認為韓維說得對——以禮相待,既然病了,就先不要跑那麽遠,令改任王安石為江寧知府。大臣們都覺得王安石還會推辭,出乎意料的是,王安石這一次卻應詔出任。
王安石感覺到了神宗的誠意。君子待時而動,蓄勢待發。王安石並非不想回到朝廷,自小便以父親為楷模,“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只是覺得時機一直未到。現在,“良匠”出現,時機已到。

王安石很快又奉詔,1067 年九月,入京任為翰林學士兼侍講,成為大行皇帝的近臣。
宋襲唐製,設翰林學士院,負責起草朝廷製誥、赦敕、國書以及宮廷所用文書,侍奉皇帝出巡,實際是皇帝的秘書處。
學士中資格最老的稱翰林學士承旨,其下稱翰林學士、知製誥。宋朝的館職包括直館、直院、修撰、檢討、直閣、校理等,能入館職的,均是詩壇、文壇的大才子。
館職通常晉升為修起居注官,包括直館、直院及修撰。再往上便是知製誥,最後才是翰林學士。翰林學士號稱“儒生之至榮”,有“儲相”之稱,這樣的安排,足見神宗對王安石的用心。
次年即1068 年,神宗改元,稱熙寧元年。四月初四,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二十歲的神宗與四十七歲的王安石第一次見面。

神宗心情急切,一上來就問:要大治天下,應當先做什麽?
王安石答道:“以擇術為先。”治天下,第一位的是要選擇正確的策略。
神宗又問:唐太宗怎麽樣?唐太宗是帝王中的佼佼者,躊躇滿志的神宗認為,以唐太宗為榜樣,志向已算是很遠大了。
不料,王安石語出驚人,他答道:陛下應當效法堯舜,怎麽能隻做唐太宗呢?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後世學者不能領會,以為高不可及。
對於王安石的這一回答,後世有許多人認為他狂妄無忌,大話欺人,蠱惑神宗。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論·神宗》中就說:“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
但哲學家賀麟先生不這麽認為,他在《王安石的哲學思想》文中說:王安石的話其實是他多年來懷抱的根本主張,神宗憧憬漢唐現實政治,而王安石“要把神宗轉變為趨向三代伊周式的理想政治”。
神宗接著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這是什麽原因呢?王安石沒有詳細作答,不久,他上奏《本朝百年無事劄子》,提出書面報告。
王安石說:我前些天承蒙陛下問到我朝之所以統治了上百年,天下太平無事的原因。我因為淺薄無知,錯蒙皇上詢問,由於時間緊迫,不敢長時間留在宮中,話還來不及說完,就告辭退朝。

私下想到皇上問到這個問題,是天下的福氣,而我卻沒有一句中肯的話奉獻,不是身邊官員效忠君主的態度,所以敢於不揣冒昧粗略地說說我的看法。
王安石說:太祖具有極高的智慧、獨到的見解,詳盡了解各種人物的真偽,指揮任命,一定做到人盡其才,設定變革措施,一定能夠符合現實情況。
所以能夠駕馭將帥,練好兵卒,對外抵抗外族入侵,對內靠他們平定動亂。於是廢除苛捐雜稅,禁止酷刑,廢除強橫的藩鎮勢力,誅殺貪婪殘暴的官吏,自身儉樸,為天下做出了榜樣。
太祖在制定政策發布命令時,一切以百姓能平安、得利為準則。太宗繼承了太祖的聰慧勇武,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謙恭仁愛,到了仁宗、英宗,沒有喪失道德的地方。
這就是所以能夠統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緣故。王安石高度讚揚了仁宗的政治美德,說:仁宗對上敬畏天命,對下敬畏人民;寬厚仁愛,謙恭儉樸,出於天性;忠恕誠懇,始終如一。
沒有隨意興辦一項工程,沒有隨意殺過一個人。刑罰輕緩而公正,賞賜很重而守信用。采納諫官、禦史的建議,多方面地聽取和觀察,而不會受到偏見、讒言的蒙蔽。
從監察官吏到州、縣的官員,沒有人敢暴虐殘酷,擅自增加賦稅徭役,來損害老百姓。從縣令、京官,到監司、台閣,雖然不能全部稱職,然而聞名一時的有才能的人,也很少有埋沒不被任用的。

駕崩的那一天,天下的人民放聲痛哭,如同死去父母。接下來,王安石指出了當朝的六大弊政:一是君主在國家治理方向上因循守舊,一切聽任自然,主觀努力不夠。
二是在吏治方面,單憑寫詩作賦、博聞強記選拔天下士人,缺乏通過學校教育培養造就人才的方法,朝廷中以科名貴賤、資歷深淺排列官位,地方則頻繁地調動遷官,缺乏考核實績的制度,誇誇其談的人能夠亂真,結黨營私的身居顯要,奉公守職的人無法被重用。
三是在農業方面,農民受到了徭役的牽累,遇到災荒也看不到朝廷的救濟撫恤,又不設定官員,組織他們興修農田水利。
四是在軍事方面,士兵中混雜著老弱病員,沒有加以整頓,又不能替他們選拔好將領,讓他們長久地掌兵守邊,保衛都城的都是些兵痞無賴,沒有徹底改變五代時對軍人縱容、籠絡的壞習慣。
五是在宗室管理方面,缺乏正確教導、選拔推薦之法。
六是在財政管理方面,基本上沒有法度,皇上儉樸節約而人民卻不富足,操心勤勉而國家並不強大。

王安石認為,國家之所以百年無事,是老天爺眷顧,“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
但這種狀況不可能長久,百年無事的背後有許多隱憂,政治上因循守舊,農民負擔很重,軍事上積重難返,“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是年距太祖立國剛好一百零八年。古人有“盛世”之說,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還來不及看到“康乾盛世”,他在《宋論·太祖》中指出,自堯舜禹三代之後,中國的盛世有三個。
第一個盛世是文景之治,但隻堅持了兩代。第二個盛世是貞觀之治,但李世民一死,這個盛世也宣告結束。第三個盛世,就是北宋的盛世,這個盛世從太祖開始,一直到英宗,歷經五世,歷時最長,有一百餘年之久。
但王夫之的北宋百年“盛世”說並未受到廣泛認同,相比之下,王安石的百年“無事”說更為貼切。王安石一對一奏,給神宗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劄子中的那句“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令神宗怦然心動。
文:陳勝利
圖源:網絡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編輯:張雪珠

作者:陳勝利
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