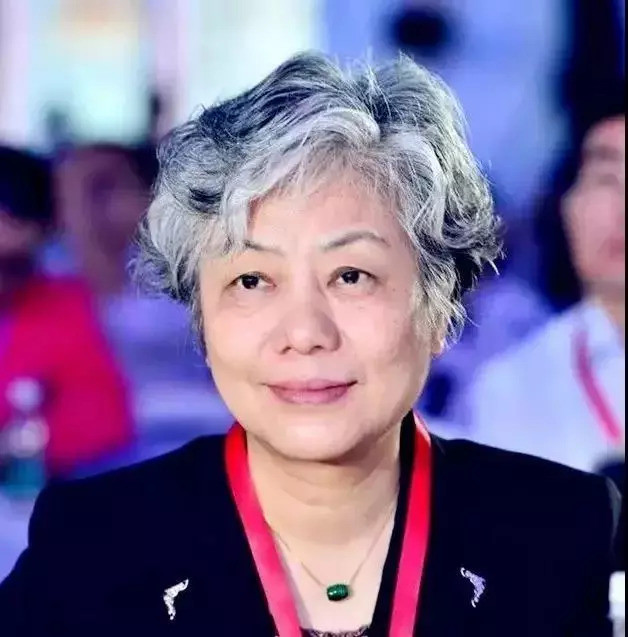1576—1744年,在英國舊的濟貧法框架下,私生子在法律上被轉給教會撫養。因為英國法律認為,父母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對其私生子女的撫養權或監護權。
1733年《濟貧院試驗法案》的通過,開始從法律上將私生子的撫養責任逐步轉移給其父母,私生子的生父要承擔孩子的撫養費用,母親在法律上有權獲得孩子父親支付的撫養費用。懷了私生子的女人首先需接受她所在教區的教會濟貧職員或季度法庭的調查詢問,說明懷孕的事實,並指認孩子的父親。然後,通常由兩位對該類案件有管轄權的治安官頒發親子撫養令,確定撫養孩子每周所需的費用,以及父母雙方各自應當分擔的份額。一經認定,私生子的父親必須簽定協定,同意承擔孩子的撫養責任,定期為孩子及其母親支付撫養費用,否則會被收監入獄。通常私生子父親的親屬也要作為擔保人在該協定上簽字。
關於私生子問題研究,Nutt(2005a, 2005b, 2006, 2010)採用Chelmsford法庭會議記錄(1814—24)和1834年《農村和城鎮調查》的樣本,對親子撫養令的發布,據此命令私生子生父支付撫養費的機制以及教區執行親子撫養令的能力(從生父處收取撫養費的能力)等問題進行了分析。Lyle(2005)利用1834年《農村調查》數據,對私生子撫養費的金額進行研究。Samantha Williams於2016年發表在EHR的論文“The maintenance of bastard children in London, 1790–1834”,則探討了倫敦在1790—1830年代“舊濟貧法”的框架下,私生子撫養問題不斷變化的過程。
1790—1830年代,私生子數量與濟貧支出都在不斷增加。私生子生父撫養制度的執行可以讓教區官員降低教區的貧困率,但據1834年的《城鎮調查》顯示,大城市教會難以從私生子生父處收取私生子撫養費。1834年的截面數據提供了教區層面關於父母和教區對於私生子撫養費用的經濟資訊,不同地區顯現出相當大的差異。父親的支付能力是影響教區收回私生子撫養費的重要因素,很多時候,父親為了逃避撫養費會選擇潛逃、遺棄私生子。
為了提供長期趨勢的證據,本文從1790年至1830年,對Southwark和Lambeth地區的私生子相關文獻進行了分析,並首次展示了私生子撫養費用中與分娩和法律有關的費用、一次性付清撫養費、撫養費支付頻率、周津貼的數額範圍、認定父親的撫養年限,以及母親應支付的撫養費等相關問題的證據。研究結果表明,每周津貼的金額可能高出先前的預期,持續支付撫養費的時間也可能會更長。
倫敦的人口在1801年約一百萬,而到了1851年則翻了一倍多。拿破侖戰爭結束後,倫敦的濟貧開支不但增加,相對於全國其他地區的支出也變得更加重要。與此同時,1650—1850年代,私生兒童數量急劇增加,這使得教會當局的擔心日益增加:非婚生子率從佔出生嬰兒的1%上升到7%,所有頭胎嬰兒的私生子從7%上升到25%左右;撫養私生子的費用上升,讓教區的支出迅速增加。人口不斷增長和貧困率攀升的情況引起了知識分子:如Malthus,政治家Nassau Senior和《濟貧法報告》的設計師Edwin Chadwick等的警覺,對待非婚母親的態度也開始變得強硬,進而促使了1834年新私生子條款的頒布。
表1 St Saviour, St George the Martyr和St Mary Newington教區的人口(1801-1831)
私生子認定生父撫養制度與濟貧法並行,為教區官員提供了縮減濟貧支出的可能性。但撫養令的頒布,並不意味著一定能從生父處成功收取撫養費。而且,一旦法官簽發了撫養令,它就有權讓母親每周獲得一筆津貼;無論認定的父親是否支付其撫養費,教區都必須為這筆財務負責,這對教區的財務有負面影響。
在Southwark的St Saviour, St George the Martyr教區和在Lambeth的St Mary Newington教區可以獲得1790年至1830年間,教區私生子撫養情況的資訊。本文證據主要來自親子撫養令和《私生子撫養費冊子》。撫養令中包含母親姓名、認定生父姓名、孩子姓名、孩子出生地點和日期、最初花費和父親每周需支付撫養金額的資訊。《私生子撫養冊子》中包含母親姓名、認定生父姓名、孩子姓名、孩子出生地點和日期、撫養費的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清還是每周支付)以及支付年限。
St Saviour教區,有21%的生父選擇一次付清私生子撫養費的方式。從圖2中可以看出,最為常見的一次付清費用是20-29英鎊。

圖1 St Saviour和St Mary Newington教區,私生子認定生父所支付的初始費用

圖2 私生子認定生父一次付清撫養費金額(1794-1807)
私生子的認定生父不一定按周支付私生子撫養費,可能是按更長的時間分期付給教堂,再由教堂按周發放給私生子母親。圖3是St Saviour, St George the Martyr和St Mary Newington教區的私生子認定生父支付的周撫養費金額。在1934年的《城鎮調查》和《農村調查》記錄中,周津貼的數額為1先令到2先令6便士之間。圖3顯示,2先令6便士是最為常見的數額。除此之外,私生子母親在某些情況下也被要求支付給教區私生子撫養費(見圖4)。

圖3 St Saviour(1792-1808), St George the Martyr(1802-35;1808-36)和St Mary Newington(1814-31)教區私生子生父支付的周撫養費金額

圖4 St Mary Newington(1808-1836)教區私生子母親支付的周撫養費
而持續支付教區私生子撫養費的時間可能會意外地長:在St Saviour教區最長達10年,在St Mary Newington教區最長達15年,均長於7年的撫養年限。

圖5 St Saviour、St George the Martyr、St Mary Newington教區支付撫養費的年限
一方面,私生子的不斷增加,加上教會濟貧職員收取的撫養成本不足,對教區的財務狀況產生了重大影響。大規模的移民給倫敦帶來了大量的流浪者和臨時乞丐,這破壞了濟貧法的穩定性。同時,私生子數量的不斷上升也加劇了城市貧困,尤其是泰晤士河南部地區。在倫敦貧困問題日益嚴重的時候,私生子認定生父撫養制度為教會濟貧職員提供了降低貧困率的方法。但實際上教區收回撫養費的能力差異很大,通常教會難以成功收取私生子撫養費。例如,倫敦南部是倫敦較為貧窮的地區之一,該區域本可以從認定生父處收取私生子撫養費,緩解教區財務壓力和降低貧困率,但許多教區基本上沒辦法這樣做。這意味著與私生子的大部分撫養成本落在教區納稅人身上,而不是孩子父親身上。
另一方面,私生子認定生父撫養制度的運作也對母親和認定生父的短期經濟狀況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於母親來說,該制度可以讓她們不用花自己的錢就能雇用助產士來生產和購買兒童床上用品,並能為孩子提供每周津貼。然而,儘管濟貧法委員們認為:“對於女性來說,一個私生子的開支很少,有兩至三個私生子可以獲得收益”,但對城鎮和農村調查的被訪者來說,津貼金額也只是勉強足夠撫養孩子。未婚母親必須努力工作才能維持生計;在沒有男性工資支持的情況下,幾乎所有的母親都必須把嬰兒送到護士站,然後外出工作或重新進入家政服務市場。此外,這項研究還發現,不僅僅是認定的生父需要為孩子提供經濟支持,母親也可能需要如此。那麽,在某種程度上,非婚生子女的養育由有名望的父親承擔經濟責任,而母親承擔培育責任的情況在倫敦並非總是如此。
對於認定生父而言,其需支付的撫養初始金額、總金額和長期支付的周撫養費很可能使許多私生子父親本就有限的工資變得更加緊張,他們必須努力工作才能付得起。另外,那些被認為最無力負擔定期撫養費的父親必須一次性支付數額較小的全部撫養費。所以,認定的生父需要持續多年支付撫養費無疑是相當大的負擔。儘管Southwark和Lambeth地區的許多男子確實想方設法支付了撫養費用,但有的人卻選擇了逃走。無論是自己帶走孩子的、還是違約的,都讓教區承擔了孩子的撫養費用,這使得教區變為了當地的“公民父親”。
簡言之,私生子認定生父撫養制度的核心是母親、父親和教區教會濟貧職員之間的博弈。因此,私生子、認定生父撫養制度和“舊濟貧法”的故事要比僅僅關於貧困和福利的故事複雜得多,它也是關於母性、父權和國家之間聯繫的故事。
文獻來源: Samantha Williams, 2016, The maintenance of bastard children in London, 1790–1834,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