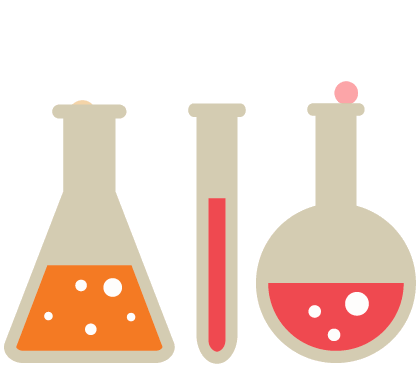來源:健康報微信傳播矩陣-文化與健康(jkb_whyjk)
點擊上方藍字關注「文化與健康」

不久前,澳大利亞104 歲的科學家大衛·古德爾赴瑞士安樂死的消息引發全球主流媒體的報導。一時間,關於安樂死的爭論再起。與以往每次一樣,大部分爭論都集中在安樂死是否人道或者是否應該合法化上。藉此機會,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羅點點梳理了安樂死的由來和現狀,並提出,與已有百餘年歷史、極度深寒的安樂死相比,年輕而有生命力的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能使人們在生死艱難抉擇中找到一條更溫暖、更有人性、更容易獲得幫助的路。
——編者
德國的「安樂死計劃」和荷蘭的安樂死「合法化」
如果被問起最先推行「安樂死」的是哪個國家,可能很多人會說是荷蘭,但其實是德國。
在上世紀30年代,德國納粹黨決定對猶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他們認為是劣等民族的人實行大規模種族屠殺之前,竟然已經有5萬~7萬德國公民被所謂的「安樂死計劃」殺死。這包括在針對殘障兒童的安樂死計劃中死去的5000多名兒童。
希特勒上台後,「安樂死計劃」變本加厲。1939年8月,他簽署一份檔案,對被確認為不可治癒的患者準許實施「慈悲的」死亡,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統的純凈和節約肉類與香腸」。這份檔案其實是後來臭名昭著的種族清洗的先聲。據統計,希特勒在1938年~1942年以「安樂死」名義殺死了數百萬人。

納粹宣傳部拍攝的「安樂死」項目宣傳片中的內容,地點為德國某精神病院,目的是向國民宣揚「安樂死」項目的必要性
當納粹政權和法西斯主義在全世界徹底失敗後,流行在歐美各國強迫結紮絕育的「優生」迷夢才最後破滅。
隨著二戰後人們的文明覺醒,安樂死開始走上了充滿人道光輝的路線。荷蘭即是這樣的一個範例。
荷蘭的安樂死「合法化」也不過實行了區區14年。為了這個結果,整個民族精心準備了好幾個14年。
荷蘭醫學界享有崇高榮譽。二戰期間所有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歐洲國家中,只有荷蘭醫學界全體成員拒絕與他們合作。在殘酷的滅絕種族和殘障人士的行為中,荷蘭醫生甘冒巨大危險,周全地保護了自己的患者。佔領當局用吊銷行醫執照、逮捕和送入集中營等恐怖手段迫害他們,但謹守職業道德的荷蘭醫生毫不動搖,而且是全體,無一例外!箇中原因也並不費解。荷蘭人大多數都有自己的家庭醫生,醫患兩者的家庭友誼會持續幾代人,所以醫患關係親如家人。
正因為荷蘭醫生有如此清正堅定的專業精神,大多數荷蘭人相信,由醫學界主導的安樂死,會一如既往地使患者利益最大化。當然,這種信心還有重要的經濟支持。荷蘭是世界領先的福利國家。在普遍充分的醫療社會保險中,對疾病終末期患者的照顧,無論從技術還是支付上都很周全。
但是,「合法化」並不等同於合法。事實上,時至今日,安樂死在荷蘭確實仍然是「違法的」。準確的說法是:安樂死雖然在荷蘭仍然違反法律,但是在執行了某些嚴格的條款之後,執行者不再受法律追究。也就是說,只有特定情況(嚴格條款被準確無誤地執行)下,安樂死才可以「合法化」。這一個「化」字,是強調只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不被法律追究行為。但從本質上來說,安樂死還是剝奪他人生命,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為了免除執行醫生(必須是主治醫生及以上)的刑事責任,荷蘭安樂死的實施必須滿足以下標準:患者安樂死的要求是自願的,並且經過深思熟慮;患者的痛苦無法繼續承受,同時病情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主治醫生和患者共同得出結論,患者的狀況沒有任何其他合理的救治方法;主治醫生必須徵詢至少另外一名醫生的意見,這名醫生必須見過患者,並且對上述幾條標準給以書面意見;主治醫生對患者實施安樂死或協助自殺時,給予應有的醫療護理和關注。
實施完成後,醫生必須按照殯葬和火葬法案的相關條例向市政驗屍官通報患者的死亡原因。要通過5個地方安樂死監督分會向安樂死委員會書面報告全程細節。安樂死委員會的責任則是仔細察看並最後判決醫生到底是提供了死亡援助還是觸犯了謀殺罪。審查者至少包括一名律師,一名醫生和一名倫理學家。同時,醫生和護士有權拒絕安樂死的實施或準備。實際上,由於種種原因,荷蘭2/3的安樂死要求都會被醫務人員拒絕。
由此可見,荷蘭安樂死的合法化過程多麼複雜,條件多麼嚴苛,一不小心,還是可能觸碰法律紅線。
澳大利亞大衛·古德爾的安樂死,為什麼是在瑞士?
我們知道,即使在荷蘭,請求安樂死的前提條件一定得是患者,是患有不可治癒的疾病,且痛苦無法忍受的人……可104歲的澳大利亞科學家大衛·古德爾沒病,只是年老,只是不想活了!這可不太符合我們之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理解。
大衛·古德爾是去瑞士實現安樂死的。為什麼是瑞士?因為它是唯一允許對外籍人士實行協助自殺的國家。澳大利亞雖然在很早,甚至是比荷蘭還早的時候也嘗試過安樂死合法化,但不到一年,澳政府就因為可以想像的原因,廢止了這個法律。

2014年比利時民眾在街頭抗議兒童安樂死合法化(來源:npr.org)
大衛·古德爾的瑞士之行讓許多人覺得協助自殺在瑞士是合法的,但事實並非如此。瑞士有關法律規定:任何人出於自私動機勸說或協助他人自殺,應判處不超過5年的監禁。也就是說,如果協助自殺的人無法證明行為無私,協助自殺仍然非法。當然,就實際效果來看,這是實際上的合法化——把本質上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化為一種在無私動機下可以不受法律追究的行為。這至少說明,在剝奪他人生命這件事上,想突破法律和人情很不容易。
在瑞士,協助自殺基本上不被認為是醫療行為,可由「非盈利」的協助自殺組織代勞,實施協助自殺的人可以是醫務人員,也可以不是。但即使是醫生,也只能提供藥物或工具。無論是服藥或是注射,患者都不能假手他人,需要自己執行最後步驟,也就是按下「死亡按鈕」。
目前,從對大衛·古德爾安樂死的現場報導,我相信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但說實話,作為一個曾經的臨床醫生,以及一個在國內推廣了多年的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的人,觀看這些影片讓我感到極大的不安和不適。一個老人,不是因為疾病只是因為年老,沒有不能忍受的身體痛苦而只是因為心靈極度疲憊,就背井離鄉、遠渡重洋,自行按下「死亡按鈕」——這些都讓我膽寒齒冷,都違背我們所提倡的尊嚴離世的理想。
與「年老」且極度深寒的安樂死相比,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更有生命力
從二戰之前算起到現在,安樂死已經100多歲了,它老了。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醫療模式的轉型,生命科學和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及人類對自身認識水準的提升,新興的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念倡導更舒適、更有尊嚴和更符合人道精神的死亡方式。與「年老」且極度深寒的安樂死相比,更有生命力的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能使人們在生死艱難中找到一條更溫暖、更有人性、更容易獲得幫助的路。
生前預囑是美國醫務界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目的是讓患者清醒時即對自己病危時所需要或拒絕的醫療措施有所交代。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國內外醫學界對於終末期患者的救治已經達成共識:關注並減輕患者的身心痛苦,既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讓患者有尊嚴地離世。我國推行生前預囑則是在2000年之後。2006年,我們成立了以宣傳生前預囑為己任的《選擇與尊嚴》網站,提倡自然死亡、反對過度搶救。2013年,我們建立了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推出了更適合我國法律環境和民眾文化習慣的生前預囑——「我的五個願望」,個體只需對其中每個願望下的問答做出「是」、「否」的選擇,就能對自己的臨終作出符合本人願望的、大致清晰的描述。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緩和醫療是為罹患威脅生命之疾病的患者及其家屬提供的全面照顧,以多學科團隊合作,實現對患者因疾病產生的各種(身體、心理和心靈)不適進行早期識別、評估和適當處置,達到最大限度改善他們生活品質的目的。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緩和醫療的原則有:一、重視生命並承認死亡是生命的正常過程。二、既不提前也不延後死亡。三、提供解除過程中一切痛苦和不適的辦法等。這些原則非常重要,它保護那些即使放棄生命支持系統或某些極端治療的患者,在疾病過程中,尤其是臨終也不至消極等死。它鄭重承諾對患者的身心痛苦和一切不適提供有效的緩解和治療,對家屬經歷的艱難陪伴和喪親的困苦提供幫助和支持。總之,緩和醫療以不涉及積極致死行為又給病重和臨終者帶來最大限度舒適和尊嚴的方式,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傳播,正超越和替代那種認為「安樂死」是人們面臨絕症痛苦時唯一選擇的想法和做法。

CFP供圖
當然,現實往往比願景更骨感和複雜。前些日子,在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的緩和醫療一線微信群裡,一位遠在昆明、國內較早開展緩和醫療的外科主任分享了他剛收治的一位患者的情況。
患者是一位大學教授,已是腫瘤晚期,呼吸困難,憋氣到不能說話。他親手給醫生寫了字條:「我希望儘快實施亞冬眠,保留我最後一點尊嚴。」字條邊上是家屬寫的內容:「我全家都已溝通過,都理解、支持。」患者接著寫道:「我知道我病情的全部,所以這次就是奔著您來的……」字條上每段文字後面都是鄭重簽名。
這位外科主任說:「他(患者)是想變相安樂死。」群裡的氣氛也因為這句話變得急切和凝重起來。面對真實的病例和真實的需求,這些臨床一線醫生第一時間考慮的不是任何理論和說法,而是如何幫助患者。但是到底該怎麼辦呢?外科主任說:「我認為他的情況還可以有一個月。他認為沒必要再活下去。這種時候對錯難分,已經不是醫學問題了。」群裡有人提出那個繞不過去的老問題:「我覺得醫務人員需要先考慮法律風險,保護好自己才能更好幫助患者,找一個平衡點。」外科主任回應說:「想要保護自己就要違背患者的意願,想要幫助患者有可能違背現有醫療制度。就算患者只有3天的生命,我們也要想怎麼辦。在醫學層面到底有沒有平衡點?」他接著說道:「這個患者呼吸困難但並不缺氧,吞咽困難但仍能進流食,腰疼是因為椎間盤突出,很虛弱,但他的訴求主因是覺得活著沒尊嚴。所以全家討論決定來我這裡儘快結束一切。我認為他還沒進入終末期,我鼓勵他換個好房間,心情先平穩下來,我答應三天以後再和他談亞冬眠。我還保證一定讓他最後不痛苦,離去的時候有尊嚴。他很配合。」群裡一片讚揚之聲。
過了一天,外科主任查完房後,在群裡說:「這個患者明顯好轉,意識到要求冬眠的想法偏激了,非常感激我們當時沒接受他們家庭會議的決定。」不僅如此,這位外科主任還想到了進一步為患者解決痛苦的辦法,他說:「只要他願意接受我的意見,我可以在他的頸部,對造成壓迫的腫瘤做消融術,這是個微創手術,緩解壓迫,讓他舒服些,死亡的時候也會平靜些。」群裡獻上了一大把花,為這位外科主任,更為那位經歷苦難不失本色的勇敢患者。
不難理解,人在痛苦和屈辱的時候往往覺得生無可戀,但當壓力稍有緩解,生命就又會變得彌足珍貴。做緩和醫療的醫生對此深有體會,大家的共識是:如果患者提出安樂死,那就是緩和醫療沒做好,沒到位。我太同意這個觀點了!外科主任的實踐就是最好的證明。
回到104歲大衛·古德爾赴瑞士安樂死這件事上,之前我說我相信這位老人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但是,如果有更多的照顧和關心,他「想要的」的東西會不會改變呢?從現有的報導資料我們知道,他曾因衰弱跌倒,因為沒人幫助而在地板上整整躺了兩天。這樣的經歷讓我痛心疾首,換作是我,恐怕也會感覺「活膩了」不想再活。至於他根本不是任何疾病的患者,只是因為高齡和「不快樂」,就要背井離鄉,在不一定是醫務人員的幫助下自行結束生命,更讓我難以接受。
當然,好制度和好法律應該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下,保障所有守法公民有實現自己願望(包括安樂死願望)的自由,有免除恐懼(包括死亡恐懼)的自由。但我想,我們與其在哲學迷宮和自殺陰影中討論「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不如回歸常識,以順應倫理的方式推廣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讓更多人知道,按照本人意願,以盡量自然和有尊嚴的方式離世,是對生命的珍惜和熱愛。
編輯 | 李陽和
校對 | 劉美琴

如果您傾心醫學人文,
如果您還想沾染些文藝氣息,
那麼,請關注我們吧??
T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