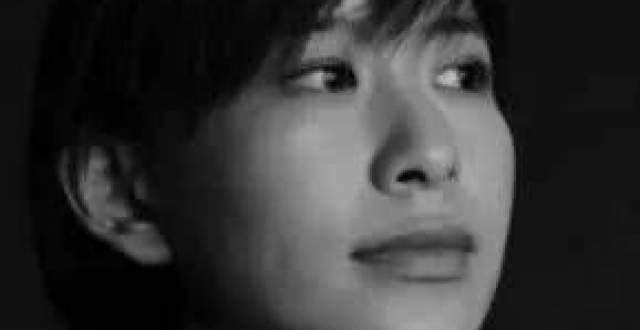卡夫卡的內心生活
文 | 謝有順
卡夫卡閱讀筆記之二:不可治愈的不幸
維特根斯坦讀完托爾斯泰的《哈澤·穆拉特》後曾感歎說:他是一個真正的人,他有權寫作。這話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樣合適。在卡夫卡筆下,我們幾乎看不到一個完整的人,許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動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職員,連卡夫卡自己看起來也是一個弱者,他在寫作中關懷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內心卻一直有著堅不可摧的東西。他的確是一個真正的人,所以他才會那麽堅定地關心人的希望和絕望,夢想和悲傷。
和許多人一樣,我讀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變形記》。應該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歲,對文學剛開始萌生興趣,還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變形記》第一次讓我知道,寫人,原來可以把人置於非人的境遇中來寫,這樣反而能夠把人內心中的隱秘事物逼現出來。接著我又讀了他的《饑餓藝術家》,當時未必能夠完全理解藝術家拒絕進食的精神意義,但那個時候,我已經隱約感到,小說原來並不僅僅是講故事,它還要解釋人的處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現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他使我知道,寫作不該放棄對存在核心的追問。
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對世界的解釋。他對生活的批判,目的是為了抵達世界的內部,抵達存在的荒涼地帶,從而為人的處境尋找新的價值坐標。對他而言,寫作就是生命的一種表達形式,他與寫作的密切關係,是不可改變的。“正如人們不會也不能夠把死人從墳墓中拉出來一樣,也不可能在夜裡把我從寫字台邊拉開。”他還不止一次說,寫作是祈禱的形式。所有這一切,都建基於他對自身境遇的敏感,對存在的關懷。卡夫卡讓我認識到,真正的寫作是獨立的,內向的,自省的,也是堅決的,因為它無法和現實輕易達成和解。寫作者需要有足夠的勇氣,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淵。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種為藝術殉難的光輝,他那堅韌的犧牲精神,幫助他抵抗著一次次的精神苦難,如他自己所說,他一直都在鬥爭。

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讓人想起《饑餓藝術家》中那個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寧死也不進食的饑餓藝術家,他簡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實寫照。饑餓藝術家為了“把藝術推向頂峰”,如同卡夫卡筆下那個“歌女約瑟芬”,為了拿到“那頂放在最高處的桂冠”,不惜毀壞自己的身體,這種為信念和藝術殉難的精神,顯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臨死前還特別看重這部作品。據羅納德·海曼的《卡夫卡傳》記載,臨終前卡夫卡在病床上還堅持通看《饑餓藝術家》的校樣,“他不禁長時間淚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從中看到了自己。或許,他在自己寫下的這段話裡,感受到了難言的痛楚:
“我只能挨餓,我沒有別的辦法。……因為我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這樣的食物,請相信,我不會這樣驚動視聽,並像您和大家一樣,吃得飽飽的。”

所有的難題,都是因為“找不到適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無法和現實達成和解。這多少有點“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經這樣自嘲過。但是,面對一個荒謬、虛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樣“吃得飽飽的”,今天的他也許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絕進食,拒絕和解,為我們洞開了一扇觀察現代人生存的窗戶,並通過他超常的想像,為我們敞開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領域。因此,卡夫卡不僅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端,他更為二十世紀的文學提供了一個精神限度——他所呈現的人被腐蝕、異化、毀壞的景象,成了整個二十世紀文學的基本經驗和基本母題。後來的文學大師,幾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裡徘徊。
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現實中的命運:“我只能挨餓,我沒有別的辦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運,而是耗盡生命的能量來為存在尋找答案。他發現,自己總是與現實處於一種膠著的狀態,包括他筆下的人物,他們周圍充滿的都是虛假的事物,許多時候,就連自己的身份都無法確認,但他們從不放棄努力,直到生命耗盡,也在尋找自己存在的真實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測量員身份一直得不到證實,那個最高當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隱匿不見,一切都變得恍惚而迷離,並充滿著難以言喻的荒謬感,而這,也許正是卡夫卡對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無法獲得土地測量員的身份,那是因為存在本身是無法測量的,或者說,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經過艱苦的鬥爭;而《約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個為了拿到“那頂放在最高處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於自己的歌唱的東西都“榨乾”了的歌女,三分鐘熱度就可以把她吹倒,這表達的不過是理想的代價和存在的脆弱……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達個人的存在境遇,其實他是在描述一個普遍的生存悖論:存在本身,往往與存在的目標背道而馳。

也就是說,卡夫卡在寫作中發現的都是人類的“存在的不幸”。勃羅德曾經把不幸分為兩種:“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於上帝創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羅德的說法,後一種不幸是不能用社會的、理性的和經濟的因素來解釋的。而卡夫卡發現和承擔的正是這種不幸:“這種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於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將會更沉重地壓迫著他。”卡夫卡終生的努力,就是試圖把自己從這種不幸中解救出來,但他沒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淵,卻怎麽也找不到向上騰跳的動力。他這樣形容自己的處境: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聯繫剝奪了我看待事物一種廣闊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個深谷的底部,並且頭朝下。”
今天,當我們重新領會卡夫卡所發現的不幸境遇,不禁要問,卡夫卡何以能在那個時代發現這麽多令人震驚的事實?我以為,“頭朝下”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時代,世界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但存在的真相依舊是隱匿的,被遮蔽的,一個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觀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視力和方法都無能為力,他需要突破。這個時候,“頭朝下”就成了一種反叛,成了一個可能帶來全新發現的角度,它意味著不符合規範,“野”的,“是從文學外走來的”(漢斯·馬耶爾語)。卡夫卡的寫作證實了這一點。他寫人變成甲蟲,寫人與城堡的關係,寫藝術家的饑餓表演,就當時的文學而言,都是“頭朝下”的方式,是一種巨大的革命。無論從話語方式還是從精神體驗上說,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學的方式發動了一場關乎文學和存在的政變。當舊有的經驗和話語無法再窮盡自己的內心時,卡夫卡毅然以一種“頭朝下”的方式從傳統的文學格局中出逃,由此,他從另一個角度看見了別人沒有看見的人性景觀。
(未完,待續)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