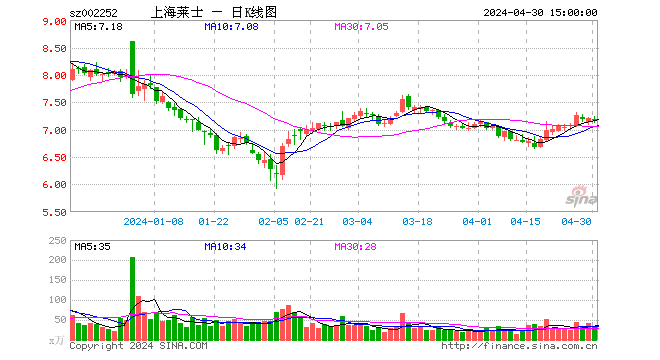自從港交所放寬上市條件後,過去一年,內地眾多獨角獸公司紛紛開啟赴港上市步伐,“虧損”成為近期眾多IPO公司如小米、美團等被提及的關鍵詞,甚至被人煞有介事地拿來吸睛。但事實上,這些公司即便業績數字表面上為負,但實際上投資者仍對其上市樂觀其成,原因除了對於其未來成長前景的良好預期,更重要的是,考慮到會計準則和存在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問題,很多公司經過調整後的業績事實上早已實現盈利。如果你深讀這些公司的招股書,尤其是財務資料部分,你就會對這些問題有了去偽存真的了解。
今天,我們以剛通過聆訊的華興資本為例,把會計準則和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問題認真剖析一番。
翻看華興資本6月25日披露的招股說明書,其財務數據中有兩個在國內資本市場並不太常見的概念,即影響公司收益和淨利潤確認的“基金投資管理的附帶權益(Investment income from carried interest)”和“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convertible redeemable preferred shares)”。後者在近期包括小米集團在內的諸多赴港或赴美上市的公司財務報表中屢屢出現,也曾持續引發關注。
坦率說,這些問題的存在看似對IPO公司業績的影響甚大,但實際細究起來,都不過是相關會計準則上的“障眼法”,投資者應當擦亮眼睛去偽存真,客觀看待公司實際業績及投資價值。
投資管理型公司的會計準則問題的“是與非”
我們先來說說第一個。華興資本招股書中關於收入的IFRS(國際會計準則)和非IFRS口徑之間的差異僅僅差在附帶權益收入。所謂附帶權益,通常是指風險投資基金經理從基金的投資利潤中分得的部分,一般是在投資者收回全部投資後,按資本增值的一定比例進行清償計算。
上半年IFRS口徑的利潤除了經營利潤,還有重要的一塊是投資收益。從招股書中的2018年一季度數字看,投資收益包括戰略投資、大資管業務下的基金布局、結構化金融產品等,一季度的投資收入有近千萬美元。
此外,為了更及時地反映PE基金的增值帶來的潛在附帶權益收益的變化,non-IFRS口徑的利潤在調整中還會加上附帶權益收益(carried interest)。根據招股書,2018年一季度附帶權益淨收益是2,483萬美元。一季度的經營利潤到調整後歸屬於母公司的利潤之間相差了3000多萬美元。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為什麽要加上附帶權益收益。實際上,在國際上PE公司上市最多、影響最大的市場美國,SEC允許上市PE公司選擇以“權益法”在當期記錄附帶權益收入和與其相匹配的成本費用。這種調整客觀上更符合收益產生的真實過程。
IFRS眾多準則設計的主要出發點就是保守、保守、保守,以及確定、確定、確定。因此,不能即刻確權的投資損益,IFRS當然就傾向採用極度保守的“收入法”來界定。
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長時間,行業內人士均對IFRS的“收入法“屢屢提出質疑之聲。因為這些業內專家認為,“收入法”對於一些行業,在一些特殊領域其實並不太試用;就拿華興的業務性質而言,如果按“收入法”確定收益,既沒有考慮到華興的行業特性,也不能反映出華興真實的公司價值。
招股書顯示,華興資本2018年一季度經調整後淨利潤達3,566萬美元,同比猛增4.22倍,其中投資管理業務貢獻顯著,分部調整後淨利潤達2867萬美元。但是,如果按“收入法”這些基金所創造的收益,很大一部分將不能被及時計入,這一塊的業績貢獻則不易凸顯,公司真正的成長價值就容易被忽略。
按照IFRS的“保守”準則,這部分業績需等到這些基金完成相當比例的退出或完成變現時,才能確認投資收益。換句話說必須要見到“真金白銀擺上桌面”才算數,否則在此之前的只能按投資管理的服務費用計入收入。
但是,IFRS可能忽略的是,對於資管行業來說,發掘並投資一隻“獨角獸”或擬IPO公司需要跟隨其發展許多年,尤其是對於“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務”的華興資本來說,IFRS硬性的收入法,顯然不符合行業與公司特性。
舉個栗子:就拿最近同樣赴港上市的小米來說,按“收入法”計算,如果一個基金投資了投資小米,在不退出的情況下,從2010年直至上市前的投資溢價,都不能被計入財報的“投資收益”,只有上市後退出變現才算。顯然“收入法”並不能真實反映出真實的投資收益增值變化;尤其對於華興這類公司來說,“收入法”不能真實的反映出華興資管業務的及時業績,更體現不出華興追逐、培養、造就高成長公司的核心競爭力與行業特性,所以業內幾乎一致認可通過可以及時反映投資收益的“權益法”來衡量特殊行業的真實價值。
對於“權益法”來說,因不用等到投資基金完成相當比例的退出或變現,就可將當期投資收益的變動直接記錄到利潤表,而倍受業內認可;事實上,從投資基金一端來看也確實如此,當期收益也確實被分配到了這些基金的账戶之中,本就不應該被視為“無物”。
也許正是為了客觀公允反映其投資價值,華興資本就在其招股書中解釋道,為了更及時地反映PE基金的增值帶來的潛在附帶權益收益的變化,華興應用“權益法”對報表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使得投資人對PE基金業績的真實情況有更好的了解。
“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正本清源
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這一概念並不新鮮,在美圖、小米等境外上市的互聯網公司的招股書中都頻繁出現,也持續引發投資者關注。
最近將上市的小米集團,其招股書中就顯示,小米2017年虧損438.9億元,若不按IFRS計量,則盈利53.6億元,兩者相差493億元,其中僅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影響就有541億元。再早之前的2016年美圖赴港上市時也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其超過60億元的巨額虧損對於此前較少接觸新經濟公司的港股市場來說頗為“震撼”,但其中一大部分虧損數字也是優先股“惹的禍”。
此次華興資本披露的招股說明書也披露了類似情況。以兩種不同口徑之下差距顯著的2018年Q1為例,按IFRS計算,是虧損[6500萬]美元,不按IFRS計算是淨利潤[3500多萬]美元。之間相差超過1億美元。更關鍵的是趨勢,如果按IFRS就是2018年虧損同比大幅擴大;不按IFRS就是業績大好,2018年Q1淨利潤已經超過了2017年全年調整後淨利潤的60%。其中,僅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就產生了[7300多萬]美元的差距。
投資者到底該如何正本清源地看待它?
一般而言,“可轉換”意味著企業上市後持有者可以按約定的價格將優先股轉為普通股;可贖回意味著,不行權的話,到期後企業按約定利率支付利息贖回。因此,會計學界普遍認為,與普通股不同,優先股既可以是“像股的債”,也可以是“像債的股”。
實際上,這種負債既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債務,也不是具有經濟實質的債務,用專業人士的說法,只能算作一種純理論的虛擬債務,一般情況下並不會實際發生。
考慮到公司上市這些優先股轉換成普通股後,持有人可以分享巨額的市值溢價,持有者放棄轉股、公司贖回概率極低。因此,這些虛擬債務並不構成公司向持有者支付現金或者轉移其他資產的現時義務,也就不會導致現金流出。而當優先股轉換為普通股時,這筆負債不複存在,雖然公司需要額外發行股份,現金流並不受影響。
而從另外一個維度上來看,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公允價值的增加恰恰說明了資本市場對一家公司價值的認可。因為公司市值越高,優先股對應的公允價值就會越高,持有這些股份的股東账面的浮盈就會越大。隻不過,由於會計準則要求,這個值在利潤表中是負數,所以就造成了公司形勢越好,利潤表中账面損失越多的悖論。
國內著名會計學者、廈門國家會計學院院長黃世忠教授不久前曾專門撰文討論小米的優先股問題,引用一個精準的評論,“(小米)這個案例說明了將優先股作為負債並按公允價值計量之缺陷,經營業績大幅改善,股價暴漲,利潤表卻體現巨額虧損,經營業績嚴重惡化,股價暴跌,利潤表卻體現巨額盈利,公允價值會計的逆周期現象令人哭笑不得”與小米類似,華興資本發行的上述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在IFRS和非IFRS下帶給淨利潤的影響是驚人的懸殊。
如此一來,既然我們已經了解了在IFRS之下,財報是按照最悲觀的預計來審視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存在(即預計到期將全部付息贖回,100%的負債),投資者當能穿透“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迷霧,辯清華興資本業績表現的真實“成色”。
寫在最後:
在互聯網公司的財報中,非公認會計原則業績指標越來越常見,此前京東財報也曾引發對GAAP、non-GAAP準則的討論。究其原因,按IFRS或GAAP準則,財務報告所體現的經營業績有時會嚴重背離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所以互聯網公司普遍將IFRS或GAAP編制的淨利潤調節為非公認會計原則業績指標,一並披露。
據報導,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理事張為國教授曾經披露,金融時報100指數公司中,81家在年度報告中披露了非公認會計原則業績指標,標普500公司中,88%的公司披露了非公認會計原則業績指標。這也表明了資本市場對非公認會計原則業績指標糾偏有強烈的資訊需求。學界也一直在呼籲,引入非公認會計原則業績指標的審計機制並加強監管,修改不合時宜的規定等等。相信隨著新經濟的發展,這一天並不遙遠。
了解完上述事實真相後,我們該奉勸那些被“虧損”表象迷惑的人們:做完功課,就洗洗睡吧。
責任編輯:張恆星 SF142